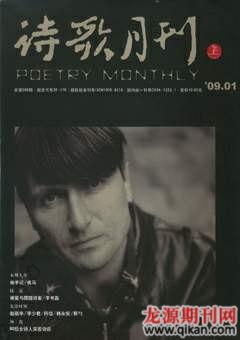《他手记》阅读手记
伊 沙
1. 秋夜微凉,在西安古城墙下一个别有风味的露天茶社里,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与本城两位老伙计秦巴子、李震,招待从四川来开会的诗人何小竹饮茶、吃酒。饮的是俗不可耐的普洱茶、吃的是名叫“女儿红”的黄酒、佐的是叫人想起孔乙己的茴香豆。席间,我们谈到了诸多话题,其中有个话题是因北京的诗人侯马而起——因在这一日的白天,我收到了侯马寄赠的他的最新诗著《他手记》,便不由得不生发一番感慨,于是激起了在座者的共鸣:在中国数得着的诗人之中,侯马所从事的职业该算是最无诗意的,以其在仕途上的越走越远似乎最有抛弃诗歌的理由,但他却顽强地坚持下来,并且坚持得如此之好!
2. 从那天开始,我一直在读《他手记》,可以无耻地说:是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读的。这一个多月,我确实把自己搞得有点忙:我的首部历史小说,每天要“走”一到两千字,为了对古人的语感保持敏感,每天还要读上两回《水浒传》,为了最终不知能否启程的英伦之行,还要温习一下英语。当然,写诗更是少不了的大事。于是,《他手记》我只能每天读上几页,一路读下来,倒不失为阅读它的最佳方式。
3. 应该从侯马的上一部诗集说起: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那本红彤彤的《精神病院的花园》,系韩东主编之“年代诗丛”第二辑中的一部。老韩的善举令1990年代出道的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获得了一次走进书店的机会,我有幸也在其中,感受到作者们对这一机会的珍惜,绝大多数都是倾囊而出:十本书中,只有我和蓝蓝是阶段性的选集,其他八位作者则出了他们写诗以来的大选集。尽管侯马此前已经出过一本半诗集(《随便吻一下》和与徐江合著之《哀歌·金别针》),但还是将《精神病院的花园》编成了他的大选集,对自己的创作生涯作了一次庄重的总结。我早就说过:出诗集是好事,但也有其残酷的一面,对有些人意味着新的开始,而对有些人则意味着就此终结。以我对这位老同学老朋友多年的了解,我不相信侯马是出一本诗集就把自己终结掉的那种人,但是从编算起两年多没有新作问世的事实,不免让我在心里产生了一丝疑问:这个老侯马,也太看重他的《花园》了吧?这一把歇得是不是有点狠?由于他是个主意太定的那种人,我就没有提醒他。
4.2005年8月底,诗人海啸帮我出了本随笔集《无知者无耻》,并在北京搞了一场以诗歌朗诵为主要内容的发布会,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刚结束了辽东行,乘船从大连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我在北京的住处还是侯马安排的,但是见到他人却很难,那天他突然出现在会场,让我和其他诸友都不免产生了几分惊喜。他拿出一个普通的笔记本给我们几个传看,一段一段札记式的文字,已有将近百段之多,尚且没有名字——这便是《他手记》的雏形。那天,我是头一个上台朗诵的,等我朗诵下来,侯马却已走了,说是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只好赶回单位去,我想他原本是想朗诵那些新写的札记给大家听的。当时为了朗诵,我将一本发有我几十首新作的诗歌刊物带到了现场,等到会议结束,我却找不到那本刊物了。事后证明:是提前退场的侯马同志偷走的,因为我回到西安不久就接到他一个电话,一张口便大谈那本刊物上的我的诗,说我的诗近来有个愈发明显的倾向:就是把话直接说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他说他现在这么写,就是为了把话说出来。他的话我当然听得入耳,因为我的大诗观就叫《有话要说》,杨黎因此说我是“有话要说”的诗人,而他是“无话可说”的诗人——如此分法虽然粗暴,但也说明一些问题。看来,侯马也是“有话要说”的诗人,他要用一种更加开放自由的形式,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
5. 接下来的三年,是《他手记》不断繁衍、频频亮相于官民各刊、好评如潮、上榜获奖的三年。直到2007年6月,我去荷兰之前,侯马在北京国宾酒店的房间中问我:“《他手记》是不是该停了?”我的回答是:“赶紧停下来,就此修改、定稿。”——我从不主动给朋友的写作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有问必答,必以最负责任的态度答之。侯马在《他手记》的后记中如此写道:“这时候,朋友们见面了。十天后,渤海上还会有一条船等待他们。突然他听到了神启:‘死去吧你!他意识到,《他手记》结束了。这是他从事三年的一项工作。”
6. 在这本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小书的封面上,在书名《他手记》之后还有点多余地印着[诗集]二字——我猜:这恐怕是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因为在一般读者看来:诗必分行,不分行者不是诗。所以,必须开宗明义地告诉他们:这是诗集。但我立刻想到:这会对专业人士带来误解,尤其是那些比较懒惰的评论家们,你说“诗集”他们就会理解为这是一些散章的集束并到此为止。殊不知,这是一首完整的长诗,是一部精心完成的巨制。
7. 至于以什么样的名称来说出这部长诗的体例?现存的文学秩序中有一个现成的名词叫“散文诗”,但我更倾向于叫它“诗”——只不过是“不分行的诗”。当年,漓江出版社曾把金斯堡的诗集列入“世界散文诗丛”出版,叫人感觉别扭,你说金斯堡的《嚎叫》《美国》《卡第续》是“诗”呢还是什么“散文诗”?关于这一点,侯马如是说:“《他手记》首先是对诗的反动,又是对诗本质意义上的捍卫。他尝试这样一种可能,就是用最不像诗的手段呈现最具有诗歌的意义的诗。”
8.至于为什么要叫《他手记》?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我想大概是侯马在以往的短诗中已经“我”烦了,索性换成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口吻,让自己跳出来写,还能多少克服一些自恋——人皆自恋,侯马偏重。沈浩波看得准:“作为朋友,我一眼看出,《他手记》里面的‘他,有很多就是侯马本人这个‘我……”在我看来,这种转变视角或人称的做法不甚要紧,有人攻击口语诗老是“我我我”——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我”呢?因为这是对在场感的强调,没有“我”的那些诗,既不在场也无个人,用现代的标准该算伪诗。那么,随着人称的转变,自恋的情绪是不是就随之取消了呢?我看不见得,即便是在《他手记》里,我也看出侯马对自己强烈的爱!呵呵!自恋无罪,关键在于:敢不敢全面客观地面对自己?像他人一样审视自己?我妄加猜度:叫《他手记》并确立这样他者的视角和口吻,是出于潜意识里的一丝怯懦和恐惧?
9. 也不是所有的“他”都是“我”。譬如加题(《八十年代》)并且分行的309:“他天才般地/用一个抽象的词/给人起了一个绰号:/“荒蛮”//一下子就叫开了/写出来不像名字/叫起来却/内圣外化地顺嘴”——这个“他”,不是侯马,而是本人。我发现:当诗中的“他”变成真正的他者时,温和的侯马遂变得犀利起来:“他去探监,希望副厅级监狱长对等接待;他被杀了,家属要求副厅级侦探办案。一生生活在等级中,一生都在自取其辱。”
10. 更关键的:这种形式打开了侯马。从思路到语言。每个人的写作都受惠并受制于他所习惯的形式,侯马过去短诗中那种温润口语轻抒柔情的调子还是限制了他,了解他本人的朋友都知道:那样的诗只展现了他才子的一面或者说只是写出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严重点说:属于往“轻”里走的路子。而在《他手记》中,一个多思、善问、雄辩、深谙世事、深通人性、与时空俱在的强有力的侯马出现了——其实,这正是现实生活中的他。是丰富的唱法拓宽了这位歌手的音域,也令他声音的力度与韧性大为加强。在《他手记》随写随发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了:其中诸多精彩的小节看似难度很大,但对侯马本人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那不过是他思维的仓库中的存货而已。一句话:是“手记体”呈现了侯马较强的理性。
11. 有人正把侯马在诗上的坚持塑造成时代的神话,殊不知,仅靠坚持成不了一个好诗人。外在的敬业远不如内在的懂行来得可靠。譬如说,理性的思考如何能够诗意的呈现?这里头的学问可就大了。在侯马之前很多年,我读过一位知识分子的“不分行”,也爱发问,也爱思考,但却全无答案,一方面他是真的没有答案(也从未真的思考),另一方面,他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掉入“非诗”的陷阱之中,于是便以追问与思考的假招子在那儿使劲地空转(连语式都是固定的套路)。还有一类,真在思考,亦有答案,一旦写出,却成了随笔杂文的小片段。这是“手记体”的内在两难,侯马处理得殊为成功,无答案者必有发现,有答案者不忘形象诗意地加以呈现,一切终归于诗。也许他写的时候,未必会想得如此清楚,但是他的诗感好,便使之得到了很好的把握。照此说来,侯马的坚持绝不是那么咬牙切齿,因为他的生命离不开诗意滋润,他是本质的诗人。
12. 还有人爱拿侯马的“做人”说事,这简直是对一位实力诗人的最大侮辱!不过是想把侯马拉入到他们这些蝇营狗苟的平庸者行列中去罢了。还有人爱拿侯马的“温和”做文章,多数时候带有明确的针对性(无非针对的是我和徐江),譬如将我和徐派去做庸诗榜男主角的同时,将侯推荐到好诗榜那边去,用心可谓良苦!对这些混混儿我顺泼一盆凉水:从交友之道来说,侯马比我和徐江更认实力。
13. 巨型长诗或曰巨制,是中国现代诗在21世纪最大的成熟标志(对比一下1990年代吧,有多少“海子体”的天马行空胡乱抒情一抒到底的无效“大诗”,早已随风而去),侯马之《他手记》便是一大明证,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有徐江之《杂事诗》、唐欣之《北京组诗》、沈浩波之《蝴蝶》,当然,还有笔者之《唐》,都属于扛鼎之作。
14.《他手记》对于侯马而言,还有一个意义,那便是:我发现他在结束“手记体”重返分行诗之后,写得更出色了,比以前的分行短诗出色不说,甚至比《他手记》本身还要出色,比如《进藏手记》。我在这个观念上保守而又顽固:诗是文字分行的艺术,分行是诗的主体和常态,是骡子是马咱们分行了看!
15. 作为老朋友,我多少知道(也能从文本中捕捉到):《他手记》的写作多少与某种情感生活的困顿有关。我不能苛求侯马的笔更狠地戳向自己,用艺术对生活作个了断;我只能欣赏他的叹息,这在很多时候于心不忍。如此说来,艺术干预不了生活,也只是生活的一声叹息。
16.我在二十三年前初见侯马时,他还是个顾影自怜的英俊少年,英俊有才,多情善感,那便只好在女性的青睐中艰难的成长了。如今,他人到中年,英俊依旧,事业有成,诗有别才,对女性感恩般的热爱有增无减,并且深入到灵魂。恕我直言:这也变成了一种累,他对女性的看法与观念让我无所适从,去年在评价女诗人的无聊话题上我们还曾出现过分歧和争论,看完《他手记》中的多节阐述和对“她”的表现,我的感觉是:四张多的侯马还在继续接受着女性的再教育,并力求做成某些知识女性(我不敢妄言人家是“女性主义者”)眼中的模范男人——这可就太累了呀!存疑。
17.说实话吧:诗歌这东西,有一些文字的诡诈术与词语的障眼法可以附着其上,有些并无真才实学者可以借此混迹其中,熬成老混名角都不是没有可能。盖因如此,我看一个人的诗,如果从中看不出他(她)全面的文学素养和才能,便对其诗也不予信任。我想说的是——是为一种提醒:在《他手记》的文字之中至少埋伏着两条道路可走:散文和散文化的短篇小说——前者侯马可以轻易玩好,后者稍下功夫也可能玩好。此次持续大半月的阅读,对侯马这个老伙计还是有些前所未有的新感受:感觉他还是文人本色,并且更像是五四那一代的文人,住在北平而不住在上海的一路,西装也穿得长衫也穿得的一路,一半是志摩,一半是废名,此等人物,两袖清风,傲然遗世,立于今日,于酒囊饭袋之中,显得清气逼人!
2008.10.9-10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