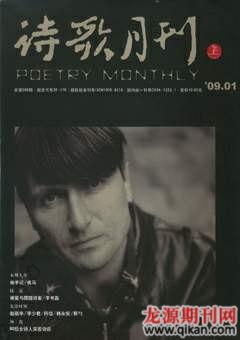谢冕与朦胧诗案
李书磊
在一个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时代里,人们往往以购物者的轻薄与愚蠢判断一切,把现实理解为一连串的时尚而把历史视为过时。文化界也深受浸染,总是倾心于新鲜与流行而忽略从前的那些质朴而深刻的话题。开始于1980年的朦胧诗论争在80年代被意识形态的变动所打断,在90年代又为商业化的社会氛围所消解,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觉得朦胧诗(乃至诗本身)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朦胧诗及其论争中所提出的疑难与困惑并没有真正解答,所包含的紧张与痛苦并没有真正消除,那些看似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语言所暗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没有被真正领悟。问题被淡忘了却并没有消失,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出于对自身现实境遇的关怀(而不是出于考古式的兴趣)我们才重新翻检朦胧诗的论争,重新解读这场论争的代表人物谢冕。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谢冕:谢冕的论说以及他所论说的对象即朦胧诗本身。或许文中的有些部分看似游离了谢冕评论的主题,却是在为理解谢冕寻找不可缺少的背景与参照。
谢冕的论说
作为论争文章,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曰报》1980.5.7)与《失去平静之后》(《诗刊》1980.12)在当时产生了强大的思想冲击。他第一次把公刘也曾注意到的顾城①与舒婷、北岛、江河、梁小斌、杨炼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思潮性现象来论说,并为其作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命名:新的崛起。这种发现、概括与命名至少表现了谢冕两种弥足珍贵的品质:敏锐与勇敢。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会理解其敏锐却未必会理解其勇敢,而我们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这一茬人却能清楚地记起我们初读谢冕文章时的那种惊讶与感奋。在对文化人长时间的、覆盖性的压迫与伤害之后谢冕竟还会这样卓然不群地立举新说,使我们隐约地感到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更使我们在选择自己入世为文的姿态时有了一个直接的榜样。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所以我们才强调勇敢对于一个学者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只有勇敢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造。从思想与文化影响的角度看,谢冕的概括与命名使原本处于朦胧状态的朦胧诗派开始自我发现,他唤醒了那些诗作者们作为一个诗人与作为一个流派的自觉并因此使他们渐成气候;同时他的命名与指认也使社会看到了朦胧诗派的存在从而使这种存在牢固起来。在文学史中,未被及时确认的文学现象往往在形成影响并达到自身成熟之前就归于湮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冕是朦胧诗派的缔造者。考虑到朦胧诗是新时期早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包含了思想方式与艺术方式的双重革命),谢冕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站在今天的水平上我们说谢冕当时越过他的同时代人只有半步之远,但在文化演进中这半步之远常常具有质的意义,常常是两个时代的分界线。
谢冕一开始就对朦胧诗持一种无保留的肯定态度。其时对一种注定要被视为异己的东西予以无保留的肯定,在那种还相当紧张的政治化环境中浑然不觉地表现出与其说是学者毋宁说是诗人的率真,是对知识分子数十年间养成的噤若寒蝉的萎缩人格的超越,更是对长期的限制性的文化教条的蔑视与挑战。在这里,谢冕打破了公刘谈顾城的文章②中所表达出来的“同情——引导”模式。公刘首先对顾城诗中悲观与怀疑情绪表示了同情与理解,但接着又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对这样的思想感情要“引导”也即限制与改造的立场。这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温和包装和文化专制主义,不承认别种的思想情绪具有同自己平等的存在权利;这种表面上的宽容远非是尊重别人精神自由的真正的宽容,之中包含着随时可能变脸、可能启动杀机的内在逻辑(如果对方不接受“引导”、不识抬举的话)。相比之下谢冕这种不在一种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强加于人,又不因那种惯常的危险而自我设防的态度是端正而且可贵的,为即将到来的文化自由时代作了良好的示范。与此同时,谢冕的文章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语调③,并且把话题严格局限在诗与艺术的论域之内(尽管他的话后来被人作了非艺术的意识形态化解释),体现了一个学者成熟的风范。
下面该谈到谢冕对朦胧诗的分析了,这种分析提供了对朦胧诗最初的、迄今为止从框架上来说也是最后的理解。《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从诗歌史的角度论证了朦胧诗的合法性。他把朦胧诗的特征定义为“大胆吸引西方现代诗歌的一些表现方式”,并把中国新诗的源起论证为“主要的、更直接的是借鉴外国诗”的结果,这就把众人眼中突如其来且大逆不道的朦胧诗同中国新诗的最初传统接续起来,将它看成是对60年代新诗“越来越狭窄”歧路的一种拨乱反正,这就为朦胧诗找到了有力的生存依据。同时,谢冕还从诗歌史接受规律出发回击了对朦胧诗“不让人懂”、“古怪”的责难,指出“古怪”正是新兴艺术在其初兴之时的必然面貌:“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谢冕由此也把诗歌史描绘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
在《失去平静之后》中,谢冕则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证了朦胧诗的合理性。他把朦胧诗中孤独、怀疑等现代主义情绪及其晦涩、曲折的表达方式同十年“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把前者解释为对后者对应性的反叛。在当时的言论限度下,这是为朦胧诗所能找到的最巧妙的辩护,因而很容易使人嗅出其中的策略性意味:然而,策略性并不是这种提法的全部,这种提法自有其主观的同时也是客观的真实性,只不过这真实性并不像谢冕所叙述的那样表面而直接而己。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体系与朦胧诗及其所引发的论争之间确实有一种紧密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比谢冕所叙述出来的更为隐密和深刻。从分析这种隐密关联开始我们可以达到对朦胧诗这一艺术现象、对朦胧诗论争这一意味形态现象历史与同情的认识。谢冕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他并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他这种提出已经给我们今天的研究提示了关键性的线索。
谢冕论说的对象
正如谢冕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朦胧诗的直接背景与反抗对象。对于“文革”,史家和文学史家都众口一词地将其定性为一场封建主义的大回潮和大泛滥,因而朦胧诗也就是从反封建的意义上获得了现代性质。不过,仔细地推敲起来,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封建主义运动虽不无理由却终嫌悖谬,这种定义缺少对史实与概念深入的体察和辨析。20世纪以来封建主义一直被中国进步文化界当成头号敌人,在长期的、严酷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定势,常常把相类甚至不相类的对手一概视为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在这里成了一只空筐,成了激情洋溢却思想懒惰的知识分子对一切当代丑恶势力的宣判词。其实,文化大革命及其所代表的体制具有中国封建时代(这里暂且不对“封建”一词质疑而采用习惯用法)所根本不具有的崭新特征,其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能力是封建社会无法比拟的,其目标和手段以及由之带来的社会状态也同封建时代大相径庭。如果抛开当代人评论当代史常有的个人化与情绪化偏见,抛开某些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宁肯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扭曲的、病态的并且最终失败了的现代化实践。上世纪30年代苏联模式的确立宣告了人类经典现代化道路的中断和一种新的现代化试验的开始,它是后发国家现代化代价巨大但在当时条件下惟一可能的选择。中国50年代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而到了60年代,由于中国最高领导者个人性格和气质的特异,这种模式终于演化为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苏联模式是对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变异,那么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又是对苏联模式的变异;尽管这种变异几乎达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但变体在本质上却仍然表现着原体的特性——对这一复杂的历史学判断我们在这里暂且取其结论而省其论述;或许下文诗论中的某些征引可以看作是这种结论的印证,但我们真正的意图则是借助这种结论理解诗。
美国文化学家M·克里尼斯库认为,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现代性,一种是以社会进步、合理化、竞争和技术为内容的主流价值,另一种则是对这种主流价值的文化批判和消解。也即是说,现代性同时包含着现代与反现代两个侧面④。这种针对西方社会的具体分析用来描述中国事实或许并不特别贴切,但这里给出的同时容纳着正反两面的现代性模型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变异的现代化运动体现了现代性,而朦胧诗作为“文革”的叛逆也体现了现代性,只是这一对立统一较之西方中产阶级精神(主流价值、现代)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文化、反现代)的对立统一要显得复杂、纷乱一些。朦胧诗乃是对一种经过双重变异的现代化运动的反叛,它一方面作为对现代化的反叛不可避免地重复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情绪与语言,另一方面作为对现代化变异性的反叛它又呼唤、赞美甚至依仗着西方现代的主流价值。这种奇异的交叉乃是朦胧诗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特征,在阅读中我们不断加深着对这种特征的认识。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顾城少年的眼睛里,最鲜明而突出的乃是工业化景观。对工业化景观的强烈感知与渲染构成了顾城早期诗作的中心意象:“烟囱犹如平地耸立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烟囱》)。巨人般的烟囱俯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这种带有巨大震撼力的现代景象占据了顾城的心,以至于他不自觉地要对自然作工业化、城市化的想像:“阳光是天的熔岩/阴霾是天的煤矿/星团是天的城市/流星是天的车辆”(《天》)。“时间的列车闪着奇妙的光亮/满载着三十亿人类/飞驰在昼夜的轨道上/穿过季度的城镇/驰过节曰的桥梁/喷撒着云雾的蒸气/燃烧着耀眼的阳光”(《社会》)。即使是在下放的乡村,在最富有浪漫诗意的乡村夜晚,顾城也难以摆脱城市与工业的高度组织化在他心中留下的深深印痕:“浓厚的黑夜/把天地粘合在一起/星星混着烛火/银河连着水渠/我们小小的茅屋/成了月宫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顺便问问户口问题”(《村野之夜》)。去月宫喝茶而“顺便问问户口问题”,这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显得过分阴沉的表达可以看作一种内心创伤的袒露。
关于对现代创伤的表达,舒婷的《流水线》可以看做是经典文本。这首作于1980年的短诗细腻地传达了人对于压倒性的工业生产/生活方式的体验。夜晚、星星、小树和“我们”都被统一成了工厂流水线的状态,疲倦的星星和失去了线条与色彩的小树印证着人的自我的麻木乃至丧失:“但是奇怪/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仿佛丛树与星群/或者由于习惯/或者由于悲哀/对本身已成的定局/再没有力量关怀”。在这里作为对象的世界和作为主体的人生达到了无差别的重合,使人陷入无可逃避的单调之中,人所拥有的仅仅是对于这种处境的瞬间的、微弱的但终于也无能为力的觉悟。这种情态自然地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业劳动的描述和认识,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等诸多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工业和商业制度下人的处境的表现。
然而,细细体味我们不难发现,朦胧诗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相近的同时还有明显的分别。其中最重要的分别就是朦胧诗从来没有过西方现代作品那种深刻而强烈的绝望,没有那种包含着紧张与焦灼、最后终于演化为黑色幽默的绝望的自虐倾向。舒婷的诗被普遍认为不乏亮色自不待言。就连更为异端的北岛,其愤怒和痛苦因为有具体的指向和缘由也显得有几分明朗。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是一种变异的现代,其变异性也正是其不成熟性和不完全性;具体地说,文化大革命及其体制作为中国式的现代状态所表现出的是对于人的一种有形强制,而不是像西方的现代那样是一种无形的、不可言说因而也不可反抗的强制,有形强制至少向人提供一种反抗并且战胜它的希望,唤醒人的斗争意志;而无形强制使你丧失了敌人甚至堕入与自己为敌的疯狂之中。马尔库塞在分析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指出,这种社会对于人的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的“能力”(思想和物质的)比以前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它的特点是“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⑤。也就是说,在这里人的异化成了如同空气和呼吸一样的正常和必然,社会加于人的是一种自由的专制和温情的恐怖。在这种气氛的覆盖和渗透下个别觉悟者的觉悟只能归于荒诞和颓废,甚至于连他们的表达的语言也变得晦涩和含混起来。弗罗姆在奥威尔《1984年》的后记中曾尖锐地批评西方人的偏见,他们认为《1984年》描绘的可怕的专制只属于苏联和东方而与西方无涉,因而不免沾沾自喜起来;弗罗姆指出现代的专制属于全人类⑥。当然弗罗姆的话是对的,但他却没有深入地辨别西方式专制与苏联式专制的区别即无形与有形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毋庸置疑是一场有形的现代强制(专制),它不折不扣是靠恐怖来维持的,它表现出的乃是对人的“基本压抑”。或许这种“基本压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压抑与剥夺,但它更直接、更残暴的表现却是政治压迫。所以朦胧诗也即中国的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主题却是政治压迫。所以朦胧诗也即中国的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主题即是政治叛逆。当北岛写他的《回答》时,他也为中国的现代主义定下了基调:“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里的反叛不是反社会、反文化、反人类,而是明明确确的反暴政。由于观念、目标、技术和组织手段的现代性,文化大革命中所体现的政治专制截然不同于古代的封建专制,它因为乌托邦的理念而变得更加狂热、残酷而泯灭人性,因为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技术化也即控制方式的巨大进步而具有了鲜明的法西斯性质,因而它对人的伤害也就更深重。这种社会作为文学对象相应地也就引发了朦胧诗的战斗性。所谓战斗性是说在朦胧诗中批判是自觉的、直接的、有主体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那种消隐了主体性的、更多的是靠历史之手书写的批判文本。“我无法反抗墙/只有反抗的愿望”(舒婷:《墙》)。墙在这里是异化了的社会机器的象征;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有“墙”,同时还有怀有反抗愿望的“我”。惟因有这个“我”的存在,“无法反抗墙”的陈述与控诉同时又是一种真实的反抗。作为男性,北岛诗中的“我”比舒婷更加突出:“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以显得刽子手们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同样是面对异己而强大的统治力量,朦胧诗中受难而不屈服的“我”与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叛》中丧失了意志与愿望也即丧失了自我的人物形成了根本的差异。
“我”是谁?在朦胧诗中,“我”即是“人”。这里的“人”甚至还主要不是指与群体相区别的个人,而更多的是指与物、与工具、与机器和机器上的螺丝钉、与奴隶相区别的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人。文化大革命及其体制把人变成了工具和奴隶,可以驱使、凌辱、残害乃至消灭,在这场经过了双重扭曲的现代化运动中人变成了可以随时抹去的统计数字,马克思所讲的“人的类本质”遭到了本质性的否定。这时候朦胧诗举起了“人”的旗帜。北岛写道:“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舒婷写道:“父亲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火力/难道我仅比爷爷幸运些/值两个铆钉,一架机器”(《暴风过去之后》)。“人”、人道主义在这里出现具有了新的、反异化也即反现代的意义,与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反神学、与中国“五四”时候的反礼教不同。或许西方的例子可以作为参证:当萨特宣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时,我们不难体味他的人道主义的现代含义。当然,朦胧诗作为对“扭曲的现代”的一种反抗形式,其内涵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它既有反对“现代”以求人的最后解放的倾向,又有反对“扭曲”以恢复正常的“现代”的倾向(如朦胧诗人对政治体制的赞美,实际上朦胧诗最早出现在“墙”上),这两种倾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殊面貌。这种特殊性增加了我们理解的困难,但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审美感觉。
在后来的朦胧诗论争中,对朦胧诗一种重要的指责就是说诗中的“我”是沉湎于一己情绪个人情结的“小我”而不是代人民立言的“大我”。这实在是了无识见的陈言。当然朦胧诗比起文化大革命那种大而空的诗歌,较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心绪乃至爱情,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朦胧中的爱情表达多带有向非人的现代体制示威的意味,表示“我是一个人”而并非工具与奴隶,这种爱情诗乃是社会叛逆的一种特殊方式。文化大革命中个人的愿望、欲望被严厉禁止,这种禁止赋予了爱情及爱情诗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所以北岛在爱情之夜的欢愉中想起的是“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雨夜》)。在这种情景中北岛笔下的爱情就获得远超出于一己私情的神圣、庄严和悲壮:“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夜晚升起在我的小窗前/唤醒忘记”(同上)。爱情诗这种“人的示威”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区别于西方的“现代”,也区别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中国的现代主义的又一种特征与标识吧。
余论
上面对朦胧诗的分析乃是对谢冕理论的生发或者说是阐释。后来(1983年左右)针对谢冕以及“三个崛起”的讨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化方式的转换(由变异归于正常即由计划变为市场)中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摩擦。目前的社会状态已与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年代大不相同了,更新的诗人也早已完成了对北岛与舒婷的“打倒”,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也与那时候大异其趣。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现在还仍然处于现代化方式的转换之中,我们的情感仍是舒婷与北岛诗的延长,所以谢冕对于我们还仍具有直接而亲切的意义。
注释:
①②公刘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中注意到顾城。此文载《星星》复刊号。
③李黎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坛奇观》一文(《批评家》1986.2)中也曾提及谢冕的平和态度。
④MateiCalinescu: Five Facesof Modernity.DukeUniversityPress.1987,P.265
⑤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P2。
⑥ErichFromm:AFterwordsof1984,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