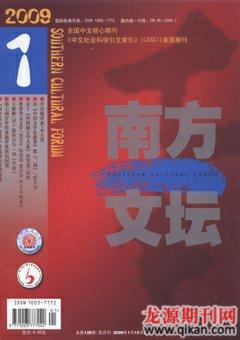新世纪的新青年
李云雷是这个时代最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来自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不同的是,他没有那些“才子们”头颅高昂眼光轻慢的优越,也没有故作的深沉或激进的面孔。接触他的人,无论年长年幼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信任;他单纯、友善,为人诚恳、处事认真;他热爱朋友,尊重别人,讨论问题从不咄咄逼人居高临下。在他身上,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他出生于1976年,今年才三十出头。当然,令人艳羡的不止是他的青春,还有他才华横溢的文章和不能妥协的批评锋芒和立场。在并不漫长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李云雷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这就是在注重文学审美标准的基础上,同时注重文学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支持先锋前卫探索的同时,更注重对传统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在密切关注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时候,也注意从其他艺术形式中看到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和同一性。因此,李云雷的文学批评不仅与当下文学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他宽阔的视野和鲜明的介入意识,使他成为维护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尊严最具活力的声音之一。他迅速地站在了时代批评的最前沿,他是新世纪的新青年。
文学批评不断遭到诟病的重要理由,就是文学批评的软弱、甜蜜,是文学批评的缺乏担当,不能直指时代文学的病症,文学批评的公共性正在丧失,信誉危机正在来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指责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这确实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而且在大众传媒中甚至是主流。但是,这却不是文学批评的主流。我曾多次表达过,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样的道理,评价一个时代批评的成就,也应该着眼于它最有力量的声音,是它突出的高音声部而不是合唱。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李云雷的批评实践就是这个时代最有力量的批评声音之一。他不那么华彩,但言之有物;他不那么激烈,但立场鲜明;他平实素朴,但暗含着内在的不屈和坚韧。
几年来,“底层文学”的出现和伴随的争论,是这个时代唯一能够进入公共视野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人为制造的文学骚乱。事实上,社会分层业已成为事实,现代性过程中始料不及的问题日益突出并且尖锐。文学当然不能无视这一存在,“底层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李云雷是一直关注这个文学现象的重要批评家。几年来,他先后发表了《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纪念《讲话》65周年》、《“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访谈等。在这些文章中我发现,李云雷的批评并不只是一种情感立场或表态式的站队。在《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① 中,他细数了《那儿》发表以来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分析了作品引起反响的社会和思想界论争的背景,评价了作家曹征路前后发表作品的不同反响等。这一细致的梳理,是李云雷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做出的。这不只是一种批评修养或学术训练,它更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他有自己的观点,但绝不忽视或轻视别人的观点,而是客观地反映了论争中存在的不同观点。这一梳理和呈现显示了李云雷文学批评的胸襟和纯粹。
李云雷参与的论争,不仅密切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况,比如他对曹征路、胡学文、刘继明、鲁敏、陈应松等的评论。这些评论分析中肯,切中要害。他评价胡学文是“底层生活的发现者”②,鲁敏“更注重从精神方面考察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不追求戏剧化的冲突,而力图在对底层生活的描绘中呈现其真实状态,在这种意义上”,鲁敏对“底层文学”的书写是一种丰富与发展③。他评价刘继明的创作“代表了一种趋向,他的写作向我们表明了‘先锋的当下形态,那就是向“底层”的转向”④。这些评论表明了李云雷对“底层写作”主要作家的熟悉,这也是他赖以建构自己批评观点的基础。事实上,分析具体作家作品或许相对容易些,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底层写作”的来源、发生以及承继关系,可能要困难许多。
与“底层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参与不同的,是对“纯文学”的讨论。李云雷显然不同意“纯文学”的说法。事实也的确如此,百年来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从来也没有“纯”过。80年代中期以来,“纯文学”离开关注社会现实的立场,在形式和语言试验中寻找新的方向是有具体语境的。文学要求自主性,要求自立,是为了反抗政治的强侵入或胁迫。但时过境迁之后,文学有理由重返现实,有义务关怀当下的公共事务。因此,在李云雷看来:“对‘纯文学的反思,是文学研究、理论界至今仍方兴未艾的话题,而‘底层叙事的兴起,则是创作界反思‘纯文学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展开。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底层叙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它将‘纯文学囿于形式与内心的探索扩展开来,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良性状态。”⑤ 将“底层文学”命名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是李云雷的一大发现。这种识见与他的文学史训练有关。“左翼文学”,特别是蒋光慈的作品,在他的时代引领了文学风潮,蒋光慈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底层写作”继承了左翼传统,说它是今天的先锋文学未尝不可。当然,“底层写作”不是对“左翼文学”简单的继承或“克隆”。他们在精神传统或文学脉流上的关系,也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这一点李云雷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认同“左翼文学”精神的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学的最大教训,则在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宣传、控制的工具,并在逐渐‘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排斥了其他形态的文学形式,而且在“左翼文学”内部不断纯粹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最终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文学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追求,不再批判不公正的社会,也不再反抗阶级压迫,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⑥。这种警醒决定了李云雷面对“底层文学”批评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
事实上,我认为李云雷对“底层写作”的研究和批评,更大的贡献可能来自他对这个文学现象的检讨和批判。他坚定地支持这个写作方向,但不是一味地偏爱袒护,而是为了它更健康地发展。他曾指出:“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凡是写底层的作品必然不足观,必然在艺术上粗糙、简陋,持这样观点的批评家颇有一些,他们还停留在反思‘纯文学以前的思想状态,并没有认识到‘纯文学的弊端,也没有认识到‘底层叙事出现的意义;另一种倾向则相反,他们认为凡是写底层的作品必然是好的,这样就将题材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从而降低了对‘底层文学在美学上的要求。”⑦ 类似的意见大概只有李云雷在强调并坚持。他在维护这一文学现象的前提下,更多的是看到了“底层写作”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因而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有:1. 思想资源匮乏,很多作品只是基于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这虽然可贵,但是并不够,如果仅限于此,既使作品表现的范围过于狭隘,也削弱了可能的思想深度;2. 过于强烈的‘精英意识,很多作家虽然描写底层及其苦难,但却是站在一种高高的位置来表现的,他们将‘底层描述为愚昧、落后的,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底层蕴涵的力量,也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和他们平等的位置;3. 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海外)市场,而不能为‘底层民众所真正阅读与欣赏,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⑧。
在具体的创作中,他发现了“作家无法对历史、现实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因而呈现出了一种雷同性”。比如:
在《受活》中,我们看不到茅枝婆、柳鹰雀等人行为做事的内在逻辑,在《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中同样如此,当一个人的行为无法为人理解的时候,作者便会将之归结为主人公性格的“执拗”。于是,在《第九个寡妇》中,当我们无法看到王葡萄20多年掩藏“二大”的合理解释时,作者便将这些归于王葡萄性格上的“一根筋”:“她真是缺一样东西,她缺了这个‘怕,就不是正常人。她和别人不同,原来就因为她脑筋是错乱的。”在《生死疲劳》中也是这样,蓝脸在“合作化”大潮中一直单干、洪泰岳在公社解散后仍然坚持“合作化”,似乎都没有什么的道理,仿佛都是因为他们“认死理儿”,是性格上的孤僻、偏执所导致的,将故事的进展及逻辑推进仅仅诉诸于人物的“一根筋”,大大削弱了作品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普遍性。
另一方面,在《生死疲劳》等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中间人物”。而在《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既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人”王金生、梁生宝、萧长春,也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中间人物”如范登高、梁三老汉、弯弯绕、滚刀肉等等。如果说前者代表着时代方向和作家的社会理想,因而不免有些单薄,那么为数众多的“中间人物”则让我们看到了农村中的更多侧面,其中既有作家对时代精神内涵的把握,也有对民间文化、农民心理的深入了解。⑨
对“雷同”现象的批评,显示了李云雷锐利的眼光。这些作品是否存在“观念化”的问题可以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在观念的统摄下,乡村中国丰富、复杂以及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一定会被遮蔽。特别是在细节的展现上,作家对乡村生活究竟有多少了解,读者一目了然。在这一点上,《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类题材创作中得到继承。事实上,即便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如果剥离了它阶级斗争的观念,那里丰饶的乡村生活气息以及生动的人物形象,仍然是今天的小说难以超越的。
另一方面,李云雷还发现了“底层写作”中对“中国”叙述的问题。他以《碧奴》、《新结婚时代》、《凶犯》等作品为例,具体探讨文学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想象,如何决定了它们对“中国”的叙述。他认为:
上述三种类型的作品视为一个“文学场”,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作品类型与生产模式:适应海外市场跨国运作的先锋派作品;面向市民阶层、与电视剧制作紧密相关的新写实作品;借助于影视媒介权力的“主旋律”作品。事实上,这三类作品构成了当前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主体。他们借助媒介、意识形态、市场的力量,构成了一个互相交错又互相制约的“文学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当代》杂志最新的一期“阅读排行榜”上,《碧奴》和《新结婚时代》分别获得了专家奖与读者奖,这反映了这两部作品在艺术与商业上的成功,但同时也说明,它们的生产方式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反思。我们不否定这些作品在某一类型中是优秀的,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真的中国”,它们所提供给我们的或是意识形态的幻像,或是商业化的通俗故事,或是“纯文学”的幻觉。而关于当下中国的真实情况,却没有被表现或者被很片面地表现了出来,呈现在作品中是暧昧不明的形象,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国。⑩
类似的问题还表达在李云雷对“大片时代”“底层叙事”的批评中。他考察了《三峡好人》、《盲井》、《盲山》、《长江七号》、《苹果》、《我叫刘跃进》、《疯狂的石头》、《卡拉是条狗》、《我们俩》、《公园》、《落叶归根》、《光荣的愤怒》、《好大一对羊》、《乡村行动》等影片。认为这些影片是当下中国文艺“底层叙事”的一部分,在突破商业大片垄断,找到了一条关注现实并进行艺术探索的新希望和新道路,但同样存在着“精英视角”以及“被娱乐遮蔽的大众”的问题。他激烈地批评了《苹果》、《我叫刘跃进》和《疯狂的石头》等影片:
在《苹果》中,虽然出现了底层的洗脚妹与“蜘蛛人”,但影片真正表现的主题却是“情欲”,底层以一种在场的方式“缺席”,并没有得到关注,而只是构成了影片的叙述元素,并被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刻意地扭曲了。在《疯狂的石头》复杂的故事网络中,也涉及到了房地产商对公共资源的侵占,以及下层小偷的困窘处境等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正视,影片以将之作为背景或者纳入到总体性的叙事结构中,成就了一场叙事上的狂欢。
《我叫刘跃进》与《疯狂的石头》相似,也力图将对底层的叙述纳入到一个大的结构中去,在“几伙人”的互相斗争与寻找中,影片试图表现小人物的无奈和世界的复杂性。然而这个影片却不是很成功,首先在娱乐性上,它并没有达到《疯狂的石头》的狂欢效果,这是因为它的线索并不清晰,出场人物比较杂乱,又过于讲究戏剧性与偶然性,这使故事本身显得支离破碎,缺乏一个稳定的内核;其次,在对底层的表现上,影片将之纳入到与不同阶层的对比中,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思,但影片虽然触及到了底层的真实处境,但却将重心放在不断地编织外部关系上,从而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滑过了对底层的关注。(11)
因此,李云雷是一个真正的“底层文学”批评家。他不止是以题材判断作品,不是写了“底层”就是好作品。他是真正关心这一文艺现象。从他的立场上看,这些批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他是在具体细致的艺术分析中概括出自己观点的。这使他超越了“左翼”以来文学批评的民粹主义立场。
与此相关的是,李云雷的所有批评几乎都与乡村中国有关。他对《苍生》、《秦腔》等的批评,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使很多人避之不及。无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时髦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是一个历史存在,而且今天仍然没有成为过去。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市场”作为唯一选择的神话不攻自破。政府干预或“救市”行为在西方世界也普遍实行。如是看来,不仅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个未竞的方案,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同样处于不确定性之中。过早地怀疑甚至抛弃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也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思想潮流。李云雷“逆潮流”而动,坚持本土关怀,持久地凝望百年中国革命历史,并将其作为重要资源试图总结出有益的经验,这一出发点和批评实践使他独树一帜卓尔不群。
对李云雷的文学批评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全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李云雷同样有为“真理意志控制”的问题。比如,“底层写作”的提出和它的承继关系,原本是在严肃文学的范畴内展开的。他在这一范畴内展开的批评几乎无可厚非,提出的问题敏感而尖锐。但是,当他把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形式也囊括其中的时候,他模糊了严肃艺术与文化产业的界限。严肃艺术是形式探索、追寻意义、表达价值观和终极关怀的艺术;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作为依托,最大限度地寻找附加值,并赚取剩余价值的产业行为。一个是精神活动,处理人类的精神事务;一个是商业活动,处理的是经济事务。如果全部用精神活动的尺度要求或度量商业或经济活动,就是一种错位的批评。如果从严肃文艺的角度说,《黄金甲》、《疯狂的石头》等是不成功的话,那么,从文化产业的角度说它们就是成功的。这也是大众文化和严肃文化或精英文化的根本区别。事实上,李云雷在分析或批评这些影片的时候,其说服力也没有达到批评《色·戒》的高度或水准(12)。这个“真理意志”还表现在他的概念的使用,比如“真的中国”,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真的中国”是无从表述的,任何一个人都只能表达部分的中国,只能表达他所理解的中国,那个“真的中国”只能是本质主义指认的“中国”。如是看来,李云雷在批判“精英主义”立场的同时,他自己就在这个立场之中。话又说回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有谁站在这一立场之外呢?
当然,无可非议的批评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也无足观。尽管我对李云雷提出了不见得准确的“批评”,但我仍然欣赏并支持他的“深刻的片面”。在7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中,有了李云雷,文学批评就有了新世纪的新青年。■
【注释】
① 李云雷:《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载(台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6年3月。
② 李云雷:《胡学文:一棵树的生长方式》,载《广州文艺》2008年第1期。
③ 李云雷:《“底层”、魅惑与小说的可能性——读鲁敏的中短篇小说》,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④ 李云雷:《刘继明:先锋的“底层”转向》,载《长江文艺》2008年第3期。
⑤⑦ 李云雷:《“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纪念《讲话》65周年》,载《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
⑥⑧ 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文学”所面临的问题》,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⑨ 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载《上海文学》2006年第11期。
⑩ 李云雷:《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之二》,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
(11)李云雷:《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载《艺术评论》2008年第3期
(12)在《〈色戒〉: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一文中,李云雷细致分析了关于这部电影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电影节的反应。他说:“最近围绕着电影《色·戒》,出现了不少评论,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倾向,一是在艺术上加以肯定,认为这部片子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永恒,是2007年度最佳‘华语片,或成为‘票房冠军,这是在主流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声音;另一方面,则对电影、以及张爱玲的原著小说对郑苹如烈士的污蔑而愤慨,将这部片子定位为政治电影或‘汉奸文艺,认为它触犯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有激进者甚至呼吁对这部影片加以禁映。”“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个案,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有关这一影片的其他事实:在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这部影片获得了金狮奖,这是否意味着它在‘艺术上获得了承认,而这艺术又是一个怎样的标准?这部影片在美国被列入NC?鄄17级,并被拒绝作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是否意味着它在情色上的大胆突破不被美国人接受,或者它的‘艺术不被奥斯卡接受?在台湾首映时,国民党2008年参选人马英九“热泪盈眶”,这与70年代小说《色·戒》在台湾发表时青年学生的反应大相径庭,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已经在向民进党的“殖民史观”靠拢?在大陆放映时,该片被删减了7分钟,主要是三次男女主人公的激情段落,但也有一处将关键的‘快走,快走改为‘走吧,走吧,模糊了女主人公放走汉奸的事实,这是否意味着色情的禁忌更重于意识形态的禁忌?可以说,围绕着《色戒》这部电影、小说及其所由来的历史事实,在政治、性、艺术与商业各个层面的张力中,我们可以窥见一种复杂的情态。”
这种认真对待而不是简单的情感立场或表态,显示了李云雷的专业素质和学术训练。但在批评其他商业影片时,强调的只是一种底层立场。两者相差甚远。
2008年10月31日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