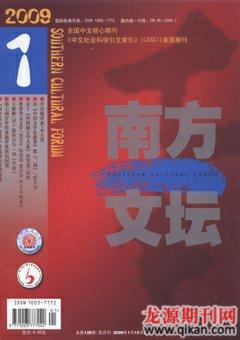当思古鼎初造时
1982年秋我考入复旦中文系,正碰上系主任章培恒先生为诸生讲上古至六朝文学。目前这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上卷”,我是听章先生用绍兴普通话亲口讲过一遍的。二十五年后再“听”,觉得比当初课堂讲授丰富多了,但框架无改,声调犹存。可惜章先生古稀刚过即染沉疴,入秋之后,缠绵病榻,竟逾旬月,虽坚持出席全国三十多位专家特别为《新著》举行的研讨会,却坐不终席,再三抱歉而告退,我作为老学生,不禁感慨系之。
本科毕业后我也偷读了章先生不少书,包括《洪昇年谱》——跟后来的《献疑集》、《灾枣集》一样,都是乱翻一气便放下了。程度低,看不懂。略微看懂一点的,是他对“三言”、“二拍”以及《封神演义》、《西游记》诸小说的考证与评介。近年来他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大思路中探索明、清两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因素,一系列论文倒仔细拜读过,因此《新著》“中卷”和“下卷”,也算零星有些接触。
凭这点因缘,评说整本《新著》,自然很不够格。不过当初被《洪昇年谱》吓着,没敢去读古典文学的硕士博士,现在仅以“槛外人”身份说点读后感,谅章先生不会见怪罢。
国人大规模撰写中国文学通史,五四前就已开始,但真具现代意识的还要到五四以后乃至三四十年代。实际发生影响的,恐怕又并非那些教授之书,而是新文学领军人物胡适、鲁迅、周作人的著作。胡适只写了《白话文学史》(上卷),鲁迅只有《中国小说史略》和上古至西汉中叶的《汉文学史纲要》,周作人只做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但他们比现在许多人称道的五四前后的林传甲、黄人、谢无量诸人更具现代眼光,也比后出的郑振铎等更富创见——自然偏颇也在所难免。50年代之后刘大杰、林庚、游国恩、余冠英诸前辈独力著作或集体合作的文学史(刘书写于抗战时期,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41年和1949年,50年代后才广为人知),规模更见拓展,体制更趋完备,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犹为自觉,但整体的创见,似乎并未超出胡适与“二周”。
章先生《新著》汲取大量文学史研究成果,以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现代形式论美学做经纬,但论其对中国文学本身的认识,以我浅见,恐怕与五四因缘更深。具体说,就是颇采“周氏兄弟”成说,对胡适则时有反动。学术统系上,《新著》是对五四至三四十年代新文学内部一系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再发挥。
比如章先生认为,“上古文学的特色对后世文学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特色是在民族文化的厚实土壤上形成的”。他开讲整部中国文学史之前,先讲中国民族文化上的三大特色,而他对这三大特色的阐述,就都与“二周”有关。
第一,崇尚群体而压抑个体。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以及20年代《热风》里反复阐明,中国自古有“以众虐独”、“众数压倒个人”、“只有合群的自大没有个人的自大”的传统,因此“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这个传统当然不利于章先生所主张的最终指向人性解放的文学,所以他大胆认为,中国文学在自发阶段就已经出现“异化的滥觞”。而且,“不但《庄子》和《战国策》不是文学作品,就连《诗经》和《楚辞》也不是文学发展的自觉时代的产物”。这是历来(包括现在)许多文学史家不敢说、不愿说的。大胆反思传统,不一味歌功颂德,这种论史的胆识,推其源头,实为鲁迅。
第二,重具体感受(主观和直观)而轻玄思。这也和鲁迅有关。1907年作的《摩罗诗力说》阐明“诗”(广义的文学)的特点在于“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究理弗存”,即不尚玄思,贵在“直语其事实法则”,即直观人生与自然。1923年印行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解释“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时,引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说法,“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鲁迅虽然另有“尤在神鬼之不别”的解释,但显然也同意盐谷温的说法,所以1925年整理前一年在西安关于《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讲稿时,就直接采纳了盐谷温的说法。竹内好说“鲁迅一生与抽象思维无缘”,胡风说“概念的字句在鲁迅作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则认为鲁迅自己的文字创作也具有中国文化这一基本性格。鲁迅确实意识到学术和文学的分途,《摩罗诗力说》即认为“诚理”是“不能假诸学子之口”的,只能宣诸诗人心声。这和萧绎《金楼子·立言》区分“儒”、“文”并进一步区分“学”、“文”,道理相通(《汉文学史纲要》已注意到萧绎这一文论思想)。章先生抓住这点多所发挥,在鲁迅的文学观与传统文论之间建立了一条显豁的联系。
第三,重文字而轻口语,认为中国文学很早就意识到文字的重要,很早就看出“言文”必须分离,方始有文学。这正是鲁迅的观点。《汉文学史纲要》一上来就讨论“自文字至文章”,明确指出“初试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鲁迅并不笼统地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汉字决定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与后来的发展,章太炎“文学复古论”早就说得分明,这个观念五四之初虽大受胡适冲击,但很快即由“周氏兄弟”加以弥补。周作人从20年代中期给刘半农《扬鞭集》作序到40年代重新清理中国文学传统,其间注重汉字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独特的修辞手段,呼吁重新研究八股和骈文,可谓再三致意而始终不改。1932年在辅仁大学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论到“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时,周作人毫不犹豫将“文字学”列在第一位:“这是不消说的,研究文学的人,当然先须懂得文字。”在章太炎和“周氏兄弟”启发下,对中国文学和汉字的关系,后来郭绍虞、朱光潜等人更加以邃密的研究,冯至、闻一多、陈梦家、李长之以至汪曾祺诸人热烈响应,现代文学终于没有完全变成“写话”,当今文学也没有整个堕落到质木无文,我觉得确乎要拜这一系文字/文学的思想所赐。
这是“第一编·上古文学·概论”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之文化土壤的基本判断与“二周”的因缘。
进入文学史正文叙述之后,“二周”的影子也历历可见。
比如,以魏晋为中国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第一座高峰,这个观点,虽然刘师培倡之在前,但章先生认为还是经过鲁迅大力推阐,才被世所公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也很清晰地发挥了这个说法。
至于主要着眼于晚明到清代的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新文学的内在关联的“古今演变”理论,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关系就更加明显。
周作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那一次(按指公安、竟陵以及两派在清初张岱诸人身上的融合)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的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从此,也更可以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了。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学内部不断进化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发生的,外来影响不过加速了这一演化而已。胡适谈白话文学形式的演进是这么谈的,但他只是就白话文的形式而论及中国文学进化的自主性,章先生则将这种自主性的看法深化到文学内容即中国人性的发展,对胡适之来说,可谓买其椟而还其珠。
从内容上谈论中国文学进化的自主性,是周作人研究明清至五四文学的灵魂,但周作人只提了个头,章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实做了,并且做得很细。
我没有细按《新著》小说部分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但见章先生凡论及重要小说,个别史实考据虽然未必尽依鲁迅成说,但内容分析和艺术评价部分,正文和注释几乎都会提到《中国小说史略》。
六朝的“美文学”,章先生情有独钟,我读书时对此印象也最深。清楚地记得,他是那么绘声绘色为诸生解释梁简文帝萧纲《咏内人昼眠》的“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两句诗,盛赞其描写细腻,观察真切,虽然香艳得很,但章先生端然授之,诸生也俨然听之。说到左思(或鲍照)一首描写寒风从门缝吹入的诗,他还特地穿得很少,把第二教学楼二楼本来就不太严的大门虚掩着,叫我们和他一道感受从齐梁时代吹来的袭袭冷风。
其实,这里面就包含着和“周氏兄弟”有关而足以支撑《新著》框架结构的两个基本的文学元素,也是《新著》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两条基本线索。
首先是注重个人情感,尤其是个人的激烈的情感,排斥超越个人的抽象真理。章先生论文,极其推重刘勰,但批评刘勰“原道”、“征圣”、“崇经”的儒家保守思想,兼及后世一切载道观念,而肯定“言志”、“缘情”与“性灵”诸说。他反复赞扬萧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也再三征引萧绎的“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情灵摇荡”(这都是我们读书时最为熟悉,茶余饭后,采作谈资的)。当然我们也很熟悉章先生大肆阐发的伍子胥“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生当五鼎食,死当五鼎烹”,以及李陵的忍辱大漠,苏武的绝情汉室,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乃至杜甫所拟想的王昭君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章先生肯定这些不平之鸣,过激之论,绝非“观奇而跃心”,乃是用他那一代人数十年心灵创伤做底子。后生不明此理,津津乐道,“童蒙者拾其香草”罢了。
章先生说起古人,并不因他们是古人就特别恭敬,而是将心比心,悬想古人临笔之际的真情实感。这就好像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所讲的那个古鼎的故事。鲁迅认为鼎在初造时必定不似后来的土花斑驳,一派“静穆”。那是古人吃饭的家伙啊,应该“热烈”才对。章先生从人性共通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竭力恢复文学史这座古鼎初造之时的耀目光彩,他的讲解自然也就很“热烈”,不然我们童子要在误解中拾得几茎香草,恐怕也难。鲁迅论文也喜欢直见性情之作,更喜欢直见作者的性情。他说诗歌“究理弗存”,杂文不讲“究竟的道理”,只是“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这些章先生都反复援引,或者不惜在注释中大段抄录。
其次是特重文采。章先生欣赏萧统把“赞论序述”列入“文”的范畴,认为昭明太子所谓“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乎沉思,义归于翰藻”,实显示了文学的基本属性。《新著》大书特书《文选》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地位,认为它不仅保存流布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明确了文学的范畴,提供了文学的范本。这对于推动文学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同样重视萧绎的“绮觳纷披”说,认为比《文心雕龙》进了一大步。
现在学术界基本认同一点,即钱玄同虽然在五四时期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但包括钱氏在内的章门弟子大多只反桐城而不反选学。鲁迅并没有正面讨论过《文选》,但他同样重视文采藻饰,自称作文有“做对子”的积习,杂文、小说、散文诗都写得妃红俪白,属对精工。他甚至说,像宋玉这样的人,即使粹然而为清客,堕落为“帮闲”了,仍然是伟大的文学家,因为“毕竟有文采”。“毕竟有文采”,是鲁迅对文学家最高的肯定的一个方面。周作人亦然,他注重因为汉字的特点而形成的文采藻饰这一中国文学固有的“传统”的积极价值,从20年代初一直讲到生命的结束。
鲁迅还主张文学是“余裕的产物”,要让人能休息,能游戏,周作人作文最喜欢“不切题”,极慕平淡而近于自然,乃至被人误解为“闲适”,这些和萧统的“入耳之娱”,“悦目之玩”之说都很接近,《新著》均有意加以勾连,使之贯成一线,后先相映。
总之,抒写情灵,直吐心声,而又错比文华,绮觳纷披,可说是章先生对中国文学从上古到近世两条演进线索的高度提炼,而这都可以看出“二周”的影响。
也许正因为推崇六朝文学,又与鲁迅的反抗的文学和周作人的美文学特多会心,所以章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学时,必然采取一个很严格的文学观念与判断标准,运用起来,有时要近于苛刻的,尤其是将章太炎所肯定的几乎等同于“文辞”的更大的中国文学概念严重压缩了(其实在这方面“周氏兄弟”也并不绝对,周作人自己所写的就并不都是“美文”,鲁迅的杂文更包罗万象)。
比如,章先生贬抑韩愈的“古文”,认为后世所推重的那几篇有名的“韩文”都不算文学作品,“自然也就无法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只有《祭十二郎文》,尚取其情真意切,忘记“道统”,而且具有骈文之长的那一面。同样,尽管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务求浅易而往往诗意尽失甚至沦为顺口溜的“诚斋体”“在近现代曾被视为诗家正宗”,章先生却仍然肯定翁方纲《石洲诗话》斥之为“诗家之魔障”的酷评,并进一步阐明,“也是因为诚斋体的出现,诗作为一种精致的艺术语言形式及充分而艺术化地表达感情的有效手段的常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对南宋及南宋以后的近世诗坛都产生了久远的负面影响”。《新著》对韩愈、杨万里的贬低,与胡适推重杜甫的打油诗而抹杀《秋兴八首》,几乎针锋相对。
其实关于韩愈的评价,章先生也是有前例可援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认为韩愈古文“实在作得不好”,“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来的,当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周作人30年代末的一篇《谈韩文》更从“道”和“文”两方面激烈抨击韩愈,甚至认为其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属于“滥调古文”的“上选”。他还大肆嘲笑后人推重韩愈这个怕死的可怜虫,是非常可怪之事。
周作人的影子,在《新著》对苏轼的评价中也隐然可见。东坡在后世差不多成了人见人爱的宝贝级人物,但水兵出生的周作人却不大瞧得起,理由还是他那个重言志而轻载道的评价标准。《新著》也是这样,虽然首先肯定“苏轼的文学天才不容怀疑”,但认为苏文“普遍缺乏一种比较深切的情感表露。这一矛盾状态的存在,深刻地反映了北宋文学因作家与环境的冲突而造成的现实困境”。这段话有点故弄狡狯,但如果看作者将讨论苏轼的一节置于“北宋诗文的重道抑情倾向”的总目之下,就不难明白其深旨。关于苏轼的诗歌,《新著》也认为虽不乏优秀之作,“然而,由于他那喜欢节制不喜激烈的性格,以及由此导出的善处逆境的人生态度,他总是将感情自然地导入节制的河床,用宏观的眼光去消解悲哀,他的诗也因而较少激情——所以他的词比起诗来更能显出文学上的创造性”。
另外,对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及其《报孙会宗书》,《新著》评价很高,用一页多篇幅加以介绍,并认为杨恽之死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字狱”,尤其推崇他的“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一句。而五四以后,率先肯定杨恽所说的“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并确立《报孙会宗书》极高的文学史地位的,正是周作人。
以上是文学的标准和具体作家的评价受“二周”影响的几个例子。在文学史编撰的体例上也还可以讲一讲章先生和“二周”的关系。
读章先生书,别人惊其发掘多名过去被埋没的小作家(如清初重要作家廖燕),使文学史变得更丰富更沉重,那当然有道理。认得一字等于发现一颗恒星,新得一古人于地下,起死回生之功又岂是识得一字可比。但我是学现当代文学的,倒不觉得怎样稀奇,因为拼命发掘小作家,正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现当代(尤其现代)文学研究无可奈何的常态。使我羡慕而佩服的,倒是章先生及其门人弟子论古代作家,可以不问其人(或其后人)的资历、名望、地位以及与论者的交情,尽量根据其行状的真实来“知人论世”。对比之下,现当代文学史一则无力触及现当代社会政治习俗的实际面貌,二则不敢触及现当代作家的真实行状,单单以美学方法分析作品,代替以历史方法来观照全人,就简直要愧杀了。
80年代以来,“回到文学本身”的口号也影响到文学史写作,加以受到“新批评”的影响,“回到文学本身”被狭隘地理解为“回到作品本身”,文学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则被理解为文学的“外部”,以现代文学史为例,又因为反感于过去“两条路线斗争”、“围剿与反围剿”的庸俗社会学,干脆把文学和社会的互动丢在一边,顶多用“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取代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得胜头回”了,结果,连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还闹不清楚,作家真实行状还一片模糊,就大写“文学本身”(按即“文本”),文学史自然就成了文学作品的封闭阅读与作家风格的悬空鉴赏。
读《新著》时,正好看到金冲及先生2007年给现代史专家杨天石教授的“文存”所写的序言。金先生竟谓中国现代史研究“刚刚起步”。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现代文学史之所以扯不清楚,主要不就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一部现代社会的信史吗?没有现代的信史,现代文学何处安置?没有现代的信史,空中楼阁的现代文学如何可得而思议?比如不了解自“马日事变”至“宁汉合流”的原委,如何解说茅盾《蚀》三部曲特别是《动摇》?不了解丁玲在“左联”时期的矛盾处境、羁押南京的屈辱经历以及到延安初期表面风光和实际被歧视,如何解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后来的创作心理?不了解华北敌后具体抗日情形以及华北民众在此期间的生活状态,如何解说孙犁“抗日小说”的特点?不了解“新生活运动”,又怎么知道沈从文的讽刺到不到位?
现代文学史如此“拨乱反正”,大概是鲁迅当年梦想不到的罢。虽然他好像也很看重“文学本身”,但他所理解的“文学本身”和产生文学的环境息息相关。他讨论文学史,多从大处着眼,力求在与社会文化习俗的关联点切入,把握一时代文学的主导精神,至于作家作品,谈言微中就够了,甚至不著一字,也显得很自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都是著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史是社会文化习俗史的一部分。完全“回到文学本身”,独立出来,就不叫文学史了。鲁迅称这种文学史只是文学史长编,不得谓“史”,因为作者没有“史识”(这大概是鲁迅最受刘师培影响的地方)。
《新著》作者团队都经历过80年代文坛“拨乱反正”的洗礼,“回到文学本身”的冲动肯定也很强烈,大段的作品分析乃至鉴赏也不少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所秉持的将文学史置于社会文化习俗史的基本修史原则,只不过竭力摆脱过去简单机械的社会历史分析而多采信史,进行陈寅恪所谓的“诗史互证”罢了。
比如《新著》虽然在每一编“概论”(全由章先生执笔)中照例先讲政治经济(过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势,落脚点却是文人在这种大势中的实际处境和选择,以及由此养成的精神特点。由此出发,谈文论艺,自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严家炎先生在研讨会上特别提出《新著》论明初文学的“第六编”,盛赞作者对当时政治环境的熟悉,洵为知音之论。这方面精彩之笔应不限于“第六编”。实际上,我这次读《新著》,虽然因为古代文学知识太欠缺,几乎等于“隔教”,至今还没读完,但在古代社会史尤其是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学的结合部上,还是长了不少知识,补了不少课。
当然《新著》并非亦步亦趋,紧随“二周”之后。许多地方“二周”没有论到或论之不精不详,《新著》却有精详之论。但偶尔也有“二周”高论在前,《新著》后出,反而失察的:当然很可能是我的误会。
比如,高启的一首并不起眼的小诗《咏水边桃花》,章先生竟然读出“极其沉重的个体失落感”,把它和鲁迅《孤独者》以及《野草·影的告别》联系起来,但周作人反复提到的李贽《童心说》所谓的“真心”、“真人”、“假人”与鲁迅1908年《破恶声论》所谓“白心”、“伪士”以及与“伪士”(“志士英雄”)相反的“人”(更不用说《狂人日记》“真的人”)的可能的联系,却忽略了。李贽将“童心”和“闻见道理”放在冰火不容的两极,跟鲁迅把“白心”和“稍稍耳新学之语”的“伪士”大肆兜售的各种“学说”、“诚理”对立起来,似乎也值得重视,而《新著》都未语及。
又比如,对明初一些作家忠而被谤或忠而见杀,《新著》判断标准不尽一致。宋濂《秦士录》,章先生认为没有高启《书博鸡者事》好,因《秦士录》宣扬的还是“秦皇汉武心目中的贤臣,集权君主的得力鹰犬”。但论到《明史·王朴传》,对王朴虽被朱元璋“催辱”而终于不屈以死却给予高度评价:“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为忠义而献身、不惜遭受酷刑的志士,但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仅仅为了维护自我尊严而对抗最高统治者并献出生命的战士。”我觉得王朴诚然可悯,但愚忠而至于死谏,“自我意识”和“自我尊严”何在?处无道之世,倘不能揭竿而起,则与其矫矫而折,倒不如效东方朔之佯狂,将人主“练成傻子”,或如鲁迅“眼珠子也不转过去”。否则鲠直也罢,谄媚也罢,都免不了“隔膜”。当然鲁迅的“隔膜”说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侯至少鲁迅自己的“人身”起码已经有些自由了,要求古人达此境界,并不公平,但现在毕竟有了鲁迅所发明的“隔膜”说,那么对宋濂、王朴这样的人物,评价起来,或者还是多留一点心眼才好。
与“二周”的关系只是《新著》的一个侧面,我偶举几点,逞臆而谈,实在不恭得很。但小子妄言,聊博先生一笑可矣。■
2007年12月1日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