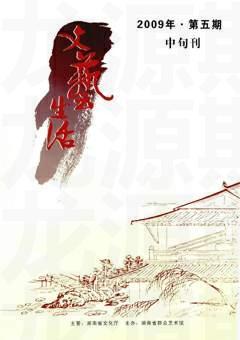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邓 韵
摘要:《文心雕龙•神思》主要集中论述了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的艺术思维(或形象思维)活动,其中“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是最重要也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集中论述了文学创作思维活动的特点,特别是对作为文学构思重要因素的“灵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分析。
关键词:神思 思理为妙 神与物游 灵感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4-
“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①在这里,“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被刘勰看作是审美创作构思活动的极致。
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这种“神妙的构思”,既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又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实现了一种审美的自由。通过“思理”这样一种超越创作者所在的经验环境的能力,使其由当下生活的经验世界,进入到先验世界和超验世界之中,思维自由地驰骋,实现“神与物游”的最高境界。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刘勰所指的并非一般性的构思,而是“思理为妙”(即神奇微妙、超然矿逸、自由奔放的艺术思维),当这种构思臻入妙境之时,才会带来“神与物游”。不仅如此,这种精妙的构思,还使得创作者在其审美构思活动中的心理机制也产生转变——“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②——“满”和“溢”表明,神思所带来的并不是简单的物我交融,而是一种“与”物的状态(既不迷失自己于物,也不将其视为外于己的单纯客体,而是主动地参与到物之中)。在这种“与”物的心理机制驱使下,“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激越的情感以不可遏止之势呈现,思如泉涌、意象纷呈,创作活动水到渠成。由此可见,虽然刘勰在《神思》甚至《文心雕龙》全书中并未直接提出“灵感”的概念,但他笔下所描绘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思维现象),所表征的正是“灵感”理论的重要特点。
“灵感”一说最早来源于柏拉图,他认为诗人之所以作诗是因为诗人被神灵附体,陷入一种迷狂状态,是一种“灵魂回忆”现象(所回忆的是理念世界)。简单来说,灵感指的是人们在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因偶然机遇而疑窦顿开,思维贯通,创造获得意外成功的一种心理现象,它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创造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构成部分。③灵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灵感到来的时间和方式是作者无法预期和把握的;其次,灵感到来的情形的主要标志是此前作者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的语言和意象,此时如滔滔之水喷涌而出;再次,灵感停留的时间往往非常短暂,稍纵即逝(苏轼由是说,捕捉灵感犹如捕风系影);另外,灵感的离开在时间和方式上仍然是作者无法把握的;最后,灵感虽然具有上述特点,但它的到来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者在此前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艰苦的艺术历史思索过程,并且对生活有丰富的积累。
回到《神思》篇,我们注意到刘勰在谈论这种特殊的思维现象到来时说,“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④当这种神妙的构思一开始运行,万种念头便竞相萌发,作品内容尚在虚空之时就已经进行了构想、搭造,艺术形象还没有形成就已经加以了雕镂、刻画。“神思方运”的“方”,说明了这种神妙的构思其到来时间的突然性和无法预期性,并且在到来方式上(作者对作品的创作活动)也是无法把握的。不仅如此,“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心神活动的关键一旦通达,那么所刻画描绘的外物其形貌就没有隐藏的;如果关键滞塞,那么这种神妙的构思很快便消失了。“神有遁心”说明了“神”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在离开时间和方式上仍然具有不可把握性。由此可见,“神思”的出现与离开是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可预期、难于把握。当“神思”到来之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眼中所见之景、心中所虑之情此刻跃然纸上,“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思维活动突破时空的局限,语言和意象以不可遏制之势喷薄而出,从而在这种神妙的构思活动之下,实现“神与物游”的最高境界:“神游”和“与物游”。“游”被道家看作是最高的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在庄子的思想中,“游”是真正的、绝对的、无所待的自由,是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最高人生境界,它没有任何外在目的,而在这随心所欲、自由奔放的游历中,却能够明了宇宙的真相,洞悉生命的真谛。刘勰所讲的“神与物游”也不例外,也是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引申出来的。“神与物游”的“神”,一方面源自中国古代哲人对宇宙本源的探讨、对世界发展变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古代“形神”论的影响。在他看来,“气”作为宇宙间万物生长的造化伟力,决定着万物的发展变化,而“神”与“妙”则是个体生命对这种作为的体现,同时,根据“形神”论的观点,“神”又被看作是人所具有的精神、灵魂,它具有极大的能动作用,是人认识世界、体认万物的根本动因。故此,“神与物游”就是人与自然的高度感应以及在这种高度感应状态下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自由,并且只有实现了这种自由,人才能够进行审美创造。而作为带来“神与物游”的臻美境界的“神思”,就是审美创作活动中,那种自由自在、超然洒脱、神奇飘逸、变幻莫测而又高标脱俗的精神构思活动。⑤作为宇宙的灵迹、天地的心源,“神思”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它的运作、它的到来必然具有作者作为有限个体所无法预期与把握的特点,同时也必然带来作者对宇宙、人生真谛的完满体悟。
既然“神思”已经带来作者对宇宙、人生的完满体悟,并且我们知道“神思”到来之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那么作者的创作活动就此便能够水到渠成了吗?非也!“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这说明,“神思”的运作是有一定的前提和基础的——“志气”、“辞令”(“志气”指的是情志意气,“辞令”指的是语言)。因此,“神思”的到来需要心理的准备和语言的储备。
刘勰认为最高的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是“与”物的状态,因此制约“神思”(也即是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关键在于人的情志意气,这就需要作者在进行创作活动之前进行必要的心理准备,也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进入的状态”、“前创作状态”。于是刘勰指出,创作需要构筑“虚静”的审美心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⑥意思就是说,酝酿文思的关键在于虚静澄澈的心境,(这需要通过)疏通心灵、排除杂念,洗净混浊的精神(来达到)。刘勰将“虚静”引入创作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中,以说明一种虚空宁静、无私无欲、精神集中、心灵纯净的创作心境。即为一种心灵搬运的过程,将此刻内心所藏的一些无关事物的念头“搬出去”,从而让内心达到“净”,达到“虚静”(“空”和“静”的目的是人为地集中人的审美注意力)。只有当我们的内心澄澈无欲之时,才能真正实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正是如此。故此刘勰认为,只有当作者的心灵保持在空灵澄澈的状态之下,思维才能迸发出充沛的活力——既摆脱主观的局限,全身心地投入到宇宙万物的深层结构中去感受、体悟;又能超然其上,不受外物的拘囿与捆绑,冷静而明敏地把握住生命真谛的幽远与深邃,也才能够真正实现“与”物,而这也正是“神思”运作所带来的效果。
文学创作除了构筑“虚静”的审美心境而外,还需要积极的语言储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⑦意思就是说,积累学识以储备(酝酿文思所需的)珍宝,斟酌事理来丰富才学,通过深研、历练来作出透彻的观察,顺着思路来寻绎、整理文辞……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意气远胜于(想写)文辞的一倍,而当我完成整篇创作的时候,发现只得到心中所酝酿的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意念凭空翻腾容易变得奇特,而语言实实在在难以穷尽其巧妙。故此,构思化为意绪,意绪化为语言,言与意贴切时有天衣无缝的效果,而疏远时则相距千里(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这段话指出了作为人类思维和表达的工具,语言(也就是“辞令”)在制约文思的利钝通塞的同时,也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果效(对“意”的传达)。关于这一点,早在陆机《文赋》中就已经得到了说明:“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在此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三项结构,即“意——物——文”。“意”指内心的一种个体化行为,即某人对世界“形成一种看法”⑧;“物”指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文”指文学作品(语言)。这三者之间“意”试图圆满地趋近“物”,但时有不称;“文”试图圆满趋近“意”,但时有不逮。这是由于作为“物”和“文”中介的“意”是主体结构的个人行为,又是以事物的内在结构为依据来判定的,因而必定出现称与不称、逮与不逮的问题。
《神思》篇中所指出的“思——言——意”(“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的关系与陆机的用意相似。思,指神思,即精神活动;意,指意象,即文思;言,指语言,即文辞。二者求得一致的关键就在于“博而能一”,这就需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需要作者在进行创作活动以先进行积极的语言储备,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艰苦的艺术历史思索过程,并且对生活有丰富的积累。
《神思》作为《文心雕龙》理论篇章之首,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意义。刘勰在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神思”,即是指心神的思维活动,具体到文学创作之中,则涵盖了作者全部的艺术思维活动(或形象思维活动),贯穿构思、写作、修改的全过程。它的运作需要主动构筑“虚静”的审美心境,积极的进行语言储备。它的到来和离开具有作者无法把握和预期的时间与方式。它的出现带来语言和意象的至精至妙,带来作者强烈的感情活动和充沛的创作力量,带来“神与物游”的臻美境界。而这正是刘勰对“灵感”理论的独到理解和精准诠释。
注释:
①②④⑥⑦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③张小元等.文艺学概论.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⑤李天道.文心雕龙审美心理学.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4—267页.
⑧【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参考文献:
[1]凃光社.文心十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周振甫.周振甫讲《文心雕龙》.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健.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