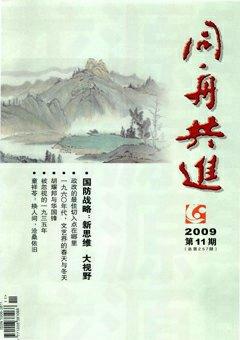1960年代,文艺界的春天与冬天
涂光群



【周恩来、陈毅连续讲话,文艺界迎来“乍暖”之春】
经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初的反国际修正主义,自1960年下半年起始,中国走向了全面调整时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7月22日至8月13日,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全体代表。
9月29日,周扬在艺术工作座谈会上传达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11月,周扬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希望历史学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并请吴晗负责编“中国历史剧拟目”。
1961年1月9日,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文艺报》率先发表“题材问题”的专论(主编张光年执笔),提倡广开文路和言路,“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解放文艺界的创作生产力。
6月1日至28日,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的初稿)。周扬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报告,他说:过去有人把政治理解得很狭隘,这是不对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不仅应该有表现社会时代的作品,并且还要整理过去的文艺遗产;在有的时候,有的场合,后者起的作用还更大。周扬还说:政治挂帅,政治就不能太多。太多,就削弱了政治,政治不是帅而是兵了。政治是灵魂,灵魂要附在肉体上。业务、艺术就是肉体。没有肉体,灵魂就无所依附了,不知它到底在哪里。周扬最后强调: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可爱的队伍,同党是一条心的。
在这“春乍暖”的时刻,也曾出现康生等人的杂音。康生斥责著名戏曲演员探索现代戏,大声发吼:“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这是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篇陈白尘回来后,说给我们听的。
但从1961年初至1962年9月之前,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实事求是总方针,还是卓有成效的。在文艺界来说就是切实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一个宽松、包容、活跃的环境。《人民文学》的张天翼主编、陈白尘副主编就是支持我们编辑这样做的。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指出:“自解放以来……文艺运动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文艺运动有很大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接下来,文艺界又举行了两大盛会。
3月,文化部、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同时在这里召开。周总理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首先说,过去两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也有些不愉快,但在戏剧写作方面,仍取得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接着他谈了6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界的定义与地位。他十分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劳动者之间的联盟。这就从根本上摘掉了长期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
陈毅同志也作了精彩报告。他对建国13年特别是3年困难时期知识分子、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今天我要向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对挤满大厅的听众——科学家、剧作家、知识分子们,行脱帽礼,并当场给剧作家海默遭批判的话剧《洞箫横吹》平反。
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主持人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邵荃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讲话。与会作家畅所欲言,谈当前农村的形势、困难,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前几年“左”的指导思想对创作的干扰。邵荃麟热望文学创作恢复实事求是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他还主张人物形象的创造应当多样化,英雄人物固然要写,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甚至“小人物”也可以写。茅盾、周扬的讲话也都反对创作中的虚夸,赞成作家写自己所信、所见、所感的东西,人物形象的创造应当多样化。
【一个多月后,形势急转直下】
1962年9月(距中国作协在大连开的会议不过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3年调整阶段迅即结束。
就像1955年的“肃反”文艺界首当其冲一样(以胡风开头),这回,文艺界也不甘落后。而《人民文学》杂志这一小小角落,也立刻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波。我从大连回京不久,大约8月下旬,《人民文学》执行主编李季告诉我,说周扬告知他,李建彤(周扬在延安“鲁艺”时期的学生、刘志丹胞弟刘景范之妻)写了陕北革命英雄刘志丹的长篇小说,建议《人民文学》派人去联系,挑选一些篇章发表。于是我去北京西城一条胡同找到素不相识的女作家李建彤。承她允诺,交给我一份打印稿。责编和我快速读毕,选出一章,经执行主编拍板,决定发在刊物第10期头条。可是还未等看校样,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传达下来,李季十万火急,要编辑部抽下《刘志丹》那篇稿子。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揭出了一个“习、贾、高反党集团”,为首的是习仲勋副总理。毛主席有严厉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曾听一位延安老同志说,“习仲勋是西北、陕北地方党造就的优秀干部,1953年曾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很正派,温和,实事求是,待人平等,没有架子”。这回是不是株连,我们不晓得。老同志嘱咐我:不要对任何人说。
好险!《人民文学》险些陷入“反党活动”的陷阱,并且差点牵连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虽然刊物及时撤了稿,有惊无险,但人们已似惊弓之鸟,再也没有上半年那样的宽松心境了。编辑部仍要我传达大连会议精神,我传达完后补了一句:这个会是低调儿的,看来有点过时了。
【毛泽东第一个批示:许多部门至今是“死人”统治】
1963年5月6日,江青组织文章《“有鬼无害”论》,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批判剧作家孟超创作的昆曲《李慧娘》。孟超写《李慧娘》,写前曾得到康生支持。演出后,康生又大加赞扬,并特地宴请作者及主要演员,表示祝贺。江青批判此戏,全国戏剧界马上转变风向,开始大批鬼戏。1964年夏,京剧现代戏会演闭幕会上,康生摇身一变,把《李慧娘》作为“坏戏”典型,号召大家批判。“文革”中,孟超被迫害致死。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这个批示下发后没多久,春节要来了。我收到一份请柬,可以带夫人出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迎春晚会。迎春晚会给人观感不同的是男男女女着装都比较整齐、讲究,女士们有穿裙装、略施粉黛的。一进大门,有年轻女子给每个来宾佩戴一朵绢花。主持人致欢迎辞时前边冠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使人感觉既有节日的融和、喜庆气氛,又似乎恢复了一点旧时的礼仪。但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是晚会策划人为使气氛轻松、活泼、新鲜而采取的一种做法,说不上有什么大不妥。至于内容,大部分节目还是健康的。我至今记得那时新上演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话剧,如《祝你健康》(又名《千万不要忘记》)、《远方青年》等,在晚会厅堂里都布置了精心设计的宣传广告。书画厅里,艺术家们在那儿挥毫写字、作画。舞厅里还有舞会,人们一边随着乐曲跳舞,一边观赏那些即兴表演。参加晚会的,对我来说,熟悉的面孔居多,除了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多半是文联大楼(作协、剧协、音协、舞协等)经常碰面的人或艺术团体的演员,当然以青年人为多。即兴表演更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有时就是随意制造一点笑料自娱、娱人,例如《世界文学》杂志我熟悉的一位男编辑(后来成为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那时还是个青年人,善于模仿《天鹅湖》舞剧白天鹅的舞蹈动作,有朋友欢迎他上台表演,他便略事化妆,作白天鹅状,穿起裙子在那儿蹦跳了几下,引来一片笑声。照我看来这仅是逗乐而已,说不上是对舞剧《天鹅湖》的亵渎,更称不上什么“下流”、“荒唐”,谁会将它当作一回事儿呢?
不料有好事者向上写信。两个人给中宣部写了信,一个给报纸投了稿。其中一个写信人是部队知名诗人。作为编辑,我和他有过浅浅的接触,此人决非古板之人,相反,具备一般文人的自由心性和相当的浪漫气质,也很有才华。但我也知道,那一两年他正处于“倒霉”时刻。他参与“告状信”,颇让人惊讶。这些“告状信”以革命大批判的眼光反映了迎春晚会的情况。但告状者本人恐怕也难以料到,一根小小导火索即将引来漫天大火,而且火势将延烧到几乎每个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包括告状者自己头上。
春节刚过,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胡海珠家串门,听说了毛主席在春节谈话中曾对文艺工作者严厉批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作协闻风而动。第一把手、党组书记邵荃麟亲自张罗,春节后立即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团赴大庆油田参观、访问,并请同去的艺术家登台演出,慰问石油工人。代表团团长是张光年,著名作家有艾芜、徐迟、赵树理、周立波、李季等;著名艺术家有中国音协主席吕骥,电影演员王晓棠夫妇,话剧导演孙维世,歌唱家胡松华、蒋桂英,评弹家赵开声、唐耿良等。作协各部门都去了人。《人民文学》杂志去了胡海珠和我。
没多久,我又被组织派去华北油田,到工人中间改造、学习、锻炼。1964年8月30日,华北油田的杨拯民局长(他是杨虎城的儿子,抗战初期去延安参加革命)接见我们。他说:毛主席对文艺界下了第二个批示,作协要你们赶快回去,现在阶级斗争很厉害,文艺界要整风,要你们参加整风,吃了早饭你们赶紧出发。
【毛泽东第二个批示:大多数……跌到修正主义边缘】
原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已对文艺工作作了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是写在中宣部上送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在中国作协的一份整风报告(类似检讨)上,毛泽东还批示:“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这个批示对整个文艺界无异于晴天霹雳。尤其后面几句话,“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主席还首次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已将它定性为以议政为主的反革命的俱乐部)来类比中国的文艺团体。那么,主席批示的根据从哪儿来的呢?大家很自然联想到半年前上送的迎春晚会情况,一定引起他老人家极大的不快。批示的分量极重,不仅是“最近几年”,而且是15年来(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并且新近写的检查,又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这个批示传达下来,作协(尤其领导层)一时都呆了懵了。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脱口而出:“这些话要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冯牧的话,不过是率直地反映了对批示的分量难以承受和极度的惊诧。这其实是很多人的想法。但这句话在“文革”中,也成了冯牧“恶攻”的“罪证”之一。
惊诧归惊诧,执行主席的批示则不能含糊,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联、作协,这时动“真格儿”了。在全国文学界,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紧跟形势,推出了中国作协原一把手、党组书记邵荃麟。邵成了斗争对象。
我想,周扬他们四位,与资历更老、值得尊重的邵荃麟并没有什么私怨。邵在大连会议的讲话也是听中央的,没什么错谬。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根据他们的经验,必须紧跟上头。上头说你们快要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就必须找出这样的“反面人物”来。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谁敢怠慢?
【周扬敲打“三条汉子”】
其实,除了两个著名批示,毛泽东在1964年前后曾一再严厉批评文化部。
1963年11月,他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4年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时说:“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呢?”因此文化部也是检查整顿的重点。首当其冲的是主持文化部常务、在戏曲改革工作上出过大力的副部长齐燕铭和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齐燕铭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夏衍、陈荒煤在电影工作上经常聆听周总理的指示。这三个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他们领导的文化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把持政权”,这就有点蹊跷了。
1964年6月至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江青插手这次会演,枪毙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在京剧会演座谈会上,她攻击戏曲舞台是“牛鬼蛇神”,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康生与江青一唱一和,把影片《早春二月》、京剧《谢瑶环》等统统打成“大毒草”。周扬再次紧跟“形势”,敲打“三条汉子”田汉、阳翰笙、夏衍及齐燕铭、陈荒煤等人。
1965年早春的一个晚上,文化部系统和文联各协会的党员被召集到中宣部教育楼,听周扬作整风总结报告。周扬的报告从天黑开始一直讲到将近午夜,听报告的人差点就赶不上电车回家了。周扬在会上点名批评“三条汉子”田汉、阳翰笙、夏衍。他这样概括,“田汉同志,你写《谢瑶环》,你‘为民请命,你把我们党跟人民对立了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是反动的啊!”“翰笙同志,你在《北国江南》里,写了个瞎眼的共产党员;你宣传虚伪的人道主义……”“夏衍同志,你要‘离经叛道……离革命之经,叛战争之道”
文化部夏、陈、齐三位卓有成效的副部长遭批判后,先被停职,后来离开了他们熟悉并长期做着的领导艺术的工作。夏衍被调到亚非研究所。齐燕铭赶赴山东济南。陈荒煤发配至重庆,在图书馆当一名普通馆员。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真是10年浩劫在文化人身上演出的一个悲怆序幕。
关于文化部,我还想起一件往事。因1963~1964年一再被点名,文化部里,就连挂名部长,毛主席、周总理的老朋友,著名左翼作家茅盾,也被整风检查组的领导人“顺理成章”地送了一顶“资产阶级”帽子。在作协整风中,一位领导人讲话说:资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他举的例子是说,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写了些新作,茅盾写文章赞扬了。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谈美感的文章,茅盾也写信赞扬。1965年5月,文化部领导改组,部长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取代沈雁冰(茅盾)。部领导成员大换班,新任副部长有萧望东、石西民、林默涵、刘白羽等人,还调来其他两位将军和一位省委书记。
【江青的《纪要》刮起“十二级台风”】
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林默涵,还有取代邵荃麟担任中国作协一把手兼文化部整风检查人之一的刘白羽,仍是那样攒劲。
1966年4月7日上午,刘白羽邀林默涵在华侨大厦会议室给作协专业创作会议的代表们讲话。这个时候,他也许已知道一点江青、康生的动向。
江青已走到前台。她和康生指责著名作家周立波新近写的毛主席回故乡的一篇优美散文《韶山的节日》,文中提及杨开慧烈士。江青显然对此嫉恨,《韶山的节日》被批评为“大毒草”。周立波的小说也被连累了。江青在《纪要》中大放厥词,说周立波在长篇小说中写了一个英雄,却让他死去了,这很坏。周立波由此被押解到湖南到处游斗,遭公安部门收审长达七八年。
于是,作协的专业创作会议上,选了周立波、乡土作家赵树理(他是个很朴实的作家,参加了大连会议。后来回到山西故乡,却被造反派批斗折磨,含冤死去)、邵荃麟作为批斗对象,罪行也升级了。林默涵讲话中说:“从丑化歪曲现实生活入手,攻击社会主义。因此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怀疑,认为大多数人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照这样,不是帝王将相,就是中间人物,动摇分子,加上风花雪月,轻歌曼舞,怎么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呢?”
更使在座者吃惊的是,作为中宣部负责人之一、文艺领导人的林默涵,不只批判“三条汉子”,而且进一步批判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也包括建国10多年来党直接领导下的文艺。在整个文化、文艺部门,难道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其实,1966年4月江青等人搞的《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传达前,作协负责人刘白羽在党内先看到。他曾对身边人说:“中央有个文件要下来,下来了将刮起12级台风!”
当《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传达后,人们才知道林默涵的讲话是提前讲了《纪要》里的内容。后来,江青称林默涵“剽窃”《纪要》——林默涵就这样倒了霉,“顺理成章”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发配江西。
1966年5月16日,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文革”正式开始了。也是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首次在北京公开露脸。新华社通知各报刊负责人开会,礼堂里黑压压坐满了人,只听会议主持人说:请张春桥同志传达中央通知。
张春桥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接着他阴森森地宣布:一、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所有的报刊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多了个字,错了个标点,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时,把内容做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二、《人民日报》 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永远不要忘掉阶级斗争 》,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 ,做自我批评……
《评“三家村”》当时是通过轰击邓拓、吴晗、廖沫沙而轰击中央大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以及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自此,“文革”炮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此后,最高领导人指向哪个,不论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不管是潜在的或未来的政敌,都可以由江青或臭名远扬的顾问康生指挥张、姚将他们轰倒。
张春桥1958年在上海市是分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我作为刊物的编辑到上海组稿自然要去看望他并约稿。他约我到办公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回见张春桥。他那时可没像现在这样板着一张阴森森的铁脸,而是热情过人,满面生春,侃侃而谈,表示了他对上海市文学创作力量的全力支持。他说,“例如老作家巴金要创作《家》、《春》、《秋》的续篇《群》,我们上海市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包括关在监牢里的人,他只要提出来,也可以让他去见、去访问……”张春桥1958年6月还给《人民文学》写了篇《“决心大变”颂》的短文。而如今,他真的“决心大变”:抛出“大写13年”以对抗全面贯彻双百方针,把在读者中极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巴金打成“反共老手”……
“文革”初期,令许多人最为忧心的事情之一,便是张、姚二人被推上了中国显赫的政治舞台。
而此时的文艺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紧跟形势者也难以逃脱噩运。周扬被江青、姚文元等诬为“叛徒特务”,长期关在牢里。直至最高领导人晚年忽然想起,周扬在哪里?才将他放出来。邵荃麟、刘白羽被关在秦城监狱。邵1971年含冤病死。刘白羽被放出来后,他说简直不会说话了。《黄河大合唱》词作者、诗人、评论家张光年被中央专案组长期审查,直到1976年才“解放”。当年陈毅副总理当面行脱帽礼的剧作家海默,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余话】
近读《同舟共进》杂志,有文章提到,还有人想给“四人帮”平反——真是匪夷所思。
想起那段日子,“四人帮”当道,打着“革命”的招牌,人民连话都不敢随便说。但我一直坚信,他们长不了。社会上不仅有黑暗,也有光明在闪烁。1969年,文艺界人士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军宣队一再讲,我们是“砸烂的单位”,是“黑线中毒很深的人”,要长期改造,不要想再回北京。我本来是湖北人,扶老携幼,全家六口都来到向阳湖,租下老乡房子,长期在这里耕田、读书,不回北京也可以。作协和文化部的文艺人才,一下子全部赶到荒湖来种田,却未必全都能适应。周总理自己此时处在很困难的环境,却还对管理我们的人打招呼:文化部和文联系统已去外省,来到乡下的人,户口还是留在北京,不要转出去。总理的决策,温暖了我们“五七干校”的每个人。说到这里,今天仍禁不住落泪——这不是光明在黑暗里发亮吗?
(作者系文史学者,长期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曾任《传记文学》杂志主编)
——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赴遵义春节慰问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