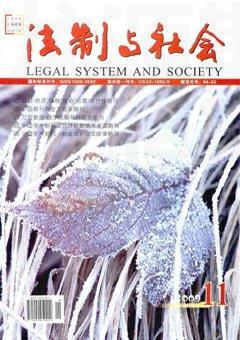“场域——惯习”理论下“感情常在”与“人走茶凉”的比较
岳 敏 许 新
摘要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是当代较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之一,用它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我国社会的非正式群体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重要现象是“感情常在”;日本社会“一族郎党”集团也构成了整个日本社会,其中的重要现象则是“人走茶凉”。本文指出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对我国的“感情常在”与日本的“人走茶凉”进行试比较,从崭新的视角探讨中日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差异。
关键词场域—惯习 非正式群体 一族郎党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235-02
一、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综述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当代影响较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打破了人们观察社会时单一的结构主义或个人主义,提出了一种辨证的关系性思维方法——“场域—惯习”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根据“场域”研究社会实践中深层的社会结构,同时以“惯习”对行动者的个体行为进行研究,以一个崭新的视角开始了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解读。
布迪厄认为,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①
具体来看,首先,他认为现代社会世界的高度分化会产生一个个不同的空间,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都是一个场域。场域不是空空如也的地理场所,而是社会场所,每个场域中都存在自己独特的规则;其次,布迪厄认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②;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其间充满了冲突与竞争,不断的冲突与竞争又进一步形成新的场域③;第四,在新的形态中,场域能够自我更新或重构其特殊的逻辑规则。新领域产生后,场域会在其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与形式。
布迪厄认为,所谓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
惯习主要强调行动者的自身方面,是指行动者通过自身对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而形成的长期的、可预见的、可转换的、构筑在实践层面上的性情倾向系统。这种性情倾向系统是开放的,可直接接触外界不同的社会环境;也是可变与可塑的,会随个人所处环境与实践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并将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自身的影响不断地内置于身体中,进而塑造出新的惯习。
布迪厄把惯习看做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化,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惯习的运作取决于行动者。身处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个体知道场域内的游戏规则,将其内化进自己的身体与意识中,并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不仅知道如何遵循规则,还会对规则进行艺术地变通,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当行动者从一个场域进入到另一个场域,他还会对惯习进行转化,运作最合适的惯习。④
场域和惯习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特定的场域产生特定的惯习,特定的惯习创造特定的场域;没有场域,惯习就没有存在的依据,没有惯习,场域就失去了意义。场域能够得以形成并且产生效应,离不开惯习的运作。⑤但惯习具有惯性和滞后性,所以惯习和场域之间时常并不吻合。当一个场域在争夺后变为新的场域,惯习会变得不适应,但不会立刻就得到调整与重构,需要行动者将新场域规则慢慢内化后,逐渐被重构出来。
二、“场域——惯习”中的“感情常在”与“人走茶凉”
(一)非正式群体中的“感情常在”
在中国,非正式群体的形成往往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生活阅历,相互间有共同的话题,以感情为群体的主要维系动力,群体没有对成员资历或群体活动的场所的要求。非正式群体主要是正式群体之外的群体,群体内部的规范、准则不会干预成员的正常生活,有的非正式群体甚至毫无规则,成员也将他们所从属的非正式群体看做是生活的占据非主导地位的一部分,不会将其与自己的行为密切的联系起来。非正式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与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因人而异,群体对此也没有硬性控制与规定。对于所属的不同的非正式群体,成员往往会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
当群体内某位成员与其他成员不能直接接触转而用书信、电话或其他方式接触交流时,双方并不会因距离而产生隔阂,感情依旧被维系着。即使很长时间不联系,再次见面时仍会感到热情与激动,在中国人看来,两个人一旦结下了友情,不管在时间、空间上相隔多远,双方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变的。当群体内某位成员因个人某种不得不的原因离开群体,只要不违背其他成员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都会受到其他成员热烈的欢迎。非正式群体的成员可多可少,新成员不会受到排斥与冷漠对待。以上现象,可将其成为“感情常在”。
(二)“场域——惯习”下的“感情常在”
对于“感情常在”的中国非正式群体,可将其称作“非正式”场域。“非正式”场域是客观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系统与结构中除了各种正式的群体与组织,还需要一些填充社会成员生活空余、维系成员感情的组织,非正式群体就应运而生。在此场域中,行动者聚集的原因不正规也不重要,所以场域的规则对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大都没有身份的要求。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场域的行动者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所谓的“缘分”,行动者之间的感情需认真珍惜与维护,共同维护所在场域的利益,此为场域的规则。此场域内行动者彼此间没有必须的权力或义务,整个场域的氛围处于轻松的状态。进入此场域的行动者们相信场域会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他们会很自觉地遵守规则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惯习。
场域内居于主导的客观关系是在“仁爱天下”、“以诚待人”等中国儒家思想基础上的行动者之间平等、互爱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决定了场域自身的运作逻辑也是以仁爱、平等为主题的:行动者进入场域后,会被其他行动者有礼貌地欢迎与照顾,共同维系场域的运作。在以上基础上生成与建构出来的惯习,是对环境的适应,更是中国历史在行动者身体中的深深积累。行动者在此惯习上进行策略性行为,与其他行动者和平共处等,当某位行动者在时间或空间上与其他行动者不能正常联系,等到恢复联系后,其他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仍然是表现得很热情,也就是“感情常在”。这些策略性行为是行动者对外在的场域规则的内在化。场域内也会有冲突与斗争,当场域内某种力量压过原来的力量,就会出现场域的改变。
(三)“一族郎党”中的“人走茶凉”
在重视“场所”的日本社会,往往会以不同的场所为基础形成不同的“一族郎党”式集团,即把有血缘或亲属关系的“一族”和家臣、部下等的“郎党”合为一体,构成一个社会集团。⑥这种集团与集团之间接触很少,甚至是冷漠和敌意的,但集团内部成员联系密切,有时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都很难区分,集团的影响力也会渗透到内部成员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在他们眼中,自己所在的集团就是整个世界。为了增强集团意识,需要成员间经常直接接触以进行情感交流。集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接触时间的长短与频率。
而这种直接接触的作用与影响,除了与接触时间长短与接触频率有关,还与接触连续性有很大关系。与中国社会不同,在日本社会的集团中,不管是普通朋友,还是亲人之间,如果长期没有联系,就会相互疏远起来。地理上的距离感则会直接给人们带来隔阂,如果一个人要调离他工作的地方,那么他不仅是离开了原工作地点,更是离开了他所有的集团内部的社会关系,即“人走茶凉”。⑦即使他们会给原来同群体的成员写信,也会收到很少的回信,因为原集团内部的成员会想着“人一走茶就凉”,没有必要再回信。
(四)“场域——惯习”中的“人走茶凉”
“人走茶凉”的一族郎党式集团可以称作“一族郎党”场域。日本社会中,几乎每个个体行动者都有自己所属的场域,没有所属场域的行动者不仅没有社会归属感,还会感到很难生存。在所属场域中,行动者的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很难区分,并不像中国的“非正式”场域只涉及私人生活的某一方面。所以,日本的社会结构不像中国有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之分,其整个社会系统就是由一个个公私难分的高度凝聚力的“人走茶凉”场域构成。行动者所在场域的强大与实力直接与场域本身及其内部行动者的生活、利益息息相关。
由于“一族郎党”场域直接导入正式社会,所以场域对其行动者特别重视资历:在日本人的惯习中,新进入场域的行动者位置是最低的,资历较深的个体都可以对其进行轻视,这种轻视跟行动者能力无关。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主要依靠周围的行动者,很注重“场所”,场域的形成也以“场所”为基础,如果某个行动者离开了所在场域,不论什么原因,他就不再跟这一场域有关联了,其他行动者会把他直接他排除在外。这种惯习也是历史在身体中的积累,从德川幕府就存在的“纵”、“横”交织体制就直接体现了等级与场域的严格划分。在以上这些内化的较为稳定的惯习指导下,行动者也会将场域规则转化为策略性行为,当某个体与其他个体直接接触频率减少,其他个体都会对其示以冷淡,逐渐将其排除在共同的场域外。“一族郎党”场域内也会存在力量的冲突与竞争,但与中国“感情常在”场域不同,日本的“一族郎党”场域内一旦发生较大的冲突与竞争,往往会对场域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带来社会变动。
三、结语
在中国,非正式场域与正式场域共同构成整个社会,这两个场域完全不同,内部有不同的规范准则,非正式场域主要是工作外的私人生活场域。日本社会则主要由“一族郎党”式的社会集团构成,这样的集团包括成员的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两方面,内在的规则也往往将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融合在内。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非正式场域与“一族郎党”场域内部占主导的客观关系不同,前者是成员间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后者是成员对集团的依附及集团对成员的保护关系。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场域规则及主导关系下,场域内行动者主观建构的惯习也截然相反:非正式场域中的行动者坚持“感情常在”;而日本“一族郎党”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则是“人走茶凉”。非正式群体与“一族郎党”集团是社会组织中两种不同的场域,其形成是由中日社会深层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中国社会,工作群体与生活群体往往有明显地区分,构成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而在日本社会,工作群体往往就是生活群体,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互相渗透,联系紧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的,各有所长,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成员不会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私人生活较为轻松;日本的社会结构则使得整个社会与国家凝聚力较强。
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的全球化发展,中日的社会结构、内在场域及社会成员的惯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中国人的利益观念越来越强,非正式群体已经不单单是成员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中放松自己的场所,里面逐渐掺杂进一些相互利用的成分;日本人在商业意识的强化下,也开始重视契约,个人能力也慢慢有了影响力,“一族”与“郎党”的地位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应根据两者的发展变化客观地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比较。
注释:
①②③布迪厄.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第155页,第139页.
④刘中一,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社会.2005(6).
⑤程春华,钟庆伦.场域、惯习、资本与贬己尊人准则.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8).
⑥⑦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