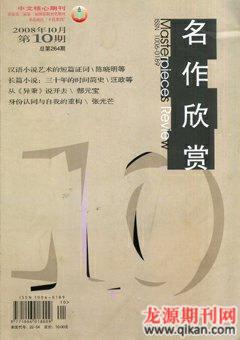始知天籁本天然
张 磊
【推荐理由】
迟子建是目前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她最擅长的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逝川》是她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特色:将审美观照的目光流连于朴素本真的民间生活,从自然状态下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追寻现代社会渐渐失落的美好的人性,用无限的爱心、善良和情意构筑起自己天籁般的诗意世界,温情浪漫,诗意动人。小说中的主人公吉喜美丽善良,虽然孤苦一生,却从不放弃对善良的追求,与前些年文坛上盛行的“审丑”、“溢恶”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唤起了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传统的记忆。小说语言雅致细腻,细节婉约饱满,展示了作家的创作才情。
凡俗生活,波澜不惊,平淡如水。如何发现平凡中的感动,写出诗情沛然的作品,进而表现出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本不缺乏这样的作家,废名(《竹林的故事》)、沈从文(《边城》)、萧红(《呼兰河传》)就践行着诗意乡土的审美取向。然而,时光进入当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消费主义的影响,商业文化陡然勃兴,文学的浮躁之气甚嚣尘上,很多作家追逐写喧哗的人生,根本无暇静坐下来品味丰富的生活,关注精神世界的超越,也没有时间对作品精雕细刻。泛滥成灾的文本充斥的只是凡庸的日常生活和故弄玄虚的个体经验,肉欲取代了爱情,刺激消解了恬淡,韵味没有了,诗意也没有了。文学是否能回到文学本身,不再满足于用喧嚣的现实生活取悦市场,而是以相对从容沉稳的心态去发现潜隐在生活背后的丰富与深邃,用语言来提升精神,已经成为当下衡量一个作家文学品格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忧伤而不绝望”(谢有顺语)的写作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作为一个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平民作家,迟子建喜欢朴素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真正的诗意是浸润在朴素的生活中的,所以我信奉用朴素的文字来表达传神的生活这一原则”(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载《花城》1998年第1期)。自1985年进入文坛以来,她一直将审美观照的目光流连于朴素本真的民间生活,从自然状态下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追寻现代社会渐渐失落的美好的人性,用无限的爱心、善良和情意构筑起自己天籁般的诗意世界。在她的所有作品中,最富艺术张力、最具人性深度的是那些表现生命悲凉况味和人生情感缺憾的小说。《逝川》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之一。
《逝川》不像其他小说那样靠故事的演进推动情节的发展,它更多的是凭借一种情绪的流动来打通全篇,这就赋予了作品一种诗化的品质。小说开篇对吉喜的介绍便给全篇定下了“悲凉”的基调。吉喜曾经是阿甲渔村最美丽、最能干的姑娘,她“丰腴挺拔有着高高鼻梁和鲜艳嘴唇”,“发髻高绾,明眸皓齿”,“不但能捕鱼、能吃生鱼,还会刺绣、裁剪、酿酒”,“在阿甲,男人们都欣赏她,都喜欢喝她酿的酒,她烹的茶,她制的烟叶,喜欢看她吃生鱼时生机勃勃的表情,喜欢她那一口与众不同的白牙”。逝川日日夜夜地流,吉喜也一天天地苍老。如今已七十八岁的老吉喜,变成了一个“干瘦而驼背”的老渔妇,“她的牙齿可怕地脱落了,牙床不再是鲜红色的,而是青紫色的,像是一面旷日持久被烟熏火燎的老墙。她的头发稀疏而且斑白,极像是冬日山洞口旁的一簇孤寂的荒草”。
和其他年轻美丽又能干的姑娘一样,吉喜也有着对爱情的憧憬,认定百里挑一的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胡会——阿甲姑娘心中的偶像——的妻子。“吉喜的这种想法酿造了她一生的悲剧”,胡会因为她“太能了”而娶了“毫无姿色和持家能力的彩珠”,留给吉喜的只是“月光下的院子里斑斑驳驳的树影”。忧伤就像悲凉的河水,腾起袅袅的雾气弥漫了吉喜孤独的一生。“吉喜过了四十岁就不再歌唱了,她开始沉静地迎接她头上出现的第一根白发,频繁地出入一家家为女人们接生,她是多么羡慕分娩者有那极其幸福痛苦的一瞬啊。”岁月的流逝,就像一去不返的河水一样,带走了她青春美丽的容颜和对爱情的梦想,带不走的是她“眼睛里迸射出雪亮的鱼鳞般的光芒”。这光芒昭示着吉喜对生命的热爱,在悲凉的尘世中,她生活得恬淡而从容。
悲凉的吉喜形象只是个铺垫,对初冬捕捞“泪鱼”的刻画则是对吉喜美好人性一次极其精彩的展示。捕捞“泪鱼”是阿甲渔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时刻,因为“泪鱼下来的时候,如果哪户没有捕到它,一无所获,那么这家的主人就会遭灾”。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胡会的孙媳妇却要生产了。一边是自己的福祉,一边是他人的幸福,而且这个胡会还是误了她一生幸福的情人,这确实是个让人进退两难的选择!吉喜没有犹豫,她去了胡会的家。门外是捕捞泪鱼的乡邻,忙碌而喜悦,门内是照顾生产的吉喜,忧伤而镇定。尽管她内心波澜起伏,但她还是尽心尽责地帮助产妇,亲手将一对龙凤胎带到这个世界上。接生错过了捕鱼的时间,她自然一条也没有捕到。不过,小说的最后,作家让善良的村民偷偷地在吉喜的盆里放了十几条泪鱼。“吉喜听着逝川发出的那种轻微的呜咽声,不禁泪滚双颊”。这个被命运捉弄的女子用宽容化解了心中的怨恨,用善良给别人带来了欢乐,也得到了大家的爱的回报!“因为懂得,所以悲悯”,作家躲在文字背后,不动声色,平静而隐忍地娓娓叙说,在拿捏故事的悲喜情绪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节制的情感表达,让北国的冰天雪地也洋溢着一丝人情的温暖。
“泪鱼”是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既给文本增添了悲凉的氛围,也是作品主人公的意象同构。这是一种美丽的鱼,有着“红色的鳍,蓝色的鳞片”,每年初冬时节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它们到来时“仿佛人世间所有的落叶都朝逝川涌来了,仿佛所有乐器奏出的最感伤的曲调汇集到一起了”。吉喜也是一条“泪鱼”。“吉喜过了中年特别喜欢唱歌。她站在逝川岸边刳生鱼时要唱,在秋季进山采蘑菇时要唱,在她家的木屋顶晾制干菜时要唱,在傍晚给家禽喂食时也要唱。吉喜的歌声像炊烟一样在阿甲渔村四处弥漫,男人们就像听到了泪鱼的哭声一样心如刀绞。他们每逢吉喜唱歌的时候就来朝她讨烟吃,并且亲切地一遍遍地叫着‘吉喜吉喜,吉喜就不再唱了……”吉喜悲凉的歌声就像泪鱼的哭声,听到的人心如刀绞,却无法给吉喜真正的慰藉,人们只能像呼唤泪鱼一样呼唤吉喜的名字。这种温情与无奈就如同流淌的河水,哭泣的泪鱼一样,让人忧伤无比。然而,也如同“泪鱼”得到渔妇的安慰之后欢快地向下游游去一样,吉喜也在温暖的人性中获得了精神的抚慰和救赎。也许生命就是这样在伤痛与感动之间不断地重复从而得以延续?的确,“泪”有时是悲伤的显现,有时又是感动的证明。作家就这样写出了人生的五味俱全。
作者有意在文本中隐去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也无意去叙写老吉喜一生的爱恨情仇,只是截选了她生命中的这样一个最具暖意的“横断面”,把自然风光、风土民情和美丽而波澜不惊的故事展现给读者,为读者再现了这块土地上单纯、朴实、真挚的美好人性。
迟子建曾经说过:“我喜欢有气味的小说……鲁迅的小说是有气味的,那是一股阴郁、硬朗而又散发着微咸气息的气味;沈从文的小说也是有气味的,它是那种湿漉漉的、微苦中有甜味的气味。……我觉得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小说气味是浓郁而别致的,如郁达夫、柔石、萧红等等。”(迟子建:《小说的气味》,载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第161页)迟子建的小说也是有气味的,它温婉细腻,空灵精致,神秘浪漫,就像雨中的丁香,微香中飘散着诗一般的伤感。这种叙事感觉使《逝川》弥漫着一股悲凉神秘的氛围。
作家生活的东北地区,人们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自然是崇高而不可亵渎的。“我生长在大兴安岭,受鄂伦春人‘万物有灵论的影响,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作是生命的伙伴”(李树泉,迟子建:《在厚厚的泥巴后面——作家迟子建访谈》,出自中国作家网)。文本中的树林、晨霜、白雪、月亮、篝火……当然还有“泪鱼”和那个美丽的传说,这一切都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流溢着诗意凄美的神秘色彩。而“逝川”本身就是一个流逝与消亡的象征。“泪鱼岁岁年年畅游整条逝川,而人却只能守着逝川的一段,守住的就活下去、老下去,守不住的就成为它岸边的坟冢,听它的水声,依然望着它。”生命易逝,时光永恒。吉喜从一个“发髻高绾,明眸皓齿”、“丰腴挺拔有着高高鼻梁和鲜艳嘴唇的姑娘”,变成一个“牙齿可怕地脱落”、“头发稀疏而且斑白”的“驼背的老渔妇”,生命由鲜艳到枯萎,在时间的长河中也不过就是一瞬。那曾带给她短暂幸福的“沸水将壶盖顶得噗噗的声响”,不时在老吉喜的耳边响起,让我们看到孤独的生命对消逝的爱情的永远难以释怀,小说因而萦绕着无法消失的苍凉与辛酸。
苍凉是颇具现代意味的审美形态,20世纪中国文学中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书写了悲凉的人生。鲁迅作为“肩住黑暗的闸门”的先觉者,用“旷野的呐喊”呈现了“五四”时期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寂寞和孤独;萧红《呼兰河传》中反复在说一句话——“我的家是荒凉的”,她用成年人的眼光消解了童年回忆中的温暖;张爱玲作品的主要基调就是苍凉。这种苍凉几乎笼罩着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一切人生的意义都指向虚无;汪曾祺主要采用回忆的视角,用过去与现在做对比,表现出一种挽歌情绪……相比较这些作家而言,迟子建的悲凉自有其特别的品格。
迟子建说:“我的很多作品意象是苍凉的,情调是忧伤的。在这种苍凉和忧伤之中,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应该是让人欣喜的。”(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迟子建的苍凉是伴随着温情的苍凉,它没有鲁迅思想的深刻,也不同于张爱玲的悲观虚无,她相信温暖常在,希望常在!《逝川》的结尾,作家给老吉喜的木桶中放进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这不仅仅是一点点同情和善意,她是力求从平凡世俗的生活中挖掘情趣和诗意,表现一种极致的平静和幸福。人生绝不只是苦难。尼采说过,生命如同一条毯子,苦难之线和幸福之线在上面紧密交织,抽出其中一根就会破坏了整条毯子,整个生命。迟子建小说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她不仅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世俗世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同时构筑了一个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充满巨大的向善的力量,将我们从世俗中提升起来,达到一个精神的境界”(张红萍:《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所以苏童说“一支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的心中”,迟子建也承认“这种温暖是值得人为之动容的”。
当下的作家能写出官场的黑暗,道德的沦丧,也能写出乡民的苦难,欲望的放纵,却常常忘了这种值得珍重的人性,忘了“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迟子建对苦难有这样一种超然的理解,更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荷尔德林说:“人类充满劳绩,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因为人类充满劳绩,我们才更需要诗意地栖居!文学的精神,小说的精神不就是在过于现实现世的生活中,为人们打开一方瑰丽的天窗,使人们的灵魂在文学的世界里得到抚慰并获得超越吗?迟子建小说中诗性的外壳和人性的光辉正是对这句名言最好的注解!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