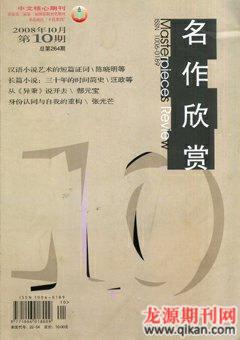一种文体的崛起
四年前,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国新时期至今的文学,以中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尤其中篇小说的繁荣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亮点。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二十多年是中篇小说最辉煌的时代,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这个现象恐怕也是值得一提的。而且在新时期文学中,代表小说创作最高水平的,是中篇小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体,如唐诗、宋词、元曲,如果要说迄今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文体是什么,我认为是中篇小说。”(夏康达:《突然风平浪静——新世纪小说印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今天回顾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历程,综述中篇小说的创作状况,我再一次重申这一评价,并在可能的篇幅内,稍作展开的论述。
一
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是在冲破极“左”文艺思潮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端的。把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变成“写十三年”(提出这个口号时正是建国十三年,其实就是要求文学只反映新中国的社会生活)、“写中心”、写工农兵,这是极“左”文艺思想一个核心观点。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造成极大障碍,解放前的一批文学大师在建国后的创作普遍走下坡路,不能不说这是原因之一。在清理这一思想时,却又产生另一倾向的问题,在躲避崇高的同时,有人也躲避现实。这就成为产生有影响的反映现实题材作品的障碍,还影响创作中应有的现实感。但是,始终有一批关注着中国社会飞速变化的有责任心的作家,以中篇小说的文学样式,跟踪时代的步伐,使三十年的中篇小说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缩影。
文学反映时代,并不等于如实记录每个重要事件。文学不是历史,也不是新闻。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不是因为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描述了俄国革命,而是托尔斯泰对俄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俄国农民复杂而矛盾的思想。
三十年中篇小说最早有影响的作品是“伤痕文学”。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能否发表,当时在北京开了一个讨论会。这两部中篇在《收获》发表后,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潮,突破了文学上人为设置的许多禁区。此后,中篇小说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始终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反映与介入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反思文学是追寻“文革”前建国十七年的往事,但它重于思索,是为了今后而反思过去。《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作品,思考的是现实中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几乎同时起步的“改革文学”,也以中篇小说为主要载体,蒋子龙笔下的“开拓者家族”身上,凝聚着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强烈的期盼与深深的忧患。90年代谭歌的《大厂》等作品则更多地流露了迷惘与苦涩,有助于人们对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认识。谌容的《人到中年》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与疲劳“断裂”,是建国后始终在调整而一直没能处理好的问题。路遥的《人生》所展现的一个农村青年进城梦的萌生与幻灭,是80年代至今中国农村青年难以释怀的人生困境。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作为下乡知青的悲壮故事,却明显带有80年代崇高浪漫的情怀,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则正视了回城知青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知青题材之外,关于青年的中篇,如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叶弥的《成长如蜕》等,每个时期都不缺少有影响的作品,不胜枚举。随着社会发展中负面影响的呈现,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受到普遍关注,在20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底层文学”形成一股文学潮流,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中篇,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映现实社会心理。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得到读者认同,首先是与读者的心理产生共鸣。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主要不是这种小说样式的新奇,而是在那个年头,普遍弥漫着一种“烦恼”心态,《烦恼人生》(池莉)等作品所倾诉的人生烦恼,当时的许多民众都感同身受。近年来,由于女性作家的成绩卓著,中国现实社会的各种女性心理,都在中篇创作中得到反映。从张洁的《方舟》到后来的一批中青年女作家以中篇为主的小说作品,使中国女界这三十年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表达。
只要我们不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成照相式的直接反映,而是把社会现实问题意识与大众社会心理的诉求作为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的重要表现,那么,有人认为现今文学的“边缘化”是因为文学脱离了现实,至少是不符合中篇小说的实际情况的。举一些例子来阐明这样一个宏观的论题,或许是最可疑的论证方法。然而,只要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又同时比较关注当时的中篇小说创作情况,你就可能会同意这样的评价: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人生状态与精神境遇,不仅构成了三十年中篇小说力透纸背的现实写照,也使三十年的中篇小说成为反射这段社会的历史存在与文化风貌的一面镜子。
这也是这个文体在当代崛起的先天性原因。长篇巨制由于工程浩大,需要更多时间的积淀与构思,难免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要求长篇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性是不现实的。短篇小说当然更具有“短平快”的优势,但是篇幅的限制使其施展不开,难以比较充分地展示时代风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以短篇小说发表与得奖的,但它的字数完全是一个中篇的规模,所以发表时列了三个小题目,成了系列短篇。后来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是中篇,内容与形式之间就不会互相掣肘了吧。
中篇小说的崛起,首先是社会现实对文学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主动适应,这是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
1
二
中篇小说在三十年不断更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中,始终居于潮头,或处于主流文体的地位,充分显示这种文体所具有的丰富的表现力与巨大的创新可能性。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坛空前活跃,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现象层出不穷,有“各领风骚三五年”之叹。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就会发现,中篇小说创作在推动文学潮流不断涌动的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潮流“伤痕文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为滥觞,如果将其与稍后出现而内容上先后承接可以视为一体的“反思文学”一起考察,那么,中篇小说《啊!》(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蝴蝶》(王蒙)等作品,有着更重大的影响。“改革文学”已如前述,而8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军旅文学”《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射天狼》(朱苏进)等也以中篇为主打文体。“先锋小说”的几位代表作家,不约而同地以中篇为主要的实验文体,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罂粟之家》等。“新写实小说”的重要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在那个时期,都以中篇小说为主来构筑“新写实”的别样风采。陈染、林白等的“女性文学”以中篇的数量为多。“新历史小说”固然以长篇称雄文坛,但其发端之作,乃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新世纪方兴未艾的“底层文学”,其优秀之作,也以中篇居多,已不必一一列举了吧。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篇小说在当代文坛上以其迅捷敏悟的思想探索和大胆的艺术表现,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风骚,并且成为三十年来文学思潮嬗变的风向标,并高居于时代文学的波峰浪尖。
中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方面,呈现着令人鼓舞的既守成又开放的姿态。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十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但在艺术表现方面则从不僵化保守,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明显地融入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诸多因素。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所侧重的是社会批判与社会人性的批判,而现代后现代主义批判则侧重于那种更形而上的哲思或人性的深度探索,这样的文学不但没有因此而削弱了它的社会批判功能,相反,其现代性的渗入加深了其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从外在表现上看,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流、荒诞手法、魔幻现实主义、叙述游戏、文化消费主义特征等等——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中已经出现过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哲学思潮或文化现象乃至话语方式叙述技巧等,在这三十年来的中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相对应的表现,虽然有些手法的借鉴在小说中还有着明显的移植痕迹,但也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学自身成长的一种历练过程,成为当代文学中一道别样的风景。像《蝴蝶》中的意识流表现,《红高粱》、《灵旗》(乔良)中有别于此前关于红色革命记忆的历史观,《黄泥街》(残雪)中的荒诞色彩,《迷舟》中的叙述游戏等,这些都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现实主义范畴,表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兼容并蓄或互相包容。这不仅是对域外现代后现代思潮流派的一种追踪或借鉴,也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本土化变异的一种心理选择和文化态势。即使是最接近传统现实主义并以写实为其主要特色的新写实小说,在贴近真实的描摹和呈现原生态的生活表象背后,掩藏的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现代意识及其“零度写作”,而是在贴近生活原生态的描摹中重塑日常生活的存在价值与普通人生的大众趣味,认同世俗人生的生活观念,这不仅形成了对曾经献身事业追求理想的崇高以及相应意义的逃逸或反抗,更是对其话语体系及其审美范式的深度疏离和自觉改变。因此,伴随着这些现代后现代手法或因素的融入,自然也蕴含了对此前以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基础的“真实”、“历史的必然规律”、“意义”等话语体系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及其认同的质疑或解构,某些方面甚至具有完全颠覆的意味。因而中篇小说在审美上呈现现实主义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融合,其实只是它的外在形态的显在变化,而实质性的潜在变化则是率先改变并标志着相应历史阶段的话语模式的转变,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认知体系乃至文化心理构成的转型。
作为一股文学潮流,“先锋文学”已成明日黄花,但这个以中篇为主的文学实验对中国文坛的冲击,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影响。它的出现与寂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现实主义的现代化和先锋小说的本土化”(陈冲:《现实主义的现代化和先锋小说的本土化》,《小说评论》2001年第4期)。我认为这种趋势在王蒙的《蝴蝶》等作品中已见端倪,“新写实小说”则是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在后来的中篇(当然也不仅是中篇)创作中,更是随处可见。天津作家王松近年写了《双驴记》等一组关于知青生活的中篇,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说是现实与荒诞的结合,我则干脆提出了“荒诞现实主义”的概念。这个名词以前也有人用过。而王松小说离奇的荒诞感与强烈的现实感,使他的知青题材小说别开生面。
现代主义元素可以被现实主义吸收的不仅是意识流、荒诞等几种。过去有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是不把两者看成水火不容。那么,我们今天是否也不必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看成不共戴天,可以提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呢?纵观三十年的中篇小说,我感到这种结合已经存在,现在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阐述。
三
1
中篇小说篇幅适中,既能比较充分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又不占用太多时间,很适合当前读者的审美需求。这是其得以崛起的读者接受因素。此外,传播手段的改善,也为中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传播手段的发展对文体演变影响很大。说书人的出现,扩大了口头传播手段,促进了章回小说的发展。印刷术的进步,催生了长篇小说大发展。没有现代报刊的繁荣,不可能有杂文的兴旺。“80后文学”能够形成青春文学前所未有的气势,互联网肯定起了很大作用。中篇的崛起与大型期刊的发展关系密切。《收获》在1956年创刊,直至“文革”,全国只此一家。新时期大型期刊如雨后春笋,几乎每个省市都有一家。接着《中篇小说选刊》应运而生,《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也把中篇小说放在主要位置。短篇小说评奖从1978年开始一年一评,第一届中篇小说奖是评1977年-1980年四年的作品,以后的评奖周期就缩短了。大型期刊的兴起对中篇的繁荣,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中篇创作的发展,也是大型期刊得以生存的有力保障。
中篇小说的崛起,也反映在对其他艺术样式的影响。建国以来,小说与电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建国初期,许多名著被改编成电影,而电影在当时又以其大众的传播形式为文学的普及开辟了更为宽广的受众群体。而近三十年的中篇小说,不仅续接了以往文学与电影的互动传统,而且,由于电视的普及和更为宽泛的收视覆盖面,使原创性的文学作品一旦被改编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后,其影响力呈现的是成几何倍数的扩大。这就使一部分人先是小说的读者,之后成为影视的观众,而另有不少人的接受顺序正好逆反过来,是在看了影视之后再去阅读文学文本。这样,影视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力,也成为理解小说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仅以张艺谋导演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而获得双赢的,就有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红高粱》、由《伏羲伏羲》改编的《菊豆》、由《万家诉讼》改编的《秋菊打官司》、由《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不仅是由于中篇的篇幅介乎短、长二者之间,赢得了因其篇幅而具有的创作发表周期短速度快的优势,也因为适量的篇幅使作家能够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心理方面可以既充分而又有节制地表达,又能在叙述技巧和故事完整方面做到收放自如挥洒从容,既避开了短篇的单薄,也免去了长篇可能的杂沓。而这种单个故事饱满的张力和相对完整的情绪,又很适合一部电影的叙述长度。这就使得中篇小说本身的创作在影视的改编上获得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影视艺术的再创作与再表现,又使其原本意义朦胧或多义的文学形象在视觉效应上被清晰和强化,尤其是那些改编成功并在国际国内赢得了一定声誉的电影或电视,使文学形象的魅力在再度的艺术阐释中得以拓展。比如获得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的《本命年》为原创中篇小说《黑的雪》增色不少;获得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的七项大奖并在第二届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三项大奖的电影《老井》,也使得同名中篇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而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样为小说《妻妾成群》和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狮奖的《秋菊打官司》使得《万家诉讼》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名篇佳作。这些事实也说明了,中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由于电影语言的视觉效果及其综合的艺术性,使之比纯粹语言艺术的小说更容易走出国门。近三十年依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被认同和获奖系数的比例显然大于原创的小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借电影的东风,我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国界的路途中,中篇相对于短篇和长篇,可能也占据表现相对快速和内涵又相当饱满的优势。
可见,中篇小说以其迅速捕捉社会价值观念及其文化心理的细微变化和表现扎实丰厚的生活内涵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再度发掘的契机,而影视改编的二次创作及其自身形式所具有的大众传媒性又为中篇小说通向更为广阔的接受空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中篇小说与影视创作互为彰显,相得益彰。
我们再来看作家队伍的成长。一般都认为初学写作应以短篇小说起步,这是有道理的。但近三十年来,以中篇小说的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不在少数。中篇创作的历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近三十年来,每一个思潮或流派的出现,都会因其引人注目的发轫之作或代表作品而成就一些作家。如果说新历史小说中的优秀中篇成就了莫言、乔良、周梅森、叶兆言等还有些勉强的话,因为这些作家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学创作,只是知名度不够,那么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及形成潮流,就是以中篇小说为先导的,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其代表作至今也仍然是中篇。当年《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的同时,也使一些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年轻作家被推到了众人瞩目的前台,其中的代表有池莉、方方、刘震云等。《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说,“余华在《收获》成名”,就是因为发表了《一九八六》等中篇小说,而此前余华没有发表过中篇,《活着》在《收获》上第一次发表时也是中篇(《〈收获〉:让余华和余秋雨成名》,《新京报》2006年9月6日)。1987年第5期和第6期的《收获》,比较集中地推出了先锋小说,看看这两期《收获》里的中篇小说和作家,就基本明白了先锋小说作家的主要阵容。人们从此记住了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不仅是每个思潮流派的出现会推出一些著名作家,就是那些非思潮性的个性化的作家,也常常因为中篇的创作而得益。考察近三十年来中篇小说这种文体与作家的关系,不能不承认,以中篇的创作成名,已经成为小说家的成长和成名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无怪乎有人说“新时期的好作家几乎都是靠写好中篇获得关注,从而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收获〉:让余华和余秋雨成名》,《新京报》2006年9月6日)。
近三十年来的当代文学经历了从主流的话语中心位置到边缘化的过程,对于这种变化,有人认为是文学的失落。我一直不这么认为。新时期初文学那种“一呼万应”的热烈状态固然令人兴奋,其实这是文学借助社会政治的原因,所产生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是不可能持久的。现在所谓的“边缘化”,倒是文学应有的一种正常状态。“边缘化”不是文学水平的评价标准,以“边缘化”作依据说中国当前文学质量下降,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所谓的“垃圾说”更不值一驳。真正能说明文学水平的是作品。以三十年中篇小说而言,我们不说其成就如何辉煌,至少也不断有佳作涌现,总体水平也在我们这个国家民众期待的应有水平线上,是承续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不断前行的。这就是我对我们的三十年中篇小说的历史性的评价。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文学系主任,首席教授;中国小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