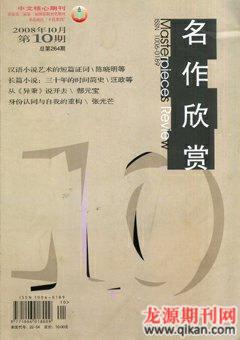打一眼深井
段崇轩
【推荐理由】
在“新时期”文学抚慰“伤痕”、“反思”传统、呼唤“改革”的潮流中,林斤澜的《头像》却把敏锐的笔触直指知识分子自身,提出了艺术家如何面对世俗社会,如何坚守艺术信念的问题。他的反省直到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林斤澜在短篇小说的表现功能、人物塑造、结构营造以及叙述方式上,不懈探索和开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体和风格,对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读林斤澜的小说,需要有一种平静、专注甚至闲适的心境。他是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出小说家之一。他倾注了全部的生命和心血,感受和思考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农民阶层的一些深层问题。他“痴迷”短篇小说艺术,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它的审美特性、源流传统、表现方法和技巧等,不断借鉴、精心实验,在“方寸之间”创造了一种丰富、独特甚至有点“怪味”的小说文体。深邃的思想、怪异的文体,构成了让人感觉“陌生”的文学世界。面对这样一种世界,没有一种恬淡的心态,你是很难深入进去的。然而一旦走进,你就会领悟到社会人生的某种真谛,享受到短篇小说的醇厚魅力。
《头像》發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7期,获同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20篇获奖作品中,排列中下游。此时,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如火如荼,短篇小说更是独领风骚。“伤痕”、“反思”文学还未过去,“改革”文学又接踵而至。刚刚获得“解放”的作家们,都在紧紧追赶时代潮流,反映身边急剧变化着的生活;短篇小说作为一种对时代最敏感的文体,他们拿来就用,还无暇顾及对它的改造、创新。而林斤澜的《头像》,表现的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认识和反思;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探索和拓展。这就与整个文学潮流,显得有点不大合拍,甚而有些“独往独来”的味道。也许是文学界特别是“评委”们已感受到了这篇小说的分量,但还没有充分看到它的价值,因此评了奖,但没有把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在随后《小说选刊》开辟的《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漫评》专栏里,12位评委的文章,绝大多数作品都评述到了,包括汪曾祺的《大淖纪事》等,但唯独对《头像》未置一词。这篇作品的发表、获奖是寂寞的,在以后的文学评论中,对它的评价似乎也不多。然而,真正的好作品是淹没不了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检视新时期文学的短篇小说,《头像》再一次跃入我们的眼中,且27年过去了,它的思想、艺术依然熠熠生辉。而获奖名单中一些名列前茅的作品,已成“明日黄花”。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优秀的乃至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有很多位,但真正在文体上有所开拓、创造的作家却不多。林斤澜则是一位真正具有探索精神的“文体家”。他上世纪50年代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在短篇创作上的独特追求,而到新时期文学的80年、90年代,更是孜孜矻矻、“一意孤行”,进入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幽远境界。对短篇小说文体的探索,说到底源于作家对其艺术特性的认识和把握。林斤澜说:“真正的文艺,总是借着形象感动读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想得更多、更大、更远,也就是有内涵,有较大的容量。那么说,小说就是要大了,要写大事件、大场面、大人物、大自然……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小说就是要说小,好的小说就是从小里见大。小口子井,井底的地下泉水却深得不知深浅。”① 思想内容的无限深广和篇幅体式的小巧精致的有机统一,这正是林斤澜对短篇小说艺术特性的基本认识。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短篇艺术观中,有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有契诃夫“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的深刻影响。打一眼深井,一眼“小口子井”,就是林斤澜毕生对短篇小说的执著追求。为了打好这眼井,他坚守的是那种真刀真枪的现实主义方法;为了打好这眼井,他借鉴了古典的、现代的诸多表现手法。但在《头像》中,他运用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方法,只是在后来的创作中,传奇的、变形的、朦胧的等手法才逐渐多了起来。
《头像》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写了一位正走红运的画家老麦,作品获奖之后顺路去看望他旧日的老同学——雕塑家梅大厦,在那里吃了一碗挂面汤,谈了谈生活问题,看了看老同学的新作品。如此而已。但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宏大而丰富的社会内涵以及斑斑驳驳的社会背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已进入万物复苏、百废待兴的新时期,文化艺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名誉、地位、金钱的诱惑也滚滚而来。而梅大厦这位杰出的雕塑家,却蜗居大杂院,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沉浸在他的艺术创造中。在这种强烈的社会与人生的巨大反差中,林斤澜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艺术家如何面对世俗化的时代?艺术家怎样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这是当时众多作家、艺术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但大家身在其中,感受迟钝。而林斤澜却敏锐地、及时地提出来了。同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要面对的长期的社会问题,20多年过去了,今天显得更加严峻复杂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裹挟下,不是有众多的作家、艺术家放弃了艺术信念,成为名缰利锁的“奴隶”了吗?读读这篇小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作品正是通过两位老同学的相见这样一个简单情节,展示了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它不仅对当时有现实意义,对今天也有警示意义,真是一眼“小口子井”,作者在选取和表现生活上,下了多少苦功啊!
对短篇小说来说,塑造人物几乎是一个刚性要求。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狭隘地理解了恩格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总是把人物等同于性格,认为只要把人物的性格写出来了,小说就算成功了。对于长、中篇小说而言,这个道理没有错。但对短篇小说就是一个苛求。因为短篇小说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让你精雕细刻人物外在的、多样的性格特点。林斤澜在这一艺术课题上,同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依然用的是打深井的办法,即对自己所写的人物,反复揣摩、探寻,努力把握这一人物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品格、灵魂等——即精神特征,一旦找到了,就以此为内核,重新想象、借鉴、构筑一个新的艺术生命。这样的人物,也许外在的性格不那么鲜明、突出,但却有一种坚实的精神特征,同样会很强烈、很感人。其艺术概括力往往超过那种性格化人物。应该说,短篇小说更适宜塑造这样的人物。林斤澜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塑造了众多的这类人物。汪曾祺是林斤澜的“知音”,他评价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不大写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的性格。他甚至连外貌都写得很少,几笔。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得其精而遗其粗。”②
《头像》中的人物就是具有独特精神特征的人物。梅大厦是作品的主角,他全部精神特征就表现在一个“痴”字上,对他所献身的艺术事业的一片痴情、忠贞不渝、甚至“舍生忘死”。数十年的历史变动、人生沉浮,他似乎浑然不觉,依然保持着学生时代对雕塑事业的那种“初恋”般的感情和激情;他淡忘了世俗的婚姻爱情生活,宁肯一个人受苦也不愿再去成家,因为他认定:“想搞艺术,就不要想好命运”,“我最幸福的时候,是艺术上最糟糕的时候”。把艺术与幸福截然对立起来了;他完全沉浸在了艺术的创造之中,从着力继承民族传统,到锐意探索现代派表现方法,又到从民间文艺汲取资源同时化入西方现代手法形成自己兼容并蓄的艺术路子和风格,他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进入佳境,自觉“看得见自由王国了”。那尊既写实又变形的木雕少妇头像,标志着他已进入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几十年的艺术跋涉,他外表已像一个“老不顶用了的泥瓦匠”,但那两只手“皮肤紧绷,肌肉鼓胀,伸缩灵活”,依然是“年轻的手”。灵感袭来,两只眼“一下子贼亮贼亮,仿佛打个电闪”。这是一个把艺术当作生命的人,是一个超然世外、漫游在精神创造中的灵魂。从这个层面上说,梅大厦具有某种抽象、象征的意味。同那种现实主义的性格人物迥然不同。而同是艺术家的老麦,他的精神特征则是一个“活”字,对社会、人生、艺术他都能左右逢源,灵活处置,应对自如。他在“文革”时所受的苦难,已变为“光荣的历史”;他的画画专长已成为不断获取名誉和地位的可靠资本。幸福的家庭、争气的儿女、优越的地位他都有了,他过得满足而惬意。他绝不把人生和艺术对立起来,一面要享受人生,一面要追求艺术。他深知自己缺乏梅大厦那种对艺术的“痴情”和激情,并理解和尊重老同学的追求,还想真心地帮他一把,但他绝不会为了艺术而放弃美好的生活。他活得滋润、活络、潇洒,但他离世俗越来越近,离艺术越来越远。这样的艺术家其实是大多数,林斤澜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精神特征。认同、赞颂梅大厦,揭示、批评麦画家,林斤澜毫不掩饰他的情感态度。作者在不到万字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两位逼真而有力的艺术形象。
短篇小说的情节结构,向来是作家着力的重心。林斤澜十分重视小说的艺术结构,他说:“情节的线索是明显的线索,最容易拴住人。但,也会把复杂的生活,变幻的心理,闪烁的感觉给拴死了。有时候宁肯打碎情节,切断情节,淡化情节直到成心不要情节。有人说靠情节作线索,格调不高。有人说戏剧性的情节,能把真情写假了。”③ 这是对短篇小说情节结构的精辟见解,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所谓情节(线索),就是一连串紧密联系的生活事件。短篇小说不能没有情节,但如果情节过分完整、密集甚至是戏剧化的,也许会吸引读者,但却会伤害艺术本身。林斤澜看到了情节的负面作用,因此在小说中很少用那种有头有尾、逻辑严密的情节;而有意识地用“散文化”的情节作为主干,这样就给他的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有利于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如前所述,《头像》的情节非常简单,二位老同学见面,自然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说什么、做什么呢?自由度很大,作家完全可以推理、想象、虚构。作家正是通过一些极平常的场景、情节和细节,如梅大厦煮挂面、给老同学讲述他的作品和想法,老麦巡视雕塑作品、苦劝老友找对象成家等等。这些看似平淡的情节和细节,却是作者苦心提炼和精心安排的,自然而然地凸现了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作品关于知识分子的反思主题。作品中的老麦是一个线索式人物、或者说视角人物,他是刚刚获奖想找老同学来显摆一番、劝说一番的。但最后被老同学感动,琢磨着要帮他一把。中心人物梅大厦,虽然生活艰难、默默无闻,但他满屋的杰作、高远的追求,照亮了昏暗的小屋,也使麦画家深受教育。这样的设计可谓别具匠心。作品结尾,那位邻居老太太“摇着头走进没有门扇的门洞,还揉她那团面去了”。不仅给作品带来一缕轻松和幽默,一个“揉面”的细节更是意味深长。整个情节结构自然、鲜活、流畅,而整体上又和谐、紧凑、完美。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批评家。
①③ 林斤澜:《论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②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文艺报》1987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