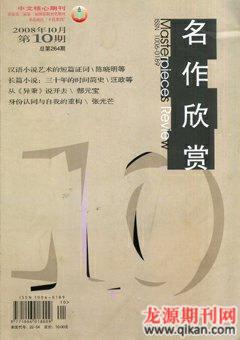孙犁的“另类”作品及其文学史意义
樊 星
【推荐理由】
谈到孙犁老人,人们都十分熟悉他那些风格清新、俊逸的小说,例如《荷花淀》《铁木前传》,熟悉他那些优美的散文,而对他“文革”后的小说成就则评论不多。其实,他的系列笔记《芸斋小说》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有特别的意义——那是他“文革”记忆的实录(因此也是当代“伤痕—反思文学”的组成部分),是他饱经沧桑后风格巨变的新突破(因此也成为老作家重新焕发创作能量、不断超越自我的可贵收获),也是他为当代“笔记小说”做出的重要贡献。在纪念新时期文学走过三十年风雨历程的今天,重温《芸斋小说》,对于全面了解孙犁老人的文学创作,对于重新认识老一代作家对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贡献,意义不可低估。
在当代文学史上,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延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派”却又不那么“大众化”;描绘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硝烟味却又明显不那么浓,倒是以清新、俊逸的风格见长。甚至他相当偏爱描写那些不仅不那么革命,甚至有点风骚、有点不“合群”、自由散漫的青年女性(例如《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在那个年代的文学画廊中也显得相当“刺眼”、特别。因此,孙犁独具特色的作品在“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艺”中,显得比较“另类”。他因此而几度受到过苛评,但又并不因此而改弦更张。他的个性因此而格外惹人注目。
“文革”以后,孙犁仍然是以“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而驰名文坛的。在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贾平凹的《满月儿》、铁凝的《哦,香雪》这些有名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在那些清新、俊逸的故事中,感受到“荷花淀派”的流风余韵。这意味着,“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艺”这独特的一脉,在新时期依然有着活泼的生命力。然而,孙犁本人却似乎无意继续沿着那条路前进。在1981年—1989年间,他陆续发表了一组总题为《芸斋小说》的笔记,显示出他晚年超越“荷花淀派”风格的可贵努力,殊为不易。
在198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新笔记小说”的创作热潮。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贾平凹的“商州三录”、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庆西的“人间笔记”、阿城的“遍地风流”,都是其中影响盛极一时的名作。这些笔记,继承了中国古典笔记的传统,显示出了一部分作家在文体上的“寻根”意识。无论是记录人情世态,还是描绘风土趣闻,或是点染人生哲理,都有西方文学(无论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或是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及之处。那分含蓄,那分玄远,那分简练,只属于写出了《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的中国文人。而在上述各有千秋的“新笔记小说”中,《芸斋小说》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其中绝大部分是记录作家自己的“文革”经历,以及由那些经历产生的人生顿悟和感慨。因此,《芸斋小说》就成为当代“伤痕—反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与一般的“伤痕—反思文学”略有不同的,是作家常常不似“伤痕—反思文学”的主流那样,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去揭示“文革”的深刻政治或历史意义。《芸斋小说》的一大看点是对人情世故的顿悟和感慨,因而更具有一分“人情味”、一分沧桑感。这沧桑感,非阅世深者不能表达。
例如这篇《冯前》,就是一篇忆旧之作。作品开篇写主人公冯前为人的“爽朗、热情”,为文也“通畅活泼”,但很快笔锋一转,写此人成为报纸的总编以后,渐渐有了官气,与“我”之间本来不错的熟人关系也渐渐疏远了。“人一阔,脸就变”,本是人情世故之常。但作家却能以寥寥几笔,勾勒出冯前在“文革”中“变”的特别:虽然“我”与冯前的关系已经疏远,可冯前却把他坐的卧车留给了“我”。在那“照顾”的后面是否别有居心?作家没有明写,但以一句“他可能是有想法的”点出不绝于耳的弦外之音。接下来,是冯前的一连串表现:批判有恩于他的老上级;并在那位老上级自杀以后特意托人告知“我”(是给已被打成老上级“死党”的“我”增加心理压力,还是有所提醒?);在“我”家被查抄以后,他竟然还来看了我一次(是关心?),却又“一句话也没说”,但很快派人来收走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枪(是掩人耳目?)……在这些匪夷所思又耐人寻味的表现中,一个在政治暴风雨中努力紧跟形势、却又不那么偏激的政客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但他终于还是被暴风雨打倒了。而他被打倒以后的表现也相当奇特:时而以恐怕“我”不能适应干校的生活而建议把“我”关起来(非常有意思的理由!);时而又在“我”去干校时帮我背行李(这无疑是关心!);在批判“我”时,他只说“我”是遗老遗少(这就明显不同于那个年代里司空见惯的“上纲上线”);在检讨自己时,他也相当实在——谈“升官要诀”(因此而不同于那个年代里经常可以听到的被批斗者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彻底否定);在逆境中,他似乎觉得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的不合适,于是以“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的说法试图求得“我”的谅解(事实上,有许多人在政治运动中都是以同样的态度去努力自我保护的——有几分真诚?又有几分无奈?还有几分文过饰非?)。而一当他又时来运转时,他的脸就又变了:先是劝告“我”不要养花(似乎不乏善意,因为在“文革”中养花被认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在“我”不听他劝时当着军代表的面揭发“我”,可惜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就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格的政客形象就站立在新时期的人物形象画廊中——他“一阔脸就变”,却变得相当独特,不那么张狂,也常常不那么把坏事做绝(正应了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做事留后路),他因此显得颇有点聪明。另一方面,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还体现在: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从中央到基层的许多干部都是在政治暴风雨来临时先是努力把部下或对手抛出来,以求自保;但到头来还是被打倒在了暴风雨中。这种损人利己、牺牲同事保护自己的做法在官场上为什么那么流行?许多干部对这一套似乎是无师自通就运用得十分娴熟了。虽然柏杨曾经十分准确地揭露了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劣根性”,但这里的问题却是:不少政客都是为了政治运动的无情,才昧着良心,以牺牲无辜的人来达到保护自己,甚至升官发财的可耻目的的。中国民间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说法,堪称生动。这,也许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潜规则”。但结果却常常是“抛”人的人和被“抛”的人常常终于一起倒霉,一起完蛋,弄到最后“抛”人的人里外不是人。在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中,在张贤亮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中,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中,我们都不难看到相似的情节。由此可见政客的无情,官场的无义,政治的险恶。从这个角度看,《冯前》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的。
问题还在于:“踩着别人往上爬”真的是官场中人难免的宿命吗?中国有句俗语:“为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有没有人就避免了“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宿命?《冯前》中的“我”就证明,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也是“老革命”出身,虽然对于冯前的小人品行知根知底,但在逆境中还是通过尽可能关照冯前显示了自己“重友情”的一面。在冯前为自己辩解时,“我”仍然可以因为“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而问心无愧。如果说,“我”是刻意与官场保持了一段距离的,那么,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军管人员(在“文革”中,在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以后,是由“军管”维护着秩序的,军管人员因此而权重一时)——也在冯前小题大做地揭发“我”养花养鱼时“没有理他”,显示了良知的存在,人之常情的坚固。
考虑到解放以后,孙犁老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处于养病的状态,因而远离了政治风雨,远离了一些可怕的是非,我们也不难看出:孙犁是早就觉悟了的。读许多人的“文革”回忆,不难发现,人们多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猛然醒悟到“文革”的荒诞的。但孙犁显然更早。这也许与他的作品早在解放区时期和1950年代初就因为充满了“小资情调”而受到指责,可他又因为对于自己的作品有“自珍之癖”而不接受那些指责这一事实有关;也许与他受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熏陶有关(他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和柳宗元的影响),而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是明显有一股清高之气的。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因此与巴金老人不同。如果说,巴金老人是因为西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熏陶而敢于“说真话”,那么,孙犁老人则是因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而有意疏远了险恶的政治运动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自有对于现代政治迷信的免疫力。保持了儒家的大丈夫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者保持了道家的隐士情怀,都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阴霾的。
最后,是作品中对于“文革”的那段议论:“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寥寥几笔,也写出了“文革”的非理性。“文革”的风雨多变,阴晴不定,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正常思维。虽然,“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但伟大领袖在呼风唤雨以后的穷于应付、心力交瘁,也一望可知。以这样的眼光看去,冯前之流的“抛”人与被“抛”,大落与大起,可能也是他们自己绞尽脑汁,仍不免载沉载浮的悲剧所在。是的,冯前是相当可厌的,也十分可怜。因此,虽然作家在篇末的议论中透出了对于冯前这个“大风派”的不屑和对于这种人一旦时机成熟,是可能飞黄腾达的隐忧,我仍然觉得作品中写活了这一类人物的可怜——无论怎么紧跟也跟不上形势的可怜,还有到头来里外不是人的可怜、可悲!有不少风派人物能够在政治运动中左右逢源的,可也有的风派人物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新时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暴露“文革”、反思“文革”的名篇佳作无数。这些作品已经在文坛上建起了一座庄严、壮观的“‘文革博物馆”。但如何写出“文革”中人的复杂性?怎样写出“文革”的匪夷所思性?今天看来,依然有许多空间可供开拓。在这方面,《冯前》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洗练、节制,在叙述语言方面的不温不火,仍然是值得借鉴的。而对于孙犁老人而言,从早年的“荷花淀派”风格的清新、俊逸到晚年的《芸斋小说》的朴素、冷峻,那风格的巨变恐怕也不只是作家个人努力自我超越的结果吧。经过了“文革”的折腾,他对世事看得更透了,于是就自然放下了曾有过的诗情,而开始回眸无奇不有的纷繁世事,记录毫无诗意却五味俱全的人生了。由此可见,仅仅只将孙犁看做“荷花淀派”的代表是不完整的。
放眼当代文坛,从描绘诗意人生转向刻画严酷人生,竟然是不少作家在冥冥中不约而同遵循的路线——例如贾平凹从1978年的《满月儿》到1983年的《鬼城》,铁凝从1982年的《哦,香雪》到1986年的《麦秸垛》,还有张洁从1978年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到1981年的《沉重的翅膀》,王安忆从1980年的《雨,沙沙沙》到1983年的《墙基》,方方从1982年的《“大篷车”上》到1986年的《白梦》……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如果不仅仅将这样的文学风格的转变看做是作家创作世界的拓展,而看做是无情的现实对作家们在冥冥中的某种驱使,也许更有可以研究的空间。常常在听到当年的过来人无限深情地回味1980年代的激情和诗意时,我会想到1985年前后“现代派”的大流行,“世纪末情绪”的大传播。是的,1980年代中期虚无主义和荒诞意识的迅速崛起是有现实的无奈为基础的。有了现实的种种无奈,才有了作家们在短短几年内文学风格的迅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写于1981年—1989年间的《芸斋小说》也是孙犁老人率先放下驾轻就熟的诗意,勇敢表达出自己在“文革”中冷眼看世事的痛苦体验的可贵收获。而这样一来,他也就成了新时期最先远离诗意的作家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