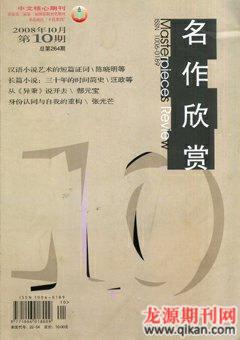汉语小说艺术的短篇证词
陈晓明 丛治辰
短篇小说历来凝聚小说艺术的精华,在机制复制文明时代,报纸副刊是文学传播的主要阵地,短篇小说一直扮演着小说艺术的主导角色。短篇后来被中篇抢过风头,那就是期刊时代崛起了。再到了长篇小说领风骚的时代,那就是印刷术、公众购买力、出版的全面市场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在今天还要加入网络电子媒体愈来愈占据文学传播的主导地位,短篇小说要生存确实是十分困难了。现今的作家看不起短篇,以为那不是大手笔所为;读者看不上短篇,以为不够过瘾。因为这样的过瘾不再是欣赏小说艺术,而是寻求更为充分的阅读快感。当今时代,我们不得不说是短篇小说衰退的时代,也必然是文学艺术性衰退的时代。当今写作长篇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没有经历过短篇小说的训练,一出手就是长篇,毫无章法可言,毫无节制的废话堆砌,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潇洒得很,但小说只能是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但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是文学走向终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文学一方面是如此繁华热闹,几乎是书写与阅读的狂欢节,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迎接它颓败的命运。在今天,作为抗拒颓败命运的一种方式,读读短篇小说或许不失为一点小伎俩;看看新时期中国短篇小说走过的历程,也不失为一种记忆。
这里所选的短篇小说,都是由国内久负盛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家定夺的,无疑都有各自极为充分的理由。只是小说实在是各有所好,要在新时期至今30年间,选出12篇小说,不是件容易的事,肯定会顾此失彼。当然,对于我们的点评来说,难度恐又更大,因为这些名家所选,有些却又未必是我们所喜爱的,但尊重既定事实又是人之常情。所以,点评有不到位之处,还请批评指教。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由林超然教授推荐,理由是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反思国民性。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论者一般归为“改革文学”,指的是关于农村联产承包制时期的农民生活状况;也有认为是“反思文学”,反思的是农民依然具有“落后”意识。其实这二者界限本就不分明,何况好的小说往往难于归类,应该说,《陈奂生上城》在这两方面都有触及。“‘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高晓声以极富动感的语言开始叙述这篇小说,小说第一节描述陈奂生上城的过程,穿插以他近年来生活的巨大改善,语言的轻快节奏更为小说添加了喜气洋洋的色彩。对比其前篇《“漏斗户”主》,陈奂生境遇的好转显然拜改革所赐,高晓声对乡村“现代化”的肯定与讴歌毋庸置疑。但同时高晓声也提出一个问题,成为全篇的关键,即日子虽然好过,但陈奂生仍觉自己在人前矮一截子,因为他不会讲话,也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好讲。“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小说由此顺理成章地转入对农民精神生活的探讨。陈奂生病倒在车站,被认得他的县委吴书记送进招待所,怎奈改革似乎仍未能使农民陈奂生的生活水平好到舍得去住5元钱的招待所。忍痛掏了5元钱之后,陈奂生的表现堪称经典:“出了5块钱呢!”很多人在陈奂生一边嘀咕一边“糟蹋”招待所房间的细节上,发掘所谓当代阿Q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更突出的,当然表现在陈奂生回村之后,将这次遭遇演义成壮举——从此之后,他终于也有了经历,有了所谓的“精神生活”。而不难看出的是,高晓声在书写这种所谓国民性的时候,其实始终有一种体贴和温情:他理解农民的感情,尤其理解,农民何以会这样。小说因此比一般改革小说更多一个追问:农村的改革深化如何解决农民的精神心理追求?农民的精神生活怎么办?陈奂生们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确是“文革”能够滋生的土壤,但这性格难道不是农村长期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吗?陈奂生身上似乎也可见阿Q的某种品性,但高晓声显然不是在严厉批判性的意义上来写陈奂生的,他还包含着对农民质朴的性格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还是反思农村依然贫困的生活给农民心理造成的困扰。
《陈奂生上城》对农民予以关注,而林斤澜创作于1981年的小说《头像》,则反思了“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损害。这篇小说由段崇轩推荐。《头像》讲述画家老麦在十年浩劫之后,屡次在全国比赛上获奖,似乎萌发了艺术上新的春天。而他的老同学梅大厦却已沉寂多年,老麦去看望这位老同学,才发现他已在默默努力下达到艺术的巅峰,只是酒在深巷无人知。梅大厦的悲剧,自然有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性格缺陷,但历数他的经历即可理解,这样的性格也是历史赋予。而梅大厦艺术上的造诣和他生活的潦倒形成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引起读者思考:新时期让一批人获得了新生,可是,还有没有像梅大厦一样埋没在历史当中的呢?林斤澜在小说的末尾似乎给出了一个希望,可是在现实当中,真的有那么多希望吗?这篇小说带有很浓的伤痕反思的意味,在文革后欢呼新时期到来的历史场景中,林斤澜先生还是颇为冷静地看到历史对一代人的耽误以及现在的忽视,林老的小说写得淡雅,叙述非常洁净,不作大悲大喜的呼喊,也不玩弄大起大落的技巧,依靠的是文字功夫,是讲述的纯粹功夫,虽然少了契诃夫的冷峻苍凉,林老如此淡雅的叙述,我总觉得有些契诃夫的味道,我以为它们是同一类的小说。
张承志的《绿夜》由傅书华教授推荐,理由是作为知青文学和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伤痕”和“反思”很快过去,张承志等一代知青出身的作家登上文坛并逐渐成为主流。对于这些知青作家来说,“文革”就是他们的青春,不管这青春究竟是被耽误了,还是仍存几分浪漫和激情。上山下乡的生活将持续作为他们创作最主要的源泉,他们一次次饱含深情地回望那里,并从那里出发展开他们对于文学和时代的思考。作为第一代红卫兵,张承志显然对“文革”和知青生活怀有格外复杂的情感,《绿夜》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感。已经回到城市八年的“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个绿色的锡林高勒草原,无法忘记那个单纯可爱的像“欢乐的小河”一样的小奥云娜,绿色的草原和纯洁的女孩,显然象征着知青一代纯净的理想主义。而与之相对,城市里的生活那么庸碌甚至肮脏。侉乙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眼中城里人的形象:卑琐粗俗,眼睛里只有钱,根本不能理解“我”的理想主义,而只会侮辱它。表弟也是一样,他是更加年轻的一代,和知青一代的“我”相比,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他没有历史,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我”那种沉重的感情,那种痴醉的寄望。这城市或许正是很多像“我”一样的知青八年之前急于回归的地方,但等到回归之后,才发现生活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城市已不是他们的故土,在精神上他们更多地和“草原”血脉相连。如果张承志止步于此,那么这篇小说不过是如梁晓声一样对于青春激情的怀想;《绿夜》的难得在于它向前多走了一步:他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锡林高勒草原。可是等待在这里的是那个纯净的精神故土么?好像是的:老奶奶还是那么慈祥,草原人还是那么好客,大草原还是那么绿……可是小奥云娜已经长大,她逐渐变成一个不再纯真的草原妇女,当她和粗俗的瘸腿会计乔洛以草原固有的方式调情时,“我”心中的理想终于破碎了:她再也不是那条“欢乐的小河”,只有“混浊的内陆河水正在干旱的大草原上无声地流”。理想主义总是美好而脆弱,而张承志的高明在于,他直面了理想主义的破裂,并在破碎之后真正认识了生活。他终于发现不但“表弟错了。侉乙己错了。他自己也错了。只有奥云娜是对的。她比谁都更早地、既不声张又不感叹地走进了生活”。如果说,在城市里的不得志和初回草原时的巨大失落,是知青一代彷徨无地的象征,那么张承志最终找到了道路,那是一种坚固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理想主义,是在活生生的未必那么完美的生活当中,依然抱有一种美好的情愫。
张承志的写作永远洋溢着太阳一样的热情,即使在理想濒临幻灭的时刻,也诗意满怀。《绿夜》像是一场诗性语言的盛宴,或壮美或秀丽的景色描写以及主观情感的抒发,几乎淹没了情节。短篇小说本来应以简洁的人物与事件为主,应是与抒情性隔绝,张承志却敢于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抒情,这也堪称是80年代的风气使然。80年代是一个抒情的年代,张承志的理想义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激情。他的理想主义即使破裂,也有一种悲壮感,他需要的就是这种破裂的悲壮感,在这里找到重新出发的全新的自我和英雄主义豪情。
韩少功的《归去来》由张光芒教授推荐,作为寻根小说的代表,它所表达的“神秘感觉”不同寻常。这篇小说很巧,与张承志《绿夜》一样,是叙述知青“回乡”的故事,与张的豪情悲壮不同,这篇小说弥漫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呈现出迥异其趣的审美意味。“我”来到一个湘西的寨子,分明是第一次来,却感到似曾相识。更奇怪的是,村民们也好像都认识“我”,他们管“我”叫“马眼镜”,而全然不顾我的本名是“黄治先”。他们和“我”拉家常,问及好多人,显然把“我”当作多年前在这里插队的知青。而“我”竟也渐渐进入村民的话语,自如地回答起他们的问题,“马眼镜”和“黄治先”重叠在一起,不分彼此。而至于“我”为什么有这样一次旅行,作者更有意隐藏,使故事失去前因后果,好像是线性历史之外的一次事故。这些含混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安知“马眼镜”不是昨日的“黄治先”,“黄治先”不是今天的“马眼镜”呢?黄治先初到土寨的迷茫,正是他丧失历史的真切感受,而当他的个人历史被唤起,当年的恩怨情仇令他感慨,令他后怕,令他愧疚,他更加不能确定,到底哪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我。是城市里的黄治先?还是那个知青马眼镜?论者常将《归去来》视为“寻根小说”,不知是因为小说中神秘的土寨风情,还是土寨人古味十足的语言风格,抑或是小说结尾那一声“妈妈”的呼唤。说“寻根”有点勉强,倒是书写一代知青对自己历史记忆颇有独到之处。韩少功试图表达的是,知青一代的记忆如同村民的记忆一样,它们是如此容易被改写,本质与真实,爱恨情仇都经不住时间的磨砺。自我与历史安在?韩少功可能想去触及自我在记忆中的相异性,这篇小说似乎包含着某种哲学意味,这是韩少功的独到之处。
王蒙的《坚硬的稀粥》由王春林推荐,理由是,它是寓言小说的代表,引起过轩然大波。王春林长期研究王蒙小说,他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80年代的文学现象往往和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因此才造成文学的轰动效应,无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还是“知青小说”、“寻根小说”,都不但是文学自身的演绎,而且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但如《坚硬的稀粥》这样,如此尖锐地指向社会现实的作品仍在少数。不得不承认,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相当大胆,不但表现在其在艺术技巧的探索上,也表现在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上。尽管当初《坚硬的稀粥》引起过种种是非,王蒙为此打官司,称“《文艺报》公然登载散布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种种谣言,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政治名誉”,但细读小说,其寓言特征是有,但说影射则难以见出实际指向。小说描述了一个家庭内部的“改革”:爷爷主事日久,接受了新思想,希望就吃饭一事进行改革,然而不管民主集中,还是内阁负责,不管保守,还是西化,终究是让人不满意。其实此类寓言小说,仅作文本与现实的简单对应,其实并无意思。更加动人的乃在作家于此改革过程中对人物心态的挖掘:爷爷让权给爸爸,爸爸仍然战战兢兢,每事必问;徐姐掌权时,人人不服权威,“下意识的不敬开始演变出上意识的不满意”。王蒙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会做简单的比喻对应,他恰是在这些细微处,揭示出改革之路步履蹒跚的根源。王蒙的小说总是洋溢着幽默,语言老辣犀利,这篇小说尤甚。作为一篇短篇小说,就写一件事,写得如此之透,之有意味,这也应看作短篇小说的艺术所能达到的境地。王蒙始终未能忘怀文学对现实承担的责任,以他当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装聋作哑,但他没有,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不少人评论王蒙如何如何圆滑,我以为,这些人如处在王蒙位置,不知圆滑成什么样。王蒙在80年代那些非常时刻,还是有他的坚持,这并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王蒙先生的《坚硬的稀粥》是我刊推荐的初始篇目——编者)
余华的《鲜血梅花》由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彭宏博士推荐。其理由是“反武侠小说,真先锋意识”。文学与现实/历史的蜜月期到先锋派这里似乎走到了尽头,尽管已有不少研究者在先锋派创作中发现其意识形态性,但不可否认,与此前的小说相比,先锋派小说依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余华的《鲜血梅花》发表于1989年,此时先锋派似乎略策沉寂,却也同时像一个幽灵一样,弥漫于其后的文学创作。《鲜血梅花》不能算是先锋派最出色的作品,但深深地烙着先锋派的印记,极具代表性,同时也表现出先锋派自身的尴尬。对于叙述本身的关注和雕琢,对于小说结构的刻意经营,对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调度,以及已被论者常说到的——对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体的戏仿和颠覆,在这里表现出其先锋小说的血统。但更令人注目的,倒在小说委曲表达的那种剥离历史之后的茫然无措。这是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因此,“父亲”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但是在传统的此类故事当中,父亲虽不在却始终如幽灵般贯穿整个小说,复仇的过程,就是寻找父亲和重新确立儿子的主体身份的过程。但在《鲜血梅花》当中,父亲只是一个符号,关于他的一切都消弭在风中,阮海阔的孱弱明确暗示了父亲的彻底缺席:“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为尘土,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父亲是什么?他是权威,是血脉的牵连,是历史的重量。背对着被大火烧成灰烬的故家,阮海阔的茫然就好像是文学丧失历史之后的茫然,因此阮海阔的游历和寻找盲无目的,像一片树叶一样没有分量和方向。他不断与自己的命运遭遇,又不断地错过,直到最后,复仇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连想象的目标都丧失之后,阮海阔的虚弱感,是否正是余华等先锋作家在9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内心的虚弱呢?先锋派如何继续,文学如何继续,需要有一个新的起点。这篇小说写出一个无法继承使命的儿子形象,如此孤独无助,却英雄主义不再,不只是因为勇敢不再,而是历史总是出错,命运成了不可抗拒的劫数。因为小说发表的特殊时期,这篇小说意外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寓言性意义。余华的这篇具有先锋性的短篇小说,显然不是在短篇小说的惯常的技巧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叙述感觉、心理刻画上下功夫。小说表现的那种荒芜感和虚无感,其中的寓言与哲学意味,是传统短篇难以承载的。
铁凝的《秀色》由海南师大文学院毕光明教授推荐,理由是女性文学代表作,表达了“底层关怀”。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当中,女性作家显然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容忽视。铁凝即是其中的代表,尽管铁凝并不刻意甚至并不十分认同把她冠以女性主义作家,但她的创作一向细腻富有诗意,饱含女性特有的敏感。她在1997年发表《秀色》,险些被有些批评家指为“粗俗”。小说讲述一个太行山深处名叫“秀色”的山村,和它美丽的名字很不协调的是,这个村子以缺水著名。每家每户吃的水,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背来,水在这里,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家家都有阔大的桦木水橱,木桶安放进水橱,水橱用铁锁锁住。三寸长的铁钥匙挂在一家之主的腰间,显示着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为了吃水,村里人请打井队来,为了让打井队坚持在秀色村的穷山沟里待下去,这里的女人用自己的身体来做挽留。于是坊间流传着秀色村的女人那个“热哟”……给男人充满了想象空间。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李技术来打井,女子们也要去献身,但被婉言谢绝,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没有女子们的献身,李技术坚持打井,虽然他几乎失去信心,但最终还是打出了井水。这篇小说构思颇为精巧,题目的秀色与村庄的贫瘠鲜明反差,直到女性英勇站出来,“秀色”才来点睛之笔。这或许就是典型的短篇小说构思。有一些暗扣,在小说的叙事中会一点一点或突然间解开。像《秀色》这样的小说,虽然写实,却更让人体味到一种情境。这里的女性作出的“牺牲”更像是奉献,被铁凝有意写得轻盈,生命越过道德伦理界线所焕发出的悲壮与绚丽,以及追求好的生活的执著信念。今天看来,这样的描写居然也触及到“道德”的底线,可见那时的道德多么脆弱。铁凝在描写女性的本真生活时,特别是乡土女人率性而行时非常生动,那就是活生生的生活,在悲苦中总是透示出生命之美好。铁凝但凡写到这种生活时,确实有一种得心应手,天然去雕饰的味道。后来出现的李技术这样一个凭着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良心做事的人,反倒与那种自然本性不太协调,突然冒出的政治,略显生硬。(《秀色》是我刊推荐的初始篇目——编者)
阎连科是一位相当具有特色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最现代的小说技巧和最真切的中国经验结合在一起,这再次证明,先锋派退潮之后,对于小说美学的探索并未终止,而是化入小说文本的肌理之内。在《日光流年》《受活》等杰出的作品里,都能看到典型的阎连科的叙事:语言汪洋恣肆,仿佛修辞的狂欢;想象荒诞离奇,却又稳稳扎根历史和现实。即使在《黑猪毛 白猪毛》这样的短篇当中,依然能够看到类似的努力:镇长开车撞了人,要找人顶罪。这样一件坐牢的差事,竟引来一批人争抢。刘根宝费尽周折,终于得到这一“殊荣”,于是村里人人巴结,刘家更当作莫大的喜事。谁料被撞的人家却不追究了,“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做镇长的干儿就完啦”。这样的情节显然超越一般读者的常规思维,村民们送刘根宝坐牢,有如欢送英雄一般的场景,更是极尽荒诞。但在镇长村长足以一手遮天的基层农村,这种逻辑似乎又不难理解。阎连科来自农村,始终保持着对农村底层社会的关注,并对他们有着深刻的理解,这荒诞的想象背后,是中国底层真实的痛楚。近年来,所谓“底层文学”成为一个话题,其实我们的文学从来就不乏关注底层的传统。阎连科写作《黑猪毛 白猪毛》的2002年,底层文学尚不风行,但此篇显然可算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了。阎连科的小说下手都狠,他的小说总是准备好猛料关键时就抖将出来,让人看到生活的绝境,以及绝境中的荒诞。对绝境的超越就是荒诞,这就是绝境中的绝境了。
孙犁的《冯前》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推荐。作为纪实之作,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中国的现代小说其实是从向西方学习开端,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创作更是深受西方影响,以“寻根小说”和“先锋派”最为显著。但也有一些老作家,重新挖掘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资源,其作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美学趣味。孙犁即是其中一例。《冯前》虽然完成于1987年4月,但从1981年孙犁就开始创作一系列短篇小说,后来结集成为《芸斋小说》出版。早期以诗化小说著称的孙犁,经历“浩劫”之后大概也深深体会到人间并不全像诗一样美好,在芸斋系列小说当中对“文革”的众生相进行了描画,可以说,这些小说是这位老作家面对“文革”的一种方式,《冯前》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一篇。冯前是“我”相处时间最长的朋友,也是“我”所在的报社的总编,他有些官僚气,但人并不坏,如果没有“文革”,可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文革”像一个放大镜一样,令冯前人格中见风转舵、恃强凌弱的一面暴露无遗,令人唏嘘。而其实,从“我”对冯前的猜疑来看,难道“我”人性中的弱点就没有因为特殊的年代和情势而有所暴露么?孙犁看似平淡的叙述,其实拷问的是每一个人的人性。同样是回顾和反思“文革”,孙犁的这篇作品和伤痕文学撕裂般的痛楚迥异其趣,他不简单地质问时代,而是审视自己,因此少了冲动的怨愤,而有一种内敛的力度。他好像真的从痛苦超脱出来,洗尽所有火气,走向了淡泊宁静。情绪的克制呈现在修辞当中,通篇小说没有抒情,议论都非常谨慎,点到为止,而基本纯用白描的办法,反而别有韵味。从文体上看,《芸斋小说》名为“小说”,但孙犁自己也认为,称为“小品”可能更合适一些 。中国古代所谓小品,指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其中既可容许虚构,也可纪实。因此《冯前》其实很难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毋宁看作跨文体或模糊文体的尝试。有论者索性将此类作品称为笔记体小说,这或许是比较多地在承继中国传统写作所探寻的汉语小说方式。在这之后,汪曾祺、阿城、贾平凹、韩少功等都有类似的创作,而《芸斋小说》可算开先河之作。
汪曾祺的《异秉》由郜元宝教授推荐。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淫,而深得美学三昧的作家,自然是汪曾祺莫属。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老辈作家,本身传统修养厚实,他们也自然把传统修养转化到小说叙事中。我们现在盛行的小说,都是典型的西方现代小说,这几位老先生的小说,都可说是融合进中国传统元素的作品,这肯定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异秉》或可见一斑。《异秉》有40年代和80年代两个版本,对比之下,尤可见出劫波度尽之后,汪老无论在人生态度还是文学主张上,都归于淡泊,臻于化境。40年代的汪曾祺更多受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把短篇小说看作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方式,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而1988年,他认为,“小说应该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因此,与40年代《异秉》在情节安排和时空控制上的严谨相比,80年代的改稿在时空上更加自由,情节上似乎也更加散漫了。但是人生的阅历和见识,艺术上的造诣,就在散漫的叙述当中流露出来,结构看似随意,实际上放而不散。在对市井细民生活的描述里,读者自能感受到如水墨画般的韵味;而读到结尾,陈相公和陶先生争着上厕所,谁不会莞尔一笑呢?如这样堪称神品的小说,除了欣赏,任何多余的评论都会显得愚蠢吧?
以有限的几部短篇小说勾勒新时期以来的短篇小说发展轨迹,显然很不现实。30年的文学纷繁复杂,各种潮流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论声此起彼伏,大多是小说艺术之外的声音。探讨当代短篇小说艺术这种问题似乎已经变得很陈腐,很不重要,很不主流。我们试图从这几篇小说“管中窥豹”,如何可见全景呢?这些篇目自成一格,只是显现了作者的个人风格趣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作品都写得相当认真,都有着独特的艺术匠心。它们或者从现实主义传统中走来,或者与西方小说相通,或者与中国传统接脉,建构着八九十年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它们是不会被埋没的,它们会证明着汉语小说的顽强不屈。
作者陈晓明系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丛治辰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