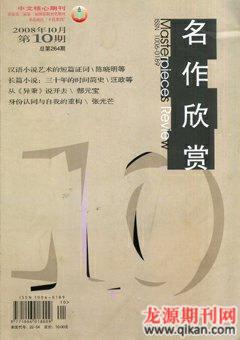黑猪毛 白猪毛
阎连科
春天本该是春天的味道,如花的草的,蓝蓝浅浅的,悠忽地飘散。或者,绿绿的,浓浓的,郁香儿扑鼻,似着深巷里的酒呢。可是,落日时分,吴家坡人却闻到一股血味,红红淋淋,腥浓着,从梁道上飘散下来,紫褐色,一团一团,像一片春日绿林里夹裹着几颗秋季的柿树哩。谁说,你们闻,啥味儿?把夜饭端到村口饭场吃着的人们,便都在半空凝住手中的饭碗,抬起头,吸着鼻子,也就一股脑儿,闻到了那股血味。
——李屠户家里又杀猪了。
静一阵,有人这样说了一句,人们就又开始吃着喝着。谁都知道,明儿是三月底,本月的最后一个集日,屠户家里当然是要杀猪赶集呢。不过,往常的集日,李屠户都是起早宰杀,日出上路,当天到镇上卖售新鲜。为啥今儿要在黄昏宰杀?为啥今儿的血味要比往日刺鼻?村人们都没有去过多思想。仲春到了,小麦从冬眠中睡醒过来,哗哗啦啦长着,草呢,也相跟着疯生疯长。要锄地,要施肥,田头有水的还要灌浇,各家都忙得如蚂蚁搬家,谁能过多地顾上谁哩。
饭场是在村头。李屠户家住在梁上,住在梁上大道的旁边,旁边是一个丁字路口。既然已经弃田从商,终归与梁道靠近好些;虽然是屠宰生意,也要图求一个运输便利。图求邻村有了红白喜事,寻上门来让替宰一头一条,也都有着许多便利。为着便利,为着兴隆,李屠户也就从村落搬到梁上去了。盖了两层瓦楼,围了一所砖院,楼下屠宰,兼卖一些杂货、吃食、炒菜;楼上住人,又辟出两间做了客房。路过的行人,腿脚累了,不想走了,便坐在楼下吃些杂碎下酒,喝得摇摇摆摆上楼。来天日出,酒醒了,乏困去了,付了店钱、饭钱上路。
别看那两间客房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十五瓦的灯泡,停电了是半根蜡烛,可县委书记还在那房里睡过一夜。有人说,是车抛锚了,书记不得不在那儿屈宿一觉。可李屠户说,说那话的人是在放屁,也不想想,司机敢让书记的车抛锚吗?说县委赵书记之所以要在他那儿屈尊一夜,就是为了到百姓家里问问致富景况,和他李屠户扯拉扯拉。无论如何,县委赵书记是在那儿睡了一夜。这一睡,李家的生意竞相跟着旺盛起来。两间客房的东屋,桌、床、被褥、脸盆、拖鞋,都是赵书记用过的纪念物,妥善擦洗保存,又仍给客人用着,于是,那间客房从每夜十元的价费涨到了十五元。行人也都长有凡贱之心,价格涨了,因为县委书记住过,也都偏要到那屋里去睡。有跑长途运输的司机,竟连三赶四,踩着油门不松,也就是为了去那东屋睡上一觉。当然,李屠户家里的杂碎肉香,杜康酒里又不对水,也是吴家坡人有目共睹的实情。现今,李屠户家生发出啥惊天的事情,村人们也都不会惊乍,连县委书记都果真在那睡过,那还会有啥事情在那梁道边上不会发生哩。集日到了,把本该下夜更时屠宰的猪挪移到头天黄昏起刀,让春日夕阳里有一股血腥味儿,这又算啥稀罕事儿呢?杀了,宰了,把两扇猪肉展在屠案上,淋上清水,用塑料薄膜盖上,来日去卖又有谁能看出它不是新鲜的猪肉呢?
人们依然在饭场上吃饭,依然扯西拉东。有人饭碗空了,起身回去盛着;有人不想回去,就差儿娃回去一趟,儿娃哩,又刚刚端着饭碗从家里出来,便对父母哼哼哈哈,他们便一脸挂了不悦,骂着儿娃的不孝,说养你长大,连让回家盛碗汤饭你都懒得起动,早知这样,倒不如不生你还好。做儿娃的觉得委屈,因为并没说不去,只是因了犹豫,父母就当众破口骂了,于是便顶撞起来,说谁让你生我了?谁让你生我了?父亲或母亲被问得哑言,就从坐着的屁股下面抽出鞋来,一下掷了过去,弄得饭场上飘满鞋灰,许多人赶快把饭碗护在胸下。就在这饭场上闹得尘土飞扬的时候,饭场外有了一声断喝,叫着说吵啥哩?有啥好吵哩?父母让你们儿娃回家盛一碗汤饭错了吗?
饭场上哐的一下安静了。做儿娃的感着理屈,不再说啥了。
村人们目沿着断喝,都朝村口通往梁道的方向望过去,原来是屠户李星从梁上回村了。
刘根宝从饭场上回到家里,就像从宽展自由的田野进了考场,怯怯的,有些不安。爹已经吃过饭了,正在院里抽烟,明明灭灭,在暮黑中闪烁着光色。娘正在灶房洗整,锅碗相撞的声音淹在洗涮的水里,听起来清脆潮润。根宝一脚踏进灶房,把还有半碗饭的瓷碗推在灶台角上,想说啥,却只是望了望娘,便又勾着头从灶房走了出来。
他蹲在了爹的面前。
爹说,有事?
他说,没啥事。
爹说,有事你就说吧。
他说,爹,我想去蹲监。
做爹的愣了一下。从猛一吸亮的烟光中,能看见老人的脸上有些僵硬,表情哩,像一块原本柔和的杂色面儿,忽然变成了生硬的石头面儿。他把烟袋从嘴里拔下,盯着儿子,像盯着素昧平生来问路的陌生人一样。
爹说,根宝,你说啥儿?
儿子根宝就又瞅了一眼父亲。因着夜色,看不清父亲这时脸上的惊异有多厚多重,多少斤两,只是看见有一团漆黑,像树桩样竖在那儿,僵在那儿。因为看不清楚,他也就索性不再看了,脱掉一只鞋子,坐在父亲面前,两只胳膊架在膝上,双手相互抠着,像剥着啥豆子,没有立马回答爹的问话。
爹又问,你刚才说啥呀?根宝。
根宝说,爹,我想和你打个商量,如果你和娘同意,我想替人去住几天监狱。
爹吼着说,妈的,疯了?
根宝把头勾得更为低些,说,爹,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嘛。
爹顿一会儿,又问,替谁?
根宝说,替镇长。
爹抬起了头,替谁呀?
根宝说,替镇长。
爹笑了,冷机地道,镇长用你去替?
根宝说,刚刚在饭场,李屠户说了,说今儿落日时候,镇长开着小车从梁上走过,撞死了一个年轻人哩,张寨村的,二十余岁。说镇长撞死了人镇长应该负责呢;可镇长是镇长,谁能让镇长负责哦,于是哟,就得有人去县交通队替着镇长认个错,说人是我撞的,是我在李屠户家酒喝多了,开着拖拉机出门撞上的。后边的事,就啥甭管了,镇长都有安排哩。说事情的尾末已经搞清,就是赔张寨的死人家里一些钱。钱当然是由镇长支出的。然后,然后哩,就是谁说是谁撞死了人,谁就到公安局的班房里宿上十天半个月。
月亮已经升了上来。吴家坡在月光中静得如没有村落一样,能清晰地听见村街上走动的脚步声,踢里啦踢踏,由西往东,渐次地远了。消失着到了李屠户家那儿了。娘好像把根宝说的缘缘由由全都听得十分明了了,她没有立马接话儿,不知从哪儿端出一小筐儿花生,端过一张凳子,把凳子放在男人和儿娃中间,把那一筐儿花生放在凳子上边。而后,她就随地坐在花生筐前,望望儿娃,又瞅瞅男人,长长地叹了口气,走进了他们父子深深的沉默内。
说起来,根宝已经二十九岁,二十九岁还没有找到媳妇成家,这在吴家坡也仅是刘家一户。缘由呢?不光是因为家穷,现如今不是哩,是在极早的年月里,各家都已盖起了瓦屋,只他们刘家还住着草房院落;再者,还因为根宝的怯弱老实,连自家田里的庄稼被畜牲啃了,举起了铁锨,联想到畜牲也有着主人,竟就不敢落将下去,只能将铁锨缓慢地收回。这样的人,窝囊哩,谁肯嫁哟。照说,早先时候,有过几门亲事,女方都是到家里看看,二话不说,也就一一荒芜掉了,无花无果。待转眼到了今日的年龄,没想到竟连二婚的女人也难碰到。半年前,有亲戚介绍了一个寡妇过来婚面,先不说对方长得丑俊,也才二十六岁,竟带着两个孩娃。根宝原是不同意这门婚配,可亲戚却说,同不同意,见面了再说。于是也就见了,想不到她一见面劈头便问,你就弟兄一个?
他说,我是独子。
她说,同姓家族村里多吗?
他说,村里就我们一家刘姓。
她说,有没有亲戚是村里乡里干部?
他摇了一下头儿。
她便生着风声,一下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愤愤地说,那你让我跑十几里路来和你见面干啥?媒人没和你说我原来的男人是因为和人争水浇地,争人家不过,被人打了一顿,回家上吊死了?没说我不图钱不图财,就图嫁个有势力的男人,不说欺负别人,至少也不受人欺负。女人这样说着,就转身从根宝家里出来,走出屋门,到院落里左右看看,又猛地回身盯着根宝,说今天正好是集日,我跑十二三里路来和你谋婚,来让你看我,耽误我整整一天工夫。这一天工夫,我到镇上卖菜卖瓜,卖啥都能挣上七八十块钱。可是今儿,是你把我误了。我不要你赔我七八十块钱,可你总得赔我五十块钱吧?
根宝怔着问,你说啥儿?
女人说,你误我一天工夫,该赔我五十块钱哩。
根宝低声咬牙,说,你咋能这样不要脸哩?
女人说,我是不要脸,要么你打我一顿我走,要么你赔我五十块钱我走;你要不打我赔我,我就在这院里叫唤,说你一见我就摸我拉我。
没有奈何,根宝只好返身回屋取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塞到她的手里说,走吧你,以后你再也别从我们吴家坡的村头走过。
女人接过了那钱,看看说,你要敢动手打我一个耳光,我就嫁给你。
根宝说,走呀,钱给你了,你走呀。
女人说,你要敢对我又踢又打,我把我的两个娃儿送给别人嫁给你。
根宝说,你有病哩,你神经有病了,去县医院看看病嘛。
女人把那五十块钱朝根宝面前一扔,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没有腰骨的男人,谁嫁给你,谁一辈子保准受人欺负不尽呢。
实在说,没人欺负根宝一家人,可就是因为他家单门独院,没有家族,没有亲戚,竟就让根宝娶不上一门媳妇来。二十九岁了,一转眼就是三十岁,就是人的一半生命了。将近三十岁还没有成家立业,这不光让根宝在村里做人抬不起头,也让父母深怀着一层内疚哩,永远觉得对不住了儿娃呢。
根宝爹又吸了一袋烟,再装上,没有点,放在脚边,不知为啥就抓了一把花生剥起来。他剥着花生,却不吃,借着月色,看看面前勾头坐在鞋上的儿娃,像一团包袱软软地浮在地上;看看那说要翻盖却总也缺钱翻盖的草屋,矮矮的,塌塌的,房坡上还有两个欲塌欲陷的深草坑,在月色里像被人打开的墓穴。还有那没有门窗的灶房,灶房门口破了的水缸,这些都被月光照得亮白清楚。身边的那个猪圈,泥墙,框门,石槽,倒是结实完整,可不知因了啥呢,总不能养成猪。喂猪猪死,养羊羊灭,后来把它做了鸡圈,鸡们倒都生长得壮实,可是,可是呢,母鸡们都是三天、五天才生一个鸡蛋,哪怕是夏天的生蛋旺季,也没有一只鸡两天生上一蛋的,更不消说如别户人家一样,一天一蛋,甚或一只鸡一天生两蛋或两天生三蛋。这就是刘家的日子。根宝爹像看透了这样的日子一样,把目光从月光中抽了回来,吃了手里的花生,说跑油了,不香。老伴说吃吧,这也是宝他舅今儿路过梁上捎来的。根宝爹就又抓了一把花生,在手里剥得哗里哗啦,说都吃呀,根宝。
根宝说,我不吃。
爹说,你咋知道替镇长顶罪至多是到监狱住上十天半个月?
根宝说,李屠户说的。
爹问,李屠户听谁说的?
根宝说,他啥儿不知道?镇长就是在他门前撞死了人,县委书记都在他家睡过哩。
娘问,替人家住监,住完了咋办?
爹说,歇歇嘴吧,女人家哩。住完了咋办?你想咋办就咋办。谁让他是镇长,谁让他让我们孩娃去顶监。
然后,爹就回过头来,望着儿娃说,根宝,你真的想去就去吧,去跟李屠户说一声,说你愿意替镇长去蹲监。说记住,李屠户叫李星,你就叫他李星叔,千万别当面还屠户、屠户地叫。
这时候,月亮升到当头了,院落里愈发明亮着,连地上爬着的蛐蛐欢叫时张扬的翅膀都闪着银白白的光。根宝从地上站起出门时,娘从后边抓了一把花生追上他,说你吃着去吧,没跑油,还香哩。根宝把娘的手推到一边,说我不吃,也就出门去了,和出行上路一样,没有回头。可没有回头,他听见身后剥花生的声音,在月色里像谁在水里淘洗啥儿般,淋淋哗哗,脆亮亮的,还是有几分让人留恋的亲切呢。
李屠户家里忙哟。院落里扯加了两个二百瓦的灯泡,把清明清明的月亮挤逼得没了踪迹。不知远处的一家矿上要贺庆啥,冷不丁,来人让他连夜赶杀几头肥猪,加之明儿正集日,又不能慢待了在集市上总去他的挂架上割肉的老主顾,于是,李屠户除了原来的屠案,又摘下门板,新架了一副屠板。自己宰,还又从外村找了两个小伙子帮衬着。每帮他宰一头猪,他给人家十块工时费。
院落里满是集合着的人,有矿上的工人,有村里看热闹的孩娃,还有连夜把生猪拉到李屠户家等着他过秤买猪的邻村庄户。根宝从村里出来,一听到屠案上红血淋淋的尖叫,身上抖了一下,像冷一样,可他很快就把自己控制住了,不再抖了。说到底,是杀猪,又不是杀人。踏进李屠户家那两扇能开进汽车的院落大门时,已经有两扇猪肉挂在了棚架下,赤背的李屠户正舀着清水往扇肉上浇洗,一瓢一瓢,泼上去,淋下来,红艳艳的血水流过一片水泥地从一条水沟流到李家房后了。一世界都是生血的腥鲜味。帮衬的那两个小伙子,一个在院落角上正烧着一口大锅的开水烫猪毛,一个正在一个屠架上用一个铁片刮着剩猪毛。猪毛味有些腥臭,像火烤了兽皮一样怪诞难闻。李屠户家一年四季都有这样的味。根宝不知道为啥在这样的气味里,县委书记会在这儿住一夜。可县委书记是真的住了一夜哩。迎面楼上二楼靠南的两间客房,东屋门口清清白白挂了一个招牌,上写着:县委赵书记曾在此住宿。借着灯光,根宝看那招牌时,他看见西客房的门口也新挂了一个招牌,上写着:县里马县长曾在此住宿。根宝有些糊涂,他不知道县长何时也在此住过,可他想那是一定住过的,没住过李屠户不会挂那么一个招牌。
看看招牌,根宝从人缝挤到了李屠户的身后,他等李屠户把一扇猪肉淋净了,轻声叫了一声李叔。
李屠户没有回头,他用手抹掉肩上的血水珠,用胳膊擦掉额门上的汗,到另一扇红血猪肉下边,又一瓢瓢舀水浇起来。虽然没有回头,他却听到了有人叫他。他舀着清水说,是根宝吧?
根宝说,哎,是我,李叔。
李屠户把一瓢水泼到那扇猪肚里道——
是想替一下镇长顶罪吧?多好的机会,别人烧香都求不到。
血水溅到了根宝脸上,他朝后退了一步——
跟我爹商量过了,我愿意。
李屠户又舀一瓢清水浇上去——
不是你愿意就能去了的。先到屋里等着吧。
到了李屠户家平常客人吃饭的那一间餐厅里,根宝才看见那儿已经坐了三个村人了。一个是村西的吴柱子,四十来岁,媳妇领着孩娃和人私奔了,就在邻村一个村干部的弟弟家窝藏着,死活不回来,他就只好独自过着日子了;另一个是村南的赵瘤子,日子原本鼓鼓胀胀不错哩,可烧的砖窑塌了,人便瘸了,日子也就塌陷了,眼下还欠着信用社一大笔贷款的债。还有一个,是村里的李庆,在镇上有生意,家里还买有一辆嘎斯汽车跑运输。根宝知道柱子、瘸子是想和自己一样,图求去替镇长住几天监,一个想请镇长帮着把自家媳妇要回来;另一个,寄望帮了镇长,也许信用社的贷款便不消再还了。他不知道李庆谋图三二四五啥哩,竟也端端地和瘸子、柱子围在那一张饭桌前。于是,待根宝走进来,他们都望着根宝时,根宝把目光落在了小他一岁的李庆身上。
李庆像抢了别人的东西一样,不好意思地把头勾下去,说我弟今年就师范毕业了,想请镇长安排他回到镇上教书哩。
柱子冷了一眼李庆说,你好了还想好。
李庆把头勾得更低了,脸红得如门外地上的血。
这当地,瘸子也包着李庆的脸,说,你走吧,让我们和根宝争这机会还差不多。
李庆没有走,又抬起头涎涎地笑了笑。
根宝坐在了那张空凳上。这是一张四方桌,先前都叫八仙桌,现在学着城里人的腔调就都叫它餐桌了。屋子也叫餐厅了。餐厅也就十几平方米大,摆了粮、面、油和七七八八的一些杂货物,在外面空着的地方摆了这张餐桌。因为不是掏钱吃餐饭,桌上有个铝茶壶,但没有人会来给他们倒上水。桌子的上方是灯泡,苍蝇和小蛾在灯泡周围舞蹈着,舞累了,蛾子竟敢落在灯泡上歇脚儿,而苍蝇就只敢落在他们身上和那油腻的桌面上喘着粗气儿。
屋外又有了一阵猪叫声,粗厉而骇人,像山外火车道上的汽笛叫,只是比那汽笛短促些,也比那汽笛混杂些。夹杂有猪的喘息和人的乱汪汪的声音。这样过了一阵,便突然安静了。不消说是利刃从猪的脖下捅进脏腑了。剩下的就是李屠户指挥着说把这头抬去煺毛、把那头挂起来开膛的指令声,还有人们这条肥、那头瘦的议论声。屋子里有些热。忙着挣钱的李屠户,顾不上进来指着哪个人说令一句,喂,你去替镇长顶个罪,再指着剩下的,说你们三个就算了那样的话。也许,李屠户并不知该把这样一件好事留给谁,所以他才只顾杀猪,不管屋里的根宝、柱子、瘸子和李庆。屠户的媳妇和孩娃们都在楼上看电视,从电视机中传来的武打声像从房顶落下的砖头和瓦片。根宝抬头朝天花板上看了看,其余三个人也都跟着抬头看了看。
李庆说,半夜了。
柱子说,着急了你先走。
李庆说,我不急,等到天亮我也等。
瘸子看看李庆,又扭头盯着根宝,说,兄弟,其实你犯不上和我们一样儿,没成家,又有文化,真替镇长蹲了监,名声坏了,以后还咋儿成家哩?
根宝想说啥,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正急时,李庆倒替他回答了。李庆说,真替上镇长了,也就成家了。根宝有些感激地望了望李庆,李庆又朝他点了一下头。因为李庆和屠户是本家,他在李屠户家里便显得自由些,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还到楼上看了一会电视,回来时还顺脚到李屠户那儿催了一下他李叔,说让李叔赶快定一下由谁明儿去顶替镇长的罪。可等他兜了一大圈儿回来时,他却进门说,李叔忙,他让我们四个自个儿选定一个去替镇长的人。自个儿选?选谁呢?当然无法选,谁也不会同意谁。于是哩,四个人就又相互望一望,看谁脸上都没有退让的意思儿,就各自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时间如牛蹄一样一踢一踏走过去。夜已经深得如一眼干枯无底的井。他们就这么干干坐熬着,直到楼上的电视不响了,李屠户一连杀了五头猪,柱子和瘸子们都趴在桌子沿边睡一觉儿,根宝以为李屠户压根儿把他们几个忘记了,他想去问李屠户一声到底让不让他去顶镇长的罪,叫了他就去,不叫了他也死心回家睡觉时,忽然有人砰砰砰地敲响了餐厅的门。
他们都惊醒过来把目光旋到门口上。
叫醒他们的不是李屠户,而是帮李屠户杀猪的一个小伙子。他是用杀猪的刀把敲的门,刀刃上的鲜猪血被震得如软豆腐一样掉在门口脚地上。看几个人都醒了,他把手里备好的四个纸团扔到了桌子上,说下夜一时了,李叔说让你们别等了,这是四个阄儿,其中有一个阄儿里包了一根黑猪毛,另外三个都是白猪毛,你们谁抓了黑猪毛谁就去做镇长的恩人,谁抓住了白猪毛你们谁就没有当镇长恩人的命。然后,说完了,他就站在灯光下,看着那四个阄,也看着那四个人。
忽然间这四个人都没有瞌睡了。原来谁去替镇长顶罪做恩人那么大的一件事情都包在那四个阄儿里。阄儿纸是一个一分为四的烟盒纸,红红花花的,有些喜庆吉祥色,可毕竟四个里边有三个包的都是白猪毛。把目光收回来盯在桌面的四个阄儿上,他们各自把眼睁得又亮又大,可就是没人先自起手去抓一个阄儿。
小伙子说,抓吧,抓完就睡了。你们还有抓阄儿的命,我和李叔商量了一夜想去蹲蹲监,李叔说我不是吴家坡的人,不光不让去,还连阄儿都不让我抓哩。
李庆望着小伙子说,你这不是讥弄我们几个吧?
小伙子说,有半点讥弄,我是你们四个的孙娃儿。说我想去镇政府那儿租几间房子做门市,可死活轮不到咱乡下人的手,你说我要能替镇长去住半月监,我在镇上还有啥儿生意做不成?我还用见了收税的像孙子一样四处乱跑吗?说你们快抓呀,你们一抓我就去杀猪了。
李庆无言了,便首先从桌上捏了一个纸阄儿。
于是都捏了。
根宝把桌上最后剩的一个捏到了手。他准备打开时,因为手有些抖,出了一手汗,也就打开得慢了些,所以还未及他把阄儿全打开,便听到柱子扑哧一声笑了笑,说我这儿是根黑猪毛,合该我媳妇、孩娃还回到我家里。说完他就把阄纸摆到桌子的正中间,大家一看,也果真是根黑猪毛,一寸长,发着光。麦芒一样尖尖刺刺地躺在阄纸里,而且还从那黑猪毛上发出一丝腥臭淡淡的膻味儿。
小伙子立在门口说,好事有主了,你去当镇长的恩人,大家都回家睡去吧。
瘤子看着手里的一根白猪毛,说他妈的,还不如早点回家睡觉哩。就把阄儿和猪毛扔掉了。
李庆看了一眼桌上的黑猪毛,没说话就先自离开走掉了,出门时他朝门框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于是都走了。根宝从李屠户家走出来,又回身望了一眼写着县长、书记在此宿过的招牌,想去和李屠户打声招呼,可看他正忙着在取一头猪的五花内脏,且又是背对着院门这边儿,便不言声儿从李屠户家大门出来了。
外边梁道上有凉爽爽的风。远处田里麦苗的青气一下迎面飘过来,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身上连一点瞌睡也没了。
回到家里时,爹娘居然都不在。根宝一进院子里,可又闻到了一院油馍味。再一看屋里正门的一张凳子上,放着一个蓝包袱。他先到屋里把那包袱打开来,果然觉和他心里猜想的一模一样,是娘为他明儿出门去做镇长的恩人准备的衣物、行李啥儿的,裤子、衬衣、鞋袜,怕他半月回不来,连夏天的汗衫和短裤都替他准备到包裹里边了。而且,包裹里还有一双千层底儿布鞋和三双新从哪儿买的解放鞋。他不知道娘为啥要给他准备那么多的鞋,不要说他已经不能去替镇长顶罪了,就是命中有喜真去了,十天、二十天也就回来了,哪能用上那么多的鞋子哩。
夜已深得没有底了,除了从梁上李屠户家门或传来的猪叫声,村子里连月光游移的声响都没了。包裹里新鞋老衣那半腐的肥皂香味和鞋底上的粮面糨糊的甘气,在屋子里散散淡淡地飘。根宝在那包裹前站了一会儿,又从屋里出来,到灶房的案前立着不动了。娘已经把他出门前的干粮全都备好了。油烙馍,葱花和香油的味道像流水一样,从案桌上哗哗淌到脚地上。每个油馍都烙得和鏊子一样大,然后十字儿切开,一圆变四页,统共十二页油烙馍叠在案面桌的正中央。
望着油烙馍,根宝竟哭了。
从灶房出来,他又立在院落里,朝柱子家住的村西那地久远地照望着,便看见睡了的吴家坡村,一片新房瓦屋,在月光中一律都是蓝莹莹的光,只有他家这方院落,沉湮在高大的瓦屋下,像一大片旺草地上的一簇干死的草。根宝的心里有些哀,他把目光收回来,刚好看见东邻的嫂子半夜三更中,竟风风火火地卷进了大门里,说根宝兄弟呀,我在那边听到你这边的响动了。说急死人了呢,你爹你娘都在我家里。说合着你命好,我表妹离婚了,今儿来看我,一听说你要去替镇长蹲监狱,再一说你还没结婚,她就同意了。说我俩在你家等你到半夜,你没回来,我们走了你就回来了。说你爹、你娘把她送回到我家和我表妹有说不完的活。说你赶快到我家和我表妹见见吧,人长得那个水嫩和没结过婚的闺女一模一样。说走呀根宝,还不赶快去?你愣着干啥哩?
东邻的嫂子是四十里外的镇上人,细苗灵巧,人儿好看,因为看上她男人会做生意就屈驾从镇上嫁到了吴家坡。她读过书,会说话,能把不好看的衣裳穿出样子来。她知道她有吴家坡人没有的好资质,所以对谁说话都没有商量的味,都像小学的老师教着学生孩娃的啥儿样。月亮已经走移到了山梁那边,朦胧像灰布一样罩在院落里。根宝看不清邻居嫂子的脸,只看见她一连声地说着时,舞动的双手像风中摇摆着的杨柳枝。这时候,这个深夜的当地里,她说完了就拉着他的手要往她的家里去,他便感到她手上的细软温热像棉花一样裹着他的手指头。他闻到了她头发上的女人味,像在酷冷的冬天忽然飘来了一股夏天的麦香味,身上燥热的激动一下都马队般奔到了他头上。他听到了他满头满脑都是嗡啦嗡啦响,努力朝后挣脱着嫂子的拉,想对她说我不能去替镇长蹲狱了,那个阄儿让柱子抓到了,可说出口的话却是,嫂子,你别拉我哩。
嫂子说,咋儿了?你不愿意我表妹?
他说,我是去蹲监,又不是啥好事。
嫂子说,你是去替镇长蹲监哩。
他说,这一蹲可不一定真的是十天、二十天,人都轧死了,说不定要蹲半年、一年哩。
嫂子立在朦胧的夜里就笑了,说你看见包袱里那三双解放鞋了吧那是我表妹连夜到邻村供销点里给你买的哩,她说蹲监狱的人都得去烧砖,说到机砖厂劳改特别费鞋子,说一去劳改最少是一年。
他说,那要劳改二三年哩?
嫂子说,我表妹是个重情的人,因为她男人进城里总是找小姐,是因为男人对她不忠她才离的婚。说我表妹不怕男人蹲监狱,就怕男人们有钱进城住宾馆,洗澡堂。
他说,嫂子,既然是这样,你就对我说,我到你家见了人家先说啥?
嫂子说,你把你娘烙的葱花油馍拿几页,说半夜了,你是过去给她送点儿夜饭。
然后,嫂子就走了。走得轻快,像草地里跳着的羊。根宝在院里看着东邻的嫂子走出大门,又回头吩咐他说,你快些,再磨蹭一会儿天便亮了呢,随后,她就融进夜色里了。
根宝没有照嫂子说的那样回身进灶房去拿油烙馍。他在原地站一会儿,想一阵,便相跟着嫂子的脚步出门了。他没有去东邻嫂子家,而是往右一转朝村西走去了。他去了住在村西的柱子家。柱子家也是一个瓦房院,连门楼儿都是砖瓦结构的,高高大大,一看便知是一户殷实人家哩。虽然是殷实人家,可媳妇还是跟着外人情奔了。那男人不光是木匠,还是一个村支书的亲弟哩。根宝到柱子家门前时,惊起了好几响胡同里的狗吠声,待他把脚步止在瓦房的门楼下,狗吠也便无声无息了。隔着门缝,他看见柱子家正房还有电灯光。自然哩,他还没有睡。明儿吃过早饭就要跟着李屠户到镇上面见镇长了。见了镇长就该乘车去县里面见公安了。然后,就会被拘留起来住进监狱等着判刑了,就要很多日子不能回家了。柱子不消说得连夜把他蹲监的行李准备哩。
根宝轻轻地敲了几下柱子家的门。
门是榆木板,碰上去的指关节就如敲在了石面上。在月落以后的黑色里,那干硬硬的响声如小石子一样飞在村街的房檐下。声音响进去,没有从柱子家响出回应来,只有狗吠在村里回荡着。
根宝又用力敲了几下门。
柱子回应了——谁?
根宝说,是我,柱子哥。
柱子问,根宝呀,有啥事?
根宝说,你开一下门,我有话跟你说。
柱子从屋里出来开门了。他到大门前先拉亮了门楼下的灯,然后哗地一下把双扇大门打开了。
门一开,根宝就扑通一下跪在柱子面前。
柱子忙朝后退一步,说,根宝,你要干啥?你这是干啥?
根宝说,柱子哥,你让我去替镇长蹲监吧,你好歹成过一次家,知道做男人是啥滋味哩,可我根宝立马就是三十岁,还不知道当男人到底啥味儿。你让我去替镇长蹲监狱,镇长肯定得问我家里有啥困难事,我对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把你媳妇和孩娃送回家里来好不好?
柱子盯着灯光下的根宝不说话。
根宝便朝柱子磕了一个头,说,柱子哥,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柱子说,我让你去了,你会替我在镇长面前说话吗?
根宝说,我要不先把你的难处说出来,不让镇长把你媳妇和孩娃讨回来,我根宝就是你柱子哥的重孙子。
柱子说,那你起来吧。
根宝便又向柱子连磕了三个响头才起来了。
匆匆忙忙一夜过去了。
来日早升的日头在仲春里光辉得四野流金,山脉间的田地、岭梁、树木和村落都在日光中透发着亮色。吴家坡在这个春日早晨醒来时,谁都知道根宝家里有了喜事了。根宝要去替镇长住狱了。包裹已经捆起来,被褥也都叠好用绳子系了哩,白面油烙的葱花饼也装进了干粮袋里。
根宝要做镇长的恩人了。
他喝了一碗薯黍片儿汤,吃了咸菜和油馍,提着行李出门上路时,看见大门外有许多的村人们。李庆、瘸子、柱子、东邻的哥嫂,还有嫂的表妹。昨儿他们连夜订了婚配,她说你去十天半月肯定回不来,说你就是去住一年、两年我都会等你。然后,她就又一早跟在表姐身后来送他。村人们大都还不知道她是他的媳妇了,只把她当做是跟着表姐来看繁闹的人。爹在他身后提着铺和盖,像儿娃出门做大事儿一样,满脸的喜庆和自豪。他把烟袋丢到家里了,特意吸了带着过滤嘴的纸香烟,可又不是真的吸,仅就是燃了让一丝青烟在他嘴前袅袅地升起来。娘手里提的是根宝的干粮袋,一出门看见东邻嫂的表妹子,她便一脸粲然地朝人家走过去。根宝没有听见娘和人家说了啥,只看见两个人说了两句话,嫂的表妹竟从娘的手里要过干粮袋儿提在手里边,又如过桥时搀扶老人一样扶住了娘。在这送行的人群里,她就像一朵盛开在夏时草坡上的花,因为也是镇上的人,家里和镇政府仅隔着一堵墙,儿娃时端着饭碗还常跑到镇政府的院落里,加之她和她表姐的识见是一般儿的多,穿戴、言说、行止,和吴家坡人有着无数的差别与异样,所以她搀扶着娘的胳膊时,看见的人便心中清明了,眼里更加有了一种惊羡的光。门前的人群原本也就十几个,可待根宝一家走出来,站在那儿和人们说了几句话,转眼间人群就是一片了。有的人正要下地去,听说根宝要去做镇长恩人了,也就慌忙过来道着喜,送送行。说根宝兄弟,奔着前程了,千万别忘了你哥啊。根宝就把目光从自己那香熟发光的对象身上收回来,笑着说奔啥儿前程哩,是去替人家蹲监呢。那人就又说,替谁呀?是替镇长哩,你是镇长的救命恩人呢,还以为你哥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前程嘛。
根宝就只笑不说了。
根宝就这么在送行的人群中慢慢行走着。前面是人,后边也是人,说笑和脚步的声音如秋风落叶般地响。爹在他的身后,有人去他手里要那行李提,他说不用不用却又松了手。而后从裤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拆开来,一根接一根地朝着人们递。人家不接了他便朝人家的嘴里塞。根宝很想朝柱子走近些,柱子和李庆、瘸子他们好像没昨夜命运相争的事儿一样,一团和气地挤在路边上,可人群围得紧,又都要争着和他说话儿,他就只能隔着人群和柱子他们招着手,点着头,表白着自己的歉意和感激。村里是许多年月都没有这样送行的喜庆繁闹了,就是偶尔哪年谁家的孩娃参军入伍也没有这么张扬过,排场过,可今儿的根宝竟获着了这份排场和张扬。他心满意足地朝村口走动着,到饭场那儿立下来,扬着手,连声说着都回吧,回去吧,我是去蹲监,又不是去当兵。然而无论他如何地解释着说,人们还是不肯立住去送他的脚。
人们都簇拥着他往梁上李屠户家门前走去。
李屠户已经在梁上的日光里朝着这边人群招了手。招了手,根宝脚下的步子就快了。可根宝的脚步越快,李屠户却越发地招着手,似乎还把双手喇叭在嘴上,大声地唤了啥,因为远,没能听清楚,人们就猜他是让根宝快一些。
根宝便提着行李小步跑起来,他不想让李屠户在梁上等得时候太久。然而在他丢开人群朝着梁上跑去时,李屠户身边那个昨夜帮他屠宰的小伙子却从梁上跑下来。两个人相向地跑,近了时,小伙子就立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可着嗓子叫唤着,说刘根宝,李叔不让你再来了,说镇长一早从镇上捎来了话,说不用人去替他顶罪了。
根宝淡了脚步站下了,像电线杆一样栽在路中央,望着那个小伙子,唤着,问道,你说啥?天呀你说啥?
小伙子大声说,不用你去了,说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做镇长的干儿就完啦——
这一回,小伙子说的根宝全都听清了。他立在那儿脚跟有些软,努力把一身的力气全都用到脚脖上,使自己不至于突然瘫下去。然后把目光投到山梁上,他看见李屠户在梁道边上正指派着几个人往一辆车上装着鲜猪肉,背对着他,舞之又蹈之,肩膀和门板一样宽,有力得没法说。
紧随着他,村里送行的人们也都说说笑笑跟近了,像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车爬到了半坡上。根宝很想让李屠户或者跑来唤话的小伙把说过的话,朝着村人们再清清白白地述说一遍,他就又慢慢朝着梁道走了过去。
日头又升高了些,艳红艳红哩。
(选自《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