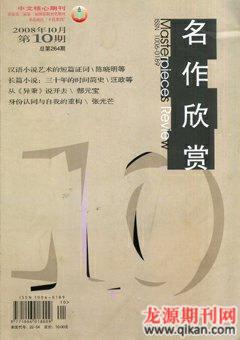先锋与武侠:歧路交叉的双重可能
彭 宏
【推荐理由】
《鲜血梅花》是余华小说的特异之作,它以戏拟武侠小说的形式,“改写”了传统武侠的“复仇”主题和“成长”模式,探索了意义的虚无、人生似迷宫、偶然改变一切等先锋的命题,完成了对武侠小说文类和价值的彻底颠覆。它亦是余华小说的过渡转折之作,预示了歧路交叉的多种可能:其一,以其徐缓的叙述、诗意的描写、绚烂的意象、新异的比喻,显示先锋小说突破形式窠臼,重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其二,如博尔赫斯一般,通过“改写”通俗文类,以兼蓄传统与现代、突破题材与文类的写法,预示了先锋小说别辟新路的可能。其三,以先锋的手法“重述”武侠小说,为当代武侠小说突破“金庸模式”,追求更具现代性的新变和
《鲜血梅花》被公认是余华对武侠小说的戏拟之作,小说虽沿用陈陈相因的武侠程式,但从内容题旨、情节模式和道德伦理等方面,彻底颠覆了武侠小说惯有的文类特征。而在《鲜血梅花》发表近20年后,纵观其间更为广阔、久远的文学发展轨迹,从中国先锋文学的断续之路、武侠小说的演进之路的双重视角,重读《鲜血梅花》这一特异文本,会发现其恰如余华一贯推崇的博尔赫斯的一部名篇《交叉小径的花园》之题,蕴含着多种意味,预示了歧路交叉中先锋与武侠的双重可能。
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往往被认为是先验地移植西方的形式主义、叙事学、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借鉴法国“新小说”等而进行的语言狂欢和叙事游戏,脱离了中国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也与当代的现实生活脱节,在1980年代末难以为继,纷纷转向历史、回归现实,这就是所谓先锋的“终结”。对此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先锋“是一种创造精神——真正的创造者,都可以视为是今日的先锋,因为创造就意味着变化,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视野和空间”①。只要新的创造和变化不断发生,先锋就永不终结,但有一个根本前提——先锋,必然从历史中走来,以传统为母体,与现实相关联。余华也不认同“终结论”,他称“先锋派就是那些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②,但先锋(或曰“现代”)在历史发展中会成为“一种传统”,而“现代并不是传统的对立,现代应该是传统在前进时自身的革新。或者说传统并不是封闭的,传统是开放的,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而每一个时代的现代性,都在逐渐完善着那个时代的传统” ③。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许三观卖血记》,从显在到潜在,余华的小说以创造革新的精神一直站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前沿,也兼具继承、发展、开放的中外文学传统,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延续性,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在多篇访谈和自述中,余华自承创作受到世界先锋文学的众多作家、流派、理论的影响,如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等;也或多或少呼应着域外文学更久远的传统,如《圣经》、但丁、蒙田、海明威等;他还自觉连接了东方作家的创作元素,如鲁迅的敏锐冷峻、川端康成的细腻感伤等。其小说的先锋姿态始终无法与中外文学的传统截然斩断,主旨超常而又超越,触摸到了人类永恒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叙事新锐而又传统,呈现出的交错丰富的“互文性”意味。《鲜血梅花》选取武侠题材,贯被视作深刻而全面的文类颠覆、价值观颠覆和“非语义化凯旋式”④,体现了对历史的拆解、文化的批判,先锋色彩强烈;但在1980年代末中国先锋文学所谓“终结”的背景下,《鲜血梅花》在让人耳目一新的先锋意识背后,也作为一个过渡,预示了先锋小说别辟新路的可能:即突破题材与文类,兼蓄传统与现代,重述历史和现实。
《鲜血梅花》中,“寻找”覆盖了复仇,成为叙述的主要指向,象征着对人生寄托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于偶然和无意间遭遇的胭脂女、黑针大侠、白雨潇、青云道长,每个人都问他类似的问题:“你将去何处?”(或“你是谁?”“你在找什么人?”“你为何离家?”) 每个人都会带给阮海阔心中的“寻父(母)”企望,促其成长,每个人都与他擦肩而过,留给他下一个使命。这是永恒的人生疑惑和生命进程,就如斯芬克斯向俄狄浦斯提出的谜语,关涉“我是谁”、“认识你自己”等人生的终极命题。在此不难看出西方古典文学传统如古希腊神话、戏剧和“流浪汉小说”等的遗泽,也可见西方现代派作家如卡夫卡等的影子。对中国当代先锋派来说,“无父(无历史或现实)的恐惧已经从潜意识深处流露出来,其写作姿态和立场的微妙改变是不难理解的”⑤,《鲜血梅花》对历史的回归和人生的思索,其意旨仍是西方文学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命题。对此还可参照的,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一个无父无母的感伤少年,孤独而盲目地漫游,漠视生活的一切目的和意义——阮海阔“在路上”的形象,与20世纪50年代在美洲大陆流浪的美国当代颓废青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无所依托的漫游如出一辙,二者的生命状态、精神指向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路上》被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宣言和圣经,绝非仅仅以纵酒、滥交、吸毒、飙车、流浪等行为方式离经叛道,其精神指向“不抱任何幻想,它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无动于衷,对政治生活的贫瘠空洞以及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敌视冷漠也同样熟视无睹……它不知道它寻求的避难所在何处,可它一直不断地在追寻”⑥。所谓“Beat”一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⑦。不由自主被抛入江湖寻仇路的阮海阔,其漫游的迢遥、心理的淡漠、人生的无谓、前途的迷茫,与“Beat Generation”取得了隔代的暗合。余华并未提过杰克•凯鲁亚克、金斯堡等的思想和作品对自己有过影响,但“垮掉的一代”在当代美国文化历程中的反叛姿态,余华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轨迹中的先锋追求,二者却产生了精神上的呼应。此外,一些论者也将《鲜血梅花》与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加以比较,可见当代先锋小说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新时期文学传统“递相祖述”的关系。这些可作《鲜血梅花》参照的中外作品,都显示了文学传统跨越国界、超脱时代的顽强生命力。
《鲜血梅花》给先锋文学的发展演变带来的启示和可能,也与其所颠覆的武侠题材和通俗文类有关。先锋文学往往题材神秘怪异,故事荒诞不经,人物扭曲变形,行为病态癫狂,呈现出非常规、非写实的面貌,挑战读者的习惯经验和现实常识。因先锋作家笔下的“现实一种”,是指更高意义的真实——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生存感受、欲望想象、精神状态的真实,与现实的混乱形成对应。余华称:“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⑧,而武侠小说,本就以暴力、血腥、混乱、疯狂、荒诞为题材的基本特性;加之其文类重在构建虚拟的世界,善用想象的笔墨,致力营造神秘的氛围,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作品”,其题材和写法与先锋文学有着许多相近之处。所以化用通俗文学的题材,借用武侠(包括侦探、冒险、传奇等类型)的故事,突破固有的模式和俗套,“重述”或“改写”通俗文类,既是对过往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的颠覆,又何尝不是对文学传统的另类继承与延续。博尔赫斯就经常对通俗文类进行自如“改写”和巧妙“重述”,他擅长利用侦探、犯罪、黑帮、西部等题材,讲述以间谍、罪犯、恶棍、海盗、毒贩、骗子、武士为主角的悬疑故事、火拼游戏和通俗传奇,如广为人知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及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中的《女海盗金寡妇》《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等篇。这些作品以通俗外壳下的奇异叙述,演绎了由多维交叉的时空关系、现实世界的多重可能、人物命运的错杂多变沟通构建的“迷宫”,传达了“人生如迷宫”“无限的偶然”“世界的虚无与荒诞”“时间的循环”等先锋的主题意旨。通过“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⑨,博尔赫斯穿越文类界限,熔多样的题材和叙述于一炉,展现了其小说“互文性”的特点,既哲思深蕴,又技巧变化、腾挪跳跃、幻彩纷呈,充分激发出阅读兴味,十分好看耐读。余华的《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对武侠、侦探、言情小说进行的“重述”和“改写”,同样是多题材、跨文类、“互文性”的艺术尝试,拓展了视域,丰富了写法,强化了叙述的表现力,增加故事的精彩性,成为中国先锋文学中别具特色的篇章,也给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破除所谓“终结”谶言,开辟更生和新变之路提供了某些启示和可能。
其实,抛开对通俗文类的偏见,视《鲜血梅花》为武侠小说也未尝不可。它依然显现出与当代新派武侠小说紧密的渊源传承和血缘联系。《鲜血梅花》的叙述进程如音乐般流动周折、循环重复,多用想象化的虚拟笔触落墨,勾画出奇幻的意象和神秘的江湖世界,这些与武侠小说的文类特征有众多相似。特别是“浪迹江湖”的情节模式和精神特征,揭示“自由”而“孤独”的人生姿态和生命寓意,更见《鲜血梅花》与新派武侠小说的精神互通。以金庸、古龙等为代表的当代新派武侠小说,已重在表现“自由”这一核心的文学主旨和人生追求,即“浪迹江湖”。陈平原提炼出四点武侠小说的类型化特征:“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其中“‘仗剑行侠注重行侠手段,‘快意恩仇注重行侠主题,‘笑傲江湖注重行侠背景,那么,‘浪迹天涯着眼的是行侠的过程。在现代读者看来,‘过程无疑比‘结果重要得多”,“蕴含着侠客感情变化的心路历程”⑨,映照出侠客的精神特征及恒久形象:“自由地上路”和“孤独地漫游”。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侠客最具魅力的人格写照,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陆小凤传奇》中的陆小凤等,皆是纵横来去、睥睨天下、自在洒脱。《鲜血梅花》虽有着鲜明的“寻仇”表象和深沉的“漫游”主旨,但对阮海阔而言,不会武功、能否找到仇人复仇都并不重要,至为重要的人生意义就是“自由”上路的“过程”。他忘却本应铭记的寻仇之任,由胭脂女和黑针大侠的嘱托推动着自己再次上路,去寻找白雨潇和青云道长,目标并未改变,目的却不知不觉发生偏移。阮海阔的漫游被机缘和偶然推动,在寻获仇人前他始终是“自由”的。但当他最后从白雨潇口中得知仇人已为他人所诛时,却“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内心一片混乱”,只因“自由”即将失去。此处既揭示了现实虚无和人生荒诞等意义,但新派武侠小说几乎皆可视为“流浪汉小说”或“成长小说”,以“自由”地“浪迹天涯”为主旨和情节,对《鲜血梅花》和正统武侠小说来说,并无二致。
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漫游”往往并非自愿,或为家仇国恨、或被追杀亡命、或因背叛离弃,每每充满了“不被社会接纳的精神痛苦。一个逃亡者,一个边缘人,一个不被理解不被承认的时代弃儿”⑩,“孤独”是侠客人格、侠客形象最具光彩也最可悲叹的特征。被社会和历史抛到种种漫游境遇,凝固成诸多孤独身影,在侠客亦是一种“自我放逐”,是从孤独、寂寞、空虚中参悟人生的必经之路,金庸笔下的杨过、令狐冲,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梁羽生《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概莫如是。《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当母亲自焚身亡,无父无母的他“再无栖身之地”,已被抛入更悲凉的孤独之中。因为特殊的家世和境遇,普通人的凡俗生活已经不容于他;但“虚弱不堪”、毫无武功的他,也与武林、江湖格格不入。阮海阔无奈地成为主流社会和亚社会的双重边缘人,成为世俗与江湖、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双重弃儿,他在无限漫游中“自我放逐”,孤独感更为强烈,他的命运更具对人类生存的反思意味和悲悯色彩。
20世纪后半叶,新派武侠小说风行天下,金庸更被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新文学的经典。但对武侠小说的未来,当时已有“武侠小说的出路”的疑虑、或后金庸时代如何“超越金庸”的思考。如陈平原探讨了新文学家创作武侠小说的可能,像熟知袍哥和帮会的李劼人、颇具诗境侠义情怀的老舍、胸怀浪漫游侠精神的沈从文,希望新文学家能介入武侠小说的创作,拓宽武侠小说的出路、提升武侠小说的品格①。但多数纯文学作家仍视武侠小说为旁门左道,不屑亲身创作武侠小说来对此作现代性的探索、艺术性的更新,倒是古龙、温瑞安、黄易等后起港台武侠小说家努力突破“金庸模式”,带来武侠小说的新气象,甚至与先锋文学形成呼应与暗合,如古龙小说塑造的“孤独浪子”形象和其人生困境、黄易小说展现的生命玄思等。但古龙早逝,黄易的《寻秦记》《覆雨翻云》《大唐双龙传》等小说日益宣扬无限膨胀的欲望追逐、权力游戏、玄思怪想,开当下网络“玄幻”“穿越”“架空”文学一脉的先河,已流于媚俗,离武侠小说也渐去渐远,金庸巅峰之下,武侠小说的凄凉“末路”景象在20世纪的后十年已然显现。从这个角度看,《鲜血梅花》以颠覆武侠的先锋姿态问世,那意义的虚无、命运的偶然、叙事的迷宫、光影的流转、意象的象征,对武侠小说的新变和发展显得弥足珍贵,显示了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的前景与可能。也许,新一代深刻浸润于余华等先锋作家的影响,又衷心热爱武侠世界的年轻作者,会值得读者期待。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湖北警官学院公共基础课部教师
①谢有顺. 先锋文学并未终结——答友人问[J].当代作家评论,2005(1):89-94.
②余华,许晓煜. 余华访谈: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谈话即道路——对二十一位中国艺术家的采访[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248.
③余华.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说话[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26.
④赵毅衡. 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余华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77-86.
⑤陈晓明. 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J].文学评论,1991(5):128-141.
⑥吉尔伯特•米尔斯坦. 评在路上,在路上[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329.
⑦约翰•霍尔姆斯. 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在路上[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333.
⑧余华. 虚伪的作品,余华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8.
⑨王永年,陈泉译. 序,博尔赫斯小说集[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
⑩ 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78-179.
① 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千古文人侠客梦[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26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