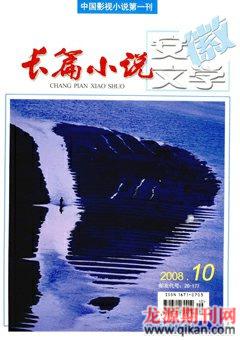年味
东 湖
入冬一冷,穿上厚厚的棉衣,再等雪花一飘,天就突然地低了许多。一进腊月,就离年不远了。
“大人望插田,小孩子望过年”。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会在腊月的某一个日子请来本村的裁缝。裁缝的徒弟则在那天的清早把缝纫机和其他的物件挑进家门。父亲会及时地为裁缝的徒弟敬上一支烟,小师傅红着脸不接,父亲会一再地说:“拿着、拿着!”小师傅呵呵地笑着把烟接过夹在耳朵上。我们几个小孩子围着小师傅转,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摸摸那,看着摸着小师傅就有点恼了,父亲呵斥道:“一边去,不要在这碍事。”
在裁缝师傅来家之前,父亲会帮着小师傅布置好一切。小师傅要把缝纫机安顿好,把机头装上,告上油拭拭运转的情况;父亲则用家里的四条长凳和一块大木板搭起一个临时裁衣的铺子。早饭快熟了的时候,大师傅才会度着方步走进家门。
吃过早饭,大师傅就按照父亲的吩咐一个一个给我们量体。量到腰部的时候,我就会扭着屁股笑,母亲恰好走过,一个巴掌会落在穿着厚棉裤的屁股上。姐姐就一个劲地催,小弟,你快点。但真到量她的时候,她又忸怩起来。大师傅的皮尺从她胸部读尺码的时候,她的脸比要裁的红褂子还要红。我偷偷地看见小师傅的脸也红了,他低着头转一边去了。
做好的新衣服,母亲会在一个好天里一件件洗了,棉质的衣服就用煮饭的米汤浆一浆,晾在竹篙上,然后一件件收好,放在木箱里,在过年的那天再拿出来给我们换上。
此时的我们一边数着日子,一边心急火燎地等新年的到来。有时会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拿出新衣服穿一下。姐姐看见的话,赶紧说:“快脱下,妈妈一会就要回来,看你不驮打。”我们穿在身上显摆的时候,母亲也没回来。姐姐看着我们,挺不住了,也拿出她的红褂子穿上,可此时我们竟听见了母亲进门的声音。姐姐飞快地脱下红褂子,可越是着急越出问题,姐姐脱的时候,褂子的扣眼挂上了门后的铁钉,一声不易觉察的闷声,让姐姐的脸和她的新衣服一样,从母亲进门的那刻起,由惊慌失措到惶恐的沮丧。母亲看见这一切,一个毛栗就上了姐姐的头,姐姐看着手里划破的新衣服,眼里噙着泪水,恨恨地望着我们,倒忘了母亲打她的痛了。
过了腊月初十以后,家家就开始熬糖了。母亲在锅台上,姐姐则在灶下塞火。熬糖特别讲究火候,母亲一边用锅铲伺候着糖块,一边嘱咐姐姐什么时候把火掏小一点。如果大火时间长了,就会把糖块熬成焦碳,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我和哥哥就一直蹭在旁边,伺机偷吃着母亲早已准备好的熟冻米、花生米和芝麻。母亲熬糖的时候是无心管我们的,姐姐老是沉不住气,用灶前火一样的眼光射我们,我们则视而不见。
熬好的糖稀要迅速地舀起放入早就准备好的盛着冻米、花生米和芝麻的盆里。此时我们不能添乱了。母亲舀一瓢冷水放在手边,糖稀放进盆里后先用勺子搅拌均匀,然后右手在冷水里浸湿,得快速地插入盆里,使糖稀和冻米、花生米、芝麻彻底地融合在一起。母亲的手要不断地沾冷水,稍微够不着的时候,我就会端起瓢送近母亲的手边。待揣得差不多的时候,要从盆里取出来,放在团莆里,趁热的时候把它们规成长方形,然后用湿毛巾搭在上面。一个个全部整好,母亲的额头上就布满了汗珠。这一切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连串地完成。母亲擦汗的时候,我们就已闻到各种糖的香味了。
接下来就是切糖了。切糖也有很多的讲究,糖块热了切不成型,凉了一切就碎。而什么时候切全凭母亲的手感。母亲要切了,我们就围成一圈,蹲在旁边看着,如果切碎了一块,就异口同声地喊道:“妈妈,快点切,快点切!”母亲摞一下袖子说:“你们这些伢子,我只有一双手啊,怎么快得起来?”母亲虽然这么说,但手上还是加快了速度。切碎的糖块母亲会叫我们吃,并问着怎么样,我们咂着嘴说:“好吃,真香。”母亲这时就会笑了,我们也幸福地看着母亲傻笑着。
做好衣服熬好糖,年就真的离我们近了。
二十四过小年,打洋尘,炸肉圆。磨豆子,打豆腐。老磨在我们还没起床的时候就响了,姐姐牵磨母亲添豆子。打豆腐有许多的工序,磨好的豆子用桶装好,然后拿来木制的四角架系在堂屋的横梁上,再把四方的老布系上成一个兜,磨好的豆子舀进里面,适当添点水反复搓揉,底下用木盆接住,这叫洗浆。洗过浆的豆渣搓成球状,搭起梯子放上屋顶,日晒夜露,到明年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拿下剥去表层,用蓝边碗装着,再舀点开锅的米汤放入,配好作料,放在闷饭的锅边一炖,饭好了豆渣也香了。就着热饭,夹一筷子在饭头,那种香味都能吞下一碗饭。
洗好的浆要在大锅里烧开。点卤是关键,点好了就是一锅好豆腐,点不好就泡汤了。点好的豆浆用缸装着养着,此时叫豆腐脑儿。早早地我就拿好了碗,放点糖在里面,等缸里面养成豆腐脑的时候舀上一碗,喝着一年只能吃上一回的豆腐脑。养好的豆腐脑就要压了,压好了才成为豆腐。母亲会用筲箕装上五六块,让我送去对门的三奶家,三奶奶乐呵呵地说:“我也过上有豆腐吃的年了。”打好了的豆腐,装在瓷缸里,用清水漂,留着过年新鲜吃。其余的炸成生腐,做成豆腐圆子,还要霉成豆腐乳,来年又是一道菜了。
二十五六一过,孩子们在家呆不住了,相互聚集到一起,比说着将要穿的新衣,谁要是比着家里已有的比同伴少了一样的话,立马红着眼回家,吵着母亲或者父亲要。运气好的要上了接着回来炫耀,不好的就传来了挨打的哭叫声,一声紧似一声地响在腊月的天空。大人们依旧是忙碌的,有也忙无也要忙着,所以说年忙呢。孩子们则不管这些,二十七,等不及;二十八,眼等瞎;二十九,精神抖。到了三十夜里,打着灯笼满屋走了。
还没点灯,就催着母亲给我们换上新衣新鞋,那白白的鞋边爬满着母亲细细的针脚。刚穿上脚的时候还知道爱惜,三十晚上一疯,不是新衣服上被炮竹炸了一个洞,就是鞋面上再也找不到母亲的线脚了。
作者简介东湖,原名李俊平,作家,1967年生于安徽望江。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