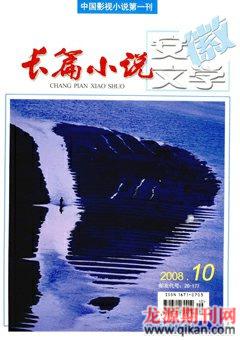阴茶籽·阳茶籽·贼古子
廖天锡
一
“钢崽,起来,天快亮了!”舅妈俯在我耳边低声叫道。
我应声爬起,其实,根本没睡着。走到窗前,见下弦月已快吻住西山山嘴。
“天一亮就走不成了!”我心里想。
昨天晚饭后,舅妈神秘兮兮把我带到楼上,揭开柜盖,指着一担乌黑发亮的茶籽说:“钢崽,你把这担阳茶籽挑去榨出,办结婚酒的油就足够了。”我们这里管含油量多的寒露籽叫阳茶籽,含油量少的霜降籽叫阴茶籽。
“茶籽,妈,你捡的?”我自幼称舅妈叫妈。懂事后,上学前,大半时间在舅家,小半时间在自家;上学后到小学毕业,每年暑假也在舅家过,舅妈待我有如亲妈。
舅妈把嘴凑在我耳根:“是队上的!”
我心里一惊,舅妈偷茶籽!但嘴上没说。
舅家住石桥,地处深山,盛产油茶。除上交国家,每年人均还可分几十斤茶油。石桥离山外有三十里山路。石桥大队规定,既不准社员,也不准亲戚来石桥捡野茶籽。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有人捎带偷队里的茶籽。这样一来,石桥对茶籽的管理很随意。历年来都是把捡回的茶籽摊在禾场上晒裂后,任由各家连籽带壳撮回去选,选净后的茶籽交队里过秤记工。舅和表兄长年在外做手艺,表弟在校读书,舅妈一人在家,选得勤,比别人交得多,根本没人怀疑她截留了一担。
但我清楚,这无论如何是偷。
石桥一带民风淳朴,对贼古子不仅惩治极严,而且一旦背上贼名即是臭狗屎一堆。去年,舅家对门的成六掰了队上几颗包谷用衣服裹着往家里带时被发现,结果罚了两百斤口粮谷。成六没脸见人,吊死在狗公坳上的亭子里。
想不到这次舅妈竟这样冒险。
“妈,我不敢,抓住我,会连累你。”我说话的声音有点发颤。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担茶籽,而是两箩筐炸药。
舅妈沉吟了一阵,生气说:“那你办酒的油呢?你爸走得早,你妈老了,队里才一角钱一个的工,这担茶籽抵得你四个月的收入。你,你还没晓铁胆大;你不干,我叫晓铁来挑。”
晓铁是我哥,比我大12岁,女儿华华都五岁了。我俩虽是一母同胞,但品性不同。我胆小怕事,老实得近乎愚蠢,村里人说我是榨不出油的阴茶籽;哥胆大心细,精明得有些狡猾,他会木工、砖工和篾工,还会刷油漆,什么事他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村里人称他阳茶籽。
明摆着一担阳茶籽,听说叫哥来挑,我有点舍不得。况且自己办结婚酒的油还没着落呢!
舅妈又低声说:“我留下这担茶籽不容易。现在队里的茶籽都选完了,放在家里,不说外人看见是个祸害,你舅知道了也不得清场。你今晚早点睡,明早天不亮就走。晚饭前,我到各家走了一圈,村里人都在家里,路上碰不到。”
经不住诱惑与劝说,我答应了。
答是答应了,但想想自己长到二十二岁,没摘过人家一根黄瓜,没扒过人家一块红薯;队上家家户户捡野茶籽,实际是合伙偷人家山里的茶籽,但我不敢。而今,想想自己也要当贼古子了,躺在床上一直没睡着。
趁我刷牙洗脸吃饭的时间,舅妈又从外面转圈回来:“钢崽,今天竹叶塘开圩,趁村里还没人起床,你现在就走,脚放快点。只要不让我们这里赶圩的人追上就没关系。”
我听出舅妈的声音有点发颤,瘦小的身子在如豆的灯光下发抖。在我漫长的记忆里,舅妈是个清清白白而又胆小的人,她头次做贼,焉能不怕。
二
我挑着茶籽正要走,舅妈又低声叮嘱:“别让晓铁知道,他眼浅。”
就着残月,我踩着拐弯抹角的麻石路溜出村,上了田垅大道。回头看了看,石桥村还是黑糊糊一片——赶圩的人还没起床做饭,提在嗓子眼上的心才渐渐放下,两腿才停止打颤。
走了一段路,我总觉得前面有人堵,后面有人追,心跳个不停。农历十月的山区深夜,温度低,冷露重,我却浑身燥热,好不容易走完两里田垅路来到猪婆坳下已是满头大汗。这时,月亮“哗”一下跌落西山,整个苍穹陡然墨黑,脚下模糊不清,一时难以挪步。我这才发现慌乱中舅妈和自己都把日子搞错了——竹叶塘逢农历三、六、九的圩,以为今天是农历十三,哪知还是农历初九,月亮落山还只半夜。
我不由停住脚步,放下担子犹豫起来。自己从没走过夜路,而今要在死山万岭走三十里夜路,沿途没一伙人家。爸在世时说过,夜路越走越亮胆就大,越走越黑胆就小……现在离天亮还有五个小时,正是越走越黑,我越想越怕,差点要哭。
“回舅家去!”这个念头刚冒出,我立即否定了。
石桥赶圩的人此时也许已经起床做饭。他们大都是去圩上卖杉板、杉条、木器。起床后,喜欢打着电筒互相串门,试试别人的担子,看看别人的伙食,聚在一起抽烟喝茶,人来人往,喊喊叫叫,很是热闹。这时进村,一旦被抓住,这不是要舅妈一家的命吗?不行,不能回去;对,把箩筐藏在路边草丛里,睡一觉才来挑。也不行,舅家没钟,自己没表,万一睡过了头,天一亮,藏在路边的茶籽被人发现,箩筐上有舅的名字,危险更大;干脆把茶籽倒掉,挑空箩筐回舅家,但我最终没这样做。舅妈说,这担阳茶籽,少说也能榨15斤油。黑市茶油两块钱一斤,15斤值30块。一头丙等猪卖给食品站连本带利不到七十块,倒掉这担茶籽等于丢了半头猪;挑回去相当净赚半头猪,这个诱惑太大了。他妈的,贼已做了,头已洗了——剃吧!我无所畏惧地撒了泡尿,山路比原先明朗了些,抖起精神挑着茶籽往上爬,竟格外有力。
爬到半坡,我陡然想起了坡顶的那座亭子。
去年来舅家时,亲眼看见成六吊死在亭子里。还是自己告诉舅妈叫成六的老婆去收尸的,顿时,我怕得不得了。也是父亲在世时讲的,荒郊野外的亭子是孤魂厉鬼聚会的地方,傍黑相聚,鸡叫后分手。胆小的父亲一辈子没独自走过夜路,也没碰过鬼,这些话他也是听人传的。既然有人传,也就有人信。这种事,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半夜刚过,正是鬼们聚会最热闹的时候。成六吊死在亭子里那鼓眼暴睛舌头伸出的恶相历历在目,尤为清晰。万一他今晚现身撞道,怎么得了?想到这里,我两腿又不由颤抖起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我想,哪怕是一担净油也不要了。
我换了一下肩,车转屁股下坡往回走。但只走了十来步,突然“砰”的一声铳响,差点把我吓瘫。
“公亮,麂牯倒了肉吗?”这是公德的声音。
“没倒肉,伤了,跑了!”公亮在回答。
铳声和喊声都是从垅口传来的。公亮是石桥的队长,他和公德又在守野狸打夜铳。
震荡山谷的铳声逼使我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往前闯。被打伤的麂牯万一往这边逃,他兄弟俩追来,那就麻烦了。他俩是石桥有名的猎手,走夜路很快很快。
我不顾一切转身往上爬,总觉得公德、公亮在后面追。我按爸在世时教的,解开衣领下两粒扣子,不回头,不低头,不往远看;不要走得太急,也不要太慢。我爬上坡顶,一脚踏进亭子,屏住呼吸,目不斜视,平平静静走了过去,其实什么声响什么影子都没有。
三
过了亭子往下走,是狗公坳。
亭子一过,我胆子大起来了,世上哪有什么鬼哟?全是老辈人吓小孩的。石桥人来吧,你们无论如何也追我不上了,再过几小时,茶籽就到我屋里了。
下完狗公坳,走过小河,紧接着是上木牛坡。
木牛坡下有块大土坪。早几年,这里有个杉皮夹墙,杉皮盖顶的木器厂。厂里长时间有三个人在这里锯木板,打制木器,石桥人赶场,来去都在此歇脚。一年前,狗公坳、木牛坡两边山上的杉木伐光了,杉皮厂没用了。哥带人把建厂的树和杉皮一夜之间全拆走了,这里成了一块荒坪,但过往的人仍习惯于在此歇脚后再上坡。
我太紧张了,想放松放松,于是放下茶担,把扁担横架在两只箩筐上,一屁股坐下来。不到两分钟,湿透的衣服贴在背上透骨的凉,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一抬头,对面的山峰向自己挤压过来,眼前闪动一个又一个高大威猛的黑影。难怪那时爸说,走夜路宁肯走慢点,千万不要坐下歇息。当时,爸没说为什么,现在,自己明白了,一是防着凉伤寒,二是害怕。
石桥的人几乎每天都在这段路上走出走进,坡上坡下沿途两边的树和草修理得像剃过一样。木牛坡属木牛大队管,木牛大队的人赶场不走木牛坡过,也就从不修理。一踏上木牛坡,情况大不一样,路两边的树枝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条天然巷道;微弱的星光透不过茂密的树叶,石板路被齐及腰胯的杂草复盖;雾气蒸腾,山岚露重,脚下一片漆黑。我要缓慢地迈出一步等踩稳了才敢提另一只脚。万一踩空,人倒了也许能爬起来,茶籽倒了是无论如何也捡不拢的。木牛坡上了不到一半,我全身湿淋淋像从水里打捞上来一样。走一步,脚下:“哗”一声走一步,脚下再“哗”一声。
“叽——嘎——扑!”
“呼噜噜——”
“叽——吼!吼!吼!”
山窝里不时传来山鸟惊飞和野狸追逐撕打的响声和各种各样的怪叫。有时从我耳边响起,传向对面空谷又被山峰挡了回来。在深夜沉寂的密林久久回荡;独具穿透力的响声和怪叫叠在一起,更加剧了夜的神秘和恐怖。
我嘱咐自己,这十几斤茶油一定要倍加珍惜,慢慢享用。
四
“妈!”我一脚跨进门槛放下担子返身拴上大门和房门,掀开盖在箩筐上的布,“妈!你看!”
“茶籽,哪里的?”妈一脸难看的严肃。
“舅妈队上的!”
“偷的!?”
“嗯!”
“你们怎做这种事,笑贼不笑乞,你爸说的话忘了?”
我解释了一阵,娘才无奈地叫我挑上楼去,放进柜里。娘还把两米筛干红薯皮放在茶籽箩上,然后叫我洗澡换衣,她生火下面条。
吃面条的时候,我又和妈谈起一路上的害怕情景。娘睁大眼睛从头到脚打量我,似乎看我身上是不是少了什么:“人都吓死!你爸说过日日设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以后,即使有金子水牛银子马我们也不要。”
“这回是一时糊涂,下次不敢了。妈!”
“村里没谁看见吧!”妈把头伸过来低声问。
“没谁看见,我进村时,天刚蒙蒙亮!”隔了一会儿,我又补充道,“喊你放大门时,哥可能听见了。”
“听见喊门没关系,只要没看见不要紧。”
过了会儿,妈又犯难,说这茶籽要晒干才能榨,我们没捡野茶籽,突然有茶籽晒,有茶籽榨,队里的干部肯定会怀疑,会查,一查,你会背贼名,还会连累你舅家。
我被娘的分析吓懵了,歪道所得给人的心理压力真的太大太大。
五
第三天吃晚饭时,娘告诉我说,那担茶籽让你嫂子看见了。我惊问,你告诉她的?娘说这两天华华总是缠着我要红薯皮吃,而且我拿都不肯,非得牵着她妈上楼拿。后来就露馅了。
“本来舅妈要我别让哥知道,说他眼浅。”
“儿子是我的,我知道!这事躲是躲不过了,我想我们自己反正出不了手,找兄弟比找别人出手总好些。”
想想,妈的话也对。
我们兄弟合住一栋四垛三间土坯房,把大门一拴便与外界隔绝。
我挑着茶籽去哥家时,哥正在编鱼篓;嫂子月花正在收捡簸箕里、门板上的红薯皮,全干、半干的都有,一块块通明透亮,把娘做的那些薯皮比得暗淡无光。我嫂子能干手巧,会炒菜,会织毛衣,每做一样都与众不同。现在清楚了,嫂子带女儿华华去拿红薯皮实际是借口侦察。娘晒的那些黑不溜秋的红薯皮都堆在桌上,可能一块都没吃。
嫂子招呼我和妈坐,微微一笑道:“晓铁,你看晓钢喊舅妈叫妈,一喊一担茶籽,干脆明天你也去多叫几声妈。”
嫂子话中有话,妈拦了一把:“月花,这是你舅妈体贴晓钢结婚没油,提心吊胆留出一点儿,现在你喊百声妈也拿不出了。还不知能榨出多大点油?”娘话锋一转探口风。
哥也不正面回答妈的话,而是问我:“你是晒脱榨脱,还是放一起晒一起榨?”
“晒脱,榨脱,河滩牯(一种鱼名)又不是鱼,别人还不是知道晓钢偷了茶籽。到时一查,连累三家。”嫂子抢先回答连带恐吓。
“放一起榨吧!”我附和着嫂子的意思说。
“不是兄弟我也不会帮你,不过话讲在前头,当面看好,我两担,你一担,榨油时一起去,榨出的油是多是少三股开,我两份,你一份。”
我一个劲说行,表示相当满意。心想,哥还是哥,到时,自己那股另给三斤给哥作为感谢,还暗暗责怪舅妈看扁了自己的哥,甚至觉得爸在世时对哥的要求过于苛严。
哥嫂1962年冬结婚分家另过。1963年,农村公共食堂解散后,饿怕了的人们见了粮食比亲娘还亲。稻熟季节,偷谷成风——夜间蹲在田埂上往背篓里撸谷的;割禾时,故意把禾线往紧跟身后的自家孩子手下丢的;把故意不扮净的稻草挑回家放在地上捶的——偷技百出,应有尽有。队里不得不通夜放哨巡逻,连抓了几个罚没口粮敲锣游垌;也不准小孩捡禾线不准往家里挑稻草,终于有效地刹住偷风,保证集体粮食归仓。
万万没想到,割禾那段日子,哥却几乎天天能偷谷回家。
那时开工是搞大合唱,重活没人肯干。比如割禾时,都不愿背禾桶,也不愿扮禾。因为热天背禾桶罩住上半截身体,不透风,太憋闷;去开工时,别人空手吊吊,自己却要负重;为防别队的人偷禾桶,每天要背出背进,负责保管。扮禾费劲大、出汗多,一天扮好多谷是有比样的;割禾则不同,不仅轻松,而且可以偷懒。哥却愿背禾桶愿扮禾,开始我认为哥思想好,但那天下午,哥把禾桶背回自家厅屋时,松开背禾桶的木杠随即滚下一个装有稻谷的布袋,才清楚哥背禾桶是另有所图。但他是怎样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把谷装进口袋的,我至今也没搞清。
那年,我正读小学四年级。每天放学后,去田里凼里捉回的鱼,爸总要我送一半过去给哥嫂吃。自从发现哥偷谷后,爸不准我送鱼过去了。
现在细想起来,我认为在那为生存而偷的年代,父亲对哥的确过于苛严。
六
油榨坊里人出人进,热闹得很。
整个榨坊分三大间,西大间是烘房,没晒干到可榨程度的茶籽在这里烘;东大间有一原始的用水鼓带动的碾槽,晒干或烘干的茶籽必须在碾槽里碾成粉;中间这间最大,两丈来宽,三丈来长,横躺着的原始木榨和蒸茶粉的灶都在这里,这里的人也最多。大家在看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学打“丢锤”,松“倒退”。油榨头罗师傅在和那人打赌,说松出了那个“倒退”,这榨油至少25斤,归你!改口,屁股讲话。那人一听来了兴趣,霜降天脱光上衣抱着悬在梁上的榨锤冲来冲去;可榨锤不是打在庞然的木榨上方就是钻进木榨底下;偏偏打不中那个倒退榨尖的钢头;偶尔挨着,也好比手锤砸在铁砧上,毫无反应——“倒退”的榨尖是上榨时放进去的,藏得较深;经一次又一次的加尖锤打已榨得绷紧;松“倒退”是榨油的最后一道工序,必须打那种力度很大的丢锤。能不能打“丢锤”是衡量一个榨油师傅水平高低的标准,打不出丢锤出不了师。这个油榨坊里也只有油榨头罗师傅能打丢锤。
那人徒劳了半个多钟头,满头大汗彻底败下阵来。
“罗师傅,敢不敢和我赌?”哥上去说。
“哦!晓铁,”罗师傅说,“你年年帮队里榨油,看是看灵了,但也不一定打得出。”
我哥脱下外衣,系系鞋带:“我来试试。”
榨锤有丈把长,比海碗口粗,是一种结构很紧,硬度很高的柞木做的,锤头套个钢帽,有三百来斤。榨锤正中间凿了一道口子,装上吊环,挂在两个结实的三叉架扛着的大梁上。开始几分钟,哥也打不中,但他很快摸清了步法和手势配合的诀窍,连连打中,虽然不是丢锤,力度不大,但赢得一片叫好声。
“我打丢锤了!”哥宣布。
只见哥右手抓住吊环,左手轻抚榨锤,两脚往前垫几步,随榨锤往后摆的惯性又往后速退几步;再往前,再往后;等榨锤往后摆到极限,抓吊环的手突然往前一送,榨锤脱手像一枚炮弹向前向上蹿去,等榨锤荡回到极限,他两手抓住锤尾再借惯性用力往前一丢,锤头几乎挨着楼枕,待榨锤再次荡过来锤尾也几乎挨着楼枕时,趁榨锤前窜的惯性,哥突然冲上去,右手抓住吊环,左手按正榨锤狠劲撞去,两个钢头相撞,发出沉闷的一声:“砰!”
我觉得哥打丢锤的场面极为壮观,极具专业水平。
如此这般,哥只三下把藏得深榨得紧的“倒退打了个对穿。观看的人发出一片“呵火”的叫好声。这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哥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特别了不起,真的不愧为阳茶籽。
罗师傅和油主人各给哥递了支烟,讲了些奉承话。哥把烟夹在两耳根上又熟练地拆榨解茶枯把油控进主人的油桶。一过秤,25斤3两。
我内心一阵窍喜,三箩茶籽为一榨,自己和哥正好两榨,两榨就是50斤,我可分16斤6两,我不要这么多,拿12斤心满意足了。
过了一会儿,罗师傅抓一把我们的茶籽在耳边摇摇说,阳茶籽,不必烘了,但要明天下午才能轮到你们榨。
哥从耳根取下一支烟递给罗师傅,把他拉到一边低声咕哝了一阵。又过来把我拖到一边神秘地说:“我和罗师傅说好了,今晚12点后给我们榨,你和你嫂回去,吃了晚饭再来,记得给我带饭。”
七
我把油桶放在桌子上。
“就这点儿?”妈惊讶地问。
“哥说总共榨出12斤,给了我们4斤。他说榨钱不要我们出了,还说我一个夜工赚了4斤油也不错了。”我说话时,比挑着茶籽过亭子时心跳还厉害。
“鬼信!”妈愤愤不平。
“他说我的是阴茶籽(霜降籽),不但没油,还害了他的阳茶籽。他说油榨师傅说,阳茶籽和阴茶籽不能混在一起榨。”
“榨油时,你看清了吗?”
“我到那里时,嫂子早把油挑走了,哥在等我挑茶枯。”
“哼,阴茶籽——阳茶籽——贼古子,我找他去!”娘咬牙切齿说。
我长出一口气说:“妈!算了,爸说过,便宜不要,浪荡不收,现在,我心里反而好受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