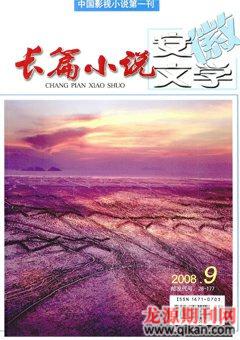塞尔维特之死
梁长峨
塞尔维特,他是一个强韧有力、思维敏捷、卓有建树、捍卫真理的“非凡才俊。”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他为伟大的神学和思想家,是“主张科学神圣的人物之一,此类人物在全部人类历史上只有十个或十二个。”但是这种从他那个世纪的黑暗之壁中冲出的天才闪电,却只活42岁,过早熄灭了。
他的死,自然是死在他直率,死在他为真理而奋斗不悔的献身精神,但还死在他的天真、幼稚、轻信和他的对手加尔文的卑鄙、无耻、专制和残暴。
他是当时最“勇敢的革命家”。他经常同所有其他刚愎自用之徒发生激烈冲突。一看到旧教与新教之间的论战,他那不平静的精神就开始发酵。“哪里在争论一切,他就想在哪里参与争论,哪里教会试图改革一切,他就想在哪里参与改革。”
二十岁时的他,就倾其所有积蓄,把他宗教改革的论点印成书籍。他以如此挑衅的态度反对极为黑暗、极为残暴的十六世纪欧洲世界,可想而知,他在欧洲“就不再有任何栖身之所了”。他要活下去,惟一的办法,是无影无踪地彻底消失,毁掉自己原来的姓名,让别人彻底忘掉自己,最好让世人感到这个世界压根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这个被当时教派声称该“受到从活生生的躯体中撕出内脏”的人真的从德国消失了。他回到法国,化了名,改为研究地理。他很快就卓有成就,成为地理学家。不过他又研究医学,成为人类第一个发现人体小血液循环系统的生理学家。由于轻率,他立即同当时的权威人士发生了冲突,受到了指控。然后,他又迅速隐遁,再次化名,以大主教保尔米尔新任的医生出现在西班牙维埃纳市。这会儿,他有点儿乖了,“处事十分沉着,绝不惹人注目”,“谨防异端的论点扩散”。
实际上,那种大异端思想绝对没有在他这个雄心勃勃的人心中死去,过去那种好探索的不安宁精神,仍然不可动摇地活跃在他灵魂的最深处,并受它控制。他不愿让这种大异端思想无声无息地消逝,他的内心不时产生激情,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空间和自由,渴望整个世界共同思考他的思想,进而接受他的思想。他想让自己“生命的理念从内心挤到外界,如同一根刺从一只化脓的手指中挤出,一个婴儿从母亲的躯体中挤出,果实从果壳中挤出一般”。对于一个急欲要表达的人,那被迫沉默的岁月,心情是沉重而痛苦的。为伪装好自己而不得不紧闭双唇,那要说而不能说的话时时都无情地折磨他。
在实在难熬的时刻,他寻到了喷泄的对象,然而就是这次的轻率和盲从导致他死无葬身之地。人说:“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塞尔维特这个好冲动、好轻信的人居然把自己的全部信任,寄托在他并不了解的陌生的加尔文身上。不知是哪根错乱的神经指挥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加尔文写信,而且把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地暴露给卑鄙、阴险而又残暴之极的加尔文。他哪里知道这等于和吃人的狼交朋友,等于把自己当作一块肉自动送到狼的口中。
长期以来,谁敢在专制独裁者加尔文的著作上改动一个字或批评一个字,谁就等于找死。而塞尔维特这个不知深浅的冒失鬼做了。他像一个小学教师对待小学生那样,在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的页边空白处记下了他认为的错误。他自己一时兴之所致,随便写写玩玩也就罢了,可他偏偏认真起来,把他写了点评的这本书寄给了加尔文。本来谁都有权利指出任何人著作中的不足和毛病,对于真正的学者还求之不得呢!然而加尔文从来都认为自己的著作完美无缺,真理都在他这边,永远都在他这边,他是真理的化身,别人都是荒谬的混合物和翻版。凡是反对他哪怕仅仅想对他提点意见,都属于他消灭的范围,都是他的敌人,都该受火刑处死。
这不,加尔文接到塞尔维特评论他的那本书后,立即卑鄙地写信给他的友人法雷尔说:“塞尔维特像一条咬着一块大石头,来回啃个没完的狗那样,攻击我的著作,用那些辱骂性评论在书上涂鸦。”
不幸的是塞尔维特没有及时感觉到,他没有把加尔文当作最危险的对手加以防备,反而把自己所准备和那份尚未付印的神学著作样本《基督教恢复》,寄给加尔文阅读。这还了得,他竟然要用“重建”、“恢复”基督教来对抗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加尔文能轻饶他吗?这时,昏了头的塞尔维特还不知道他自己把自己推到何等危险的境地,竟还敢写信要求见加尔文,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你听加尔文怎么说,他立即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雷尔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在这个城市还有一些影响,就不会容忍他活着离开。”
直到这时,不知是加尔文直接的警告还是塞尔维特从别处获悉加尔文对他的威胁,他从内心第一次感到不安起来。于是,他立即写信给加尔文:“请把我的手稿寄还给我。”怎么可能!加尔文“他像对待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异端著作保存在一只抽屉里,以便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把它取出来使用”。殊不知在加尔文的抽屉里保存的还有塞尔维特给加尔文的暴露自己全部观点的信件呢!直到现在这个莽撞和轻信的人才以阴郁的预感写信给一个神学家说:“我现在完全明白,我即将为这件事而死。”
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岂止是塞尔维特,都深深体验到,哪怕只有惟一一次,哪怕只在加尔文教义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反对加尔文,都是一件大胆鲁莽而又具有生命危险的事情。“他的仇恨有着一种非常好的记忆力”,“他只要有一次在心里写下了一个人的姓名,在这个人不从生死簿上自行消失之前,这个姓名就不会在他的心中抹去”。这种记仇的人该是何等的可怕!
塞尔维特尽管表面彻底平静了,但暗地却仍顺从一种内心的神圣渴望,继续投身于他的《基督教恢复》的写作。书悄悄写出来了,也秘密印出来了。塞尔维特很得意。他哪里想到那个曾经要置他于死地的大魔头、道貌岸然的加尔文的魔爪正悄悄伸向他的咽喉和心脏。加尔文“貌似瞌睡,实则目光敏锐地潜伏着的仇恨,老早就在为此操心”。加尔文在日内瓦愈来愈系统完善、网眼细密的监视组织,活动范围远及所有邻国,而且在法国甚至比那里罗马教皇的异端裁判所更为严密。塞尔维特的著作还在包扎未解,塞尔维特从自己手中也只发出少量书,而加尔文当时已经一册在手。他立即着手一举消灭两者:异端和著作。这个“宗教改革的头面人物”,每当事关他的信条、教义和宗派他立即就会变得毫无廉耻,不择手段。他要杀塞尔维特,绝不自己出面。他通过渠道秘密把塞尔维特的著作和给的信件中的一部分转到裁判所,使塞尔维特被捕。当时就有人怀疑加尔文从中做了许多卑鄙的手脚。为此,加尔文还多次做了欲盖弥彰的诡辩,也许历史想充分暴露加尔文的残暴和无耻,又想充分显现塞尔维特的莽撞和轻信,塞尔维特从监狱中竟有幸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之后,塞尔维特在几个月内无影无踪,下落不明。突然有一天,他这个被追捕的人竟进入了日内瓦这个对他来说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他简直昏了头,疯了,敢来到加尔文这条毒蛇的眼前。岂不知这条毒蛇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到处追寻他。他要路过这里,第二天立即逃走还好,可是他刚刚抵达日内瓦,就竟然前往加尔文派全体教徒正在其中集会的教堂。他这一举动,确实表现出一股英雄气。但是只有极傻的人才会这样做。他只身一人,赤手空拳,面对欧洲宗教势力最大且又最残忍最专横的头面人物,究竟有多少胜算?!更何况他是自投罗网,进狼群之中呢?!可怕的事终于出现了——加尔文刻不容缓地向自己的帮凶下达命令:在塞尔维特离开教堂时加以逮捕。一个小时以后,塞尔维特就镣铐缠身了。他好糊涂好健忘啊!前不久,他不是还给朋友写信说 “我即将为这件事而死”吗?他怎么这么短时间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这种逮捕塞尔维特的行径,是对世界各国奉为神圣的宾客权和国际法的一种公然冒犯,一种粗暴违背。塞尔维特是外国人,是西班牙人;第一次且又是刚刚踏进日内瓦,因而绝对不可能在那里犯下一种需要逮捕的不法罪行。他所写的著作全部在外国印刷,因而绝对不可能以自己的异端观点,在日内瓦煽动过任何人,玷污过任何虔诚的灵魂。此外,一个“《圣经》传道士”,一个宗教界人士,在法庭事先没有宣判的情况下,无权下令逮捕日内瓦城范围内任何一个人,并让他戴上镣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袭击,都是独裁者卑鄙的专制行径。
“按照真正典范的日内瓦法制,每一个指控另一个市民犯罪的市民,必须与被告同时被监禁,而且在狱中一直待到他的指控证实为无懈可击为止。”“如果议会承认塞尔维特事实上无罪,而加尔文本人作为告密者不得不待在狱中,那究竟会怎样呵!这对于他的威望来说是何等深重的灾难……”然而善于坑害和灭绝自己对手的加尔文就没有想不出的孬主意。他像往常一样老练圆滑,派自己的秘书充当原告这种尴尬的角色。然后,他利用塞尔维特好冲动的弱点,采用种种卑鄙手段让塞尔维特在法官面前失去理智,恼怒愤恨,从而露出把柄,被治死罪。他给一个朋友写信就明白地说:“我希望,判他死刑。”
为此,加尔文及其帮凶在狱中用蓄意而又诡诈的严酷手段对待塞尔维特。几个星期以来,这个自感纯属无辜的人身患疾病,精神烦躁而又歇斯底里,像一个杀人犯那样,戴着手铐脚镣,被关在一个潮湿而又冰冷的地牢里,黏附他那挨冻忍寒的躯体上的衣服已经腐烂。尽管如此,仍不准许他换上任何新的衬衣,最原始的整洁戒律被置于不顾,不许任何人哪怕给他最微不足道的帮助。在深不见底的困境中,塞尔维特在一封致议会的令人震惊的信中,请求多一些人道的待遇:“我正在被跳蚤活活吞噬,我的鞋子已经穿破,我再也没有衣服,再也没有可以洗涤的衣服了。”
然而,尽管议会立即根据塞尔维特的申诉,下令消除这些不良状况,但加尔文这只秘密之手,如同一把老虎钳那样不近人情地阻止塞尔维特命运的各种改善。人们继续让这个勇敢的思想家和自由精神的学者像一条癞皮狗躺在粪堆上一样,在他那潮湿的洞穴中久病不起。而且,几个星期之后,当他简直要在自己的粪便中窒息而死时,第二封信的呼救声显得更为恐怖和刺耳:“我请求你们,为了基督之爱,不要拒绝给我以你们会给一个突厥人和罪犯的待遇。你们为使我保持整洁而下令实施的一切,丝毫没有实施。我的处境比任何时候更糟。不给我以弥补这种肉体所必需之物的任何机会,是一种严重的暴行。”
塞尔维特的确是英雄。即使他们在狱中折磨他,在法庭拷问他,要烧死他,要把他一块一块撕碎,他也丝毫不放弃自己的世界观。恰恰这最后的日子,这个漫游的科学骑士升华为一个信念的殉教者和英雄。他声称 “一种世俗的判决,永远不能当作一个人在宗教事务上正确或错误的证据”。“谋杀并不叫做信服”。“人们并没有向他证明过任何东西,而仅仅企图扼杀他”。他们无论用威胁还是用许诺,都不能迫使这个戴着脚镣手铐、已经陷于死亡的牺牲者哪怕仅仅说出放弃信仰的一句话。
1553年10月27日上午11时,这是世界一切尊重科学、尊重真理、尊重人权的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最耻辱的日子和时刻。这时,人们从狱中提出穿着破烂不堪衣服的囚犯塞尔维特。这个被判死刑的人胡须蓬乱,全身肮脏,精力渐尽,镣铐锒铛,步履摇晃,脸色灰暗,只能用膝盖缓缓艰难前行。临死前,他恳请给予用剑斩首这个小小的恩惠。此时,加尔文的干将法雷尔大声问他,是否发誓放弃他以反对三位一体为目标的教义,以此获得较为温和的处决的恩惠。然而,塞尔维特又一次重新拒绝这种交易,果断地实现自己从前的誓言:准备为自己的信念忍受一切。
刽子手用一根铁链把塞尔维特吊到火刑柱上,用一根绳子在那精力渐渐耗尽的躯体上缠绕四五圈,接着把书和塞尔维特当初寄给加尔文、以求得加尔文兄弟般意见的手稿,塞到活生生的躯体与那根残酷地切入肉体的绳索之间。瞬间,火焰升腾,无情地吞噬这个备受折磨的活生生的肉体。人们连续不断地、愈来愈刺耳地听到这个遭受难以形容痛苦的人尖利的痛苦呐喊。
在这个极为恐怖的时刻,加尔文在哪里呢?他为给人以不参与的假象或为保护自己的神经,就小心翼翼地留在家里,坐在自己书斋中那紧闭的窗户旁边,听凭刽子手和更为残忍的教友法雷尔去处理残酷的事务。可当正需去追究、指控、刺激无辜者,并把他送到火刑柱时,加尔文曾无数次不知疲倦地跑在别人前面。然而在处决时,人们只看到他付酬的刀斧手,却没有看到曾经要求实施,并下令实施的真正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有多少这种极其残暴又诡计多端的伪君子呀!
责任编辑苗秀侠
----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