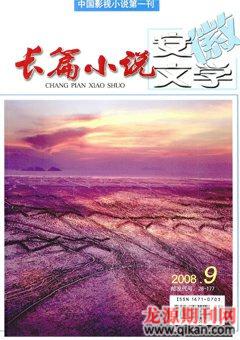自动取款机
许 侃
在电玩城,叶童看一个女人玩吃角子老虎机看得入迷。
那台被叫做老虎的机器,罩在一只玻璃罩子里,像嚼糖果一样把叶童身上的零钱换成的角子全吞了下去。再玩就要掏一百的票子,那就有点儿伤筋动骨了。他注意到一个拎白色坤包的女人,她的脸像用久的磨刀石,中间是凹进去的。她站在旁边目光灼灼地看别人投币,轻易不出手。只要她一出手,马上就哗哗地淌出一大堆硬币,好像有什么魔法一样。
叶童想琢磨出她的窍门。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在暗暗用功,他在计算她出手的时机和成功的概率。那女人又赢了一把,不动声色地莞尔一笑,将大把的硬币捞进坤包,横着小臂,挺胸扭胯地到收款台兑换她的猎物去了。
叶童沮丧地剜了一眼她的背影,心想她好像知道有人在研究她,是第六感觉?还是有什么门道?那磨刀石脸女人出了门,叶童的沮丧变作无聊,看了一会几个半大的孩子在荧屏前左右摇摆地玩仿真摩托赛,走出了电玩城。
大街上日头明晃晃地照着叶童,令他的瞳仁迅速收缩。他来到一架冷饮机前,想买一杯顺着玻璃罩内壁淋成一片冰凉的东西,让干涩发黏的嗓子爽一爽。摸摸口袋里只有瘪瘪的两张一百的整钱,再没有零票,他咽了一口唾液,忍了。
拐过街角,蓦然看见一家银行门口有一台自动取款机。取款机的屏幕变幻着诱人的画面,不停地把一沓钞票从画面的扁嘴里吐出来。仿佛一个顽皮的孩子把好吃的东西给叶童看一眼,马上又收回去一样。
一个胖子忽然出现在自动取款机前,挡住了取款机对叶童的诱惑。那胖子牛哄哄的,脖子后面的黄金项链在阳光下耀了叶童的眼,令叶童愈加生气。叶童觉得这人此时取钱成心就是表演给他看的。TMD,叶童的心里骂了一句在网上常骂的字眼,他觉得他被这小子戏弄了,还找不到借口还击。
叶童转身走掉的时候,扭头瞥了一眼,他看见这一回是真的扁嘴里吐出了钞票,而不是在屏幕上。那一沓钞票厚厚的,足有一千元。那胖子就像采韭菜一样把它们采到了自己手里,然后塞进屁股后面的牛仔裤口袋里。
叶童想:我要是贼就好了!我怎么不是贼呢?哼,会有贼来收拾他!
叶童这样骂着,差点撞在一根光溜溜的金属旗杆上。叶童抬头一看,他正走过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大厦。大厦门脸上一排烫金的大字触动了叶童的思绪,他下意识地将手伸向自己的屁股口袋,那里面装着他的房产贷款经纪人证书。他花钱取得这个证书已经三个月了,可是至今没有一个人来通过他贷款,也就是说他连一分钱的贷款佣金也没有拿过。和那个证书叠加着的还有一个让叶童苦熬八年拿下的律师资格证书。他先考了六年成人自修考试,又考了两年律师资格,现在他逢人就散名片,希望有人找他代理打官司。可是,法院天天有官司开打,就是没有一个是他叶童代理诉讼的案子。
TMD,世界上的好事到了我叶童身上,怎么就全走样了?叶童这样想着,就把他引以为骄傲的两张派司从屁股兜里抽了出来。那是一张黑色的和一张绿色的小本本,很精致的模样。叶童把证件打开,就看见里面那个宽腭大嘴的家伙傻乎乎地向自己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再打开一个,还是这家伙!
瞧你!小样儿……叶童对着自己相当不满意地撇撇嘴。然后将两张派司重新插回屁股兜里。伸手在头上抹抹三七开的分头,又将脑袋酷酷地朝后一甩。虽然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很不满意,叶童其实还是很在乎他的这两张派司的。连走在路上都忘不了拿出来欣赏一眼就是证明。可是,妻子却老是给他泼冷水。
啊,妻子!他想起妻子还要他买菜,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哟!都快十一点钟了。
叶童忽然着急起来,看见路上有个三轮车拉了一些硬纸壳子,紧跑几步,赶上前去,打量了一下拉车的,是个瘦弱的收破烂的,就一屁股猴了上去。收破烂的感觉有情况,立马伸手拉了闸。叶童被惯性从车上甩了下来,险些轧了脚。正要发火,收破烂的抢先大喝一声:“你干什么?!”
叶童自知理亏。脑门子上的火气就像受潮的柴火冒烟,蔫了。他讪讪地给收破烂的人一个发霉的笑脸,挥挥手,很大度地允许那人走自己的路。收破烂的还不省事,又骂了一句:“吃饱了撑的。”骑着三轮车悠悠地走了。
TMD,叶童叹了口气。想起早晨离家时骗老婆说,要到图书馆看书。要是老婆看到他这一幕,还不知道要怎样笑话他。唉,我叶童怎么尽干这等没屁眼的事。真是糊涂啊!叶童狠狠地责怪了自己一通,想起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转念一想,一个大人物在出名之前有时也难免有些奇奇怪怪的举动吧?这么想着,叶童的心就放平了。
拐进一个悠长的巷子,走到底就是农贸市场了。叶童在菜场的肉案前掏出舍不得破开的大额钞票,买了一根肉骨头。老婆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需要适时补钙。叶童看见一个妇女指指戳戳地在一个大盆里捞虾,便问这虾怎么卖?虾老板说:“二十八块钱一斤。”
叶童嫌贵,虾老板便一脸的不屑,只顾做那女人的生意,不再理睬叶童。叶童触了霉头,心里憋气,看见地上有一只蹦出来的活虾,个大须长,一脚将那只虾子碾成了肉泥。偏偏虾老板看见抄网里蹦走了一只虾,正从柜台里伸出头来寻觅,见到的只是一小摊白里掺黑的肉泥,还有叶童离去的背影,气得破口大骂:“狗日的,吃不起虾踩老子的虾。”
叶童明知道是骂自己,也不回头,径直走了。
叶童提着两块豆腐、一斤鸡毛菜,还有一根给老婆补钙的肉骨头走回家来。他心里还不能释怀被人骂了“狗日的”,愤愤地想:瞧你那熊样,敢小瞧老子。老子住八十平米的房子!想到房子,叶童的腰杆子就挺直了。一般人住的都是两室一厅五十几、六十平米不到的房子,叶童按揭拿下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提前迈入小康,使他有资本骄傲。
叶童的房子大,大得几乎空荡荡的。这套房子榨干了他的全部积蓄,使他既没有力量搞装修,也没有能力添置像样的家具,就连日常开支也不得不精打细算。每月不吃不喝先付出五百元的贷款按揭,对于叶童的生活着实有不小的压力。他时常想发一笔意外之财,这种想法好像一块火炭,有时灼得他的神经都有点儿疼痛。
站在门前掏钥匙的时候,他想像是从吃角子老虎机里掏出了一把硬币,那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真是美妙无比啊。
门,在他面前自动地打开了。老婆小枝横眉立目地站在门里吆喝他:“死哪儿去了,这么一个上午!”
叶童拎起手里的肉骨头,说:“我买了你喜欢吃的肉骨头。”
小枝不领情,仍旧没好气地说:“现在才买回来,吃个屁!”
叶童也觉得晚了,低头走进厨房忙活去了。小枝像个爬粪团的屎壳郎那样跟在后面,不时絮絮叨叨地发着牢骚。
叶童在厨房里忙得大汗淋漓,还要听老婆唠叨,心里窝火得要命。他做了一菜一汤,菜是麻辣豆腐,汤是没有煮好的肉骨头汤,下了一把鸡毛菜。
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小枝只吃了半碗饭就吃不下了。叶童看见小枝没胃口,自己的胃口也倒了。
远处传来知了的叫声,一声声叫得日头起火。天气是无比的炎热,客厅里的吊扇虽然开到最大档位,可是风是热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小枝是个怕热的人,她对住这么大的房子竟然买不起一台空调早已埋怨了不知有多少遍了,此时,懒得再说,只是恹恹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像一个作风不正的女人那样扭搭着,那一张脸阴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叶童其实更怕热。因为他心里的懊恼随着小枝的不满成几何级数上升。百无聊赖中他想出一个降温的法子。不是有电冰箱吗?他用七八个碗盛了自来水,一一放在冰箱里冷冻。等到它们都变成了冰疙瘩,把它们拿出来,放在吊扇底下吹。按他的想法,冰在融化时要吸收热量,这样屋子里会凉快一些。他为自己的这个发明感到兴奋。忙活了半天,房间里的温度不但丝毫没有降低,自己反倒又忙出一身汗来。
这时,他感到家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氛,好像什么地方不对劲。回头看见小枝歪斜在卧室的凉席上,用一种毒蛊的眼光嘲讽地盯着他。他陡然明白了自己在做一件近乎白痴的事情。他恨不能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叶童真正有一次重要发现,那就是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从前他总是自视甚高,觉得自己什么都行。虽然大学没有考上,可是他还是好学上进的,而且通过自修考试,他也拿到了大专文凭。他觉得自己还是蛮不错的。尤其在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和贷款经纪人证书之后,他更是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儿了不起。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怀疑。当他忽然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重要缺陷时,这种感觉是惊心动魄的也是令人心碎的。
叶童丢下小枝在家睡她的午觉,来到大街上。家里八十平米的房子虽然令他骄傲,可是,这所房子好像越来越盛不下他了。他在家里时常感到憋闷,需要到外面来放松放松。近来他迷上了上网,要不就去电玩城打游戏机,把零钱换成硬币喂吃角子老虎机。那台老虎机出现在电玩城里的时间还不太久,可是累计起来,已经吃掉叶童好几百元钱了。唉,钱啊钱!都是叫钱害的。要是有钱了,生活还会是目前这个熊样吗?
夏季城市的午后,人迹稀少。太阳挥洒着寂寞的热情。叶童漫步在滚滚热浪之中,昏昏然把自己变成了一台自动取款机。
这是一台长了两只蚂蚱似的长脚的自动取款机,它在城市的大街上蹦达着,逃避着顽童的追捕。一群戴着圆顶宽檐制帽的孩子拿着长长的竹竿,竹竿顶上是一个白色的纱筒,要将蚂蚱似的自动取款机罩住。可是,蚂蚱似的自动取款机个头那么大,纱网怎么能罩得住呢?自动取款机还是铁制的,一下子就将纱筒戳破了。叶童哈哈大笑起来。他太高兴了,没想到他自己就是一架自动取款机啊……他的嘴里吐出的话,马上就变成了钞票,这些钞票上印着精致美丽的花纹,就像苏打饼干上印制的那样。可是,他不能多吐,因为一吐出来,马上就被那些拿竹竿网兜的孩子捞了去。他不能便宜了他们。叶童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好孩子,都是自己前世的对头和敌人。他要耍弄他们,把他们的热情和精力耗干,把他们的膏血和体力榨尽,让他们像一群讨饭花子那样跟着自己。
这台蚂蚱似的自动取款机在大街上边走边跳,手舞足蹈,他太得意了,几乎是得意忘形。他还在跟身后的那群贪得无厌的孩子厮缠,他骂他们没有素质,戴着大盖帽,人五人六的。可是,大盖帽那么大,人却那么小,罩得几乎就只看得见下巴颏了。他们追着他跑得渴了,除下帽子来舀水喝。喝水的时候伸出舌头来舔水,这个动作让他看出来了,什么孩子呀,其实就是一群狼孩。
“嘿,狼孩,这块饼干沾了敌敌畏,你吃吗?你吃吗?”
他吐出一张张精美的钞票来逗他们说。可是,这种警告就像风对芦苇说“你不要摇不要摇”一样,越是说得狠,越是摇得厉害。敌敌畏怕什么!就连砒霜、氰化钾都不在话下。你吐出来,吐出来呀,他们追着他逼着他,一个个像发了疯那样,他只好又逃跑,这回可是跑不掉了,他们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几乎将他按倒在地,从他嘴里掏出他们想要的饼干。他们细长的爪子探进他的喉咙,把他搞得恶心起来,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呕吐了。这时候,狼孩们可高兴了,并不嫌他呕吐出来的秽物肮脏,大把大把地捞将起来。
蚂蚱似的自动取款机抽个冷子,从地上蹦了起来,一下子摆脱了狼孩们的围追堵截,拐过一个弯,甩掉了脏兮兮的人群。这时,他感觉到自己灰头土脸的,像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囚犯,又被人痛揍了一顿。
“锵,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叶童变的自动取款机在大街上唱道,“将你打……”
迎面开过来一阵游行的队伍,队伍中间缓缓行驶着一辆纸板扎的车子。车边插着彩旗,彩旗下,一群戴着钢盔的卫士做威猛狮虎状,他们保卫着社火芯子里八仙造型的戏角儿。
蚂蚱似的自动取款机寻思不妙,恐怕又将遭到洗劫,连忙逃进一个僻静的巷口。这时,从巷口里走出一个熟人来,叶童刚要大叫:“小枝救我!”不料,小枝上前劈面打了他两记耳光,骂道:
“你好大的胆子!跑到外面来找死,有屎不晓得屙在自家田里。”
打完了,嫌手痛,揪着他的耳朵拎起有一尺高,吆喝着:“吐!吐!把你肚里的货都给我吐出来。”
蚂蚱撑不住自动取款机的模样,现形为一只瘦弱的蚂蚱本相,并且终于吐出了黄水。叶童小时候捉过无数的蚂蚱,他知道蚂蚱一吐黄水,就完蛋了。
叶童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恍惚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里他像一只蝴蝶追逐着金色的花朵,可是那些花朵都是纯金制作的,非但不能采蜜,还把他的喙弄伤了。
小枝午睡已经起床,穿了一件孕妇穿的连衣裙,在镜子前试看腰身。离胎儿出世的时节还早得很,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娇惯得了不得了。已是做晚饭的时辰,小枝什么也不做,一切都等着叶童。叶童虽然老大的不乐意,可是遇到小枝这样的,他也毫无办法。
晚饭时骨头汤已经熬得相当浓了,下了木耳,味道很好。叶童尝了一口,啧嘴称赞道:“哈,太好吃了。”
一个满足迅速消退,一个不满足迅速来临,小枝说:“比鸡汤的味道差远了。”
叶童看小枝贪婪的样子,忍不住想起他们之间关于吃的一个典故。那是恋爱的时候,小枝因为家里人反对,声称要自杀,跑到桂林去找死。叶童一路跟着小心劝解,不幸他们的钱差不多花完了。在最困难的窘境里,叶童掏出仅有的零钱,买了两只茶叶蛋,递给小枝。按他的想法,小枝肯定会让一枚给他,他和她一样饿得头晕眼花。可是,小枝飞快地剥了蛋皮,眨眼之间把两只鸡蛋全吞进了肚子,叶童在一旁傻看着,伸长了脖子咽口水,口水真多啊!稍不留神几乎要呛了他。这事叫叶童明白了,小枝绝不可能自杀。
吃过晚饭,叶童早早地躺下。夜里十一点,他要起床去上大夜班。他在钢铁厂上班,干的是行车工,要是不休息好,迷迷糊糊的出了事可不是玩的。可是,叶童却睡不着,那个自动取款机的幻影像一支打进体内的兴奋剂,让他觉得有什么好事正等着自己。
叶童穿上了工作服,骑了一辆吱吱作响的破自行车,一晃一晃地到单位去上班。他想上班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挣钱?如果上班是一种精神的需要,那样的日子才是人的生活吧?他迷迷糊糊地爬上了行车,开始了这一个大夜班的工作。
行车吊起了一排三根通红的钢坯,那些沉重的钢坯在行车的吊钩下变得像几根火柴棍一般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叶童变得自豪起来,觉得自己是力大无比的大力神似的。他操纵着把杆,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感觉就是一个主宰世界的神祇。
这种感觉欺骗了他,使他再一次变得像一台自动取款机那样倨傲。可是,他看见的却是吊钩下的通红的钢坯撞倒了发青的钢垛。一个领行工在钢垛下立即被轧得发出红色的呐喊。
呐喊声叶童并没有听到,叶童是从他张开大嘴的姿态判断他是惨叫了起来。看见鲜红的血液喷溅在青色的钢垛上,叶童下意识地觉得好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经事,火柴棍似的东西轻轻触碰一下,就出血了。但是,仅仅是极短的几十分之一秒后,叶童的冷汗就下来了。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
他的自动取款机的梦还没有完全破碎,他看见领行工咧开的大嘴里吐出一股股鲜血,就像自动取款机吐出的钞票一样。他的意识像镭射舞台上忽明忽灭的灯光,一会儿是事故现场,一会儿是自动取款机。在这种朦胧迷离的情境中,他就像一只大鸟,从十几米高的行车上飞身扑下,向着那喷涌而出的钞票似的鲜血一头抢来。
责任编辑苗秀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