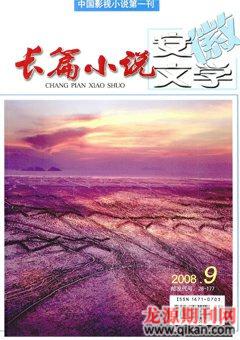乡野人家
孙流航
萍子坐在场上一个小木凳上奶孩子。小木凳又矮又小,萍子就像坐在地上。她一边奶孩子,一边又给另外两个稍大点的孩子喂饭,同时又不停地瞅一眼晒在场上的粮食,有时也会瞥一眼在老樟树下闲话的男男女女。萍子放下碗筷,轻轻拔出怀里孩子的奶头,孩子吞下口里的奶水就“哇”地一声哭起来了。萍子抱起孩子调个头,赶忙掀起上衣,挺挺胸,把另一只奶头塞进了孩子的嘴里,孩子含糊不清的哭声在吮奶过程中渐渐平息了。这时,谁家的鸡一前一后一步步探了过来,萍子赶紧大声地叫了几声,鸡们被撵跑了,怀里的孩子却受到了惊吓,又“哇”地一声哭响了。萍子低下头,轻轻呼唤着三丑,三丑。说,别怕别怕,妈妈在这里。她拍拍孩子的小屁股,又连忙揪揪孩子的小耳朵。这揪小耳朵可是山里人的讲究,意思是魂魄就不会被吓跑了。这山里的男女老少,小时候都这样,被他们的母亲揪过不知多少回了。萍子扭身准备捡起放在地上的碗筷,却见大丑二丑两个小家伙,正伏在碗旁用小手抓着吃得很香甜,弄得满手满脸,脏兮兮的。萍子生气地抬起手要打下去,但那只伸在半空中的手又软了下来,想想孩子也可怜,半年都没吃过一次肉,更何况这还是伴有香菇的红烧肉,别说孩子,自己口水也一股股往外涌啊。
太阳渐渐西沉,一会儿就躲进山背了。今儿太阳好,家里的粮食都晒上了。萍子的丈夫贺平来收粮食,走过来就绷起脸在三丑头上敲了几下,说,狗吃的就知道吃。三丑吐出奶头,扭曲得嘴不是嘴鼻不是鼻,可怜巴巴的看着娘,萍子眼泪却先流了出来。她顾不得孩子哭泣,赶紧去帮忙。他们小心地收拾着,没把一粒粮食掉在地上。
乡野安静、平和。夕阳西下的时候,山民从田间归来,女人忙着收捡晾晒在外面的什物,时有吆喝牲口,呼唤孩童的声音,几声狗吠,又几阵寂静,随着缕缕炊烟的飘起,山村的夜色就不声不响地降临了。
一灯如豆,照着祖辈留下来的老屋,屋内简陋的陈设和农家一些乱七八糟的工具隐约可见。这没关系,祖辈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悠然自得地生活着,就算是黑灯瞎火,闭着眼他们也能找到需要的东西和做着该做的事情。萍子洗好了锅碗,接着帮孩子洗澡换衣,打水洗衣服,她不喜欢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做。
萍子说,妇女主任又来过了,纯女户也要扎了,不扎罚款五千,哪罚得出啊。贺平闷闷地坐在灶前,头深深地埋在两腿间,一句话也没说。
秋季计划生育,萍子做了手续,夫妻俩既痛苦又无奈。
萍子站在家门口,抬头是一派山脉,似近似远,朦朦胧胧,要是一阵雷雨过后,那山就走了过来,花草树木格外地清新悦目,少妇似的妩媚妖娆。村庄前后的山却很平缓,山脚下有一垄垄稻田,一条小河从稻田穿过,七弯八拐的不知要流向何方。村庄是美丽的,村头有棵古老的樟树,村前后有果树、菜园、池塘、竹林……一条古道从村口伸出来,通向了外面的世界。
村落古老,山民在这里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一代又一代,不记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萍子结扎休养期间,也会带着三个小女儿到村头老樟树下去玩。老樟树枝繁叶茂,像把巨大的凉伞。老树的虬根盘根错节,有的凸现在地面而又深深地捉牢大地。人们坐在凸起的根系上谈今论古,絮絮叨叨,说的也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没什么新鲜,不过是穆桂英劝父投宋嫁了杨宗保,刘邦最终还是打败了楚霸王。再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谁家夫妻闹别扭了,谁家婆媳闹不和了,谁家生了儿子或女儿,谁家某某和某某偷情了……有些事说起来神神秘秘,绘声绘色,说完或心情沉重地叹几声,或挤眉弄眼地笑一笑,也就完了,就又各自忙自己的日子去了。
萍子生下的三个女儿,也和她一样美丽可爱,玲珑乖巧,每个人见到这三个孩子都想抱一抱,亲上几口。萍子就这样在失落与盼望,痛苦与喜悦中抚育着她的女儿们。看着三个女儿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懂事,一天天漂亮起来了,萍子感到这就像她种下的庄稼,总有收获的一天在那里等着她。
那天萍子从田地上归来,经过老樟树,树下正在说话的人们见她过来,谁也不做声了,萍子感到非常蹊跷,她意识到刚才的谈话肯定与自己有关,便停住脚步,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们。其中一个说,你老公和人吵架了。萍子听了抬脚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看见贺平气鼓鼓地坐在屋里,口里喘着粗气,一副非常骇人的样子。萍子小心翼翼地问,出什么事啦?话音刚落,贺平的拳头就打了过来。萍子不明不白地挨了打,她委屈地躲到房里去偷偷哭泣。萍子习惯了,贺平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变得粗暴蛮横,很少给过她好脸色,若是与外人斗嘴吵架了,回来总拿她出气。萍子知道,就因为自己没生儿子,使他在人前抬不起头。乡下人最怕别人说没人接香火。如果有人骂了一声“绝代鬼”,贺平会像疯狗一样和人斗起来,回到家萍子准要挨揍。俗话说,母随子贵,这话自古就有验证,别说平民百姓,就是皇宫妃子,生了个龙子,皇帝老儿也会对这位妃子格外施恩。可这生儿生女又不是工厂制造产品,要想自己的产品成什么样子就能成什么样子的。每对夫妻干的都是盘古开天地以来同样的“生产过程”,可得出来的“产品”,从来就不会像工厂产品一样,大小、规格、性能等等完全相同,他们有的是男婴,有的是女婴,有的脸蛋漂亮,有的并不雅观,有的聪明乖巧,有的拙笨迟钝,甚至还有些次品、等外品,那些更是千奇百怪,不谈为好。这两个人办的“工厂”,出什么样的“产品”,为什么总把责任推给女人呢,这太不公平了,也太没道理了。
春花秋月,几度夕阳,古老的樟树却年年总是这样,不愠不悦,无喜无忧,惯看着山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多的惊喜,像对面的山脉,衣着颜色,四季轮换一下,它的高矮胖瘦,恒古如此,是个永久不变的主题。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山村的崽哩妹咀背起了简陋的行囊,从村口那条逶迤的羊肠古道出发了,赶赴远方的沿海发达地区,他们背叛了父辈的生活规律,他们鼓起了稚嫩的翅膀,向着蓝天开始了艰难的飞翔。
这个时候起,老樟树下人们的话题就有了新的内容,开口闭口就谈海南、深圳、打工、经商,这些都是人们极感兴趣的话题。
这个时候起,山村开始在悄悄发生着一些事,先是像山藤似的长丝牵进了村里,于是山村的夜不再黑暗,从土屋窗口射出来的光,照耀着门前远处的树林,像月光,冷静,却美。
山村的女人也在悄悄地显露出一缕时代的气息。冷不丁,一位小妇人脚下穿了双薄薄的袜子,能紧能松,穿上它就像是生在脚上。还有那双皮鞋,浅红色的,后跟是个细钉子,走在山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响声很富乐感,让人听着听着,好像那小妇人就是用那铁钉子在山石上奏着一首乐曲呢。过不了多久,又一个小妇人(也许是大姑娘),穿出了一件花里胡哨的的确良衬衣,垂直而平整,透亮而光滑,真是美极了。萍子好羡慕,虽然自己三十多了,但毕竟是女人,多么希望也能时髦一下啊。也别说,萍子不老,如果打扮打扮,一定是更漂亮,更有韵味的一个女人。新年临近,萍子从城里买回来一条仿丝织品翠花围巾,躲在镜子前认真细心地摆弄着,镜子里显露出她的天真和稚气,羞涩和娇美。萍子又像回到了少女时代,绯红的脸上盛开着一朵美丽的花儿。二丑歪头仰视着妈妈,偷偷讪脸。萍子发现了,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头,笑着说,鬼妹咀。这时贺平走了进来看见,劈手夺过了围巾,接着就是一巴掌,萍子头一偏,身子就软了下去,蜷缩在地,捂住脸无声地啜泣起来。二丑一双茫然的大眼,呆呆地望着身边这个高大的男人。
山村的新年不比从前了,从外地回家打工的青年人,穿戴举止时髦洒脱,给山村增添了新鲜血液,一改从前的沉闷和苦涩,村头巷口时时飘来他们爽朗的笑声和流行歌曲。他们穿着令村里老人目瞪口呆的服装,说着一句半句令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有位老婆婆拉住她的孙子说,崽呀,快脱下这条裤子来,让婆婆帮你缝补缝补,看我孙子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照料,裤管都烂成了这样,也没人拾掇拾掇。婆婆眯起老花眼凑近又仔细看了看,说,唉,这裤脚像个喇叭,腿部又这样小,多难穿,快脱下来……孙儿听了,笑嘻嘻地说,婆婆,这叫牛仔裤,买来就这样,不是穿烂了,现在外面很流行。婆婆听了,还以为孙子在戏弄她呢,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时兴穿烂衣服呢,怎么会时兴穿烂了的衣服呢?这时,几个青年崽哩妹咀站在门口,有人问,哎,去县城吗?青年忙接嘴说,ok,马上动身。说完从后房提出个包就飞出了大门,出了门青年又转头扬起手,对着婆婆说了声Bey bey。接着便一阵风样跑了。婆婆不知所云,说,这崽哩,唉,抿嘴笑了笑,转身走进灶房忙去了。
在外打工回来的青年中,有两个趁过年把喜事办了。婚礼的程序还是按乡俗进行,所不同的是新娘穿了身白色的婚纱,在城里照了个相。那相照得很大,不像他们父母那时结婚的相片,一个梳头用的镜框背面都夹得下,而是高高地挂在新房的床头,像过年买回来的一幅贴在壁上的画,色彩非常漂亮。就这相片,父母气得很厉害,说,结婚穿白衣,像什么话?青年说,白象征纯洁无瑕,爱情天长地久,全世界的人结婚几乎都这样,你们又不懂。
大丑随时代洪流也卷去了沿海。但大丑没有回家。她来信说,过年春运拥挤,车票加价,不回家了,就在那边过年,照常上班,老板说了,春节工资加倍,希望双亲不要牵挂。同时萍子还收到了一张汇款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六千元,萍子看了心里一震,她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钱呢!?萍子看见别的孩子回来了,心里暗暗埋怨女儿,为什么不回来呢?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年大节大么。特别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结婚了,心里更是空落落的。女大是别人家的人,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到那时,心里不知会有多么难过啊,萍子不知怎么眼睛竟汪满了泪水。
女儿慢慢都大了,家务琐事也就渐渐少了,晚饭后,萍子会早早地和丈夫进房去,其实也没睡,只在房里坐着,萍子做点针线,贺平坐在一旁抽抽烟,两人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不关痛痒的闲话。有一次,贺平却对萍子郑重地谈起了家里的一件重要事情。他说,想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了有个依靠。萍子听了心里一颤,一是女儿小,二是招上门女婿不比女儿嫁郎,这事弄不好会废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如果女儿大了,自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愿进门,那还可以,要是现在父母包办,只为找个女婿上门了事,不管他是好是坏,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是个公的就行,那肯定以后会招来一些想不到的后果。萍子一边做针线,一边微微抬了抬头,说,你看着办吧。不过女儿太小,又在外地,你总应让她看上一眼才行吧。贺平说,帮老二找,老二更听话,留在身边好些。萍子说,她更小,还在读书呢。贺平说,马上就初中毕业了,毕了业别读,先帮她找个进门,让他们熟悉熟悉,待大了就结婚。再说,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早一点总比晚一点好。萍子低着头“嗯”了声。贺平接上说,这事还是你去办好,男人不方便,尽和些女人说过来说过去的,我没这个耐心。萍子说,好吧。
萍子虽不愿,但丈夫有了这个打算,不去办肯定不得安宁。同时,萍子也有点幻想着真能找到个娘疼女爱的好郎崽。萍子要把这个意思传达出去,可这又不是按常规婚嫁讨娶,更不是推销产品,可以大张旗鼓打广告。这是一种特殊的婚姻,虽说不违法,但在乡下也不是很体面的事,所以只能在适当的时候向有点交往的人,含蓄隐约露出一些意思来,表示虽出于无奈却十分诚心,以便引起外人的同情和支持、理解和帮助,争取更多人的努力,精心物色中意的崽哩。所以萍子有闲时,便有意去老樟树下坐一坐,玩一玩,遇上平时玩得好的姐妹或婶婶大娘什么的人,她就由远而近,由浅而深,把话慢慢拉近主题。山民都淳朴、热心、肯帮,还没等萍子把话说透道明,大家就忙着出主意,定点子。说,三个女儿嫁两个,留个招上门女婿,老来才有人端茶送水,传接香火。萍子见有这么多人帮忙,心想也许会如愿。可过了一段时间萍子才知道,办这事远比她想象的还要难。是啊,有谁会愿意来这个山旮旯呢,有谁会愿进萍子这个破屋烂舍的家呢。愿来的全是……所以一些好心人四面张罗,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到处打听说合,虽介绍了那么一些,却没一个能中意的。
二丑人小鬼大,家里似明似暗发生的这些事,她慢慢摸清了底细。有天她伏在娘怀里哭了。说,我太小,我什么也不懂,我就是死也不干。可就在这时,好心人介绍了一个崽哩来,不要说人长得太一般,书连小学都没念几天,但贺平却中意了,而且谈得八九不离十了。萍子就急了,她劝丈夫再缓缓,再找找。贺平找得有些心急,有些气馁,说,就这个吧。萍子就更是慌了,她找来二丑商量。二丑骇得粉红的脸都变黄了,急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哭。萍子搂着女儿,母女俩哭成了一团。
毕业考试过后,二丑突然失踪了。萍子夫妇四处寻找,但没一点音信。萍子起初在丈夫面前伤心地哭泣着。贺平因二丑一不听话,二来也为找她劳民伤财,气不打一处来地骂萍子,你哭死,只当没生这狗吃的。萍子的哭泣就真的停止了,说,你心真狠。贺平的心也不一定真狠,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二丑还是没一点儿消息,本来沉默寡言的贺平就更加寡言少语了。有一天,萍子看见贺平坐在那儿,头又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半天也没见他把头抬起来。萍子轻轻地走过去说,贺平,你也别太难过了,二丑那么大,又读了那么多书,我想她是不会有事的。贺平猛地抬起头来,问,你知道她在哪里?萍子骇得连连后退,忙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劝你啊。萍子以后再见到贺平郁郁寡欢、失魂落魄的样子时,欲言又止,犹犹豫豫。但还是一转头走开了。
二丑失踪了两年,后来才知道逃往姐姐那儿打工去了。这一年,三丑考进了县城重点高中,贺平淡淡地说,不要读了,读那么多书,花那么多冤枉钱,不如去打工更合算。萍子很生气,可又不敢顶撞丈夫,于是偷偷写了封信去远在外地的两个女儿。女儿很快来了回信,还寄来了钱。钱是走学校寄来的,寄给了妹妹的老师,也是两个姐姐的老师,两个姐姐原来读书也是又聪明又用功,很受老师喜爱的。本来读下去很有希望,但大丑因家贫,二丑为逃婚,都失学了。因此两个姐姐求老师,帮助三丑办好进城读书手续。说现在已经是一九九三年了,新世纪都快到了,没有文化科学知识不行了。现在有条件,做姐姐的就不能再让妹妹错过机会,误了前程。贺平在女儿的资助和老师的劝说下,也没话可说了。
家里有了两个赚活钱的女儿,日子渐觉宽裕了。两个在外面的女儿也很争气,一面打工,一面学习文化和技术,还到深圳培训了一年,两人都取得了一个什么证书了。萍子心情渐渐好了起来,脸色又开始红润了,人也精神了。没事的时候,萍子会打开那只半导体来听广播。虽然有的人家已用上了录音机,但萍子还是喜欢她的半导体,小巧、省电、方便。听听新闻,听听歌曲,还有天气预报和故事等等。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听着歌曲,眼睛看着手上的针在上下晃动,脑子里却在想着家里哪些衣被鞋袜需要换洗一下,明天做什么饭菜给贺平吃,两个大女儿在上班吗?小女儿下课了吗?自己也就大女儿这般年纪嫁了过来,日子好像没过很久,怎么女儿也就这般大了呢。这日子看起来过得慢悠悠的,但一转眼,怎么人就好像都老了呢。萍子一回神又责骂自已,这乱七八糟尽在想些什么啊!一时想到东,一时又想到西的。这时间明明是过去了嘛,刚嫁过来时,大家还是一窝蜂地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呢,现在分田到家都十几个年头了。从前生产队一年四季忙得团团转,老牛耕田,跪着耘禾,铲草积肥,采叶灭虫,栽、刈、打、碾等等的都是这双手。现在就不同了,手扶拖拉机、栽禾机、收割机、刮米机、除草剂、化肥、农药等等什么的都现代化了。就是看电影也不用放映队下村来,有几户人家已买上了电视机,想看什么节目就有什么节目,怎么能说没过多久呢?当然,论起人类的历史来,这真就一眨眼功夫,在这一眨眼功夫里,却有这么大的变化,萍子感到比起她的父辈来真是幸运啊!想到这些,萍子就笑了,笑得很满足。
村里有几栋新盖的楼房,萍子心里好生羡慕,那么气派,那么适用,顶层好晒物纳凉,室内光线明亮空气新鲜。贺平不让小女儿读书,为的也是想累些钱盖个小洋楼。他说,女儿读书都装在她脑子里,待长大了嫁人时,什么也带出去了。让她打打工,赚些钱,盖个楼房还可留在娘家。萍子虽喜欢小楼,但她更不愿误了女儿。萍子想,知识才是无穷的财富。如果没有科学知识,没有人发明“除草剂”,现在还得跪在水稻田里耘禾,乍暖还寒的季节,又冷又脏,一身都在淤泥里滚来爬去的。水田里还有那个讨厌的蚂蟥,没骨没肉,软软绵绵,咬住你脚上的皮肤拼死吸你的血,吸得鼓鼓胀胀,抓都难抓脱,真是叫人恶心透了。女儿会读书,说不准将来也会发明一项什么,让全国人受益,那才不叫枉做一个人呢。
为招上门女婿,十几岁的二丑逃跑以后,和大丑几年都没回来过。萍子想女儿都要想疯了,但不管家里怎么写信、打电话,发电报,她们就是不回来,好像她们有千里眼,看出了家里的谎言。总是说,我们在外好、忙、老板不放等等。萍子对贺平说,女儿大了,我也拿她们没办法,我也是一样想女儿啊。贺平就更没辙了。
这一年夏天,三丑高考后盼来了一纸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萍子喜不自禁,贺平这时也高兴了,两个在外的姐姐更是兴奋得没法说了。她们主动打来电话,说马上请假回家,合家庆贺一下,要欢天喜地送妹妹去上学。萍子接了电话后,几个晚上都没睡觉,高兴得什么似的。
萍子两个女儿回村的时候,引来了一村人的目光。那是个下午,两姐妹都是穿的一身浅底碎花连衣裙,天仙样的美貌动人。村里人原先还没有发现她们的美,就像她们的父亲,当年帮她们取名一样,一个一个都叫丑!丑!丑!
大丑二丑还带来了一个高个子男青年,那青年领带系在花格子衬衫上,飘逸的西裤,锃亮的皮鞋。这三人把一个村子都映得亮了起来。萍子屋里挤满了人,萍子的屋太小,大门外也站满了人,大家议论纷纷。三丑看一眼男青年,转头用询问的目光盯着二丑,说,二姐,他是……二丑说,他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三丑做着怪脸不依不饶嘟着嘴说,我不是问这个。二丑就附在三丑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句,三丑张嘴“啊”了一声,看着大丑就坏笑起来。大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时二丑问,爸爸呢?大丑也问,爸爸呢?萍子说,他去商店打酒了。二丑突然想起什么,神秘兮兮地把妈妈拉到房里,叫妈妈闭上眼睛,等一下又叫妈妈睁开眼睛,萍子就看见一方漂亮的真丝翠花围巾。但二丑的美貌冲淡了围巾的色彩。二丑一把抱住妈妈,萍子感到二丑的力气真大。她偎在女儿的怀里,感到非常的幸福。
这两天,老樟树下聚拢了很多人,他们感慨、赞叹、津津有味谈论着萍子三个女儿的事。这世上一些事,也真是不可一言而定,喜、忧、祸、福,谁能料呢?
责任编辑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