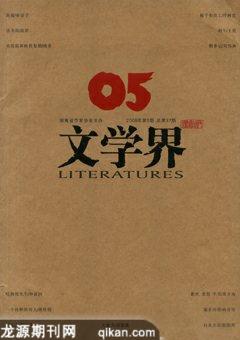唁燕郊先生
编者按:今年3月31日凌晨3时56分,我国著名“七月派”老诗人、本刊顾问彭燕郊先生因病去世,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刊出不少纪念文章。对彭燕郊先生的去世,我刊同仁在震惊和悲痛之余,不仅撰文寄托哀思,也特意将钟叔河先生和唐浩明先生对彭燕郊先生的怀念文字辟专栏刊出,以表达我们对彭燕郊先生的敬意和追思。
彭燕郊先生长我十一岁,确实是先生,八十八岁了,遽尔辞世,得讯愕然,因为春节打电话来拜年,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爽朗;既而怃然,觉得认真写作者又少了一个,尤其是写了一辈子七十年的,恐怕真已为数无多了。
几年前黄永玉来长沙,约彭和朱健和我吃饭闲谈,彭的谈锋最健(本也只有他跟黄认识最早)。黄对他说:“还记得吧,你最早的诗集,封面还是我画的,这也是我最早画的封面啊!”这引起了他二人对文坛旧事的回忆,慢慢便谈到了如今人称“大师”的某某某,说他五十年前为大人物供奉春药秘方,又将大人物同众人合影中众人抹去,只留下贴身站在大人物后面的他自己。于是引起一阵哄笑,这是讥嘲大人物的笑,是鄙薄奸佞者的笑。彭的年岁最大,笑声却最响亮,精神特好。
在那次以后,我跟彭又有过几次同席或同车时的交谈,谈勃洛克,谈劳伦斯,谈戴望舒,`也谈胡风,他的兴致都极高。有次我表示不喜欢胡风,虽然我1955年挨整,一条罪状便是“竟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不喜欢胡是因为胡其实更左,周扬还要朱光潜和沈从文,胡却认为不该要。彭虽是老“七月派”,又谈得正在劲头上,却没跟我争辩,这看得出他颇有容人之量,对于满口伊里奇约瑟夫和苏联“文艺政策”的理论,也未见得那么认同。而他对中外作家和作品的博识,则更使我佩服。他说家中藏有印度的《爱经》,阿拉伯的《香园》,还有日本的画册,欢迎我去开开眼界,因素性疏懒,迁延未去,如今天人永隔,想去也去不成了。
在我心目中,彭始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老少年,从未显出在我身上早有了的暮气和老态。他兴致勃勃地谈话,兴致勃勃地交友,还兴致勃勃地买书。有回在张国强老板的书店里,一买便是一大堆,也不管有不有人开车送,还对我说,刚刚从别的店里买到一本你的《儿童杂事诗笺释》,看了看,觉得很好。我说,何必买呢,送你一本就是。他说,还是几年以前印的,你的样书早送完了吧。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在他来电话拜年时便说,要送本《青灯集》把他,随即托友人带去,此人因病耽搁,送到时彭先生已经快要易箦了,听说还亲手拆开了包封,拿出了书本,唉!
彭是著名诗人,诗如其人,也是生气勃勃的。近年他诗作更富,诗思更新,在诗中完全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谁知竟说走就走了呢?不说什么震惊与悲痛之类套话,刹那间充塞在我`心间的,只有一种感觉,人生无常,太无常了啊……
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八十多岁时写回忆,说她年轻时仿佛觉得自己是不会死的,极其执着和勇敢,敢于抗拒任何人或神鬼或命运,如果它们想来要她死;老后则一切都改变了,想到死时,只将它看作生之否定,看作“一条末了的必要的弦”,故并不怕死,怕的只是病,“即坏的错乱的生”。“可是病呢,直到现在为止,我总逃过了。”老太太说:“我于个人的不死已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希求。我的意识很卑微地与我的身体同时开始,我也希望它很安静地与我的身体一同完了。”接下去还有两句诗:
“会当长夜眠,无复觉醒时。”
我想,对生的执着和勇敢,比起哈理孙女士来,彭先生决不会逊色;她老来的思想和态度,即是上面最后这两行文字和诗句,颇带灰色,当过新四军宣传员的彭先生则未必能赞同。但我觉得,彭先生说走就走,也逃过了病,逃过了“坏的错乱的生”,其福气实不亚于哈理孙老太太;加上他又曾如此兴致勃勃地生活过,这兴致差不多一直保持到了最后,更为难得。那么,在长夜眠中的彭先生,应该也会得到真正的安息,不会再有什么遗憾和惊扰了吧。真的,如果我在死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一定是会十分满足的,故以此唁燕郊先生,并慰己怀。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