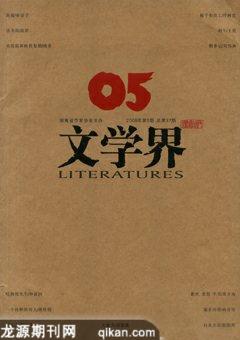劝胡霜和杨栓复婚
晓 苏
1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儿害怕见到我老婆了。在南方打工期间,我曾经和一个从贵州来的女人睡过一觉。当时,我身体一冲动就和她睡了,压根儿没想到对不起自己的老婆。现在马上要见到老婆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起来,感到没脸见她。
走到村口,我一抬眼就看见了那个废弃多年的砖窑。其实我最想看到的是我家的瓦屋,可惜它离村口还很远,被一道秃岭隔着,我踮起脚尖也看不见。砖窑却近在眼前,就耸在那道秃岭上,孤零零的,有点儿像我从前在电影中看见的碉堡。
我是开春以后离开油菜坡去南方打工的,记得那天我走出村口后还回头看了一眼砖窑。砖窑上竖着一根很高的烟囱,我看见有一只乌鸦落在烟囱上。当时我还想,等那只乌鸦飞走了我再走。可我等了好半天,它却一动不动。后来我只好先走了,要是再等下去我就会误过那趟开往南方的班车。
将近一年没见到砖窑了,它看上去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我没看见那只乌鸦,看来它早就飞走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只乌鸦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一年呢?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那根烟囱居然冒烟了,我看见几缕灰黑色的炊烟在空中摇摇摆摆。看来砖窑里住人了。
我一时想不出谁会住进砖窑。油菜坡这几年变化不小,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盖了房子,有几户人家还建了小楼,有谁还会去住那个破破烂烂的砖窑呢?后来我想,也许是外村来了一个叫花子吧?不过我没有肯定,砖窑是我回家必须经过的地方,心想走到砖窑门口一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砖窑离村口只有几分钟的路,我一支烟没吸完就走到了砖窑旁边。时间是中午,明亮的阳光照着砖窑,看上去像我在南方见过的一幅油画。我正要朝砖窑门口走近,一个穿红棉袄的女人突然从砖窑里面走了出来。她是低着头走出来的,我看不到她的脸。我故意咳了一声,她听到咳声猛然把头抬起来了。女人的头刚一抬起来,我就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天哪,原来住进砖窑的竟然是我的姨妹胡霜!
胡霜看见我也有点儿惊奇,她小声地喊了一声柳条哥,苍白的脸上陡然红了一下。胡霜是一个瘦女人,一年没见显得更瘦了,脸上好像一两肉都没有。她对我很热情,很快从砖窑里搬出一把椅子让我坐。不过我没马上坐下去,我呆呆地看着她,问她怎么会住在这里?胡霜没有立即回答我,又转身进了砖窑,给我端出了一杯茶。虽说我嘴里早就渴得快冒烟了,但我接过茶没有急着喝。我又一次问,胡霜,你怎么住在这里?胡霜突然低下了头说,我和杨栓离婚了!
我顿时大吃了一惊,差点把手上的茶杯掉在了地上。胡霜和杨栓在油菜坡是一对家喻户晓的恩爱夫妻,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们两个人会离婚。如果这话不是从胡霜嘴里说出来的,那我肯定会笑掉大牙。
过了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我先喝了一口茶,然后坐在椅子上。直到这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胡霜和杨栓真的离了婚。我还对胡霜说让她不要骗我。胡霜却说她没有骗我,还说她要是骗了我就是小狗!她这么一赌咒,我就不得不相信了。胡霜接下来告诉我,她和杨栓离婚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还说她离婚的第二天就住进了这个砖窑。
胡霜当时正煮着午饭,我正要问他们为什么离婚,她说她要进砖窑去给灶膛里加一把柴。看着胡霜的背影进入黑洞似的砖窑时,我的双眼猛然黑了一下。在胡霜从砖窑里出来之前,我使劲地想她和杨栓离婚的原因,但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一个眉目来。
胡霜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开水瓶,她默默地给我茶杯里加满了水。我喝了一大口,然后开始向她提问。我先问他们是谁提出来要离婚的,胡霜说是她提出来的,还说她提出离婚时杨栓死活都不同意,哭得三行鼻涕两行泪,后来还跪在地上求她不要离婚。
接着我问胡霜为什么要和杨栓离婚,胡霜先张开嘴巴想回答我,但刚一张开就闭上了。见她欲言又止,我就感到胡霜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过我没有就此罢休,反而越发想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接下来我就想方设法地开导胡霜,说婚都离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还对她说我又不是外人。经过我的再三央求,胡霜后来总算是开口了。胡霜说,杨栓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好像我的屁股坐到了一枚钉子。我起身的时候,茶杯里的水都泼了。胡霜也以为我屁股下坐到了什么,还急忙低头看我的椅子。我这时哈哈地笑了两声,一边笑一边说胡霜在开国际玩笑。胡霜说她没开玩笑,我说要是没开玩笑就是在编故事。我对杨栓是太了解了,如果有人问油菜坡最不好色的男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杨栓。杨栓从小正派,不近女色,平时连玩笑都不和女人开一个,怎么可能会在外面有女人呢?再说,杨栓又特别喜欢胡霜,爱都爱不过来呢,哪有闲心去想别的女人?
我笑了一会儿,突然严肃下来,指责胡霜一定是错怪了杨栓。胡霜却对我拍胸发誓,说她一点儿也没错怪杨栓,还说她把杨栓和那个女人当场捉住了。胡霜这么一说,我就傻了眼。
沉默了好一阵子,我问胡霜,杨栓在外面的那个女人是谁?可是,胡霜却不肯告诉我,不管我怎么问,她都守口如瓶。
砖窑里飘出来一丝饭香,胡霜说她锅里的饭熟了。她说完就转身朝砖窑里走,说她要进去炒两个菜,好像有一点儿留我吃饭的意思。我也随她进了砖窑,发现窄小的砖窑被胡霜摆得满满的,一边是床,一边是灶,中间摆着一张小方桌。不过她收拾得很干净,窑壁上还糊了一层报纸。胡霜一边炒菜一边问我喝不喝酒,看来她是真心留我吃饭了。
但我那天没在胡霜砖窑里吃饭。快一年没见到我老婆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和她团圆。临走的时候,我认真地劝胡霜说,你还是和杨栓复婚吧。胡霜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了。
2
翻过秃岭,我就看到了我家的那栋瓦屋,它坐落在秃岭对面的一个山凹里。瓦屋旁边有一棵柿子树,眼下树叶都落光了,树枝上只剩下红彤彤的柿子,远看上去像挂了一树红灯笼。
我没有看见我老婆胡雪,她这会儿可能还在田里忙着。胡雪贤慧又勤劳,我去南方打工后,家里的活儿都甩给了她一个人,真是把她辛苦坏了。一想到这,我就很后悔和那个贵州女人睡觉。要是胡雪知道我在南方干了这种事,她说不定要气昏过去。
走下秃岭是一条水沟,水沟边上有一栋石头房,胡霜离婚前就住在这里。本来我没打算进石头房的,可杨栓当时正巧在水沟里挑水,他一抬头就看见了我。这样一来,我就只好进他的石头房坐一坐了。
我开始差点儿没认出杨栓来。原来杨栓是一个白净而清秀的小伙子,穿着也很干净,看上去像那些来油菜坡扶贫的干部,现在杨栓完全变了一个人,蓬头垢面,胡子长得像野草,棉袄上脏兮兮的,五颗扣子掉了三颗,如果他不主动喊我姐夫,我还真认不出他了。
杨栓刚见到我时显得有点儿恐惧,手中的扁担突然落在了地上。我想,他肯定是害怕我骂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不过,杨栓很快就平静下来了,马上走过来跟我握手。我问他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说胡霜和他一离婚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他我见过胡霜,还说我在砖窑门口坐了好半天。杨栓一听马上就向我打听胡霜的情况,还问她吃过午饭没有。我发现杨栓虽然和胡霜离婚了,可他心里装的全是胡霜。
我和杨栓握了好一会儿手。松开后,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了他,质问他有胡霜这么可爱的老婆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我这话刚一出口,杨栓就抬起手来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同时还骂自己真不是一个东西。我接下来问杨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栓就邀请我进他的石头房坐一坐,说有些事只能坐下来慢慢地说。
石头房里静悄悄的,一点儿人气都没有。我问怎么没看见老人?杨栓说他们一个去地里扯猪草另一个上山捡柴禾了。房子里乱七八糟的,这里一只破袜子,那里一只烂鞋子。杨栓见我东张西望,显得很不好意思,连忙解释说一个离婚的人也讲究不了那么多了。
杨栓让我在火坑边坐下来,火坑里虽然烧着柴火,但不怎么暖和。他给我冲了一杯糖水,我接过来就喝了一口,这样才温暖了一点儿。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离婚的事情,杨栓却抢着说起来了,像是有满肚子的苦水急着找人倒似的。
杨栓的确和外面的一个女人睡了。事情发生在秋收季节,也就是玉米成熟的时候。那天早晨,那个女人突然来到了杨栓家,要请胡霜去帮她家掰一天玉米棒子。那个女人的男人外出打工了,她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这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油菜坡到外地打工的男人太多了,在家留守的女人经常请人帮忙干活。不巧的是,胡霜那天身体不舒服,她于是就派杨栓去帮那个女人掰玉米棒子。杨栓一向是个听话的男人,胡霜让他去他就乖乖地跟那个女人去了。那天的天气一开始是很不错的,天上还悬着太阳。临近中午时,太阳却一下子不见了,陡然下起了暴雨。谁也没想到那天会下雨,他们什么雨具都没带。幸亏玉米地边上有一个草棚子,那个女人就提出进草棚子里躲一躲。
说到这里,杨栓突然停下来,似乎不想再往下面说。其实他不说我也能猜出后面的事情来,杨栓和那个女人肯定是在草棚子里躲雨的时候发生了那种事。
我又喝了一口糖水。也许是杯子里的水冷了,我舌头上感觉不到一点儿甜味。杨栓朝我手中的杯子看了一眼,又往里面加了一些开水。然后,杨栓开始一边摇头一边自责,说他真不该进那个草棚子里去躲雨。我这时猛然想到了胡霜。我问胡霜是怎么知道草棚子里面的事情的。杨栓埋下头告诉我,胡霜看见天下雨了就去玉米地送雨衣,到了玉米地里没见到人,便找到了草棚子那里。胡霜一到草棚子门口就看见了杨栓和那个女人,他们那会儿正在慌慌张张地穿裤子。胡霜当场就晕头了,她的身体先晃了两下,接着就像门板一样倒在了草棚子门口。
杨栓一直没告诉我和他睡觉的那个女人是谁,好像是在有意回避什么。而我心里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见到杨栓就想问他了。那个女人对我来说简直成了一个谜。
后来,我直截了当地问了杨栓,杨栓的反应却让我大吃一惊。我刚一问,杨栓就愣住了,身体还剧烈地颤了一下,眼睛里闪出两道怪异的光。杨栓没有回答我,他突然将头垂下去了,像夹一只水壶一样夹在两腿中间。
我迷糊了一会儿,继续问那个女人是谁?我问了一遍又一遍,有点儿不达到目的就誓不罢休的意思。杨栓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就只好说出了那个女人。他的声音虽然细得像一根游丝,但我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杨栓刚一说出那个女人,我手里的杯子就砰的一声掉在了火坑边的石条上,玻璃的碎片顿时四处飞溅。杨栓说出的那个女人不是别的什么女人,她是我老婆胡雪!
我也算是一个聪明的男人,按说我早就应该猜到胡雪的。事实上在杨栓说到那个草棚子的时候,胡雪就在我脑海里快速闪了那么一下,因为我们家玉米地边上也有一个草棚子。但胡雪当时只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我实在没想到把胡雪跟那个和杨栓睡觉的女人联系起来。我想油菜坡上的草棚子到处都是,杨栓说的那个草棚子怎么可能就是我家玉米地边上的那一个呢?更主要的是,胡雪的为人我是了如指掌的,她是一个作风很好的女人,嫁给我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花花草草的事,甚至连一点儿风言风语都没有。像胡雪这样的一个女人,我怎么可能想到她会和杨栓睡觉呢?
过了许久,杨栓把头微微地抬了一下,用眼角的弱光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我当时的样子很吓人吧,杨栓只看了我一眼就又把头勾下去了。他勾下头说,柳条哥,我对不住你,要骂要打你随便吧!我保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但我没有把杨栓怎么样。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很想朝杨栓裤裆里踢一脚,恨不得把他的那玩意儿踢破。但我还没来得及伸脚,那个念头就没有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四肢无力。我当时的心情复杂极了,好像装了一肚子的乱麻,憋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外面传来一串轻微的脚步声,我想可能是杨栓的老人回来了。我马上站了起来,拔腿就往门外走。我不想遇见杨栓的老人,要是见了面大家都会很尴尬。我刚走出石头房,杨栓快步追上了我。他对我说,我想和胡霜复婚!我气不打一处来地说,要复婚你去跟胡霜说呀,跟我说有球用?杨栓说,他找了胡霜好多次,什么话都说过了,可她就是不答应。杨栓最后求我有时间去劝劝胡霜,说胡霜有可能会听我的话。我冷笑一下说,我也劝不了胡霜,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3
我是怀着一腔怒火回家的。离家越近,怒火越旺,我甚至听到了火焰烧心的声音。看到我家敞开的大门时,我情不自禁地捏紧了拳头,真想一进门就揪住胡雪,把她一口气揍成肉饼。然而,当我走到门槛外,我的脚步却一下子停住了。奇怪得很,我这时陡然又想到了和那个贵州女人睡觉的事。一想到那件事,我的脚步就停止不动了。与此同时,我捏紧的拳头也慢慢地松开了。后来,我扭身走到了瓦屋旁边,一屁股坐在了那棵柿子树下。
那个贵州女人在我打工的那个厂里煮饭,年龄跟胡雪相仿,就住在食堂后面的一间平房里。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睡不着觉就一个人出门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间平房前。平房的门没关严,有一丝灯光从门缝里流了出来。我从门缝里朝里面偷看了一眼,竟看见贵州女人在揉自己的乳房,她揉乳房的样子就像她白天在食堂里揉面团。可能是好久没看见乳房的缘故吧,我一看见她的乳房就激动得不行。当时我简直是疯了,一推门就冲进了房里。贵州女人被我吓了一跳,惊慌地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帮她揉乳房,说着就把手伸到了她的胸脯上。开始我还以为她会大喊一声抓流氓,结果她没喊,反而还双手一张抱住了我。
一只柿子突然从树上掉下来,啪的一声落在我的脚前,把我吓得大吃一惊。我伸手捡起那个柿子,看见它红得像火一样。这时我感到我的脸也红了,火辣辣的。我想我的脸看上去肯定像一个大柿子。
就在这个时候,胡雪提着猪食桶从瓦屋里走出来了。她是出门喂猪的,猪栏就在柿子树后面。胡雪很快看见了我,她一下子愣在了那里。我没有跟她打招呼,只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比我春天走的时候老了一些,面黄肌瘦的,脸上好像一点儿水分都没有。胡雪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她对我苦笑了一下,然后朝我慢慢走过来。她问我,回家了怎么不进门?声音里有一丝责怪的味道。我没有说话,我实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她。我也对她苦笑了一下。
我的行李包放在我的身边,胡雪这时看见了它。她赶紧放下猪食桶,提起了行李包,然后轻声对我说外面风大,让我快进屋暖和暖和,还说我的脸都被风吹红了。我犹豫了好半天,才慢慢站起来,很不情愿地跟胡雪进了瓦屋。
胡雪已经吃过午饭了,桌子上还摆着剩菜。她麻利地给我泡了一杯茶,亲自端过来放在我的手边。胡雪一放下茶杯便开始收拾剩菜盘子,说她马上就去给我煮饭。我仍然不说话,嘴巴闭得紧紧的,像一个天生的哑巴。
胡雪本来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现在却变得话多了,在灶台上一边炒菜一边对我说个不停。她先告诉我父亲到姑妈家给姑父祝寿去了,明天才能回来,接着说镇上的中学放假时间推迟了,儿子到腊月二十六才能回家,然后又说年猪早已喂肥,就等我回来请屠夫杀了。胡雪每说一句都要摆过头来看我一眼,看得出来她非常希望我能说点什么。但我真的无法开口。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胡雪把饭做好了,她一下子做了好几个菜,鱼和肉都有。胡雪还提来一壶酒,给我满满地倒了一杯。我没有讲什么客气,端起酒杯就喝了起来。将近一年没吃到胡雪做的菜了,我感到味道真好。胡雪坐在桌子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吃肉喝酒。
我不知不觉地喝多了,浑身开始发热,头上滚汗。胡雪这时把椅子朝我这边移了一下,问我,柳条,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也许是酒精起了作用,我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我大声地说,胡霜离婚了!
我的声音大得像一声惊雷。胡雪被我吓呆了,脸色一下子白得像纸。她用惊恐的眼神看了我好半天,然后瑟缩着说,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胡雪说完低下头去,嘤嘤地哭了起来。
胡雪哭的时候,我神情麻木地看着她。她哭得很伤心,肩头一上一下地起伏着,哭声由小逐渐变大。我的心开始硬梆梆的,她哭了一会儿后,我的心就变软了。有一会儿我还想劝劝胡雪,劝她别哭。但我没劝,我想让她哭一哭也是应该的,谁让她做对不起我的事呢?
我没料到胡雪哭了一阵之后会突然给我下跪。她刚溜下桌子时,我还以为她是身体支持不住歪倒了,直到她双膝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我才意识到她是在给我下跪。胡雪直直地跪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她错了,要我骂她,还要我打她。
看着胡雪哀怨的样子,我的眼前猛然浮现出我在南方遇上的那个贵州女人。顿时,我心里一颤,忽然觉得胡雪有点儿可怜。接着我就原谅了她,马上伸手把她拉了起来。胡雪起身后顺势扑进了我的怀里,我赶紧用双手抱住了她。胡雪在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她不停地说她对不起我,还说她今后再也不会做那种事。
胡雪的哭声停止后,我再次说到了胡霜。我说我倒是可以饶恕胡雪,可惜胡霜却不能饶恕杨栓。胡雪听我这么说,忍不住叹了一口长气,然后对我说,那件事其实不能怪杨栓,要怪只能怪我。我愣了一下,问胡雪这话是什么意思。胡雪迟疑了一会儿,就回忆起了事情发生时的情景。
掰玉米棒子那天,胡雪和杨栓在进入那个草棚子躲雨之前,他们谁也没想到要做那种事。那天的雨很猛,胡雪和杨栓跑进草棚子时,他们的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那天他们穿的都是很薄的单衣,淋湿后贴在身上看上去就像没穿衣服似的,身体的凸处和凹处都隐约可见。杨栓无意中看见了胡雪的胸脯,脸一下子羞得通红,他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胡雪的眼睛也是无意之中看到杨栓腿间去的,那个高挺的东西让她两眼一亮,心一下子狂跳起来。胡雪本来也想赶快将目光拖开的,但她却怎么也拖不开,好像被什么东西钳住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胡雪开始想杨栓的心思了。她说杨栓腿子中间也有个玉米棒子,说着就伸手去掰。杨栓起初是躲闪的,但胡雪却执意要掰,杨栓没办法就只好让她掰了。
胡雪讲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气愤了。我对胡雪说,这完全是你在勾引杨栓嘛!胡雪说,是的,是我勾引他。我那会儿实在管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过了许久,我说这事看来真的不能怪杨栓。胡霜说一点儿都不能怪他,责任都在她一个人身上。我说,你应该把事情的经过说给胡霜听,没准她听了会同意和杨栓复婚的。胡雪说她给胡霜一五一十地说过了,可胡霜还是不原谅杨栓。我叹息一声说,既然是这样,那胡霜就没有可能回心转意了。
4
腊月二十八是胡霜的生日。这天下午三点多钟的光景,我和胡雪,还有杨栓,三个人一起来到了胡霜住的砖窑跟前。我本来是不想来的,但胡雪一定要我来,杨栓也再三求我走一趟,没有办法,我只好陪着他们来了。杨栓和胡雪都说来给胡霜过生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们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劝胡霜复婚。我当然也是衷心希望胡霜和杨栓复婚的,马上就要过年了,胡霜一个人在这个砖窑里怎么过呀!但是,我觉得胡霜是不会和杨栓复婚的,她是一个犟脾气,遇事从来不回头,离婚已经好几个月了,要是能复婚她早就复了。就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才不愿意来给胡霜过生日。我认为这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走到砖窑门口,我们才发现砖窑的门锁上了。砖窑本来没有门,那扇门肯定是胡霜住进来时才安上去的,看上去和砖窑很不般配,就像一个白花花的姑娘嫁给了一个黑黢黢的男人。一见门上挂着锁,我们三个人都傻了眼,谁也不知道胡霜到哪里去了。在门口站了一刻钟后,我提出回去,但杨栓和胡雪都反对,他们一致说要等,还说一定要等到胡霜回来。我能理解杨栓和胡雪,他们的心都很诚,来的时候还提了生日礼物,杨栓提了一包穿的,胡雪提了一包吃的。既然他们坚决要等,我也不好一个人先走。
我一边等一边吸烟,脚下的烟头越来越多。一包烟快吸完的时候,胡霜终于回来了。她一手提着一个塑料包,两个包都鼓鼓囊囊的。我很快上前跟胡霜打了招呼,问她去了哪里。胡霜不冷不热地喊了我一声,说她去老垭镇办了一点儿年货。杨栓和胡雪也马上走拢来,小声地试探着跟胡霜说话,胡霜却不搭他们的腔,甚至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胡霜打开了砖窑的门,让我进去了,却把杨栓和胡雪挡在了门外。杨栓和胡雪都央求胡霜让他们也进去,还说只进去坐一会儿就出来,但胡霜却坚决不让他们进,还张开两只手把门挡着。我这时劝了胡霜几句,说杨栓和胡雪是专门来给她过生日的,要她放他们进来。胡霜却一点儿也不听劝,说她才不稀罕他们来给她过什么生日呢,还说一见到杨栓和胡雪就感到恶心。胡霜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杨栓和胡雪也就不指望进砖窑了,他们把礼物放在了门口,硬着头皮说了几句祝生日快乐的话。不过胡霜也太绝情了,她居然连礼物也不收,杨栓和胡雪刚放下来,她就拎起来像扔垃圾一样把它们扔出去了。
杨栓和胡雪都觉得很尴尬,也不好意思在砖窑这里再呆下去,他们从地上捡起被胡霜扔出去的礼物,转身走出了砖窑门口的土场。
太阳已经下山了。杨栓和胡雪一走,我也坐不住了。我对胡霜说了一声再见就走出了砖窑,然后匆匆忙忙去追杨栓和胡雪。我很快追上了杨栓和胡雪,可他们却把我拦住了。他们说我不能马上就走。我问他们原因,他们说我得留下来陪胡霜吃晚饭,说她过生日总得有一个陪她一下。我开始不同意留下来,担心天黑了回家看不见路。杨栓和胡雪却执意要我留下,说我留下来陪胡霜就等于是他们陪了胡霜。为了我走夜路不栽跟头,杨栓还把他身上的手电筒给了我。这样一来,我就再不好说什么了,只好乖乖地留下来陪一陪胡霜。
我再次走进砖窑时,胡霜已在烧火煮饭了。她问我又回来干什么,我说我留下来陪她过生日。胡霜要我也走,还说一个人照样过生日。她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她却马上给我上了一杯茶。
胡霜把饭做好的时候,砖窑里已经看不见了。我正要去找电灯的开关,胡霜突然点燃了一支蜡烛。原来这砖窑里压根儿就没牵电线。蜡烛一点,淡黄的光茫立刻洒满了砖窑,砖窑里像是贴上了一层明亮的糖纸,它的光线虽然没有电灯耀眼,但它很柔和,还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胡霜心灵手巧,一会儿工夫就做出了四菜一汤,摆在桌子上非常好看。胡霜还拿出来一瓶酒和两个酒杯,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两个酒杯倒满了。我说我不能喝酒,过一会儿还要走夜路呢。胡霜却坚持要我喝,她说,柳条哥,你是我住进砖窑后的第一个客人呢!她说着就敬了我一杯。在我的印象中,胡霜是不太会喝酒的,所以我敬她时就让她只喝半杯。可胡霜却不依分说,非要喝一满杯不可。
几杯酒喝下去,我和胡霜的话就多了起来。这时,我突然提到了杨栓,劝胡霜还是和杨栓复婚,还说了一些一日夫妻百日恩之类的话。胡霜本来情绪不错的,可我一说到复婚的事,她的脸马上就变了,显得很生气。胡霜一气之下又连喝了两杯酒,然后一边打着酒嗝一边要我再不要劝她复婚。见胡霜对复婚这么反感,我也就没有再提了。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喝酒。胡霜好像有点儿醉了,说话舌头已经不怎么灵活。我也喝多了,心里烧得很厉害。我站起身来,对胡霜说我该回家了。胡霜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口齿不清地说要我慢走。
我快步走到了门口,正要伸手开门时,身后轰隆响了一声。我慌忙回头去看,发现胡霜倒在了地上。我赶紧折身回到桌边,蹲下身去扶胡霜。胡霜这时已经醉如烂泥,四肢软弱,好像连知觉都没有了。我扶了她半天也扶不起来,后来只好张开双手去抱她。
我把胡霜抱到床边,将她平放在床上。这时,我突然感到有点儿为难,不知道是马上离开还是留下来照顾一会儿胡霜。就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胡霜呕吐了,吐出来的食物把她的脖子和胸脯都弄脏了。床头有一卷卫生纸,我先用卫生纸给胡霜擦了嘴和下巴,然后我又去找了一条毛巾,想用热水打湿后给她擦擦脖子和胸脯。为了擦得干净一些,我把她棉袄上的扣子解了几颗,这样就能把整条毛巾都伸进去了。
我给胡霜擦脖子的时候,她还显得很安静,双眼闭着,像睡着了一样。等我把温热的毛巾伸到她的胸脯上时,她的身体却突然颤动了一下,嘴里同时发出一声呻吟。胡霜的呻吟有点儿像春天的猫叫。这时我猛然又想到了那个贵州女人,记得当时我给她揉乳房时,她也呻吟了一声,也像春天的猫叫。胡霜的呻吟把我吓了一跳,握毛巾的那只手立刻就停住不动了。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毛巾从胡霜的胸脯上拿出来。我忽然担心再擦下去会擦出什么问题。可是,我的手刚一动,胡霜两手一张抱住了我,嘴里的呻吟又响了起来。我顿时热血沸腾,心跳加速,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好意思多说了,但有一点我却非说不可,腊月二十九,胡霜主动和杨栓复婚了。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