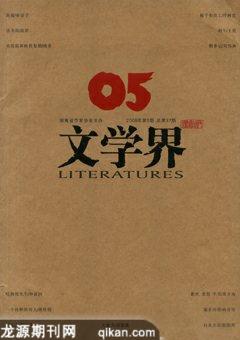读书郎
高 君
父亲捏着我的成绩单,抠掉眼窝里一坨眼屎,眯起眼睛。那个复写着我各科成绩的小纸条薄得像蒜皮儿,父亲立刻把它放到炕沿上,在裤腰上抹了两把手。他刚从江沿回来,光着两只脚,绾起的裤腿一高一低,正往下滴着水,小花猫卷着尾巴边嗅边叫,起上来的鱼网挂在园杖子上,一些小鱼在上面跳,闪着耀眼的光。父亲把小纸条在眼皮底下送出一段距离,嘴里叨咕着上面的分数。8分,多玄,就差8分,我看明白了,就让英语给拽下来了,你咋没考及格?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少偷点懒,再一使劲就整上去了。我说我没偷懒。父亲用鼻子哼了一声,蹲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撮烟末洒在纸条上,我说爹你别用它卷烟,还有用呢。父亲咳了一口痰吐到门槛上,鸟用?跟蒜皮似的,连烟都卷不上,父亲不屑地把纸条放到炕沿上,重新卷好一支烟,然后很响地抽了起来。抽了一会儿,父亲又捡起炕沿上的小纸条,父亲问,你们班考上几个?我说一个也没考上。光秃?父亲说,那这书还念个啥劲头?不是瞎子点灯白熬油吗?干脆撸锄杠算了。我说我才不撸锄杠呢。那你说咋整?父亲白瞪我一眼,又吐了一口痰,站起来走了。
母亲把背筐里的玉米倒在院子里,隔窗向屋里看了一眼,哎呀叫了一声,我儿回来了?快告诉妈考上没有?我从炕上坐起来,又躺下去。母亲的神情暗了一层,摘着衣襟上的玉米胡子,愣了一会儿。母亲说,啥时回来的?饿了吧?妈这就做饭去。我说妈我啥也不吃。母亲说,那哪成?啥天大的事也得先吃饱了饭再说。我说妈我没考上。没考上咱再念,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早晚能考上。母亲扎撒着两手在屋地中央转了一圈,问,你爹呢?先别告诉他。
掌灯时,父亲回来了,脸红红的,眼睛也红红的。母亲听到父亲开门的声音,丢给我一个眼色,立即去外屋打开灯。母亲故意大声说,他爹回来了,品红正要给你烫酒呢,我去把菜热热。父亲咣当一声把门关上,别瞎忙乎了,我吃过了。又跑哪抹的油嘴?母亲回头看看我,品红特意跑腰屯小卖店给你打的酒,你再喝两盅。我可喝不起他打的酒,父亲没解鞋带,把两只鞋从脚上使劲地扒下来,一前一后甩到墙根上,其中一只打到我的腿肚上,酒壶里的酒窜出来一些。父亲拽下柜盖上一只枕头,头朝里躺下来,父亲说,等喝他的酒,大牙早馋掉了。母亲说,等把品红供成了,给你泡酒缸里,到时你大牙要是不掉,让品红用老虎钳子给你掰下去。敢?父亲抬手打掉母亲端着的菜盘,菜盘哗地一声在地上碎了。父亲说,他敢?翻了天了?这书我不供了!谁爱供谁供!母亲说,放屁!喝二两尿水子你就人事不懂了,冲孩子耍啥威风?有章成跟外人耍去,孩子够上火的了,嘴唇都起泡了,你还给火上浇油。父亲说,他那是自作自受,他上火?我还上火呢!母亲嘟哝着,这又不知是在哪喝的,是谁冲了他肺管子。我说,我知道,他是去乔中河家喝的。中!父亲忽地坐了起来,你还知道我在哪喝的。我问你,你们班今年到底考上几个?我说,我是说重点高中一个也没考上。你少给我打马唬眼,我没问你什么重点不重点,我是问你考上几个?我说他报的是师范,比重点高中分低。父亲说,那你为啥没给我报师范?我不是跟你说啥能考上就报啥吗?我说我不想当老师。那你想干啥?想当国家主席?没那造化!那也是随你的根儿,怨你祖坟没冒青烟。母亲说。父亲说,我早告诉你了,先爬出这地垄沟再说,你可倒好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净想高口味,你自己说吧,就是考上重点,这三年咋念?我说我自己念。废话,父亲说,你不自己念还让我替你念去?我是说咋供你?人家老乔家那小子开学就国家供了,三年后自己都挣钱了。我说不是三年是四年。父亲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我让你犟嘴,翅膀没硬就说不了你了,今个儿把话跟你说明了,这书我不供了!我没钱!不供就不供,能咋地?我捂着脸说,我还不想念了呢!好!父亲说,明天就给我上山扒苞米去!母亲抬腿踹了父亲一脚。
第二天一大早,我背着背筐就上山了。出门时,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小兔崽子还真犟。母亲说,兔子没尾巴随根儿。这么大了你还说打就打。父亲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我从来没动过他一手指头。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不再跟父亲说话。而且睡觉时,把位置换在挨着母亲一边。我早早地走,晚晚地回,为的就是不跟他打照面说话。其实没过两天我就看出来父亲有点憋不住了,比如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亮,我一睁开眼睛就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掀开窗帘一角,见父亲在院里一边忙着翻弄豆子一边往屋看,四只眼珠儿一下子对上了,因为猝不及防,彼此都愣了一下,父亲正要往一旁扔一大捆豆子,忽然停住了,由于惯性他的上半身往前一送,打了一个趔趄,我呼地放下窗帘,听见他干咳了一下,操了一声。我立即倒头装睡,屏神谛听,窗外的声音立刻就大了起来。母亲在外屋正忙早饭,开门对父亲说,你轻点,孩子还没醒呢。父亲又操了一声。吃早饭时,父亲还在院子里翻弄豆子,母亲喊了一声,父亲没搭理,又喊了一声。父亲说,喊我干什么?别碍了你们眼。我吐了嘴里的牙膏沫儿,拎起背筐开门走了。母亲追出来喊。父亲说,喊什么?进屋吃你的得了,谁不吃谁不饿。母亲被院里的豆子绊了一下,骂道,一个老犊子,一个小犊子,一对犊子。
在山上,母亲把一兜煮鸡蛋给我。我在母亲脸上亲了一口,把一穗玉米倏地扔出去,躺在玉米堆上。十月的天空湛蓝如洗,云飘着,像棉花。江风吹来,裹满鱼腥味儿,我叹了一声。母亲说,你爹说明天不让你来了,这点活妈再有几天就干完了。我说得了吧,想让我跟他下江啊?美的他。母亲说他让你在家写作业,别把书本上的东西扔了。我说我都不念了还写啥作业?母亲说,妈跟你说,这话你可千万别跟你爹说,那老犊子可吃软不吃硬,咱别吃那眼前亏。我说我才不怕呢,我还吃软不吃硬呢。母亲说,那我看你们两个犊子谁能犟过谁。
中午时卢瘸子拄着棍来了,他隔着园杖子就喊亲家亲家,我蹲在茅坑里听见父亲跟他打招呼。不冷不热的。卢瘸子腿瘸人却贼精,两个儿子虽没读书却都弄到了城里,这让他获得了很多名声和尊重,人也跟着威风起来。母亲常常以他为例激励父亲,最常说的是,你看人家卢万山,一条半腿比两条腿的都厉害,这要是两条腿一般齐还不得上天呀?真了不得。有时当着人家的面也这样说,卢瘸子就捡便宜地笑两声,说我上天干啥去?先上你炕再说。母亲也笑,说那你可废了,连裤裆里那条腿也得造没喽。不知道从哪论的亲家,在农村,亲戚都是拐弯抹角一圈套一圈地论,拐来拐去,套来套去就都成亲戚了。
卢瘸子说,亲家,小子呢?
父亲说,这么闲着啊,地收完了?
卢瘸子说,嗯。小子呢?考中了吧?
父亲说,你整的倒挺麻利啊。
卢瘸子说,嗯,我刚从朝阳老乔家回来,小子呢?
父亲放下手里晾晒的烟叶,走,咱屋里唠去。
卢瘸子说,不了,你忙吧,我刚从老乔家回来,我看人家屋里的正给孩子做被褥呢,红红堂堂的绸缎面,里外三新,你看人家爹妈养的孩子。争脸哪。
父亲干咳了两声,走,进屋进屋。卢瘸子说,不了不了,你忙着,我在道上还跟人说呢,这上下十里八屯还就出息人家那孩子了,不用再顺地垄沟刨食吃喽。小子呢?我看这两天跟大嫂上山忙活呢。没考中?父亲顿了顿,说,要考师范那是绰绰有余,比老乔家那小子还多5分呢,是我没让考,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岁数还小,慢慢念,将来给我考大学。那敢情好,我那小子也念大学呢,是电视大学,你看看这形势,城里这脑筋好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怕……都奔大的到时连小的也难考啊。我在茅坑里蹲得腿都麻了,走出来时有点瘸,我一拐一拐地走到卢瘸子跟前,拎起背筐说,你怕什么?我他妈都不念了你们怕什么?杞人忧天!我瘸着腿飞快地走出院子,一穗硕大的玉米跃过头顶飞到我的前面,我撒腿就跑。父亲在背后喊道,给我远点扇着,少在我眼皮底下晃悠!
在山上玉米地里,我对母亲说,我要出门。母亲愣了一下,上哪?我说随便上哪。母亲说你想离家出走?我说算你猜对了。母亲正撕开一穗玉米,忽然停住,母亲说,为啥?我说我得离他远点,要不他要打死我。母亲扑哧一声乐了,净扯呢。他那是吓唬吓唬你,就他那手把,要真打你还会让苞米从你头顶过去,不打中你后脑勺也得消你后背上。你也是,咋地也不能学人家腿瘸吧?矬人面前不说矮话。我没解释,我说得了吧,那是我躲得及时,要不后脑勺得开瓢。母亲说我不跟你犟了。我说他不是让我远点扇着吗?我也不能赖在他眼皮底下,好像没志气似的。母亲又乐了一声,你傻呀?你爹那是指鸡说狗,还志气呢,没用到正地方,我再告诉你一遍,今后不许再提不念书这茬。我说反正我要出门。母亲说,越远越好,走到天边都不拦你。
那段时间,父亲白天在山上打过冬的烧柴,晚上在江里撒网,捕到的鱼淹成鱼干卖掉,这反倒避免了我们彼此不说话的尴尬,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彼此似乎已经习惯了不说话,好像本来就该这样,有时觉得非说不可的时候,父亲就用嗓眼咳一声,算做打招呼,或提个醒。要不就指着母亲说。比如父亲每天早上拎着鱼网回来,边摘鱼边问母亲,这钱攒得差不多了吧?怎么还没动静?母亲说什么动静?父亲说你老糊涂了?什么动静?那重点没考上普通的总该考上吧?这眼瞅着就要开学了。母亲说你不会问孩子?我知道什么?父亲就用嗓眼咳一声,并向屋里望一下,我知道他是要我说话,可我一声不吭。父亲就很用力地往盆里摔鱼,弄出挺大声响,噼噼叭叭的。还比如有一天早晨背筐突然不见了,我问母亲谁看见背筐子?母亲说别问我我不知道,你问你爹去。我就又大声问了一遍,然后也用嗓眼咳一声,然后看一眼在一旁的父亲,父亲一声不吭,脸上却有些得意。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为了不让我上山,才故意把背筐藏起来。我的手掌起了一层血泡,我找出针要挑开,父亲看了一眼对母亲说,说让你戴手套你就是不听,不信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拿针的手停了一下,父亲用嗓眼咳了一声,继续说,那泡能用针挑吗?多疼,过两天自己就瘪回去了。母亲看看父亲问,你跟谁说话呢?父亲抬腿走了。
但尴尬还是有的。有一天晚上天很黑,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去房头厕所小便,不知道父亲在里面蹲着,我径直过去掏出就尿,父亲正使劲屙屎,没顾上用嗓眼发信号,结果我的一泡尿差不多全浇在他的身上。父亲突然操了一声,说你小子都整到我脸上了。我吓了一跳。父亲却笑了,接着整吧,别遭尽了。我也笑了,心想,还是没犟过我吧,到底还是先跟我说话了。至此,我与父亲长达20天的冷战宣告结束。睡觉的位置也随之改变,偶尔半夜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枕在父亲的胳膊上,还有点不好意思呢。父亲小口喝着酒,对母亲说,这个小犊子还真随我,犟得跟毛驴似的。母亲说,还恬脸说呢,一对犟种。
我的同学乔中河在去师范学校报到的前一天,家里准备杀一头猪请客,这当然忘不了请父亲。头天晚上,在被窝里我听见父亲的叹息声,父亲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对母亲说我得去学校一趟,这都开学了,咋啥信也没有呢。母亲说等过了明个再说吧。父亲说,明个你去随一份礼,我们爷俩坐早车走,你多煮点鸡蛋我俩道上吃。父亲说,从今往后,别说师范,就是再好的中专咱也不稀得念了,非考大学不可,到时我雇个吹喇叭的,杀它两头肥猪。
小船在江上摇,天上还挂着星星,雾气浮在水面上。父亲用力划着船,我不时地往外淘着渗进船舱里的水,父亲把外衣脱下来递给我,到最后只剩件短袖汗衫了。父亲说,我都出汗了。我披着父亲的衣服瑟缩在船头,父亲衣服里弥漫着浓烈的旱烟味,还有些微的汗油味,它们温热地包围着我,让我有些泛困。父亲绷紧牙帮骨,用力地划着浆。黛色的山峰在父亲背后一点一点远去,深蓝的波浪一层一层涌来。父亲说,儿子,你别打盹,这船晃得挺厉害。父亲又说,你把住了,这风真他妈大。父亲不停地跟我说着话,为的就是不让我泛困。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水性好着呢。父亲哈哈笑了,你小子还敢跟我吹,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说不信给你瞧瞧。我故意向一边一歪,一个浪头哗地窜进船舱里,父亲喝了一声,变了脸色。我说你胆儿还真没我大。父亲说,练胆儿能在这上练吗?水火不留情!我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父亲说等来年暑假,我跟你小子好好比试比试。我说这书还不知上哪念呢,还暑假呢。父亲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儿,父亲使劲咳了一口痰,吐到江里,操了一声。父亲说,操,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告诉你,你小子可不要给我泄气喽!我说爹,咱们这是去找谁呀?父亲立即变得胸有成竹起来,并且一脸神秘的样子。父亲说,你就别管了,你就把那小纸条揣好就行了。我说你把钱揣好了,车上小偷可多了。父亲又是一脸成竹在胸的样子。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父亲把小船靠上码头,取下双桨藏到江岸的草丛里,然后开始往船上搬石头。父亲说你一边呆着,不用你沾手,不久小船就沉进水中。父亲远远近近地看了一会儿,说大客车还早着呢,撒泡尿吃点东西。父亲回头看我一眼,你还愣着干啥?太阳从江面上升起来,宽阔的江面金光闪闪,像洒满成熟的谷粒。我说真美啊。父亲说,美?再美这也不是你呆的地方。顿了顿父亲又说,你看电视上人家城里,那才叫美,茅房修得比咱房子都敞亮,街道比咱炕头都光溜。我要是倒退二十年,也早不在这呆了。父亲把剥光的一只鸡蛋给我说,咱就说卢瘸子吧,他有啥牛的,说白了他俩儿子在城里那是在吃下等饭,斗大字不识一升他不搬砖扛水泥还能干啥?乔老四倒该牛,人家儿子是凭学问考出去的。父亲眯起两眼,虚无地向远方看了许久,轻叹一声。其实,父亲说,乔老四也没啥牛的,话说回来他儿子将来也不过就是一个教书匠,你说那有啥牛的?一辈子下来光粉笔灰得吃多少?咱将来考大学,说啥也不吃那粉笔灰!
父亲说完,飞快地吃了几只鸡蛋,敲敲裤腿拎起半袋干鱼,响亮地说,走!儿子,咱上车站去!
下了客车,我发现父亲的腿瘸了。
发往公社的客车,不但小,而且破得让人心疼,三分之一的座位只剩下了铁框,每周跑两趟,头晚在小屯里住班,既使农忙季节也总是人满为患。天不亮就坐满了占座位的人,连只剩下铁框的座位都搪上了木板。有的是让家里女人孩子来提早占座位的,都冻得流出了鼻涕,七吵八嚷的。我和父亲上车时,连过道都站满了人。父亲把半袋干鱼往一个座位底下塞,被一个女人嘟着嘴用脚抵住,父亲撅着屁股用劲,操了一声,咋这么紧呢?父亲说。女人一脚把袋子踹了出来,呸了一口。父亲愣了一下,女人说,你在我屁股底下鼓捣啥呀?父亲说,谁在你屁股底下鼓捣了?我是要把袋子塞到座位底下。女人说,还狡辩咋地?刚才你的手都捏到我的屁股了,你以为我还没感觉?父亲看了一眼,女人的屁股很大,下面的木板却很窄,木板被压弯了,女人的大半边屁股似乎要从木板缝里漏下去。父亲说,真肥实。女人说,你说啥呢?父亲咧咧嘴说,我是说你咋不弄一块宽绰的?刚才我没看见。女人说,起早赶二十里路,连耳朵都嫌沉呢,还拿宽绰的?要不是送孩子念书,我可不遭这洋罪。你也送孩子念书呀?父亲把袋子挪到两腿间夹着说,我也是。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问,啥学校啊?父亲咽了一口唾沫,是……是县城的重点高中。女人唔了一声,挪了挪屁股,放进来吧,女人回头看我一眼,挤挤身边的男孩说,让孩子过来搭个脚吧。我是送儿子去省城念师范。父亲说不用了呆会儿兴许有下车的。客车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中途,父亲给我占了一个发动机盖上的位置,我一坐下来就打起了盹。
中午时分,客车在一个岔路口还没停稳,我就迷迷糊糊被父亲一把拉起来,父亲说,咱下车!我揉揉眼睛问,到了吗?父亲说下车!一迈车门,父亲使劲吐了一口唾沫,操,跟我扯?你们才吃几年咸盐?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都多!父亲还没说完,客车就启动了,紧接着从半开的车窗伸出一个留披肩发青年的脑袋,妈的,今个碰见老狐狸了,真晦气!披肩发骂完随手扬了一沓花花绿绿的碎纸片。有几片落到我和父亲的肩上,父亲又操一声,扑了一下肩膀骂了一句,臭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看看路边一大片玉米地,说,我去撒泡尿,你去不去?你瞧瞧车上那女人的大屁股,跟脸盆子差不多。我说你说啥呀?还有10里路呢,干吗下车呀?刚才那小子为啥骂你呀?父亲说骂两句也不能掉块肉,他妈这帮小兔崽子。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往玉米地走,我说爹你的腿咋瘸啦?
解完手,父亲摸摸裤裆,一脸自豪的样子。父亲说,上次我他妈都吃过一回亏了,这次逗乐他们一回,扯平了。干他们这行有说道,要是掏出一把揩腚纸比骂他们祖宗还狠,不吉利。父亲又摸了一把裤裆,咋样?父亲说,昨晚上我让你妈把钱都缝到裤衩上了,就留了车票钱,还特意揣了兜揩腚纸。刚才半道那几个小子就上来了,我认识他们,上次给你送的钱就是让他们几个给掏去的,整的我半路下车硬走回去的,你看他们上车那眼神就不对,一顿疯挤,我小声给那女人提了提醒,就故意闭上眼装迷糊,我心里有底,他妈的再能耐还能掏人家裤裆里去?那俩小子一前一后挤了我一阵儿,又用胳膊肘捅了我几下,见我还迷糊着,就开始下手了,前边的一个用后背挤住我,后边的一个就把手放在了我的裤兜上,捏了几下就开始慢慢往里伸,我故意挪挪屁股那手就拿走了,一会儿又在上头捏了几下,这回我没动,那手就伸进来了,我觉得裤兜一下子空了,就挤到前边来了,他妈的这帮小子,父亲乐了一声说,我特意把厚书皮剪得跟真钱一般大,我都试过了跟真的一样,一点都感觉不出来。该他们上一回当了。让他们下车后空欢喜一场,净让别人难受了。这帮小兔崽子!父亲点着一支烟使劲抽了一口说,我还以为这俩小子掏完了就揣腰包里了呢,后来八成是忍不住看了。这下可倒好,我听见后边那小子骂了一句他妈的,随后我的屁股就重重挨了他们两脚,我赶紧挤到前边,要不这腚帮骨非给踢裂了不可。我哈哈笑了一阵儿。我说,爹你也挺黑,你这不是玩人家呢吗?他们其实也不容易。屁!父亲瞪了我一眼,把半袋干鱼扔给我,扛着,还有10里路呢。
几乎没费周折,父亲领我找到了曾经在我们那儿插队的一个知青,知青的哥哥在县城城郊一所普通高中当教导主任。这样,我就十分顺利地去了那所条件简陋,校址荒凉的城郊中学。为了不让我再受颠簸之苦,父亲让我在知青家住了两天,然后回家拿了行李。临走前,我陪父亲在学校四下走了好几圈,父亲边走边自言自语,我去重点校看了,这跟那比是破了点,可我听你们教导主任说,去年你们学校考上好几个呢,有一个还进了京城,叫什么来着?对了,叫李孟贤。父亲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学校破点,没关系,我问过了,那念的书都是一样的,你的分儿在这还是第二名呢,到时候只要考出去两个,就有咱,你要是再使使劲把英语整上去,超过第一名那个丫头,咱也能进京。我都看了,那丫头除了英语哪门都不如你,你多跟人家打打交道,偷点窍门。不过,父亲担心地看了我一会儿,可不能把劲给我整到那上头去。父亲说,我说别把劲儿整到那上头去,你懂是啥意思不?我没言语。
临走时,父亲在学校围墙跟一棵大树后解开裤带,费了好半天劲才从里面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来,父亲说,听爹的,也像我这样缝在裤衩里头。我接过那沓钱,感觉手心里是一片潮乎乎的温度。
期末考试还没结束,父亲就来了,他没让我知道,悄悄地在校外一个小旅店住了下来。交上最后一科试卷,一出教室我和阿铁立刻朝山墙头跑,那儿围墙被人凿开了一个窟窿,我们钻出去躲在树后面抽烟。我们蹲在树后,把下巴缩在竖起的军大衣的毛领里,大口小口地抽着一种叫佳美的云烟,看着一些喇叭裤角和像火箭头一样的皮鞋尖从眼前偶尔停下或走过,丝毫没有什么反应。烟草带来的美妙刺激让我们的身子微微发颤,我们留着过耳丫的长发,往雪地上叭叭吐着唾沫,无暇旁顾。
父亲在傍晚来到我们宿舍,吓了我一跳。父亲阴沉着脸坐在我的床铺上,打量了我半天说,都考完了?我点点头说,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父亲说。我从床上爬起来说,下午才刚考完。父亲说,你们学校这儿不缺理发铺吧?我住的旅店旁边就有一家。顿了顿父亲又说,小卖铺也不少,都卖烟卷儿,我捎带给你买了一盒,咋样?整一根?我捋了一把头发,抬眼看看父亲,父亲笑笑说,中,你留这么长头发,把我给你买帽子的钱都省了。父亲从兜里掏出一盒佳美烟摔到床铺上,抬腿走了。我追出去,在旅店旁的小饭馆,点完菜父亲对我说,我都看见了,猫在树后面,跟做贼一样,瘾头还不小。要不是有你同学在,我当时非给你一嘴巴不可,给你一回面子。头发不爱剃就不剃,我看街上还都是留长头发的,八成现在时兴这个,我不管,可这烟坚决不能抽。停了一会儿父亲说,要抽也不能现在,等考上大学我给你小子买贵的。菜端上来,父亲冲服务员要来一只小酒盅放在我面前,然后给我倒了一盅酒,这大冷天沾点酒暖暖身子我不反对,烟那玩艺对身子一点好处没有,最好一辈子都别动!
我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了,你还来干啥?父亲说,眼看来到年了,给你们教导主任带点农村东西。咱不能忘了人家。我再顺便买点年货等你考试卷子一发下来咱俩一块家去。父亲说,我问过你们教导主任了,说你英语撵得挺快,父亲滋地喝了一口酒,一脸神秘的样子,父亲说,你跟那丫头偷来窍门了?
父亲看着我们全年段的成绩单,一屁股坐在了小旅店的炕沿上,过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摸出烟点着抽起来,父亲抿着嘴唇,绷了一会儿牙帮骨说,咋出溜这么快?像窜山涧似的。这英语倒是上去了,可别的都下来了。父亲自言自语地叨咕了一阵儿,突然转过脸盯着我。我明白是咋回事了,父亲说,你小子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把劲儿都给我整那上头了?我说我不明白你是啥意思。父亲把成绩单扔过来,你自己看看,这俩人一块堆出溜下来了,要不是把劲整那上头,是整哪了?我说你这是胡乱联系,她的成绩下来跟我有啥关系?相反,我的成绩下来跟她有啥关系?她是她,我是我。父亲被噎了一下,半天没找到合适的词儿,停了停他说,就算真有那心思,我和你妈也不着实反对,成天啃这死书本,跟和尚念经差不多,只要不办真事,搭个伴念书兴许还能有点乐子,可那得把分数整上去呀,可你俩倒好,一块堆出溜下来了,我看这窍门从今往后咱就别偷了。我说这偷和不偷都让你说了,还给不给别人一点自由?父亲倏地甩了烟屁股,自由?再给你自由你非得和那丫头一块抱孩子回家种地去不可!父亲的话难听得让我脸红,我忽地站起来,从衣服里面的口袋摸出一支烟点着,我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学校去年一个也没考上,那个姓李的是临高考时出点事转到我们学校来的,这学期没到期末我们班几个学习好的就都走后门转到重点高中去了。那里年年全班抬。父亲愣了一会儿说,都是念一样的书本,人家是咋学的?你们天天在这白吃饭呢?我说,这你不懂,书上说,教和学是一对矛盾,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学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你别跟我说绕口令,父亲打断我说,学咋就成次要的了呢?古语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翻开哲学课本指给父亲看,父亲抽着烟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也是这个理,要是全靠自个儿,把书本领家来能念,谁还花钱跑这遭洋罪?学校还养一帮老师有鸟用?我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学校搞对象成风,上课时纸条乱飞,校内跟社会上搞,老师跟学生搞。父亲顿时瞪大了眼睛,那不乱套了吗?父亲说,你们学校不管?我说,谁敢哪!校外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动不动就在晚自习时从窗户跳进来,向男生要完钱拽过来女生就亲,连我们看一眼都得挨一顿饱揍,老师见了那帮人像耗子见猫了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父亲的脸变得乌青,那这书还咋念?考个屁去?父亲突然问,你跟我交个实底,你和那丫头到底搞没搞?我说搞了又怎么样?父亲扬手打掉我嘴上的烟,搞了?搞到啥程度了?我说我怎么知道?是没法子知道,父亲绷紧牙帮骨,嘴唇均匀地颤抖了一阵儿说,我就简直杆儿问你吧,你搞没搞大人家丫头的肚子?我用鼻子哼了一声推门出去了。完了,我听见父亲在我身后悲凉地长叹了一声,这回是哪也去不上了,非进笆篱子不可。
事隔多年,父亲那声悲凉的叹息时时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心上,时间冲走许多事情,我为那个冬日下午说谎而难过,更为父亲竟然信以为真而生出的悲哀和失望而不安。在父亲临去世前,我曾认真地跟他解释过那件事,其实我不过是将父亲一军,要他想办法把我弄到重点校去,可父亲不相信。父亲慈祥地看着我,宽和地笑笑,说,只要你不记恨我就行,说不定是我错了,拆散了你们,你还在心里念着她,所以一直不结婚。我又解释了一阵儿。别说了儿子,父亲把手放在我肩上,我懂,人要干成一件事非得舍去点什么不可,父亲叹息了一声,我像你那岁数和你妈都有你大哥了。父亲把头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叹了一口气说,你瞧瞧那女人的大屁股,多肥实,跟脸盆子差不多。母亲一愣,说,你说啥?谁的大屁股?我说,妈,你别问了。过一会儿,父亲把眼睛睁开,艰难地冲母亲笑笑,你说,也怪有意思的,大冬天晚上,正是小鬼冻得龇牙的时候,小丫头小小子抱在一块儿,像鲶鱼咬尾一样,末了我还挨了他们一顿狗屁哧!父亲喘息了一会儿说,我琢磨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刷锅是啥意思?母亲说,你老傻了,连用刷帚刷锅都不知道了。大侄摘下随身听耳塞在一旁抢过话说,奶奶,不对,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两个男生一块干一个女生,后边上的就叫刷锅。大侄戴上耳塞走了。我们一齐望着15岁的大侄,张大了嘴巴。
那个冬天飘雪的晚上,父亲一个人在小酒馆里喝闷酒,喝到快半夜时,突然决定到宿舍找我谈谈,可那时学校的大门已经锁上了,父亲无可奈何地沿着围墙走了一圈儿,后来发现了围墙上的那个窟窿,父亲弯腰钻进去,还没走几步就看见我们班山墙头有一对男女生嘴对嘴地抱在一块儿,父亲使劲揉掉眼窝里一坨眼屎,越看那个留长头发穿军大衣的男生越像他的儿子,他先用嗓眼咳了两声,见没啥反应,这时父亲干了一件蠢事,他走过去支着了刚从小卖铺买来的手电筒,并喝了一声。那对男女生吓了一跳,当他们定下神发现站在面前的不是班主任,不是社会青年而是一个乌青着脸的农村老头时,顿时镇静了下来,那男生还凑过来冲父亲干笑了两声,说,吓了我一跳,老东西,你是不是刺挠啦?想刷锅吗?
父亲敲开我宿舍的门,一把把我从床铺上拽起来,父亲说,他妈的啥玩艺儿?啥地方?走!儿子!这书咱不在这念了,我豁出去了,就是砸锅卖铁咱也非上重点校不可!第二天一早父亲捆上行李就把我领走了。父亲对那位教导主任说,管管这帮毛头孩子,家里省吃俭用供他们念书不易,不往书本上用劲,净扯王八犊子,想抱孩子回家抱去,在这花钱遭洋罪干个鸟?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年夏天父亲终于把我送进了那所省重点高中。
在财务室,父亲背过身解开裤带,从裤裆里掏出一千元皱巴巴的票子,交到财务主任手里。父亲两手捏住像蒜皮儿一样薄的收据看了半天,然后叠成火柴盒大小的方块揣在怀里。父亲的脸上泛出一层光亮来。财务主任说,等把孩子供成了,让他连本带利一块还。父亲笑了一声说,养儿养儿,别说利,连本都收不回来啦。父亲没吃午饭坚持要走,我送他到学校大门口,父亲说,回去吧,我看这地方能行,戴眼镜的这么多,连进茅坑屙屎都看着书本,这回就看你的了。我回头走出很远被父亲叫住,父亲小跑来到我的面前,他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对我说,品红,这书咱得悠着点念,你可千万别弄残了眼睛,考不上学戴个眼镜将来咋回家种地?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