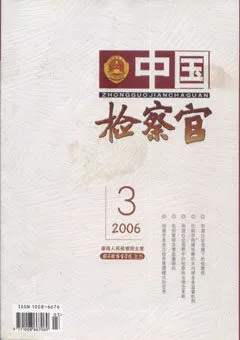漫游乌镇
记忆的深处总有副画面水印般淡进淡出:晨曦中,青青的石板桥泛着冷光,两岸浮雕般的木屋鳞次栉比,仿佛沉睡了千年。河面笼罩着一层牛奶般的轻纱,氤氲深处,一声矣欠乃,乌蓬船划破静谧,荡着绿波由远而近……
七月,考研、离校、就业,似乎所有的硝烟与喧闹都开始尘埃落定。心境终是慢了一拍,是啊,即将迈入的社会将会是如何纷纷扰扰。高中老友又聚首了,“劳燕分飞终归巢”,我们笑着感慨,轻轻一叹,“我们似乎都没变……”。“呵,只是年华似水流!”走吧,一起旅游去吧,有人提议,这可是我们四年前的约定,顺便也祭奠一下已逝的流金岁月吧。
我们选择了乌镇,说那是个古老的江南水乡,说那里有座“逢源双桥”,说黄磊和刘若英在那演绎了段欲罢还休的爱情故事,说那剧名叫“似水年华”……
乌镇,不经意的选择,却撞开了记忆深处的那扇门:居然这般熟悉……一样的白墙黛瓦、雕花门窗,一样的古桥流水、潺潺袅袅,一样的古朴宁静、悠然闲适。
说是水乡,乌镇名副其实。河水蜿蜒着穿镇而过,面河的一排房屋均用木桩或石桩打入水中,架起一个个小木阁,三面环水,称“水阁”,坐在窗边,可以看到整个河面的景致与对岸的风景,也许那时的小家碧玉正是这般慵懒地倚着木窗,看着河面穿梭交织的船只,眼角悄觅对岸某个芳心暗许的踪影吧。这一排房屋也有个美名叫“枕河人家”,掀开地板就看到河水了,茅盾散文《大地山河》中写到:“……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矣欠乃,飘然而过……。”枕水而睡,说的就是这情景了。
午后的太阳照得河水直晃人眼,我们踅进边上的一家茶馆避暑,挑了个临河的窗边坐下,泡上几杯绿茶。两根棍子撑起的厚重的木窗射不进一丝阳光,却能让我们居高临下偷觑窗外的动静,对岸迂回曲折的长廊,红阑杆上歇满了游客,不远处一只大拳船,操练着十八般武艺,哼哈之声不绝于耳。唯这里是清净的,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窃喜,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木凳,我们懒散地坐着,闷热的空气撑得胸口发胀,不觉生出些惆怅来。脚下的木板在吱嘎作响,这些发黑的木头是在沉吟历史的沉重吗?往事如烟云,年华似水流,年轻人的怀旧有轻叹,但总是轻松的,手中的绿茶续了一杯又一杯,话闸却始终未关上。
走出茶馆时,太阳已收起它的金箭,带上了柔柔的红晕,似乎在为它刚才的任性害羞。信步走来,逢源双桥已伫立眼前,我们慕名而来。这是两座并肩而立的石桥,中间隔了层镂空雕花栏杆,顶上还撑着个“屋檐”,造型果然独特,更吸引人的是流传着关于它的各种版本的优美传说,赋予了此桥极大的浪漫色彩。而《似水年华》中的文说得也有道理,“谁也做不到左右逢源,这座桥,你只能从一边走过来,不是左就是右……”人生如是,或左或右只能择一,只愿回头不遗憾。而现在我们情愿叫它“逢缘双桥”,两座不孤独的桥,三个人手拉手站着拍照,将双桥连成了一体,是啊,相识相知至今至此不是缘分吗?
此后,我们一路漫步,走过高公生酒坊、蓝印花布作坊、织布坊。当地有自酿的白酒,唤作“三白酒”,因以白米、白面、白水酿制而得名。听说此酒度数挺高,我们颇有自知之明地要了盒酒酿解谗,也不辜负这满屋的奇香了。织布坊里老婆婆们身穿蓝布褂,头带蓝方巾,围坐在古老而笨重的织布机前,梭子灵巧地飞来飞去,齐整的纱线在一推一接中,土布就成形了。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欣喜地依葫芦画瓢在机上推拿了两下,但不敢妄动,惟恐一个小疏漏毁了整块布。蓝印花布作坊是最值得一去的,整个场子都晒着染好的白花蓝布,从高高的木架子上径直垂下,一条就是一丈,风起处,袅娜轻舞,道不尽的风情。夕阳暖暖地笼罩着我们,将余辉撒得满场子都是,我们陶醉在这镶着金边的蓝色海洋中,嗅着淡淡的豆香(据说花布是用蓝草与黄豆染的),让心境似这土布一般熨帖、质朴。若隐若现中,朝我们翩翩走来的那小姑娘,敢情不是翠翠?不经意间,一条悄无人迹的深巷召唤了我们的脚步,乌镇有很多巷子,狭长的,深深的,我们刻意放慢了脚步,轻吟着《雨巷》,抚一抚斑驳墙面上的青苔,蓦然回首,只见那丁香般的女人撑着油纸伞从我们身边飘过,带着迷茫的眼神,哀怨又彷徨。
夜幕终于降临,喧嚣了一天的乌镇终于沉寂下来。再次踱进老街时,我们已是一身的蓝底白花,凉风如习,精神飒爽,此时的乌镇亲切无比,感觉就像在自家门口散步。夜色为乌镇平添了几层凉意,河边设有桌凳,我们只静静地坐着,一如对岸黑暗中沉睡的木屋,看翰林食府门前的红灯笼映在水波中一漾一漾,任由这被冰镇过薄夜在我们身边肆意流转,一瞬间突然感动得想哭。随意叫了几个家常小菜,几瓶啤酒,三个女孩在这异地的水乡高诵着《将进酒》豪迈地举杯再举杯,将脑中能记住的诗词从李白到李清照胡吟一通,酒不醉人人自醉啊。还记得那天为什么事回校晚了,不敢叫门,我们在操场上游荡了一夜的情景吗?还记得高一第一次数学考试全班考砸,我们蒙着被子哭的样子吗?还记得有次夜自修我们逃到外边小店看《还珠格格》,不好意思干坐着,每人连吃三碗水饺的情形吗?笑得满眼泪花,笑容和着泪水跌进酒杯,百般滋味……定格,任岁月流逝,这画面永不褪色。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为了看晨曦中的那桥、那水、那人家。乌镇散尽昨天白日里的喧闹烦躁后终于把最美最自然的部分展示给我们,静极了,听得见屋檐上露水的滴答声,路面上的青石板湿漉漉的,尽头在雾气中隐隐绰绰,街两旁清一色的乌檐青瓦、紧闭着的雕木门窗,透析出的是含蓄的乌镇……吱呀,一扇门开了,探出个花白的脑袋,紧接着商铺的门三三两两被卸下了,主妇们提着篮子准备买菜去,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来自上班族,每个人的脸都是恬静、从容的。我傻傻地看着这平凡的一天开始,只在想这小镇深处该藏着多少故事啊。
午后即将离别,我坐在乌篷船里,已心静如水,看两岸景致在我眼前浮光掠影而过,像极电影中的倒带,两天来的漫游已将心中的感伤烦闷驱散干净,剩下一身轻松。不由自主,沈从文在家书中的一段话浮现脑海:“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中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水流在我指缝中欢畅地穿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生是一场经历,逝去的也即得到的,用心了都能品味出一番滋味,又何必走着左边,看着右边,犹疑之时,岁月蹉跎。
责任编辑: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