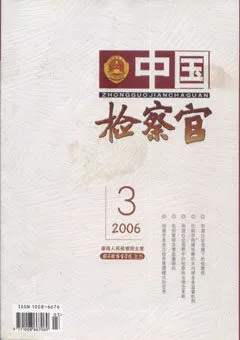个案中自然行为的综全评价
[基本案情]
2005年1月8日晚7时30分左右,吴晶晶在杭州市清泰街附近乘坐勾海峰开的出租车回家。当车行至吴晶晶家所在的滨江区水电新村停下后,双方因服务态度、车费等问题发生口角,勾海峰盛怒之下,用手掐住被害人的颈部,又用座位布套上的绳子勒吴颈部,看到吴晶晶不再动弹,勾海峰认为对方己死亡后,将她运至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抛到一个窨井内藏匿,终致吴晶晶因溺水合并压迫颈部而机械性窒息死亡(系法医鉴定结论)。之后,勾海峰还将吴晶晶随身携带的康柏手提电脑、三星T108移动电话、U盘、MP3各一只及人民币300元占为已有。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勾海峰因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被两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分歧意见]
在本罪中关于勾海峰的杀人行为和侵占财物的行为的定罪有很多争议,对于其杀人行为主要有三种观点:
(1)故意杀人罪(即遂);(2)故意杀人罪(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罪;(3)故意杀人(未遂)。
关于其侵占财物的行为的定性有三种看法:(1)盗窃罪;(2)抢劫罪;(3)侵占罪。
[评析意见]
一、关于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后一行为被前一行为吸收。在本案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一共有两个自然行为,即第一个行为“掐”和第二个行为“抛尸”,如果严格按照犯罪构成学说,则当吴晶晶被勾海峰掐致昏迷时,行为人发生认识错误,误认为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犯罪结果,这并不影响到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属于犯罪未遂。而此时勾海峰实施了第二个自然行为,将其“抛尸”河中,此时行为人又犯了一个认识上因果关系的错误,即其实施了“掐”与“抛尸”两个行为,伤害结果由乙行为“掐”造成,而行为人却误以为甲行为造成。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存在着杀人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杀害行为,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也确实是由被告的伤害行为直接造成的,具有因果关系,完全符合法条规定的所有犯罪构成要件。因而其错误认识不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应定故意杀人既遂。[1]
也有论者认为应定为故意杀人未遂。在该案中第一个自然行为确有杀人的故意,之后的第二个自然行为并没有杀人的故意,而是杀人行为的事后行为中由于不可能预见的原因所导致的“意外事件”或过失致人死亡,法律不应对被告无过错的后一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作否定评价。且因为法律不对事后行为作双重否定评价,而只评价先前犯罪行为。所以应以故意杀人未遂论。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1.所谓后一行为被前一行为吸收,即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我们可以比照非法买卖枪支后的非法持有枪支行为,以及取得犯罪所得后行为人转移、销售赃物的行为并不作否定评价而只是以前罪处理。但这样做并非刑法不否定后一种行为,而是与前一犯罪行为作综合评价。而且也应该看到,所谓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所作侵害较先行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较轻。本案中的“抛尸”行为虽然是杀害行为的事后逃避行为,但后一自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并不能被前一行为的否定评价所包含,并不能使用吸收犯原则。即不具有吸收关系,不成立“前行为是后行为的所经过的阶段,后行为时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2]这一特征。
2.关于两个行为不应一起做否定评价,即认为两个行为是在不同的主观条件下进行的,前者有犯罪故意,而后者无过失。这一点笔者不能同意。法条中所谓“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在本案中并不单单指前一行为,也包括后一自然行为,即两个自然行为都是在同一个犯罪故意下实施的,而且后一个“抛尸”行为应被认为是特别恶劣的情节,如果说前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充分说明有“直接故意”的话,那后一行为更加说明了被告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杀人。
3.我们可以类比交通肇事罪。当行为人在发生重大事故后,将伤者遗弃于荒野等难以被发现的地方而逃逸,使其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以故意杀人罪论处[3]。
由此看来无论从主观恶性还是客观伤害效果看,交通肇事罪中的遗弃行为都比本案中的“抛尸”行为较轻,而其所受的评价为故意杀人罪。所以说,即便第一个行为没有符合故意杀人罪即遂的犯罪构成,那么单看第二个自然行为,也完全可以以故意杀人既遂论处,并不存在故意杀人未遂。
4.关于“单独评价与综合评价”的问题。本案中所有关于罪名的问题实质上都是针对这三个自然行为究竟是应该综合评价还是单独评价的问题。勾海峰被判处故意杀人既遂与盗窃罪并罚,实际上把掐人致“死”与“抛尸”行为作一个故意杀人行为作否定评价,而之后的非法取财作为另一个对象作否定评价,我认为是合理的。
(1)前两个自然行为的主观方面相同,均为故意,虽然第一个行为故意的内容为杀人行为,第二个行为的故意是基于第一个故意而产生,第一个故意的效力及于第二个故意。是在同一个动机,即除掉对我的威胁而保护自己的主观方面支配下的。
(2)客体相同:都是侵害了死者昊晶晶的人身权,而后一种行为侵害的是死者的财产权。
(3)客观方面:都是以伤害行为为手段的侵害吴晶晶人身权的行为。
(4)有关联性:“抛尸”行为是杀害行为的后续行为,是对前一行为的补充。
如果前一行为单独评价,而后两性为综合评价,即只看到了’勾海峰主观的认为“掐死”行为为杀害行为,而后两个行为是为先行行为的隐匿罪证而采用的从行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片面注意了行为人主观认识方面,没有注意到主客观相一致的问题,是主观归罪的一种。
事实上本案中很难做到主客观相一致。主观上后两个行为是以毁灭证据为目的的,前行为是杀害行为,而客观上前两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后一行为造成了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以客观行为所表现出的主观恶性考虑,并不能单纯以被告供述的当时的主观思想为准。综合以上观点,本案中的杀人行为完全构成故意杀人罪即遂,吴晶晶的死亡结果并不是由于勾海峰的过失行为或意外事件引起的,而正是由于其故意杀人心态支配下的杀害行为所导致的。
二、关于取财行为的定罪问题
关于勾海峰事后取财的行为如何定性更应该仔细斟酌,现在就出现了关于抢劫罪、盗窃罪、非法侵占罪、杀人罪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等多种观点。我认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对于实施侵犯人身犯罪以后非法占有财物案件的定罪不能一概而论,要贯彻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后行为的非法占有行为符合什么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就定什么罪[4]。在杀人后的取财行为中,其财物的所有权已经因为继承关系即时转移给了其法定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的,所有物依法归国家所有。在本案中其物品所有权在被害者死亡以后就由其继承人共同共有。依照《继承法》第二条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这是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的。而由于其他原因故意实施杀人行为致人死亡,然后产生非法占有财物的意图,进而取得财物的应定为故意杀人罪与盗窃罪[5]。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6]。
1)主观方面:具有以秘密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和目的。至于在本案中,其动机是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而并非享受占有物之利益,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主观方面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2)客观上是秘密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侵犯的是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秘密指的是“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使他人发现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本案中勾海峰在被害人被“抛尸”之后,也即杀害行为完成之后,占有其财产,其主观上有“此行为不会使他人发现”的认识,即认为无论是被害者本人或其继承人都不会发现并认定是其所为。
3)其非法侵占数额法院认定为9000余元,大于500到2000元的数额较大起评线。
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被告人判处盗窃罪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3]邓又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与司法适用》,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7页;转引自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
[4]赵秉志主编:《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5]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页。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6页。
作者:浙江大学法学院 [3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