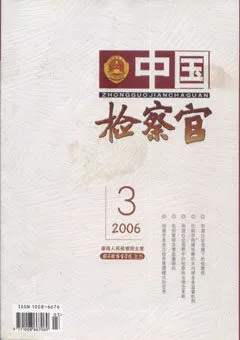法律是什么
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如果没有分类的能力,人类将无法生存和采取行动。某一行为恰当与否,往往取决于行为者是否符合社会普遍承认或遵循的社会关系分类。事实上,正是分类使我们每个人获得了秩序的感觉,把我们周围的一切变成了有秩序的存在。如果把法律视作文化,分类则是法律的核心,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分类的实现过程。当立法者开始创制法律之时,首先要明确究竟将要运用法律来处理哪些事实,法律的管辖范围究竟到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形成过程都是对本国的法律现象的分类过程,都是本国的立法者的分类观念的运用和体现。
另一方面,法律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每个国家的法律其实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一种规模巨大、效力层次极高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人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到处存在着不同的法律意识,法律以地方性知识的姿态存在并运作着。如在我国某一少数民族的宗教观念中,鬼是普遍存在的;佛寺中具有巫的能力的经师,可以运用他们熟识的驱鬼方法驱逐某种类型的鬼,并且认为被他们视为鬼的人其实已经不是人,而只是鬼的一种。所以在他们的分类系统中,人们对被视为“鬼”的人进行殴打只是驱鬼的仪式,而不是对人的伤害。如果法律是地方性知识,那么就必然存在地方性规范、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
现代的国家法律和地方性规范、习惯法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套分类体系。但是国家法律作为一套精英阶层的知识产物,与地方性规范、习惯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地方性的分类体系中容纳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神的态度、对宇宙的想象、邻里相处之道等非技术性的意义因素。国家法律则是一套被认为是理性建构的分类体系。这套体系也包含着价值,但它所包含的价值对社会大众来讲CJaeQy8anfRj1KDwgWX68aqJEhiNVQlIrHRPuL5yO5s=是抽象和遥远的,而且它是具有普适性、技术性的分类体系。国家法律与地方性规范、习惯法发生冲突的根源在于,特定知识型支配下的分类体系出了问题。因此,用一种强力压制另一种强力,或采取立法上的变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地方性知识所引起的法律冲突。实证经验告诉我们:地方性知识并非一层不变,人们的分类体系以及支配行为的逻辑是可变的。解决之途在于:(1)改变地方性规范或习惯法的分类观念;(2)弥补这类分类观念之不足。只有通过上述方法,我们才能解决国家法律与地方性规范、习惯法间的冲突,达至法治建设的目的。以法律多元主义立场考量,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来讲,不是如何去消除法律间的差别,而是如何处理差别的法律。
(作者:云南大学法学院教师。文会摘自《现代法学》第26卷《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