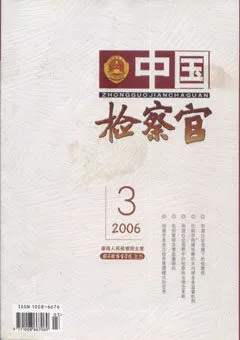监督,能否与法治自兼容
“监督”是从古到今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汇。中国传统监督制度历来发达并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却难以产生廉明高效的政府。与之相对,在西方制度体系中并不存在被冠以“监督”之名的公法意义上的制度,然而其发达的法治与有限的政府却相映成趣。中国与西方监督制度上的差别引起我们的反思:监督究竟是不是法治的范畴?它能否与法治兼容?
自秦汉以降,监督制度就开始在中国形成,并日趋发达。究其原因,它与中国社会以权力为核心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化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制相关。在一元化的传统社会中,所谓“监督权”只是国家权力一部分,和一般官僚权力并无本质区别:权力来源君主,机关层层设置、权力层层下达、监督者层层向上级负责,完全是以行政的方式运作。传统的监督制度模式是典型的人治方式,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法治意义上的制度。但它所承载的“以权力进行约束”的功能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比如,在西方也存在着与中国类似的弹劾制度。但西方的弹劾制度以权力分配和制约为基础,以正当程序为保障,以对行政权的制衡为归依。这在法律制度中就表现为法治的重要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中国的弹劾制度则与之相左,为君主所利用,成为君主操纵的“术”与“势”,离“法治”非常遥远。
以法治的立场分析传统监督模式,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1)以“人盯人”的方式实行监督,虽操作灵活,但效力缺乏稳定性;监督或可能归于无效,或可能异化为专制工具。(2)倡导清官能吏,制度上严重依赖于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是制度外的因素,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无法成为制度化的基础。(3)监督权力范围宽泛却缺乏规范化。监督者的权力界限不明确,监督权被滥用的现象难以从制度上加以避免。(4)监督效果虽能立竿见影,但困于出事后察办的意图、制度设计上对监督主体及其级别的倚重、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等,传统监督虽可治标却难以治本。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监督模式,还需要以法治的方式,从权力分配和权力制约人手、借助正当程序、根据监督对象的特点使各种监督法治化,从而将监督制度纳入现代法治系统中来。
(作者:浙江大学法学院。文会摘自《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