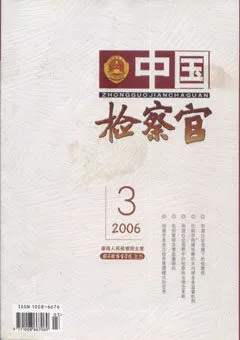我国刑法中若干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完善之研讨
内容摘要:具体犯罪法定刑的设置,是以通常情况下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和最低程度为标准。倘若法定刑与犯罪不相适应,刑事司法就不可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针对我国刑法中几种常见犯罪的法定刑配置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的立法规定。
关键词:犯罪法定刑刑罚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之法定,是指立法机关在刑法分则性规范中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予以明确规定。具体犯罪法定刑的确定,是以通常情况下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和最低程度为依据的。国家认为某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大,就会规定较重的法定刑;国家认为某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就会规定较轻的法定刑。一般情况下,法院只能在法定刑的范围内选择与犯罪相适应的刑种和刑度。只有在刑法有减轻的特别规定时,法院的量刑才可以低于刑法配制的法定刑,但这种减轻即在法定刑度最低刑以下裁量刑罚仍是以法定刑为依据的。[1]倘若法定刑与犯罪不相适应,刑事司法上就不可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适度的刑罚才能有效地保障刑罚目的的实现,不适度的刑罚,过度如重刑化,不及如轻刑化,则不能有效地实现刑罚目的。“刑重于罪的重刑化,不仅使犯罪人不再产生痛苦与后悔心理,反而使犯罪人滋生仇恨与对抗情绪,其反社会心理因过度的刑罚而强化,为了补偿过重刑罚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他完全可能再次犯罪。刑轻于罪的轻刑化,因适用的刑罚是轻缓的,没有制成罪犯预想中的痛苦,其惩罚效应也就难以实现。犯罪人不再惧怕刑罚,甚至可能轻视刑罚,今后实施犯罪更加肆无忌惮。”[2]总的说来,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法定刑的规定已充分关注到刑之适度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综观我国刑法分则的一些罪刑规范,仍然存在可商榷之处。我们仅选择其中几种常见的犯罪的法定刑配置问题作一评析,并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一、对在绑架犯罪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在其法定刑立法中增加无期徒刑的规定
刑法第239条第1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条中对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的规定,即是针对绑架犯罪中出现的特定情节采用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绝对确定的法定刑适用特点是,只要确定被告人行为符合罪状的规定,即可依法判刑,无须对刑罚轻重进行考量。具体到绑架罪来说,如果在犯罪人实施绑架过程中致死被绑架人死亡的,即对犯罪人适用死刑。显然,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在具体案件中,根据同一种罪的各种不同情节,对被告人判处与其罪行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轻重适当的刑罚,从而影响刑罚目的实现的效果。[3]司法实务中,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往往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后果,有的是故意杀死被绑架人(即俗称“撕票”),但有的却是在绑架过程中,过失造成被绑架人死亡,或者引起被绑架人自杀,或者由于犯罪行为人对被绑架人使用暴力过重造成被绑架人伤害致死。如果不考虑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差异而一律科处被告人死刑,也有失公平。为了弥补绑架罪中法定刑立法的这一缺陷,我们认为,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在其法定刑立法中增加无期徒刑的规定。这样,既能避免出现过度刑罚,又不影响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绑架犯罪行为人的严惩。
二、应从立法上废除盗窃罪的死刑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犯盗窃罪,有下列情节之一的:(1)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2)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由此可见,现行刑法对盗窃罪适用死刑的条件作了严格限制,即必须具有两种法定情形之一的,才能适用死刑。盗窃罪属于典型的侵犯财产关系的犯罪,这种犯罪行为并不危及国家、社会安全和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盗窃罪的危害性也不同于职务性的经济犯罪。我国刑法中职务性经济犯罪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行为的廉洁性,破坏党和政府的声誉。立法者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对贪污贿赂罪的最高刑规定为死刑,符合我国当前同这类犯罪斗争的实际情况。[4]而对盗窃犯罪,其法定刑中则不应规定死刑,对其适用死刑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我们认为,对盗窃犯罪,只要刑法达到一定的严厉程度,如判处无期徒刑并附加财产刑,而且刑罚具有不可避免性,不适用死刑,也可达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基于此,我们建议,应从立法上废除盗窃罪的死刑。
三、取消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入户抢劫的;(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3)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4)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5)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6)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本条第6项规定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是指冒充军人和警察实施抢劫犯罪,其中警察包括公安民警,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冒充”的含义是以假的充当真的。“冒充军警人员”是指通过着装、出示假证件或者口头宣称充当军警人员的行为。[5]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法定加重处罚的情节,显示了立法者对军警人员这一特殊身份的重视和保护。冒充军警人员身份的抢劫行为在侵犯了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利之余,还极大地破坏了军队和警察部队在人民群众中良好的声誉和正义形象,从而不利于军队和警察部队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利于国家安定和社会团结。较之那些没有冒充军警人员身份实施抢劫的行为,冒充该身份而抢劫的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大。而军警人员自身抢劫对军队和警察部队形象的破坏更为直接,其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则更大,因此建议将刑法第263条第6项修改为:“军警人员抢劫或者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6]我们认为,关于是否应将军警人员抢劫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则恐有不当。刑法理论上认为,以身份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为标准,可将刑法上的身份分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身份、影响刑罚轻重的身份、排除行为犯罪性或可罚性的身份。由于一定身份而成立的犯罪或影响刑罚轻重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叫做身份犯。影响刑罚轻重的身份,又叫加减身份,即具有一定身份犯某种罪时,法律规定予以从重、加重或从轻、减轻处罚。由于一定的身份影响刑罚轻重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叫不真正身份犯或不纯正身份犯。[7]例如,诬告陷害罪是一般主体均可以构成的犯罪,但我国刑法第243条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我们认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不属于身份犯的范畴,冒充军警人员实施抢劫行为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影响并不具有刑法上的直接意义。司法实务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行为人主要是利用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恐惧心理,在不需要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种胁迫型的抢劫的危害性与一般胁迫型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毫无二致,而且比直接使用暴力手段的抢劫行为的危害性要小。因此,立法上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不具有合理性。我们主张,从维护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实现刑罚目的出发,应取消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规定。
四、贪污贿赂罪应增设罚金刑,对受贿罪应规定独立的法定刑
我国刑法对抢劫、盗窃、抢夺、诈骗等财产性犯罪规定了必并制罚金刑,而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行为人没有规定罚金。除了对单位受贿、行贿规定了并处罚金外,在许多条款中,只规定了没收财产;而没收财产,也是在犯罪行为有特别严重的情节,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才并处没收财产。这实际上给司法实践留下一个缺口,有可能使许多贪污贿赂犯罪分子逃避经济上的惩罚。并且,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既没有规定罚金也没有规定没收财产,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贪污贿赂犯罪具有职务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社会危害性及对国家财产的侵害与盗窃、诈骗、抢夺等犯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种贪利性犯罪必须在经济上给予严厉惩罚,如并科罚金刑剥夺其金钱,破其所图,灭其所欲,才能有效地遏制贪污和贿赂犯罪。[8]因此,立法上对贪污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不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要求,而且与当前罚金刑被广泛使用的世界性趋势是相一致的。
此外,我国现行刑法单独规定了贪污罪的法定刑,但对受贿罪却未规定独立的法定刑。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到数额及其情节,依照贪污罪的处罚规定予以处罚。我们认为,虽然受贿罪与贪污罪在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有某些共同点,但两罪在其构成上却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贪污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贪污罪既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的客体的差别决定了两者应有不同的处刑标准和依据。对于贪污罪,法定刑设置的基本依据是贪污的数额和情节;对于受贿罪,除了数额情节影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外,权钱交易行为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造成损失的大小,应当是其法定刑配置的一个基本依据。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建议,应根据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和处刑要求规定单独的法定刑。法定刑的确定,要体现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主,兼顾法定刑配置的横向协调,即既要依据受贿行为给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造成损害的大小,又要考虑受贿的数额和情节,相比较来说,对受贿罪规定的法定刑应重于贪污罪。
参考文献
[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 527-528页。
[2]周光权:《法定刑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3]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4]参见曹子丹:《我国刑法中贪污罪贿赂罪法定刑的立法发展及其完善》,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
[5]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下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6]刘艳红:《冒充军警人员实施抢劫罪之法定刑设置疏漏》,载《法学》2000年第6期。
[7]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8]参见韩轶:《对必并制罚金刑立法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陈冰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