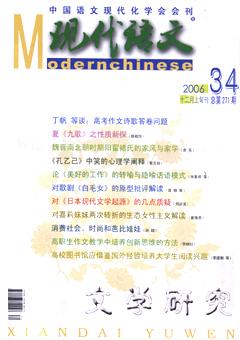生命气韵的人类学之思
冰 虹
李存葆是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军旅作家,他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的十九座坟茔》等作品不仅家喻户晓,而且对一代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塑造的立于老山的英雄群像,关涉着青春、奉献、抉择,铸就了一个民族向上的灵魂。他的小说注重感性表象的细描与理性精神的渗透和升华,充盈着对时代精神的张扬,弥漫着对生命的颂扬,使国人读到了悲痛却不失雄壮、哀婉却境界博大的故事,使国人理解到军人的精魂。在新时期,李存葆逐渐把创作重心转向散文,推重智性写作,强化介入事件的多角度分析并注重叙事的多元化手法,把生命中的点滴感悟延伸到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思索,重视散文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对于李存葆来说,散文是暴露生命疤痕的阵地,陈列人性病症的展厅,因而,他的散文题材广泛,但其笔意却大致不脱离对生命气韵的反思与追问。借助散文叙事,李存葆以游刃之笔,描画生态环境的问题、追问精神的病症,或者借用游记散文的传统笔法,梳理景物的历史源流,虚与委蛇,启人智性,引来反思,或者直言水患、污染、残杀生物等现实问题以及伴生的生存危机,重析理的清晰透彻,层层推进,直陈思想,发人深醒。
进入历史河流寻觅传统文化中的语句诗韵,对于李存葆来说绝不是一种文人复古的表面装璜,而是贯通着一种依恋儒家心系当下的入世情怀,他以散文之博采万象,游走历史,关切现实,其中也不乏愤慨与遗憾。在《大河遗梦》中,他实写自1985年至2000年间黄河的几次断流,且在时间长度和断流的距离上一次比一次严重,描述黄河与沿河省份的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曝露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带来的生存困境等;虚写却是黄河断流表征的民族灵魂的失落和遗忘,并由此把社会的浮靡、焦躁以及各种低迷的精神现象统合一处。《霍山探泉》则以大西北水资源的匮乏映显珍贵,他曾如此描述“走陇西,穿定西,越西海固”目睹的自然风貌,“那一座座窳劣的远山,像头头被剥了皮的巨兽的干尸,僵卧天际;那一道道突兀的近塬,像只只筋骨风干的鸵鸟爪子,死箍在没有半点绿意的颓壤上。水在‘三西的奇缺、稀贵,任凭人们怎么想象也不以为过。”水的危机引发了洪洞与赵城两县的世代争战与男女不通婚的结局,而波及动物则有了“狼抱水”的传说、老牛拦截军用运水车为小牛讨水场面等。但即使如此惨象依然难以阻止“偷挖陶土,偷钻小煤井,偷劈山烧石灰”的人类不智之举。黄河、泰山、永济、临汾等山川地域是李存葆展示其历史想象、抒发其幽古之思的理想之地,在回望历史的文本中李存葆秉承着传统文人的浪漫,使景物描写兴味昂然,诗韵婉转,极富田园野趣;而逼近现实场景时,他却时时以冷静的析理展示生存中冰冷的苦涩,在比较中使人超然景外,于历史场景中的色彩斑斓与现实场景中的浮靡动荡的冲撞中反省、沉思。另外,李存葆把其社会人生阅历与对世事人情的思考融注其中,注意客观形象与事件的象征、隐喻的一面。在物质性与精神性并重的叙述中,彰显精神层面的思考与追问,用以抒发其内心世界的焦灼以及劝阻世人去净化自己的心脉。他细致地捕捉现实表象,以隐喻或直喻串连当今社会中纷繁的事件,并以“殇”字等统合文明社会中的“不文明”、人性世界中的“非人性”,批判在科学化、工业化图景中人的理想、道德信念等的坍塌和毁灭。比如鲸鱼的自杀之谜背后影射的人类的残忍与利益驱动下的对自然的损毁(《鲸殇》)。
李存葆的散文理论与实践,拓宽了散文书写空间,使它不仅是文人表达情感的“小散文”样式,而且能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能回到人的本质层面上审视并揭示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问题。“文化散文”之谓,也就不仅指向对社会世像、精神流脉的文化梳理,而成为知识者以现代性眼光透视日常生活,以当代哲学反思人文信念的阵地。这类散文有别于主写日常情感、日常事件或人物回忆性的散文等,而是具有浓郁的人类学意味。如《祖槐》等作品借一句儿歌,“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进行农民家族的寻迹。有论者把李存葆的散文界定为“智性散文”,但在笔者看来,李存葆是以“智性眼光”、“审慎的析理”与“审美精神”等共同构建了“文化散文”的阵地。如《飘逝的绝唱》从表面看是在为古典爱情的飘逝黯然神伤,而实际上却是在思索人性底线到底推至何处?他写永济普救寺,移步换景,作品借“待月西厢下”的现代叙述,把永济普救寺的山势水脉,房舍连廊描摹与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事件复述交错进行,把佛家哲理之思与古代情致之妙贯穿其中,使当年的爱情随着景物渐次推进。而现代社会诸种关于爱的“新现象”在与张生莺莺的古典爱情的比衬中,让人感到有贫血之憾。通过对现代情欲事件的层层剥离,尽显“物欲”下的血腥、残忍以及冷漠与贪婪中的浮靡与精神萧瑟。现代人生活的多姿多彩与爱情故事的变化多端并不能冲淡当下人等精神上的低迷,而私欲的升腾与不加节制则逐渐变换为吞食人性的怪兽。文末“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一语,既做点题之用,更显作者痛愤之情。
在20世纪文学处于文化转型之时的中国,崇尚私人体验、个性写作的诸多写手,逐渐视社会万象于不顾,以偏激执拗之语为本根,破除历史之限度,打烂传统局囿,一任情感的汪洋恣肆,迎合世俗,违背文责。可以说,在当代有相当一批作品,只注重潇洒、轻佻而轻松的写作语言,注重事件的无厘头表述,或者以娱乐为本,或者成为新兴哲学理念的某种文学图解。他们无助于当下社会的人文精神建设,缺失了直面社会的历史进程并展示过渡时期人类内心的孤寂、痛苦,表达疯狂与寂寥、娱乐与道德失衡以及轻佻与无奈之间的悖谬。有论者指出“文学要回到基本问题”,但我以为这并非关于文学自救的新创获,因为文学与生活的差别在于能否为世人提供另一重世界,而“文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只是迎合了当下文学转型关于边界、观念的困惑,但目前文学所需要的是对优秀文学样式与内蕴的探究。李存葆在《也谈散文》中的思想更值得重视。他说:“常听人说散文‘贵在散,可‘随意去写,心中不免戚戚……散文的‘随意不是信笔涂鸦。大匠运斤、大巧若拙的随意只有那些天赋很高、艺术功力很厚的散文大家才能获得。这种随意是无技巧之技巧,是一种朴素的到极处的境界。”这里透露着作家对目下许多以形式上的散乱、杂糅以及所谓“新潮”的写法的不满,其中部分导致了一些散文作品徒具其表,而言之无物的弊病,也因此导致了散文的式微。他不仅仅提及了散文注重“法度”而求形式美,把创新阐释为“合乎情理的突破”,而且总结了散文的四个原则,即“讲究气、韵、趣、味”。这里,李存葆表露出其新的散文理念,即散文要追求优秀,而不是界定散文的边界。如他所言:“也许我们倾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但达到优秀并非靠无病呻吟,去关注风花雪月,而应该 “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急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李存葆重视“万物人格化”的艺术表达,这一思考反诸其散文创作,则有了对鲸鱼的人道主义思考,黄河的母亲意象与民族意象的遐思、峨嵋塬下飘逝的绝唱,使其散文充满着情与理的妙趣,而在其关于画家、绘画的评论同样立足于此。《大河遗梦》收集了大量的画论与画家评传,可以看出,李存葆非常重视个人的生命经历的艺术化书写,关怀时代的周转变迁对画家的成长影响。他写人重在人物呼之欲出,评画则重具象分析与理论上的抽象提升,其评传画论真正做到了言语有实、兴味有加。如写评传,他抓住林凡先生老骥伏枥的韧性与诗性、冯大中画虎的坚执与顿悟、刘大为身上的宽厚儒风与对艺术的细密敏感、张道兴的蔼蔼长者风与悠悠艺术情,以之铺展他们的画虎成迷、绘佛着魔、戏纳百家。李存葆对他们的艺术之途叙述的张驰有度,精选他们的人生事件勾勒出一副完整的人生图景,以文字勾勒“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的求知之图,把“待得云开见月明”的那份既苦涩又欢悦的过程烘托而出。在言简义丰、余味邈远的叙述中,画家们勤奋、执着以及对艺术的特殊的喜欢和参悟的机心随之浮现。他论画时,虽注重画作的气韵,但更强调“万物的人格化”。在描述林凡的画时,他指出画中“小草、青萍、藤萝,经画家的‘诠释,生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具有读不尽的人生况味,甚至令人摇魂荡魄”;而冯大中的《觅月》、《惊梦》之所以为艺术界高度评价,也正因“大中把‘对象化的虎视为人类的契友只因,用人情美攫住自然美的感知,在虎的艺术天地里徜徉。”辰生绘佛之所以鲜活、灵动,颇具个性,也正在于他“陛下的佛是走下神殿的活生生的‘人化佛,颦笑之间,透露出人间的种种风情;行卧之中,勃发着生命灵动的可爱。”推崇艺术的人生化,重视“清泉出山未染尘”的气质,在总体上显示着对生命趣味的重视。
人的存在总与时代、文化相关,而艺术之于社会同样要应时而动,恰如约翰·拉赛尔所说:“当艺术更新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随之更新。我们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种休戚相关之感,有一种与之分享和被强化的精神力量。这正是人生所应贡献于时代的最令人满意的东西。”散文的更新不仅指向文体的变革、散文观念的变化,而是体现了一种对审判力的要求:即不要单纯描摹生活,而要“避免给社会制造文字垃圾,而应为人民多提供一些精美的精神食粮”。李存葆以对自然万物的观审,进行精神的淘洗,使之灼显光华,既含蓄蕴藉,又密合时代。在当下高喊个性的时代,李存葆于散文中体现的审美情怀与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自有其卓越不凡的魅力。
(冰虹,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