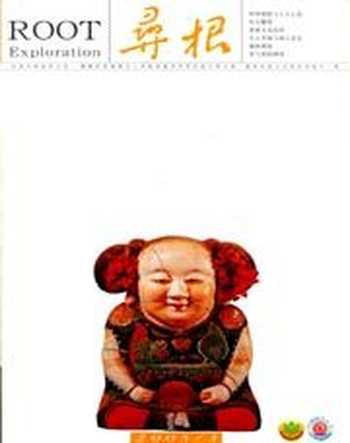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
石焕霞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继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文官选拔制度,它创始于隋,废止于清末,历经1300多年,为历代统治阶级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也为世界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科举制度亦是如此。它虽然是为了革除历代铨选制度中的积弊而创立的,但“十年寒窗无人间,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使科举之中的作弊方式更加形形色色,毫不逊色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察举制,而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九品中正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弊的泛滥最终把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但是却把科举制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然而一千多年之后,作弊又把科举送向了历史的终点,同时葬送的还有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运。这就是科举与作弊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共同演绎了“十万进士”悲壮而又绚丽人生。
一
唐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严密的考试规范,虽说凭考试成绩举人,但权贵的意志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由于人为的干预,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公开而且难以遏制。唐玄宗时有一个叫张爽的纨绔子弟,世人皆知此人不学无术,但因其父官拜御史中丞,竟被录取为第一名,舆论大哗。玄宗不得已,只好对原取中的进士重新考试,张爽手持试纸终日不下一字,被人称为“曳白”。这件事被人们视为科举史上的笑谈。
唐朝统治阶级看重诗人,世人仰慕诗人,在这双重社会导向下,许多文人学子都把吟诗作赋当成自己入仕的敲门砖,并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风尚“行卷”。所谓“行卷”,即应试举子将自己平日所作诗文择其佳者,投呈给当时的名公巨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求其赏识,为之制造声誉,以增加及第希望的一种途径。李白刚到长安时,因没有什么名气,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荐给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扬天下。
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行卷”的确曾使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崭露锋芒,然而这种做法至唐后期却变了味。历史上虽有张籍与朱庆馀和诗的佳话,但也有“杜牧文章只得第五”的慨叹。不过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杜牧已经够幸运了,更多的寒门士子,虽有诗卷却无处投呈,虽有文名却无人为之延誉,如晚唐诗人杜荀鹤,诗名虽高却屡试不第,只好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哀叹。另外,还有许多人钻“行卷”的空子,弄虚作假,欺世盗名,“——鹤声飞上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的是杨衡的一位表兄弟,窃取了杨衡的诗文,应举及第,杨衡知道后,赶到京城应举,也被录取。一次,他见到了这位亲戚,愤怒地问道:“‘——鹤声飞上天这句诗还在吗?”此人回答说:“我知道这是您最爱惜的一句诗,不敢辄偷。”话说到这个地步,我想读者应该已经很明白了,除了杨衡的个别名句外,其他作品很少有不被他窃取的了。面对科举及第的引诱,士人竟无耻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让人深思。
“行卷”促进了唐文化的繁荣,尤其是促进了唐诗的兴盛。然而“投卷”的泛滥也为很多权门贵戚进行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严重削弱了科举考试成绩本身的分量,“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诠实用,百无一人”(张鷟著,袁宪校:《朝野佥载》)。
二
宋朝科举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自宋太祖禁止“公荐”以来,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弃取,各种考试法规也越来越严密。其中“十人互保连坐制”的出现完善了科举考试的报考手续,对于防止考生冒名顶替起过很大的作用;锁院、弥封、誊录、对读则可以防止考官漏题、泄题和徇私舞弊;而殿试的制度化则主要避免了官僚贵族弄权舞弊。这些防弊措施的推行限制了很多因科场管理不严而产生的弊病,像冒籍、挟带、倩枪等作弊形式。同时,严格的管理也打破了土族与庶族甚至平民知识分子间的界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然而古语有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宋代虽采取了诸多的防弊措施,但由于朝廷吏治的腐败,许多考官贪污受贿或者逢迎权贵,每每使这些有效的防范措施成为一纸虚文。宋徽宗时,皇帝宠幸的宦官梁师成去参加科举考试,考官畏惧其淫威,另一方面也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居然使其中了进士,而且投靠他的储宏等人也都考中,被赐进士及第。可见当时权贵干预科场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北宋出现的形式隐蔽的“通关节”也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作弊手段。具体讲就是考生与考官串通作弊,考前约好在试卷内作好记号,考官入场后留心于他要关照的人,凭手头字条上的关节暗号录取,决不会遗漏,那些送了银子通了关节的考生哪怕是答卷驴唇不对马嘴也能取中。其中最典型的暗通关节的例子就是“丕休哉”,说是北宋有个叫杨亿的翰林学士,声名很高,在省试开考前夕,他特地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举子们求他赐教,他勃然变色,口中边说“丕休哉”,边甩袖而去。“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在场的同乡举子们,死脑筋的以为碰了钉子,聪明点的则听出话中有话。果然,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都被录取了。由此可见,“通关节”是一种很难杜绝的作弊方式,不光因为它行事缜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和朝廷的政治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要说宋朝,就是明朝、清朝,直至今天,这种作弊手段依旧是屡禁不止。
南宋立国之后,政治腐败日益加剧,科举考试中的作弊方式更是花样百出。上面朝廷苟且偷安,下面士风委靡颓丧,科场内外行贿请托之风益加猖獗,尤其是秦桧当权之时,科举考试甚至成了他提拔亲信、排斥异己的工具。绍兴二十四年省试,秦桧派亲信魏师逊、汤思退等同知贡举,一致议定秦桧之孙秦埙列入榜首,秦桧的亲信周寅第四,秦桧的姻亲沈兴杰等为进士及第,公然利用手中的职权使自己的亲信高登科甲,其肆意妄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可见,宋朝虽然是科举制度发展较为完备的时期,但由于其政治上的昏庸腐败,导致科场上乌烟瘴气,种种作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真正的人才根本难以崭露头角,科举制度网罗优秀人才的社会功能逐渐被淡化。
三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有了较完备的制度和规则,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弊之风一如既往。明代舞弊之法,贿买、钻营自不待言,关节之弊更是比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夹带、枪替、割卷、换卷、传递、顶名、冒籍,更是
常见。挟带是将马二先生之流的程墨选本,藏在隐蔽的地方带进去。官家为防止夹带,采取了搜身检验、沐浴更衣、衣履必须拆缝、物件不准夹层,甚至所带食品都得切开过目等防弊措施,可是夹带窍门也层出不穷。据《泾林杂记》记载,明代夹带者一般事先请人将经书用蝇头细字写在金箔纸上,或者藏到笔管中,或者放在砚台底下,或者放在鞋夹底之间;又有用药煮后写在青布衣裤上,涂上泥巴,入场后擦拭干净,马上能够看见文字。枪替是请人在科场代劳,当时还没有相片可以验证,只要年龄、相貌相近,方言相同,代考一般很难查出来。传递是请外人做好文字后,托闱中的官员、胥吏送进去。甚至有遥点竿灯、连燃炮竹、纵放铃鸽、抛掷砖瓦以为信号。由此可见,当时士子为了能够科举及第,真可谓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除了这些暗中做手脚的平民士子之外,当朝权贵仗势压人、横行科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万历五年会试,张居正的儿子原来是二甲二名,后来在宦官冯保的活动下,改为一甲二名。我们知道,张居正在明代官僚中,还属于有为之士,他为了一己之私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一般的昏庸之辈,甚至贪宫污吏了。此外,明代宦官干预科举也是常见的。正德三年会试,太监刘瑾将50人的名单交给考官,考官无奈,只好增加50个名额。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科举制中,权贵的滥施淫威比起那些士子的小打小闹来说,是更大的危害。
时至清代,尽管江山易主,然而科场积弊却沿袭下来,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科场已经成为了买卖市场。《清稗类抄·考试类》中记载,一个老童生每逢童试必带一蟋蟀盆入场,且自标于桌曰:“出卖警句,每句钱七文,不二价。”每到日暮时分,盆中钱满,缴卷径出。如果说这种公然在科场前作八股文进行买卖的行为已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那么在清代出现的几次科场大案则让人怵目惊心。
科场案并不始于清代,但是清以前发生的次数不多,而在清朝则发生颇为频繁,而且影响比较大。比如说嘉庆三年的乡试案,这是湖南最大的舞弊案。彭峨是岳麓书院的高材生,为山长罗典所赏识。这一年彭峨在秋闱出场后,便将文稿交于罗典看,罗击节赞赏,认为解元非他莫属。可是榜发时,彭峨竟然名落孙山。这时罗典除了大骂主考官有眼无珠外,也无可奈何。不久闱墨发刊了,第一名宁乡傅晋贤的文章竟与彭峨的文章一字不易。罗典怒发冲冠,当即跑去质问监临的巡抚,要求调出原卷,核对笔迹。巡抚大为惊恐,即日审出实情,原来是傅晋贤以重金贿赂了弥封官,移花接木,将二人试卷的封面换掉了,这种做法叫做“剥皮鬼”。人奏,傅晋贤不消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咸丰戊午科的顺天乡试案,也是一次引人瞩目的科场大案。这次案件事发于戏园玩票者平龄中第七名举人,舆论大哗。因为按照科举条例,职业演员即所谓的“优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玩票”并非职业演员,自然不适用于这一规定。然而平龄中试人们却议论纷纷,因为御史孟传金疏劾平龄朱墨不符,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主考官柏葰受人请托,撤换试卷;副主考官程庭桂收受关节,接纳“递条子”百余张;同考官受贿等。这次科场案先后牵扯到91人,上自朝廷大员下至士子举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大学士柏葰不仅是清代科场案中被斩决的惟一的一品大员,在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官员中,他的职位也是最高的。
这两次案件并非清代科场案的起始,也并非科场案的全部。然而以往科场案中血的教训却如此让人漠然,这也许就是科举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魅力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末的科举制度就像一根被积重难返的舞弊行为蠹空的擎天柱,终于难以承受封建社会这片天空的重压,于1905年走完了它的人生旅程,为其漫长而又精彩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纵观科举制度在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越是到封建社会后期,科举与个人的前途,甚至与整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得越紧密,所以,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王”是士人参加科考的最终目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读书人甚至文盲都会背诵这样一首流行一时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在这段崇尚“学而优则仕”的时代里,人们逐渐从家世门第转向了对人自身能力的关注。然而作弊的存在又使人情门第观念重新跻身于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中,严重损害了科举考试中“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也消解了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但是,作弊在客观上却也有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从历史上来看,作弊和反作弊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正是有了作弊和反作弊之间的较量,科举制度才越来越成为一种趋于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且看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正是有了官僚贵族舞弊,才有了殿试;正是有了关节作弊,始有了延续至今的弥封制;正是有了知贡举漏题泄题,才出现了锁院、回避和别头试……总而言之,正是有了形形色色的作弊手段,才制定了各种反作弊的制度和措施。也就是说,由于作弊手法的多样化,科举制度才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过多的作弊手段,致使科举制度行至明清已然积弊丛生,于是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又制定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防弊措施——八股文。八股文的出现,虽说是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产物,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阅卷官的主观好恶以及徇私的可能性,从而保证了国家科举取士的公正。随着科举考试中的主观性越来越少、客观的限制越来越多,培养的“人才”都变成了一群热衷于科举钻营的“禄蠹”,一群不会思想、不会思考的庸碌之才,人才的匮乏最终使科举制度迈入了死胡同,继而又间接导致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消亡。
作弊是人们永远试图消除、但又永远无法消除的弊病,它和科举制度相伴而生,促使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但最终又导致了趋于完善的科举制度走向灭亡。这就是科举与作弊之间永远难以理清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作弊、败也作弊”。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教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