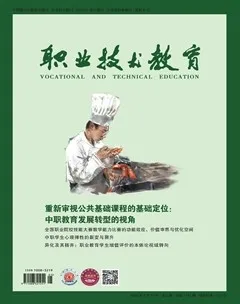异化及其扬弃: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本体论视域转向
摘 要 教育评价是引导教育发展方向的指挥棒。立足本体论视域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评价现状进行哲学反思,其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主体的异化现象映射了本体论之认识论传统与人之生命实践要求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增值评价因其本身的生存论特征,代表着教育评价之哲学本体论基础从认识论传统向生存论的转向,为扬弃职业教育学生评价异化问题提供了可能路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概念,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需要正确处理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在三者协调共生中走向完善。
关键词 职业教育;增值评价;异化;本体论;生命实践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5-0070-06
异化,原意为分离、疏远、陌生化。哲学上,指主体活动的后果变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指向复归人性、全面恢复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1]。因此,只要劳动仍然充当人类生存的手段,人的自我异化就不可避免。而职业教育因其与社会生产的紧密联系,其本身的异化具有通过劳动的传导机制渗透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扩大化效应。教育评价是引导教育发展方向的指挥棒。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增值评价”。增值评价作为教育领域评价改革的关键词,获得了广泛关注。然而,当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增值评价的概念辨析、历史溯源、现实意义与困境探讨、对策建议等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其学术话语仍然未深入到对人之存在这一本体论问题的探讨。所谓“本体论”,是关于“存在者”的学问[2]。它涉及到对于人“何以存在”以及“怎样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因而为一切人性活动提供着原始思想及其超验的价值根据。因此,立足本体论的哲学视域,以对异化评价的理性反思为逻辑起点,论证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必要性、可能性并提出其理性建构的基本构想,是回应“教育为人生”之规定的根本性要求。
一、职业教育学生评价的异化:本体论之知识论传统的映射
自巴门尼德(Parmenides)将存在等同于思维范畴以来,到黑格尔(Hegel)历史哲学对理性本体论的完成,人类关于自身生存之根的探求始终围绕作为概念思维的理性而展开,这即是本体论的知识论传统。这一知识论传统使科学思维及其客观化理想广泛渗透于人类生活之中。然而,伴随着理性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高歌猛进,抽象理性法则所带来的异化问题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凸显。以职业教育这一特定的社会领域观之,其教育评价的异化构成本体论之知识论传统与人之生命实践要求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的映射。
(一)评价目标的异化: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
“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3]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非外在于人、先在于人,并在价值维度上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抽象实体。然而,本体论的知识论传统使理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走向工具化,个体的生命异化为社会大机器正常运转的微小零部件,仅仅被用来增长以经济学上的价值尺度来计算的抽象的社会物质财富。其结果是人的物化,个人沦为实现社会这一悬置于自我之上的抽象实体之目的的手段。从职业教育领域来看,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突出表现为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学生评价目标。毋庸置疑,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彰显。然而,在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职业性之“满足应时之需的社会功能”被无限放大,与之相关的就业率,初次就业单位规模、性质和薪资水平成为职业教育评价的核心指标[4]。而学生个体的职业理想、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以及职业生活的精神价值受到忽视。于是,对于职业性内涵之社会本位的片面化理解,使外在于人的甄别筛选成为职业教育评价的主导功能。职业教育学生评价,作为教育育人活动的重要环节,其促进个体发展的内在价值被湮没。
(二)评价内容的异化:导向“单向度”的人
从内容构成维度来看,人的需要是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体[5]。其中,对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的自然需要,构成维持人作为生命有机体之生存的基础。而关涉交往、认同与尊重的社会需要,关涉理想、信念的精神需要,使人超越自然需要这一无法摆脱的“动物性”,体现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因此,人的需要是全面而丰富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然而,困于知识论传统的本体论思维,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财富的激增,人的丰富而全面的需要被人对商品与货币的占有欲所裹挟,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金钱的奴隶。其结果是,人的片面的需要之实然状态与人的丰富的需要之应然诉求背离。以这一异化逻辑对我国职业教育评价的现状进行反思,当前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学生评价内容取消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所谓专业技能,表征为一系列与特定职业岗位相关的技术规则、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等。而人作为感性的生命存在,其在职业活动中的情感、态度、价值、信仰等内容被忽略。以专业技能为核心,意味着一切以职业岗位的需要为转移,并将对这一需要的满足作为获取物质财富,以满足个人吃穿住行的生存需要,以及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之异化需要的手段。这就导致人的社会性需要与精神性需要在职业教育学生评价中的缺席,使职业教育面临着人之“单向度”发展的合理性诘问。
(三)评价方式的异化:确定性对人的反叛
“无神论、共产主义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它们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7]。马克思在《手稿》中扬弃了费尔巴哈(Feuerbach)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先验预设,它源于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因而是开放的、生成的,而生成的过程必然蕴含着偶然性、不确定性。因此,作为独特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其身上所内聚着的共同的人性潜能,在应然的状态下会以独特的发展水平和形式,即个体的个性方式,在现实中存在[8]。然而,知识论传统的本体论视域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仍然囿于其对待自然事物的思想方式,理性至上的唯科学主义试图通过普遍的因果决定关系实现对人之必然性的把握。人的类本质成为某种固定不变的、具有抽象的确定性及终极意义并等待人去最终完成的东西。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办学实践中所普遍开展的统一量化标准的结果性学生评价,正是对人作为类存在物之本质的认识采取唯科学主义态度的深刻体现。所谓统一量化标准的结果评定,是从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先验预设出发,依靠人之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做出关于“人应该如何”的标准化要求。这一标准化要求是量化的,是可以精确测量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横向结果比较的,以确保其始终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然而,这一评价方式,其对于抽象的确定性的追求,却恰恰否定了人的类本质的生成性,否定了人的类本质在人类个体身上具体的、历史的、多样性的呈现形式。
(四)评价主体的异化:人之自由意志的压抑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9]在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意识不是去直接肯定自然的欲望的满足,而是去把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实现在某一自然物之上。正是通过这一对象的持久形式,意识得以直观自身,亦即“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10]。这意味着意识开始摆脱由自然的必然性所规定的直接的、本能的东西,赢得了属于人的自由意志,即主体性。然而,在认识论传统的本体论视域下,理性作为思维的纯粹活动,被实体化为自有的、外在于人的范畴之世界。理性的先天法则被看作历史之必然性的主宰,一切历史性都成为了其借以演示先验逻辑的材料。从人之主体性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评价的现状进行反思,以教师为主导的评价模式,消解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人之自由意志被压抑。“教育是使人在已有规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规定性”[11]。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己的判断、选择、规划、努力是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由教师主导的评价模式,将教育看作是一个与学生个体之主观能动性无关的,完全由外部加以干涉的过程。教育评价结果与学生无涉的假设,使学生在评价中的话语空间被挤压,教育评价的结果仅仅被用作教师单方面改进教学的参考依据,而未能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成为学生自我反思、成长的经验素材。
二、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异化扬弃:本体论之生存论的转向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2]。对立统一原则推动矛盾的一方向另一方辩证发展,从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开创解决矛盾的道路。因此,本体论之认识论传统在不断加深对人本身之遗忘的过程中,同样孕育着新的思想。这一新思想的诞生,即是本体论的生存论转向。所谓生存论转向,是重新记起被遗忘的存在,从抽象的理性原则中拯救出人的生命实践活动。增值评价,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论特征,使其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评价的异化扬弃提供了可能性的道路。
(一)评价目标的异化扬弃:人作为目的的价值回归
教育评价目标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学生评价目标更多地呈现为社会本位论的价值取向,个人被异化为一种手段性的存在。那么,作为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良方”,增值评价如何在评价目标维度上体现个体作为目的之解放的生存论转向呢?“增值”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经济学领域,其原初内涵指“用于生产产品的原材料成本或供给成本与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13]。这一概念在教育领域引入的前提假设是将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看作是类似商品生产的过程。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报告》的增值评价教育实践,主要指向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并以此提供对教师和学校问责的依据[14]。从中可以发现,增值评价在其产生之初具有显著的管理至上与绩效主义的倾向,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然后,伴随着增值评价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的不断深入,重塑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15],确立教育评价之“学生立场”[16]的呼声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职业教育领域,以“生涯导向”取代“就业导向”的价值选择,以激活内生发展动力超越充当外部筛选机制的功能期待[17],不断赋予职业教育增值评价以积极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意蕴。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概念,职业教育增值评价的内涵呈现出逐渐脱离经济领域之原初规定,不断切中“教育为人生”之真谛的发展趋势。这一切中,即是人作为目的的价值回归。
(二)评价内容的异化扬弃:超越自然性的生存需要
从应然的层面来看,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构成教育最崇高的使命,回应人之为人的社会尺度与精神尺度构成“自由全面发展”的最深刻的人学内涵。伴随着我国教育领域人本价值的回归,以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法律地位的确立,如何在学生评价内容维度回应教育之人本价值回归的一般性要求,成为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议题。从实践进展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增值评价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已经并且仍在继续不断拓展职业教育学生评价的内容。当前,国际职业教育增值评价已经发展到基于多元化数据的评价阶段。从单一的职业资格测试向标准化技能测试、标准化学业测试、自陈式评价量表等多元化数据来源的发展[18],表明国际职业教育增值评价已经超越了学业成绩的局限性,以自陈式评价量表进行评价的情感、态度、价值、信仰等心理因素进入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内容系统。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内容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进路。综合职业素养渐进取代专业技能,对与职业相关的个性、 态度、德性、精神等内容的评价,在当前我国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正在成为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改革的核心话题。这一评价内容的嬗变,在本体论的层面反映职业教育超越自然性的生存需要,通过回应人之社会性与精神性需要,履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神圣使命。
(三)评价方式的异化扬弃:在过程中生成人的本质
基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人是非预定的、创生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刚刚降临人世的婴儿不能称之为人,而只是具有一种成为人的可能性的存在物。那些专属于人的尚属空白的规定性,只有在其与社会的互动——最广泛的学习中才能被创造出来。这一过程,即是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19]。在这一“学以成人”的过程中,教育提供理想人格的发展愿景,在代际间传播既成的文化成果,从而使人之“学以成人”的过程表现出显著的预设性特征。然而,相较于教育活动,人的本质的生成性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规定,教育的预设性在应然的层面上应服从于人的本质的生成性,其价值意蕴在于深刻把握生成性之规定,为生成的过程性展开开辟道路。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增值”二字,即是对学生连续学习过程的状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描述。当前,关于“增值”的标准具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结点值与起点值的差值。二是结点值与预测值的差值。这里的预测值指的是在综合考虑学生家庭背景、先天能力、学习基础等禀赋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基于群体增长率的估算[20]。这两种理解方式,就其内在一致性来说,都将增值标准的确定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相联系,所不同的只是对学生个体差异性的解释是否在测量模型中予以清晰界定。因此,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在实践中正在逐步瓦解无差别的统一性标准的统治权。以追求具体的确定性超越对人之抽象确定性的理解,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独特性纳入评价视域。
(四)评价主体的异化扬弃:自为存在实现自我超越
主体性使人成为自为的精神性存在。人能够将自身的生命活动纳入到自我意识之中,在精神层面为自我“应如何存在”提出某种想象或期待,并通过计划或筹划使自我的生命活动不断地朝向这一想象或期待而现实地展开。这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是超越于自然限度之上的,人作为自为的主体,能够运用自身的能动性、主动性,其生命活动要以自我的方式让世界的意义敞开,从而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从这一根本性规定出发,任何教育都具有外铄性,学生在教育活动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使教育所提供的外部发展机遇向学生内在发展动机转化的必然要求。增值评价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引进,已凸显出学生主体性的实践进路。一方面,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不断扩大学生自身在评价活动中的话语权。自陈式量表的数据收集方式实际上代表了在评价活动中倾听学生声音的实践尝试。虽然学生作为评价主体其话语权重的设置问题仍然有待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明确,但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应在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打破仅仅由教师或专业人员完成评价活动的传统桎梏,已经成为一项共识性意见[21]。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强调结果反馈机制的构建[22],以促进学生自我反思性的成长。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在功能定位上是以诊断、改进促进学生发展为核心取向的。因此,其在实践中更加强调评价结果的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反馈的对象不仅包括教师,更包括学生个人。评价结果向学生个人的反馈,为学生对自我发展过程进行反思,进而调整学习策略,实现自我超越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三个世界”的协调: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之理性建构
从本体论的视域来看,增值评价所具有的生存论内涵,使其为扬弃认识论传统下职业教育学生评价的异化问题提供了可能路径。然而,正如异化是将本体论之知识论传统推向极致的结果,以增值评价解决异化的问题,同样需要警惕绝对化思维可能导致的矫枉过正的风险。因此,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绝不是对当前既有评价模式的全盘否定,其理性建构需要站在人的生命实践的高度,批判性地继承知识论、发展生存论的合理之处,协调好“三个世界”的关系。
(一)立足科学世界: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合规律性确证
科学世界是建立在数理—逻辑结构的基础之上、由概念原理和规则所构成的世界。科学世界秉持因果联系的普遍性解释,寻求对世界万物之客观性、确定性、必然性的把握,以确证人的生命实践的合规律性。从人的智力发展的维度来看,与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先天才智在人类总体中呈正态分布,人脑及其精神系统的发育也具有一致性。基于此,人的认知发展呈现出随年龄变化的阶段性规律。但这种规律有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抽象精确性,表现出在一定可能范围内的差异性波动特征。从人的社会化维度来看,社会规范作为社会意识范畴,是人类主观建构的产物。个体的社会化建立在个体认为自我“应该”遵从社会规范的信念或信仰之上,其价值渗入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然而,社会施予个体特定的规范、命令及个体遵从特定的规范和命令都以对潜在行为及其可能后果的前后联系为前提,这又赋予人的社会化以科学的因果逻辑解释。因此,可以说教育活动具有科学性,但其在科学性的表现形式上有别于自然科学支配的实践活动。教育活动在整体上的科学性特征规定着教育评价作为特定教育环节的科学性特征。而职业教育生源结构日益复杂化的办学现状、职业教育基于特定工作情境的实践导向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其评价活动的差异性、生成性及偶然性。
科学世界与本体论的认识论传统相联系,然而当代本体论的生存论转向并不是对认识论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要通过对其施予必要的限度为异化问题的纠正提供实践进路。一方面,人的生命实践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科学世界所提供的关于对象特性及其规律的认识,代表着人类社会整体不断积累并实现代际传递的知识性成果,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着方法论上的指导。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应立足科学世界,在准确把握学生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制定评价方案,并按照评价方案所确定的工作流程有序开展评价工作。这是确保职业教育增值评价活动的规范性,避免陷入随意、无组织困境,使评价活动得以持续性推进的基础性前提。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实践也是自我的、创造性、生成性的。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作为对本体论之知识论传统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同时需要与科学世界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确定评价标准、制定评价内容、解释评价结果等评价活动过程中,要始终贯彻预设性与生成性、统一性与差异性、确定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原则,并结合生源及专业特点不断使之精细化,以回应教育科学性的特殊性表达要求,以及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之规定与办学现状的诉求。
(二)回归生活世界: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合现实性源流
生活世界是“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的被给予的、总是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3]。生活世界将人从科学世界的理性、精确、冷峻中解放出发,以情感、想象等复杂细腻的人性质素赋予人的生命实践以真实性、直观性和具体性,从而构成其合现实性源流。教育作为人的生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有其必然性。从作为整体的教育活动来看,师生间通过互动交往建构知识、形成规范认同。这种互动交往在其理想形态上应该是平等的、协商性的。同时,这种互动交往展现为一个过程,教育的生长即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生长。基于科学世界的知识权威,师生关系是不平等的,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难有知识的建构、规范的认同。而生活世界具有主体间性特征[24],回归生活世界,师生互动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生长。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来看,其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面向特定的职业领域从事实践性工作,这种工作是真实的、具体的、可感的,是根植于生活世界的,这就要求其教育的过程要更加强化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如前所述,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实际上已暗含了回归生活世界的意蕴,只是其现阶段的实践推进相较理想化的状态仍存在明显差距,需要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不断弥合。立足于生活世界,作为人的生命实践的教育活动不断促进着人的全面生成、生长。这一过程所提供的丰富的事实性信息构成学生评价的重要依据,而这些事实性信息有赖产生的具体情境也为评价结果的解释、分析提供着可靠的背景性支撑,并通过师生间的平等互动交往获得进入评价视野的机会。因此,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需要树立起整全性评价的理念,推动构建家校企社协同的评价工作机制,全面收集学生在不同生活世界场景中的真实行为信息,构建学生评价的完整证据链。同时评价过程应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协商性对话,结合特定情境对评价结果进行具体的解释,并尝试以学生发展档案袋等形式形成学生评价结果的文本载体。通过上述举措的实施,推动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超越当前对学生评价做碎片化分割、以脱离具体情境的事实呈现取代关联具体情境的价值判断等。
(三)指向意义世界: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合目的性归宿
意义世界是由超验的价值理念构成的形而上的观念性精神文化世界。“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25]。从生存论的视域来看,一方面,人通过自身的生命实践,终其一生探求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证赋予个体以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而对这种终极关怀的需要正是对人之“为人性”的深刻反映。另一方面,意义世界的核心是理想的追求与使命的意识[26],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导着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激励着人在现实中进取,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汲取新的精神涵养,促进自身的生成性发展。因此,意义世界构成人的生命实践的合目的性归宿。教育是促进教育对象向人生成的活动,教育活动指向受教育者意义世界的建构有其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其类型特征不是要以工具性价值否定精神教化的规定性,而恰恰需要将职业活动作为人的生命实践的重要形式,为促进这一特定形式中受教育者意义世界的建构开辟道路。
意义世界的建构表现为对象的意义呈现与主体的意义赋予相统一的过程[27]。所谓对象的意义呈现,与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相联系,它以被普遍认可的“理”“义”为内容,赋予意义世界以个体间的开放性特征;而主体的意义赋予,渗入人的内在反思、感受与体悟,它将普遍性的对象意义呈现纳入个体的意识之域,更直接地指向个体自身之在,从而最终完成意义世界的自觉建构。当前,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的生存论转向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在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而从生活世界上升到意义世界的建构仍存在着较大努力空间。从对象的意义呈现之维来看,整体性精神文化氛围的营造为意义世界的建构提供着社会性基础。因此,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需要在社会层面大力宣传和弘扬“劳动伟大、技能宝贵”的价值观,以校风、学风建设为重点加强校园整体文化氛围的塑造,进一步强化评价激励机制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外部引导作用。从主体的意义赋予之维来看,自我反思是意义世界建构的关键环节。因此,职业教育学生增值评价在持续推进评价结果面向学生反馈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后反馈阶段学生自我反思环节的关注。以开展书面总结、进行师生启发式对话等形式,使意识通过自己的对象化结果得以直观自身,从而完成自我的意义世界建构。
参 考 文 献
[1][3][6][7][9][10][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84.85.85.56.57.75.
[2]王德峰.哲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52.
[4]谢盈盈.钟摆现象:高职学生评价取向的选择与反思[J].职业技术教育,2021(22):45-50.
[5]谢卓芝,刘秀萍.何以走出人的需要异化之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J].理论视野,2023(6):5-11.
[8]田夏彪.走进“生活世界”:新时代学校育人的实践向度[J].学术探索,2023(11):141-150.
[11]鲁洁.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J].教育研究,1998(9):13-18.
[13]胡娟,徐鑫悦.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缘起、争论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22(6):5-18.
[14]刘玉勇.增值性评价缘起、现状与未来指向[J].教育评论,2023(9):67-74.
[15]陈允龙.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增值评价探析[J].教育评论,2019(9):30-34.
[16][21]安富海.学生发展增值评价的“学生立场”及实现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23(10):27-32.
[17]孙田琳子,胡纵宇.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增值性评价的逻辑与路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2(28):50-55.
[18]陈元媛,吕路平.职业教育增值评价:演进、逻辑和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2(16):47-52.
[19]王南湜.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新解——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阐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41-52.
[20]汤建民.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的现实挑战与因应策略[J].江苏高职教育,2023(3):94-102.
[22]朱永丽,李同同.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理论逻辑及其实现框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24):84-90.
[23]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9.
[24]吴宁,许慧.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及其对我国现实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5(3):48-53.
[25]赫舍尔.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46-47.
[26]杨国荣.论意义世界[J].中国社会科学,2009(4):15-26.
[27]杨国荣.意义世界的生成[J].哲学研究,2010(1):56-65.
Alienation and Its Sublation: the Diversion of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of Students’Value-added Evalu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i Hongbo
Abstrac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the baton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reflect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evalu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alienation of objectives, contents, methods and subjects reflect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ontology’s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and life practice requirements of humans. Because of its existential characteristics, value-added evaluation represents the divers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ontological basi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to the existential theory. Therefore, it provides a possible way to sublate the problem of students’evaluation alien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concept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ormed, the value-added evalu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needs to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tific world, the life world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to improve itself in the coordination and symbiosis of the thre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value-added evaluation; alienation; ontology; life practice
Author" Shi Hongbo, PhD candidate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ilin 541004)
作者简介
史洪波(1989- ),女,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桂林,541004)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测度模型、驱动因素及路径优化研究”(VJA220006),主持人:徐国庆;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VAA230006),主持人:孙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