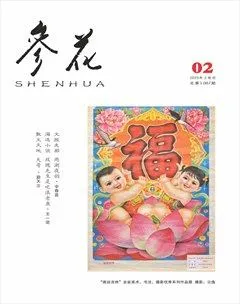大哥
大哥是抱养的。大哥与我虽非一母同胞,但流淌着同一个祖先的血,有同一个曾祖父。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 一九四九年,年近四十的我妈依然膝下无儿。那时,一个家庭没有儿子是一种缺憾。那年,五婶和七婶同时怀孕,她俩同时向我妈许下承诺,如果生了姑娘,她们自己留着;如果生了儿子,就将儿子抱给我妈。结果,五婶生了姑娘,七婶生了儿子。当我妈满怀希望去七婶家抱孩子时,七叔却反悔了:“哼!让孩子到你家挨饿,还不如让他在我家挨饿。”我妈哭着回到家,泪水洒了一路。
一个月后的一天,七婶突然叫我妈去抱孩子。我妈急忙赶过去,只见孩子奄奄一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屁股下一片绿屎,显然他已经病得很重。七叔家没钱给孩子看病,而七婶还没有奶水,孩子从出生起就只能靠喝玉米糊糊度日。我妈看着孩子,摇了摇头说:“这孩子我不能要。如果我抱回去后孩子死了,人们会笑话我‘命里无儿,逼死侄儿’。”这时,在场的一个邻居发话了:“我们知道你能耐大,你一定能救活这个孩子。如果你不抱走他,不出三天,这孩子就得被扔到野外去。你行行好,救救这孩子吧。”邻居把孩子抱起塞到我妈怀里。我妈心一软,再也舍不得放下孩子,她含着泪,走出了七婶的家。从此,这个孩子就成了我妈的儿子。
我妈用两篓珍贵的小米换回了几粒西药片。要知道,在当时,小米比黄金值钱。在给我大哥喂过药后,我妈抱着他去了一个正在坐月子的邻居家。我妈向她说明了来意,那位善良的女人毫不犹豫地轻轻将自己的孩子从乳头上移开,让我大哥吮吸那甘甜的乳汁。这是我大哥出生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品尝到奶水的滋味。
我妈回到家里,轻轻地将我大哥放在炕上,然后抱回一捆柴火,舀水点火,精心制作了一碗香气四溢的拌汤,给那位好心的邻居送去。
从此,这便成了一种默契:孩子享用人家一顿甘甜的乳汁,大人便回赠一碗暖心的拌汤。我妈每天需要寻访数位哺乳的村妇,同时也要送出一碗又一碗精心制作的拌汤。为了省事,后来我妈每次出发前都会提前做好一碗拌汤。
为了给我大哥寻一口奶水,我妈一手紧抱着我大哥,一手端着那碗拌汤,东门出西门入,穿梭在村庄的大街小巷。她的身后,常常有从院子里追出来的狂吠的狗,而天空中盘旋的老鹰也时刻准备俯冲而下,意图从她怀中夺走那弱小的生命。街上的人们用吃惊且充满怜悯的目光注视着我妈,偶尔发出几声无奈的叹息。我妈端着拌汤,一路飘香,她那瘦小的身影和蹒跚的脚步,诠释了一个母亲的坚强不屈、惊天动地的爱。
当大哥三岁脚步初稳之时,我妈便牵着他的小手,出东门,进西门,重走她曾经走过的路。她让大哥向每一位曾喂过他奶的女人深情地唤一声“妈”。 在这小小的村庄里,我大哥有好多个妈,生他的妈,养他的妈,还有众多喂他吃过奶的妈。
一九五六年,七岁的大哥,活蹦乱跳地背着书包上学了。可能是我妈对我大哥的无私大爱感动了上苍,这一年,已经四十六岁的我妈怀孕生下了我。
在我家,大哥是抱养的,我是亲生的。如何对待这两个儿子,无疑是对我妈品德与良知的严峻考验。
一九六六年,我年仅十岁。那时,大姐与二姐已然出嫁,家中便只剩下父母、我大哥和我。一家人全靠那块自留地维持生计,而要让土地多产粮食,关键就在于充足的肥料。俗话说得好,“会耕会种,不如愣汉下粪。”于是,寒假期间,我妈便让我去拾粪。
我左手拎着粪筐,右手握着粪铲,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四处转悠。数九寒天,冻得我耳朵通红,脸颊肿胀,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每当鼻涕快要流进嘴里时,我便用袖子一抹了之。粪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粪便:猪粪、驴粪、牛粪、马粪,甚至还有人粪。碰上同班同学,尤其是女生时,我总觉得无比尴尬和丢人。
在当时,拾粪的人往往都是那些生活条件较差的人,我妈却坚持让我拾粪。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有一天,天气异常寒冷,我拾了一整筐粪,冻得手脚生疼,几乎要哭出声来。一进家门,却看见大哥坐在暖炕上享受温暖。我顿时感到委屈和不平,向妈妈抗议道:“为什么不让我大哥拾粪而让我拾粪?为什么让我大哥坐在热炕上,而我却要在外面受冻?”不知是冻得太厉害还是受了委屈,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妈妈赶紧过来安慰我道:“你大哥正在找对象呢,不能出去拾粪。”我赌气地说:“那我也要找对象!”这句话一下子把全家人都逗笑了。妈妈用双手捧住我冰冷的脸颊,试图让我快点暖和起来。
妈妈对待我和大哥不公平的地方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全村人都穿着土布衣的时候,我大哥却穿上了时髦的灯芯绒衣服和皮鞋,而我依然穿着打满补丁的土布衣。十岁的我并不能理解这种区别对待背后的真正含义,只是不断地抱怨。我抱怨我大哥穿得如此光鲜亮丽,不用做脏活儿累活儿,而我却穿得破烂不堪,脏活儿累活儿全都由我一个人做。
然而,长大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母亲有多么了不起。她以宽广的胸怀和深沉的爱意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是亲生的还是抱养的。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大哥身材矮小,容貌平凡,然而在精明能干的母亲的庇护下,人生路可谓是顺遂无比。在十八岁那年,他娶了邻村村支书的长女为妻。我大嫂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继承了她父亲的优秀品质,言辞果断,举止干练。街坊邻居都说,我大哥长得不怎么样,却找了个百里挑一的好媳妇。
大哥没啥本事,然而心地善良,孝敬父母。自成家立业后,他便和大嫂另立门户,独立生活。
一日,大哥的岳父前来拜访。为了款待他,大嫂特地准备了一碗白面面条。在那个年代,白面面条无疑是难得的美味,平时我们家中多以红面或玉米面为食,唯有逢年过节方能品尝到白面的滋味。
中午吃饭时间,我大哥端着一碗白面面条从他的正房来到我们住的西厢房,当时,我和父母正端起饭碗,吃着红面(高粱面)剔尖。我大哥一把把妈妈手中的红面饭碗夺了过去,把他端的白面饭碗给了我妈,让我妈吃白面面条,他吃红面面条。大哥没舍得吃一口白面面条,端着那碗粗涩难咽的红面面条,背靠门扇蹲在地上,吸溜吸溜的,吃得很香。妈妈从碗里夹一筷子白面面条给爸爸,夹了两筷子白面面条给我。我舍不得一口把白面面条吃完,而是把白面面条和红面面条混在一起,挨着大哥,背靠着门扇,蹲在地上,吸溜吸溜地吃起来。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天的白面面条加红面面条是那么好吃,那吸溜吸溜的吃面声依然回响在我脑海里。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我村几十里地的县城教书。此时,父母已步入晚年,身体抱恙,照料他们的重担几乎全落在了大哥一人肩上。
父亲肠胃不适,在从他居住的西厢房前往南厢房茅厕的途中,常常因憋不住而弄脏裤子。为此,我特意准备了六七条内裤,并嘱咐大哥道:“咱爹的屎裤子,你也不用每天洗,攒到星期天,我回来拿到村边水塘里去洗。”可是每当我星期天回到家里,院子里总晒着六七条洗干净的裤子。我责备大哥说:“你在地里劳动那么累,我回来洗就好了。”大哥总是说:“你是吃公家饭的,不能让你洗屎裤子!”
在大哥的心中,我是吃着公家饭,受国家重用的人。
大哥有一子二女,三个孩子都朝气蓬勃。如今,我大哥已七十五岁高龄,然而身体素质极佳。医生笑着说,这得益于他从小吃百家奶,营养全面,抗病毒能力超强。
大哥饲养了一院子的羊。其实,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家一直养羊。只是,那时满院子都是人,只能养一两只羊。岁月匆匆,昔日热闹非凡的几十口人的院子,有人乔迁新居,有人远走高飞,有人已入黄土,如今换成了满院的羊,仅剩我大哥孤独的身影。
侄子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气派的二层楼房,一楼开超市,二楼做卧室,格局如同别墅。然而我大哥却不愿搬离这老院子,他甘愿与羊群为伴。这些羊,不仅是他晚年的伴侣,也是他正在上大学的孙子的学费。
大哥只养母羊,让母羊生羊羔,当它们脱离哺乳期后,就将羊羔卖掉。为了让母羊得以繁衍,羊群中还有一只威严的公羊,它头顶长着长长的、弯弯的角,高大雄壮,我大哥称之为“圪羝”。在我眼中,这只公羊宛如一位皇帝,占有一院子的母羊,且无任何竞争对手。
满院的羊群之中,唯有那只雄壮的公羊,被粗重的铁链牢牢束缚。我疑惑地向大哥求解,他解释说:母羊怀孕后便会失去交配的意愿,而暴躁的公羊则会发怒,用坚硬的羊角猛烈顶撞它们,作为对它们不顺从的“惩罚”,这种激烈的行为,有时甚至会导致母羊流产。闻听此言,我不由愕然——想不到这公羊竟会对它的“后宫”施展如此暴力。
与此同时,羊群中还有一只特殊的羯羊。羯羊就是在年幼时被阉割的公羊——人们为了让其专心地长肉,不再对母羊有非分之想。羯羊的肉质鲜嫩、口感极佳,堪称羊肉中的上品。母羊肉质较柴,不易咀嚼,公羊肉膻味浓重。以前农村卖羊肉,摊贩们不时地向村民展示羯羊的生殖器官,以此证明所售的羊肉既非母羊也非公羊。
大哥一生虽没什么显赫成就,但对我这个弟弟却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大哥知道我爱吃羊肉,每年冬天,即便我身处海南,大哥也会将半只羯羊肉邮寄给我。而当我次年从海南归来,回到村里看望他时,他总会将剩下的半只羊肉塞进我的后备箱。自从大哥开始养羊,我便再也不用去超市购买羊肉了。自认为大哥给的羊肉堪称天下最好吃的羊肉,无论是外出旅游时品尝过的宁夏烤全羊、甘肃烤全羊,还是内蒙古烤全羊,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每当咬下一口香喷喷的羊肉时,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和内疚。大哥作为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每年都如此慷慨地赠送我一只昂贵的全羊。而我这个吃公家饭的弟弟,却几乎没有为大哥带回过任何东西。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为大哥付出,而是他总坚决地拒绝我的好意,他总是说:“我儿子的超市里啥都有。” 这让我感到既温暖又内疚。
大哥为了这一院子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一年夏天,我回家看大哥,侄儿说大哥去河边地给羊割草去了。我立即开车去了河边地,在杂草丛中找到了大哥。大哥满脸汗污,一身泥土。我帮大哥割草,大哥不让,怕弄脏了我白色的T恤。小时候,大哥常带我来这里打羊草。六十年过去了,大哥还在这里打羊草。我每月领着退休金,可以清闲地过退休生活,而大哥却仍在40℃的高温下为生活辛勤劳作。我心痛得犹如在滴血。我曾想,把我的退休金分给大哥一半,不让大哥这么辛苦了,可那样做,不仅大哥不会接受,我的侄儿也会感到尴尬。侄儿开着那么大的超市,比我有钱多了。侄儿早就劝大哥别再养羊,可大哥执意要养,还理直气壮地说:“哼!不让我养羊,让我做什么?!”我曾说:“大哥,我带你出国旅游吧。”大哥说:“那羊呢?”是啊,我不能把羊也带上啊。
回家的路上,我开着小车在前,大哥驾着装满青草的三轮车在后。这一幕似曾相识。小时候,大哥背着一大捆羊草在前,我背着一小捆羊草在后,一同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透过汽车的后视镜看着大哥,大哥的脸庞却因为我这个弟弟回来看他笑成一朵盛开的花。
今年春天,我一如既往地回老家看望大哥。我站在院子中央,满院子弥漫着羊膻味和屎尿味,一院子的羊用温婉、慈祥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我。环顾四周,目光所及,那些伴我成长的破旧屋舍,在岁月的侵蚀下,如同大哥的容颜一样,愈发沧桑。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这个曾经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的院落,如今却只剩下大哥和羊了。
作者简介:蔚天立,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号)《天津日报》《对联》《名家名作》《读者文摘》以及中国作家网等各类报刊、网站,已出版专著一部。
(责任编辑 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