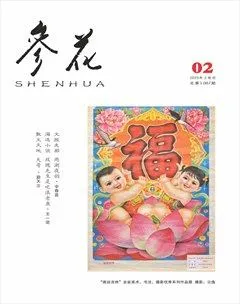文昌笔
我第一次发现葛吟红有远超常人的文学天赋,是在一个平平无奇有些燥热的五月下午。当时我在尝试一种新的改稿方式——把文章打印在A4纸上,页眉上注明文章标题,正文使用小四号宋体,段落之间空出一行,再设置两倍行距。当每句话都切实印刷成铅字,整整齐齐如兵马俑般立在雪白的稿纸上,你下笔时的每一寸犹疑、局促、忐忑和松懈都无法遁形。那天我刚把一篇熬夜写就的小说打印好,就接到刘诚阳下属的电话,说时近端午,供应商送来了礼品,让我下楼一趟。那是印着对方公司LOGO的粽子礼盒,和牛海参,瑶柱鲍鱼,分量不轻。把东西放进床头柜里,我发现午睡的葛吟红已经起了床,静悄悄地在厨房里忙活,而我放在客厅角落书桌上的纸张挪了位置,上面有红色的笔写的批注。
她的字清瘦颀长,和她这个人一样,脖子总是不自然地挺着。纸上改动的地方也不多,一个量词、三个形容词、两处语序,又把收尾的那两句话划掉重写,表意一致,阅读体验却天差地别。我曾为这结局苦恼良久,只觉得写至最后,一口气泄得精光,如同干瘪的彩色皮球,怎样充气都有难看的褶皱。但经葛吟红一改,整篇文章都因为结尾而鲜活灵动了起来。我曾在一次画展见到徐悲鸿的《奔马图》,画家最后以淡墨枯笔轻扫鬃尾,骏马这才有了飞扬之姿。葛吟红那几笔正是如此,栩栩如生,浑然天成。
我捏着稿纸,一遍遍阅读良久,哪怕是一些专业的编辑,也不曾在短时间内给予我如此确切的修改建议。我看向厨房里葛吟红的背影,难掩惊讶,我之前知道她有一定的语文功底——是了,语文,不是文学,因为她做了三十几年的小学语文教师,去年才刚刚退休。但一个语文教师,会有如此惊人而准确的对文字的直觉吗?
我妈是小学语文老师,过几年退休,我爸很早就去世了。我和刘诚阳第一次相亲见面时,他就这样跟我讲。我们约在一家主打意大利菜的西餐厅,他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看上去文质彬彬。你是中文系的?挺不错,我也很喜欢看书,大学时还参加过征文比赛呢。他替我剥好一只西班牙红虾放到碗里,抬起头来看我,眼睛熠熠生辉,流露出历经世事后很难得的真诚。我就是被他那一眼打动的。
认识半年后,我们就领了证。家人朋友都对刘诚阳很满意:小公司老总,有房有车,对你也好,还有哪里不知足?只可惜我成为裁员大潮里最先被冲走的那批浮木,领了“N+1”的补偿金回家。刘诚阳从公司回来,看到我放在桌上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他静了静,揽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别着急上火,家里有我顶着。
诚然,他是个慷慨的伴侣。但让我下定决心暂时不再出门工作的,不是他放在我肩膀上的那只手。它在稍后灵活地舒展开来,像一只通体黏腻的章鱼。刘诚阳喘息着说,庄旻,我们要个孩子吧。
我和他一前一后倒在客厅的沙发上,透过他的身影,我看到一只瘦小的绿头苍蝇,扑闪着落在茶几上的黄色文件袋上。文件袋里装着出版社刚刚寄来的合同,他们邀我写一本童书——这是我安心居家最主要的原因。我的思绪情不自禁飘去了草原,雨水、云朵、黄色的雏菊和牧羊的小姑娘——我拟定的童书故事的主角,如果我真的有个女儿,会和她一样吗?
几个月后,我写完了那本书,首印三千册,读者圈内反响不错,拿了不大不小的两个奖,又被教育局评为当年的推荐儿童读物,勉强向出版社交了差。这算我从业余作者迈向职业作家的第一步,之前在广告公司从事文字工作时,我只是闲时写作,零散发表;而书出了之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其他的机会找上门来。我主要写小说,那段日子里,儿童文学、科幻奇幻、言情、悬疑……我尝试了个遍,有的被编辑委婉退回,也有的被印刷成铅字,具象为银行卡入账提醒的丁零一声。
我曾试图描写我琐碎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却抓不住回忆的浮光掠影;人间对我来说像隔着重重纱幕,现实太沉重,我的笔又太轻;我试图让想象像鸽子一样飞远,它们却始终只在我头顶的一小片天空盘旋……我惊觉自己是如此贫瘠,下笔如隔靴搔痒,有时是不敢,有时是不愿,但更多的是不能。我让自己尽量放松下来,靠在椅背上,然而还是感觉四周的空间扭曲变形,只能看到头顶雪白的天花板,离我如此之近。
我买了一台碎纸机,投入大量废稿。刘诚阳不关心我写了些什么,他对我的关心都体现在订购的花束、微信的大额转账以及快递寄来的衣服里。我问:上次托你朋友买的那本国外的绘本,到货了吗?他心不在焉地说:什么绘本?明天我问问。
两个人的激情似乎无济于事,半年后,我的肚子依旧风平浪静。很难说我对此没有预感,我决定去医院看看。
多囊卵巢综合征。医生把病历单递过来。你结婚了吗?要趁早备孕,后期怀孕有点困难。
我把病历单放在床头柜上,刘诚阳看完,安静了几秒,却很快又把手臂环绕上来。他说:现在医疗条件发达,这个病好治,可你也得好好调养,外卖这些乱七八糟的食品都不要再吃了——刚好我妈退休了,让她来给你做饭好不好?
葛吟红就这样一手拿锅铲一手拿笔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批改了几十年的学生作业,上衣口袋里时常插着一支红色墨水钢笔。退休后,的确良的衬衫换成了全棉汗衫,然而那支笔一直放在她随身的包里,时时擦拭、上墨,光亮如新。她做饭非常清淡,还喜欢把奇怪的食材放在一起煮,并不合我的口味;她的生活习惯严谨且苛刻,掉落在地上的一根头发都会让她如临大敌。出乎意料的是,她对我本人还不错。有时赶稿至深夜,我一口气睡到中午十二点,半梦半醒中听到她在客厅边拖地边发出不满的啧啧声,可当我梳洗好走到餐厅时,饭菜和汤已备好,葛吟红坐在角落,小口啜饮着一碗汤,吊起眼梢,偷偷看我,一句话也没说。
汤是鲫鱼汤,不加一粒盐,经过长时间烹煮呈现奶白色。鱼腹剖开,粘连着大量密密麻麻的鱼子。葛吟红很热衷于做这个——仿佛我连着喝上一天、一周、一个月,我的腹部也会肉眼可见地鼓起来,在十个月后呈上手术台。
我听诚阳说了你的病。葛吟红给我夹了一筷子豆泡。现在的小姑娘家家,毛病就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但也没办法。杂七杂八,没我们老一辈人吃得健康。我坐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个菜市场,那里的菜和肉都是一大清早从下面乡镇运来的,不打农药,新鲜得很。
我扒着白饭,没应声。她不断地给我夹菜,鲫鱼、豆腐、猪肚、木耳依次“退场”,盘底雪亮,图穷匕见:可你自己也要上心,每天熬夜,怎么可能容易怀?过两天你跟我去见个老中医,据说他医术很高明。
还没等排上老中医的号,我和刘诚阳便在家中起了争执。由于每日长时间写作,我需要一个书房。主卧并不适合,一张大床占了主要位置,处处都被生活的针脚填满,容不下一个空白的田字格。家里是有书房的——三室两厅的其中一室,走廊右边第一个房间,采光和隔音都是极好的,僻静,独立;只是,它归刘诚阳所有。
我提出我要这个书房,刘诚阳拒绝了。他是怎么说的?老婆,不是我舍不得,只是做生意的人,讲究书房能聚财,而且,有时候开个会或者接待个客人,我大小也是个老板,总不好让人家看我直接坐在客厅里。
可是你一周六天都不在家。
那也不行。主卧还不够你用?实在不行还有客厅呢。
过了两天,他提回来一个香家专柜新款送给我,在三个人的饭桌上有意无意地提起此事,似是彰显他的大度,宽容我的无理取闹。他伸过筷子夹起一只鲍鱼,油亮的嘴唇一张一合:庄旻,等你生了孩子,我们就换个大房子——到时候,你的书房、孩子的玩具房,一切都有,好不好?
晚上,他独自在书房办公,葛吟红做了一锅酒酿丸子,让我给他送一碗。我推门进去,放下碗准备离开。和刘诚阳打闹时,我一把将他推倒,瓷碗碎裂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葛吟红甩着手上的水匆匆赶来,她看一眼满脸怒气的刘诚阳,又看一眼我,扬起头说,地太滑了是不是?怪我,拖地拖太晚了。
想出去散心,回老家太远,于是我去好友家住了几天。再回来时,客厅窗边隔出一个角落,纱帘掩映之处摆了一方书桌。葛吟红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仿佛这一周什么也没发生:回来啦?我做了你喜欢的炸藕盒,洗个手就可以吃了。
我决定和刘诚阳结婚,与我想潜心写作脱不了干系。我选择和刘诚阳继续这段婚姻,与葛吟红也脱不了干系。她给我改好的那篇文章登上了某家省刊,编辑发来终审意见时说,庄老师这是又有进益了?这次的文章很好,结尾尤其好。
我想与葛吟红坐下来聊聊文学,可是这样的话题出现在一对婆媳之间,未免太过诡谲。我只好佯装好奇,问起她的过去。葛吟红是恢复高考后最早那批大学生,很幸运地押中了高考的大题。她本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为了早日养家才读了师范,毕业后去小学教书,此后薪火相传四十年,克己奉公,直至退休。我年轻时候也喜欢写东西,她语气平常地说。当时给校报写了一篇文章,被省文联看到了,还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上班。
你去了吗?
没去。省文联在另一个市,诚阳他爸走得早,我得在那边陪他读书,哪里走得开。后来他们选了隔壁学校另一个老师,她写的东西我也看过,没我写得好哩。
她平淡地报出一个名字,我上网搜了搜,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女老师目前已经是某直辖市的著名作家,公众活动频繁,出版作品多部。我掩饰住内心的惊涛骇浪,问她:校报上的那篇文章还有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哎哟,那哪能有,都多久前的事了。她忙着收拾桌上狼藉的餐盘。我年轻时也没写过多少,不过有一本日记,跟着我几十年了,你想看就看吧。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仍然把几十年前的日记携带在随身的箱子里。她把本子递给我,没有叮嘱一句,就又忙起了家务活儿。我坐在卧室的床上,打开那本厚厚的红色硬壳笔记本,走进了葛吟红的前半生。
可它还远远不能够被称为她的前半生——只是她前半生中再单薄不过的一个切面。葛吟红毕业之后,曾有两年在乡下支教,后续在镇上赶集时偶遇来出任务的刘诚阳他爸,两人情投意合,在葛吟红回城后结婚。这本日记就是写在葛吟红独自支教的那两年,她写高山,写草原,写河流,写赶牛车的汉子、耕作的老妪、泥湾里嬉笑打闹的孩子,有时候也写她自己,属于一个二十岁少女的心事。我逐页翻过,像一个初次到访应县木塔的行人,为那无比朴素但美丽的用词心颤,为她笔下生动而鲜活的人物心动,为字里行间流淌的对文学极高的敏感度与绝佳的掌控度而心惊——抬起头塔尖高耸入云。我终于确信,不得不确信——
葛吟红是个写作天才。
而天才正在我家的客厅里,本应该拿笔的手握着拖把。我此刻的自由何尝不是一种对她的剥削?她蹉跎了三十多年没有再拿起文昌笔,那本日记在她回城结婚之后便只留满纸空白。我走出房间,久久凝视着面前的女人,张口却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妈,你还想写东西吗?
哦哟,写什么?都多少年不写了。再说了,现在也没空。
我可以请个钟点工……
浪费那钱干吗?她瞪了我一眼。以后生小孩了,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
我之前也不知道要个孩子是件如此劳民伤财的事。老中医给我号了脉,捋着胡须,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开了一剂方子,昂贵的中药抓了一把又一把。家里因此时常萦绕着中药的味道,我喝一口,只觉得再苦不过。但又怎么苦得过我婆婆那段宝剑封箱、明珠蒙尘的岁月?
葛吟红终究是没有再写作了,我和她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我会把新写好的稿子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短则一个中午,长则两天,葛吟红会修改好放回原处。我猜她改我的文章的心态和改学生作文没什么差别,这种交流让我放松且安心。每次读到她的批注,喜悦都将我如茧般重重包裹,每一位创作者此刻内心都会飞出蝴蝶,但狂喜很快如黄昏时分的烟岚一样消退。我看见她的背影,矗立在厨房里,像一块巍峨的木雕。
有半个月,我在准备别的事情,没有在桌上放新的稿件,葛吟红发现了,给我盛鲫鱼汤时问了一句,最近很忙?
我决心暂时保守那个秘密,喝了一口汤后答,不忙,这不是在准备去云南嘛。
去云南旅游是刘诚阳的主意。刚好去过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他笑着在我脸上亲了一口,道:酒店我都订好了,蜜月大床房。
临出发前的一周,行李已被收拾得七七八
八,刘诚阳突然说去不了了,公司有笔重要单子得跟,机票只能退30%,提前订的酒店一分都退不了。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说,要不我和你妈一起去?
他一愣,丢下手机扑上来,喜笑颜开:可以啊老婆,最近跟我妈关系这么好呢?
葛吟红只在年轻的时候出过两次省,是去外地学习,这次旅行让她诚惶诚恐。她像收拾公开课教具一样谨慎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在飞机上正襟危坐,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我提醒她座椅靠背可以往后调。她调好后,露出惊喜的表情,然后扭头看着舷窗外悠闲飘浮着的云朵。
我承认我有私心。葛吟红无疑热爱着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从她那本日记中就能看得出来。这次出游,或许会让她重拾对写作的渴望。
我们在丽江的高级度假酒店里住下来,这里的时间流速似乎比大城市里慢上许多,太阳慢悠悠地升起,又不疾不徐地落下。我带着葛吟红逛四方街,登万古楼,在狮子山上俯瞰古城全景,和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起排队吃土鸡火锅。她的身上终于展现出我不曾见过的那一种感觉——松弛。原来当一个女人松弛下来,她看上去会是那么的美,那种美无关身份与矫饰,只在她眼边的皱纹与嘴角的褶皱里昙花一现。
你想不想写点什么?我和她坐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看着星空,我问道。
写点什么?葛吟红侧过脸来,为什么要写呢?
你不想记录下看到的这一切吗?
我拍了很多照片。
我努力组织着语言,告诉她:你写得很好,比很多作家写的都要好,你应该被更多人看见……你不想留下一些作品吗?
葛吟红看着我。刘诚阳就是我最好的作品。她说。
他不到十岁他爸就死了。葛吟红说,我要照顾四个老人,还要一直看着他读书。我还连续十几年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他是我们两家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现在又自己开了公司。我对得起他早死的爸,我对得起所有人。
只要你再生个孩子……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言辞恳切,眼睛里多了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抽回了手。星星很安静。
早点睡吧,我说。明天还要去爬玉龙雪山呢。
我们起了个大早,一路行至山脚下,游客不多不少,天气也正好。排队买了缆车票,我先带葛吟红去了甘海子。甘海子是一个天然草甸牧场,水草丰美,牛羊成群,高大的乔木直插云天,抬起头能仰视雪山的全貌。葛吟红很喜欢这里,她披着一条丝巾,让我给她拍了好多张照片。我知道,这里让她想起曾经支教的地方,那时候天也很高,风也很轻,日子很漫长。然后像小说里写的,她遇到了一个人,从此改变了一生。
再优秀的小说也描绘不出真实的人生。而她站在我面前,像一本活生生的书,没人愿意翻开她,他们把她当作一块做家务用的抹布,随意使用、揉皱、放置,一放就是三十几年,愿意翻阅她人生的人竟只有我。可书打开的一瞬我就又合上了,我窥不见她的内心,走不近她的灵魂,我又常常不断地自我诘问:我翻开她,又有谁来翻开我?
离开甘海子,我们去了蓝月谷。峡谷风光雄奇壮丽,蓝色湖水宛如玉液琼浆,传说这便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消失的地平线》中蓝月亮山谷的原型。这里聚集了大量拍摄婚纱照的新人,耳鬓厮磨,言笑晏晏,我和葛吟红的组合显得格格不入。她坐在我身边,我们看山、看云、看水,我竟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我清楚地明白我们的心里有着一样的感受,区别在于我可能会付诸笔端,而她会深藏在心底。
我们没有继续往上爬。到了云杉坪,葛吟红开始面色发红、呼吸不畅,这是高原反应的体现,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我带着她紧急下撤,缆车里她靠在我的肩头,低声说,真可惜。
对不起,你还想去冰川公园的吧?现在去不了了。
没关系。我安慰她,只是丽江而已,想来随时能来。
葛吟红不说话了。我只能听到她逐渐平缓下来的呼吸。下了索道,走了一段路,我们准备去找景区接驳车。我去买瓶水的工夫,转过头竟不见她人。
我着急起来,赶紧拨通她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的声音竟不虚弱,指挥我,向前,向右,看到路牌朝左拐——我急匆匆地跑过去,发现她站在一个湖边。
那是一个很小的湖,没有介绍牌,也没有游客,湖水清澈见底,光可鉴人。风吹过她花白的头发,她低头看着水里的倒影,那竟然是一个完整的雪山的倒影。
看——她很高兴地指给我,在这里也能看到雪山顶呢!棒不棒?
遥远的雪山,她上不去的雪山,只可远观而不容她登攀,像是一种名为幸福或者成就的东西。她明明离它如此之近,但只要轻轻触碰一下,一切就碎了,水面的波纹是最伟大的谎言。
手机响了,是刘诚阳的来电,我挂断电话,在葛吟红惊愕的眼神中扑了过去,把她拽到了湖里。湖水不深,只漫到了我和她的半身;湖水也不冷,在盛夏甚至还带着暖意。她在惊讶过后哈哈大笑,用手撩起水花,哗啦啦地落在我的肩上和脸上。
连接我和她的那一座桥断裂了,我向她游过去。又或许,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同一片湖里。
从玉龙雪山出来,葛吟红说想去看看玉峰寺。山茶花刚刚开过一季,残红凋落满地。我和她裙子裤子湿透,进殿实不雅观,最后只在寺外遥遥望了一眼。我问她许了什么愿,她叹了一口气,说当然是希望我和诚阳早得贵子。我们一前一后往外走,沿途有很多当地居民摆的小摊,她在其中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问,这个多少钱?那人回,八十。她没多问,也没砍价,递过去一张红色的钞票,然后把那个小玩意儿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低头看了看。原来是一支小小的文昌笔,木头雕刻,光滑圆润,中间打了个小孔,刚好可以穿根绳子挂在脖子上。
我把文昌笔捏在手心,一时恍然,想说些什么,抬起头来,天高路远。葛吟红已经独自走到前面了。
我和葛吟红回到家时,刘诚阳刚好去邻市出差,门前堆了几件快递和信件。我将快递分门别类放好,然后开始拆信。第一封信来自某杂志社。去云南之前,我把葛吟红的日记整理成电子稿,打印好后寄了过去,收到的回信里写着:
尊敬的葛吟红女士:
非常感谢您向我刊投稿,我们已经认真阅读并评审。尽管您的作品在文字和描写方面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我们认为其内容和主题可能尚不完全契合当前读者的兴趣和时代背景的需求。在经过编辑部的慎重讨论之后,我们遗憾地决定暂时不予采用。
我无声地吐出一口气,放下信件,开始拆第二封。这封信包装精美,看信封上的印刷可知,它来自某家私立医院,收信人是刘诚阳。我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精子形态学复查报告单,白纸黑字,赤裸得像一个新生儿:患者精子正常形态为0。
我死死盯着“复查”两个字,电光石火间,真实与谎言都昭然若揭。报告单从我的手上飘落,葛吟红还在房间里,她哼着歌,大概是在收拾行李,歌声一直飘到客厅,又飘向书桌上方的窗外。我蹲下身来,感觉有湖水慢慢漫过我的脚趾、膝盖、脖子、头顶,让我逐渐不能呼吸。水草摇曳着,星辰陨落,雪山崩塌,万物腐烂殆尽,我触摸不到任何东西,可又像有什么东西悬在我的胸口,一下又一下敲击个不停。我伸手握住它,原来是那一支文昌笔。我向水的深处走去,雷声和风暴就要来了,而我只拥有这最后一刻的宁静。
(责任编辑 肖亮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