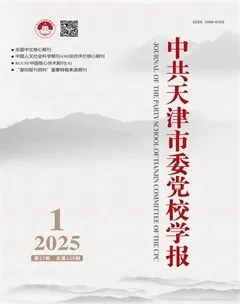注意力适配:数字技术驱动下基层行政负担的治理转化
[摘 要]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和应用落地,数字技术被视为解构基层行政负担、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手段。领导注意力以不同的分配策略牵引数字技术的作用方向,数字技术通过纵向压力传导、横向资源竞争、内部行动路线细化加剧基层行政负担。基层行政负担呈现三种基本样态,即技术性负担、制度性负担与互动性负担。技术性负担源自注意力错位与技术认知失调引发的目标偏差,制度性负担源自注意力短视与制度不稳定性引发的价值偏差,互动性负担源自注意力失衡与利益竞争引发的跨部门协同乏力。科学、合理地运用数字技术化解基层行政负担,要明确领导注意力分配限度,建立差异化分配机制;构建数字治理规则,推进注意力与数字治理的平衡;完善数字治理的配套制度,厘清各级权责体系;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推进基层行政负担实质性减轻。
[关键词]
数字技术;基层行政负担;注意力分配;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5)01-0074-11
一、 问题提出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被确立为我国发展的关键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数字化时代,更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其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基层治理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与社会矛盾的重任。基层政府既要遵循科层制的指挥链条,落实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又要及时回应社会问题,满足民众多样化的利益诉求。
在此过程中,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作为基层治理“减负增能”的重要手段被寄予厚望,数字技术以转移、减少、转化与消除等策略降低基层行政负担[1]。然而,在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基层政府持续减负却“越减越负”的现象屡见不鲜,数字技术异化为加剧基层行政负担的枷锁[2]。一方面,技术赋能要求基层政府在软硬件配置、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及资源整合等方面投入更多财力与精力,导致平台复杂、数据重复、数字官僚、数字悬浮、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频现,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基层政府关注民生问题、解决实际矛盾的注意力[3];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干部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系统,这无疑给他们带来更加复杂的、新型的行政负担[4]。
近年来,基层减负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话题,集聚广泛的关注与深入研究。从理论视角看,数字技术与公共管理痛点、难点问题的契合,可以推进组织流程再造、组织效能提升甚至治理方式变革,但在实践中,数字技术可能异化为加剧基层行政负担的障碍。关于基层行政负担生成逻辑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层行政负担内嵌于政府组织架构的运作体系中,其产生是组织对科层制规范服从的结果,甚至是被策略性“建构”的过程[5]。二是基层行政负担源自民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的摩擦与障碍,与冗余性程序规定、行政程序困扰及官僚主义困境密切勾连[6]。三是政府内部契约的不完备性是基层行政负担生成的结构性因素,正式与非正式契约的交错及隐性契约的张力,共同触发了基层行政负担[7]。那么,在基层治理场域下,数字技术化解行政负担的愿景缘何演变成基层行政负担?已有研究从四个方面给出回应。一是技术本身的兼容性难题及访问可及性障碍衍生了技术不平等,使基层弱势群体面临不同程度的数字技术歧视,加剧了基层政府调节社会公平性、包容性的行政负担[8]。二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是行政负担生成的制度因素,尤其是在职责同构的政府组织结构下,基层政府更容易面临不同条块下达的冲突性任务,导致执行负担加剧。三是自上而下数字化绩效评估压力的层层传导与层层加码,导致基层政府承受了数据重复录入、过度记录等行政负担[9]。四是行动者的利益偏差与策略应对衍生了数字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进一步加剧了基层行政负担[10]。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从数字技术自身局限性、管理体制与考核机制、行动者认知框架等中观层面阐释了基层行政负担的生成逻辑。然而,关于数字技术赋能缘何异化为技术负能的微观作用机制及行动者策略选择,尤其是领导注意力分配何以加剧基层行政负担,现有研究尚未给出充分的思考。为回应这一议题,本文从注意力分配视角出发,结合江苏省S市Z村数字积分运行的具体案例,探究领导注意力错配下基层行政负担的具体样态。在此基础上,重点解构领导注意力驱动下数字技术加剧基层行政负担的逻辑,探讨构建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领导注意力分配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期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注意力分配:理解基层行政负担生成的新视角
从理论上讲,数字技术仅具备工具理性,其设计旨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但在实践中,技术使用者赋予其价值理念和目标导向,催生了问题的复杂互动机制。那么,数字技术是如何形塑领导注意力分配,进而加剧基层行政负担?在基层治理中,领导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呈现显著的选择性、稀缺性、潜在性和可传递性[11]。它决定了决策者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以及优先处理哪些任务与信息。领导注意力分配通常涉及决策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不同领域活动中,以达到预期效果。其中,数字技术在领导注意力分配过程中起双重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促进透明与问责、增强决策科学性、提高信息处理效率等途径优化领导注意力分配;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加剧了技术依赖、形式主义、信息过载,导致领导注意力分配偏差或分散,增加了数据上报、系统运维、过度监督与考核、技术可及性障碍等不同程度的负担。
基层行政负担加剧的背后,既是数字技术将基层问题数字化、技术化与标准化,使基层干部陷入能动受限、责任加码、考核提速的困顿,更是数字技术加持下领导注意力在基层政府的错配[12]。基层政府行为及其变化很大程度由领导注意力分配所形塑。例如,实践中频现的运动式治理归因于领导在短期内将注意力聚焦于治理绩效快速彰显的业务[13],领导批示影响政府决策的逻辑是领导注意力的变化[14],政策实验的效果取决于领导注意力的分配[15]。在数字治理的背景下,基层干部需要在海量数据与信息中,依据目标重要性、外部环境变化及自身认知资源限制,制定有效的注意力回应策略,以确保将有限的注意力精准投入到领导关注的任务中。在这一过程中,领导注意力分配策略及基层干部回应策略,不同程度发生偏差和错配,并直接影响基层行政负担的生成。
(一)注意力的纵向分配:以压力传导强化纵向控制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领导注意力的纵向传导构成基层治理体系中注意力分配的核心机制。数字技术的嵌入,虽然提升了治理过程的透明化、高效化与智能化,但进一步强化了控制机制。上级政府运用数字技术精心设计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如明确的任务指标、严格的考核体系及配套的奖惩措施,实现了对基层政府注意力的有效引导与调控。任务指标的设定是这一控制机制的基础。上级政府通过数字平台量化工作任务,为基层政府提供了清晰的工作路径与明确的考评指标。这些标准涵盖了经济收入、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各个维度,体现了上级政府的考评导向。基层政府在接收到上级下达的指标信号后,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指标作出解读、分解和执行[16]。自上而下考核体系的建立强化了控制机制的效力。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上级惯用的策略是通过数字技术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对基层工作成果进行阶段性检测及年终评估,并根据考核排名决定注意力资源分配的多寡。其中,以职务晋升为核心的政治资源输入对基层干部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注意力资源的向下传导,不仅激励基层政府全力以赴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指标,而且激发基层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创新[17]。然而,注意力的强分配也面临资源过度集中、分配失衡及区域间恶性竞夺等诸多挑战。同时,强大的注意力分配抑制基层政府的自主决策和创新空间[18],导致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核心业务的注意力失焦。
数字技术虽具备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但在压力型体制下,却异化为上级政府控制基层政府并转嫁行政负担的有效工具。上级政府通过考核指挥棒将注意力转化为对基层政府的明确压力,形成注意力的强分配。注意力强分配的本质是行政负担转嫁,其转嫁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考核指标数字化。上级各委办局将政策目标与紧迫任务转为具体、可量化的指标,并以数字平台向基层政府传递。指标设计与政绩勾连,基层政府为了在政绩竞赛中登顶,不得不加大对数字指标的追求,这往往导致形式主义和应付式的工作策略,从而增加了实际的工作负担。二是技术依赖与资源投入。为了满足上级政府对数字化的要求,基层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数据收集、处理和上报系统。这些资源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负担的增加。三是数据上报层层提速。随着数字技术普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报送机制逐渐建立,但在操作中呈现层层提速的趋势。上级政府为了获取更多实时数据,要求基层政府频繁上报信息,使基层政府在信息收集与处理中不得不加速。这不仅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还迫使基层政府策略性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上级政府的期望,导致基层政府采取简化或机械化的数据处理方式应付上级的报送要求。
(二)注意力的横向分配:以政绩牵引强化横向竞争
在压力型体制框架下,基层政府间为争夺上级政府的青睐与资源支持,借助数字技术形成了更为激烈且复杂的注意力竞争态势[19],不仅体现在任务完成的高效与高质量追求中,还深层次地表现为对领导注意力的积极吸引与竞争。基层政府一般会采取政绩展示、合作联盟及差异化竞争等策略,努力吸引上级政府注意,以期在注意力竞争中脱颖而出。政绩展示成为吸引领导注意力的有效手段,基层政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精心策划和包装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特别是那些能体现创新、亮点或特色的项目[20]。可视化的数字政绩大幅提升了基层政府业绩传播的速度与效果。同时,面对激烈的横向竞争,部分基层政府选择与其他区域建立合作联盟关系,共同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项目或平台[21]。项目的规模效应和集聚造势更容易获得上级领导注意力的投射。这类合作模式建立在区域间资源互补与优势共享的基础上,共同应对区域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除了联合发展外,大部分基层政府会基于存量资源,聚焦特色领域,制定差异化的错位竞争策略。其中,部分基层政府会利用大数据深度挖掘自身优势,通过打造可视化的数字景观,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创新项目。然而,以政绩竞赛为驱动的注意力竞争导致资源过度集中于“明星”地区、“创新”项目,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发展失衡及资源错配。更为严重的是,区域间注意力竞争引发的面子工程泛滥、数字形式主义,导致项目烂尾和破产[22]。
数字技术成为基层政府竞争领导注意力的有力工具。注意力的横向竞争也导致基层行政负担的裂变与增大。一是政绩可视化的持续性和吸引力导致基层行政负担持续加剧。基层政府为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上级政府的关注与支持,纷纷将注意力投射到政绩的数字化展示中。为确保政绩展示的实效性与生动性,基层政府不断更新数据、优化展示手段,这无疑会加重其日常行政负担。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对数据进行收集、核实,确保数据的真实、完整和准确;另一方面,为确保政绩展示具备吸引力和新鲜感,基层政府需要不断创新展示方式,如制作精美的图表、视频、动画,以提升政绩传播效力。二是合作联盟过程中的决策一致、利益分配及责任共担,增加了基层行政负担的复杂性。为确保合作方对项目进度、预期成果有清晰的认识,基层政府不得不频繁举行会议、研讨和工作对接,消耗大量时间和人力资源。加上不同基层政府的利益诉求、政策导向及发展规划的差异,这就要求各方在项目进展中不断协商以达成共识,无形中增加了沟通成本。此外,合作联盟的项目进展需要建立公认的监督反馈机制,这就需要合作方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制定合作细则。当合作规则不符合双方期待时,甚至会陷入囚徒困境。三是错位竞争的策略衍生更多新型负担。尤其差异化发展策略需要基层政府在对本土资源深入研究及优势精准定位基础上,探索本土化的独特路径。贯彻这一策略涉及人才引育、资金投入、政策制定、市场推广及管理协调等复杂工作,给各地基层政府带来持续创新的压力和资源配置难题。过度的横向竞争不仅增加了基层行政负担,还可能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三) 注意力的内部分配:以细化行动路线促进责任内化
在数字化考核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数字平台将考核指标量化与分解,引导基层政府将注意力聚焦于考核权重较高的业务指标。当接收到上级政府的注意力信号并感知到考核压力时,基层政府迅速捕捉上级政府的关注重点,并采取具体的策略来消化、分解考核指标。一是对组织架构进行适应性调整。基层政府成立由主要领导挂帅的专门领导小组,负责业务的跨部门协调,确保组织内部对指标认知的统一性和执行的高效性。二是任务指标的进一步细化与落实。基层政府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将任务指标进一步细化至具体部门和责任人,并配套详细的执行方案、时间表和路线图,最大程度降低政策执行的模糊空间和指标落实的不确定性。三是资源的调整与分配。基层政府依据考核指标的权重灵活调整资源配置,将重要资源投放在考核权重较高的经济创收、社会稳定等领域,确保领导关注的重点项目得到最大程度落实。各部门内部在完成本职工作基础上,承担来自本级领导及部门领导分摊的考核指标。在任务指标分摊的过程中,经济创收等重点指标通过数字化工作逐步细化、标准化,进而将某个部门考核负担平移至其他部门,实现责任共担。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帮助领导实时掌握各部门指标完成进度,而且帮助基层政府建立实时的绩效评估体系,以确保上级政府的负担在基层政府内部得到有效内化。
基层政府在内部消化领导注意力的同时,行政负担的总量并没有消减,而是在不同部门之间平移甚至呈现增大的趋势。一是协调负担剧增。一方面,跨部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需要打破部门壁垒,确保信息流通、决策一致和行动协调,并进行持续对话和协同,增加了沟通成本;另一方面,在面对考核指标权重差异时,决策者如何在不损害其他部门利益前提下,合理分配有限资源实现考核绩效最大化,这考验决策者的协调能力。二是执行负担剧增。尤其当任务指标进一步细化与落实,给基层政府带来额外的负担。上级领导在下达指标时,往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基层政府需要将抽象的指标进行本土化解读,并转化为具体、清晰的执行路径,同时配备执行路线图与时间表,无疑加重了基层政府执行的复杂性和工作量。三是责任转移负担剧增。在考核体系中,主要领导一般分管经济创收等考核权重较高的业务。为了保证任务指标的顺利完成,主要领导一般使用制度化权力建立一套内部认可的责任共担机制,确保考核指标在各部门之间被消化,并建立详细的责任清单和执行标准以免部门间推诿塞责。基层政府在内部消化上级注意力的过程中,不仅要细化、分配考核指标,还承担由此衍生的额外行政负担。
三、注意力错配:数字驱动下基层行政负担的生成逻辑
江苏Z村作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及农村数字化改革的试验村,其数字积分的运作不仅揭示了基层治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遭遇的挑战,而且展现了基层行政负担的共性样态,对深入探讨数字技术驱动下基层行政负担的具体样态及生成逻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是在技术层面面临数字积分运维衍生的技术性负担,技术的嵌入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标准化控制,并在注意力的错误引导下衍生目标偏差。二是在制度层面面临动态变化与调整的挑战,加上领导注意力短视,导致数字积分演变成数字创新项目表演及领导政绩可视化的工具。三是数字积分推行关涉数字治理创新项目指标的达成,围绕数字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形成横向的注意力角逐,加剧了横向区域的互动性负担。这些基层行政负担在其他地区具有普遍性,因而Z村具有问题的代表性;Z村原先被定为省级经济贫困村,其信息化水平的起点与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相似,使其在这一背景下的经验和问题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Z村的数字积分运行涉及上级政府、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及民众等多层级治理主体,映射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具备制度与组织层面的代表性。
(一)技术性负担:注意力错位与技术认知失调引发目标偏差
从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看,数字技术的嵌入旨在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再造及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从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具演变成对基层干部劳动过程的标准化控制手段,衍生技术负担。一是行动者对数字技术功能的认知失调。数字积分推进过程中设置了一系列复杂规则和标准,基层干部被要求建立电子台账,实行一事一记录、一周一审核、一月一公示,同时,还被赋予数字平台注册率、使用率、积分清单统计等标准化的任务。每个任务的操作流程与时间节点被清晰地罗列在积分平台,一旦超时或不符合标准化要求,系统便发出警示。标准化的控制限制基层干部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使其在面对复杂情境时很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适,不得不采取应付式执行策略。
二是数字技术对基层干部劳动时间的变相延长。虽然数字积分操作系统被精简,但其背后的流程要求基层干部进行大量的信息上传、轨迹记录、积分统计、奖品兑换等重复性劳动。机械的劳动无形中延长了工作时间并降低了工作效率。这一劳动过程在算法平台被抽象为简单的运行流程与操作角色,基层干部在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循算法预设的既定流程。流程固化与执行刚性使原本需要灵活应对的社会问题和权力运行变得僵化。三是上级政府以数字化系统对基层治理的直接介入和干预[23]。在后台数字大屏,社会问题与权力运作被简化为可视的数字画像,领导注意力随时可以投射并越级介入基层治理。这一监督模式压缩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上级政府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对基层干部实施跨层级监督,导致基层干部陷入纵向压力网络中。当基层干部被限制在算法预设的框架内,便逐渐失去处理基层问题应有的自主判断与能动性。
行动者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失调进一步引发目标偏差。数字技术不仅沦为标准化的控制工具,而且使基层干部陷入技术捆绑的全角色冲突与全时段任务捆绑。数字积分的运行使基层干部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模糊了工作与生活时间,导致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剧增。基层干部需要时间关注数字积分平台的任务派遣与任务转发信息,以便及时回应领导注意力要求与民众的诉求。全时段的任务捆绑使基层干部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角色紧张与压力增大。数字积分加速基层干部的角色分化与工作去边界化。在数字积分平台,基层干部需要扮演多个角色,如积分政策解读者、积分监督员、积分矛盾调解员等。角色分化使基层干部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强化不同角色的压力,导致角色冲突。换言之,基层干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行政领域,不仅需要承担积分统计、积分兑换、过程监督、矛盾化解、信访回复等多元化的社会责任,还需要通过积分平台与民众进行沟通与互动,回应民众多元化的诉求。角色分化及工作去边界化对基层干部的沟通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提出挑战,使基层干部不再局限于既定的工作区域,往往需要与上级政府、组织内部各条线、居委会、民众等进行跨空间互动。这种跨空间的工作要求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需要他们在不同地点之间频繁奔波,导致角色冲突和压力增大。此外,随着数字积分的长时间运行,信息过载的问题凸显。大量的信息涌入使基层干部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登记、处理和筛选信息,以保障及时回应领导注意力要求与民众的诉求。数字积分在领导注意力投射下被异化为超越时空限制的任务分配手段,将基层干部时刻锁定在紧张状态,偏离了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的目标取向。
(二)制度性负担:注意力短视与制度不稳定性引发价值偏差
数字积分设计初衷是创新基层治理范式、激活民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然而,在数字积分推进过程中部分领导决策陷入注意力短视化误区。面对上级领导对数字化成果的量化考核指标,基层干部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民生服务、经济创收等多任务嵌入数字积分实施方案,试图将多任务指标一揽子打包,加快政绩可视化并赚取政治资本。这种短视的功利导向,导致基层政府在制度设计时仓促推进与本地实际不相符的数字积分政策。尤其在老龄化趋势严重的乡村,数字积分的推广频频遇到操作壁垒,增加了技术适应的心理成本。部分民众可能因无法顺利使用技术平台而产生抵触心理,不仅影响他们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还引发其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和质疑。为了缓解这种心理成本,基层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帮助民众学习使用数字积分系统的责任,这不仅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基层政府的行政成本和负担。数字积分的制度设计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显著脱节,使原本提升治理效能的工具变成了被普遍排斥的技术障碍。为了加快完成创新任务指标,基层政府强行硬推数字积分,忽视制度设计与目标群体需求的匹配度。这种技术驱动与人文关怀的断裂导致数字积分在实践中遭遇效用质疑与执行梗阻。为应对层层加码的考核指标,基层政府关注的焦点逐渐偏离技术赋能以减轻基层负担的价值目标,导致数字积分治理变成了基层干部创新项目表演、达成政绩考核要求、服从领导注意力的亮点工程。此外,上级政府在推进数字治理创新项目时,频繁更迭政策内容与形式。
为适应持续调整的考核政策要求,基层干部不得不持续调整数字积分设计的工作重点与考核方向。政策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基层行政负担。
压力型体制下的层层加码与数字化监督引导基层干部转向下级单位要数据,导致“数字生产”[24]及数字形式主义泛滥[25]。面对层层加码和变换多样的考核指标,基层干部进一步衍生出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为。一是考核指标的细化导致基层干部重数据轻治理。尤其当数字积分的推进本身成为被考核的项目时,系统填报率、平台注册率、互动活跃度成为基层干部常态化的考核指标。这一简化的考核方式使基层干部将注意力集中于美化数据而非实质性治理任务,甚至为完成考核指标,编造数据、虚报数据,进一步加剧了基层行政负担[26]。尤其面临多任务叠加且无法兼顾时,基层干部的避责行为应运而生。
基层干部通过对升职空间、政策执行成本、生存状态、权力寻租等要素理性计算,并采取策略性的避责行为。
例如,基层干部在面对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民生服务、经济创收等多指标叠加时,工作难度与工作压力剧增,往往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等变通式执行策略,敷衍塞责以减轻行政负担。二是过度细化考核指标导致“事事留痕”现象泛滥。由于考核指标过于细化,基层干部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难以全部达标。为了掩盖未达标情况,基层政府采取“拍照、定位、记录”等留痕策略[27],以象征性内容替代实质性执行、以线上数据跑腿取代线下群众工作来制造痕迹,展现工作成效[28]。实际中的过度留痕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留痕,部分基层干部为吸引上级领导注意力,主动在社交平台发表工作日常,生产“功绩”痕迹;另一种是被动留痕,基层干部需定时在工作群中发送照片、表格、文件等材料,“文山会海”现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甚至个别部门为了提升政务平台的点击率和阅读量,下达“数字指标”要求基层干部通过签到、打卡、共享等方式体现工作的日常性[29]。
(三)互动性负担:注意力失衡与利益竞争引发跨部门协同乏力
基层在推进数字积分的实践中,领导注意力分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基层互动负担。一是数字积分推进需要增设新的组织机构。为推进数字积分的有效实施,基层政府在原有职责基础上增设专门的积分管理专班来规划、协调、督促积分制工作开展。积分专班的增设旨在发挥数字积分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却导致组织职能扩张及基层干部职责加码。基层干部不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还需承担积分制管理的额外负担,如积分清单的更新、积分收集汇聚、积分兑换审核、积分上报等叠加任务。多任务叠加使基层干部陷入频繁的数字操作,忽视了干群互动及基层治理的实际问题。二是数字积分效能评估需要一套设计科学、执行严谨的监督考核机制。然而,数字积分衍生的增量考核指标对基层干部形成全新的问责和约束机制,如积分治理满意度、积分平台注册率、积分治理效率等指标给基层干部带来额外的负担。为如期全额完成考核指标,基层干部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频繁使用数字工具,确保数据及时上报更新。这种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考核机制需要基层干部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数字操作中,忽视了部门沟通与协作,加剧了协同互动的负担。
数字积分作为地方创新举措,亟须领导注意力资源支持。围绕领导注意力配置,区域之间展开横向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政府的互动负担。在数字积分推进实践中,基层干部为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加持,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显示度较高、容易出成绩的数字创新项目及示范项目竞争。一是就数字创新项目与晋升动机而言,领导注意力往往成为基层干部工作的风向标。基层干部意识到,数字积分能快速展现成效并吸引上级领导的注意,从而快速积累政治资本。在政治利益的诱导下,数字积分成为迅速凸显基层干部政绩可视化的亮点工程,而非助力治理效能实质性提升。二是聚焦示范项目竞争。随着技术赋能基层行政的趋势日益增强,基层政府纷纷投入数字建设的浪潮中,试图打造具有全域示范意义的标杆项目,在同级政府间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竞争格局。这种竞争促使基层政府在数字平台上投入大量资源,热衷于打造省级示范项目,甚至全国示范项目,以期在横向区域比较中脱颖而出[30]。横向注意力竞争的背后潜藏着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及对政治生态的深刻侵蚀。在错误政绩观引导下,基层干部将有限的资源集聚于上级领导关注的项目,挤占了其他项目发展空间,影响整体治理效能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
四、注意力矫治:基层行政负担的化解路径
在基层治理场域下,领导注意力牵引着政策落地与资源流向。面对注意力错配及数字技术异化引发的目标偏差、价值偏差及由此衍生的基层行政负担不断加剧,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成为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减轻基层行政负担的关键突破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探讨注意力分配的理论与实践,寻求合理配置领导关注焦点的策略,确保领导注意力能够聚焦于基层治理的核心环节和关键领域。
(一)明确领导注意力分配限度,建立差异化分配机制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领导注意力配置方向与领域对基层干部行为塑造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明确领导注意力分配限度,不仅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更有利于塑造良性的上下级关系。尤其在数字治理的体系下,上级领导要把握注意力资源分配的总原则,确保注意力资源得以高效配置与利用。这就要求上级领导在政策制定、指标下达的过程中,充分调研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并确定对接指标的承载能力,摒弃考核指标直接下沉的“一刀切”强推模式。在全面剖析基层政府的人力、财力、基础设施等现状基础上,制定一套既符合宏观战略导向,又契合基层政府实际需求的注意力分配策略[31]。该策略应详尽阐述各项任务的核心构成、执行标准、预期成效及评估体系,为基层政府执行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引,从而确保注意力资源能够精准投放至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上级政府还需实施差异化的注意力分配策略,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治理基础、资源条件及治理挑战上的显著差异[32]。通过建立基层治理能力综合评估体系,对各地区的治理水平进行量化评分,并以此为依据灵活调整注意力分配的重点与方向。对于治理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的地区,适当精简非核心任务的分配,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关键问题;对于治理成效显著、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则可适当增加创新性、探索性指标的比重,鼓励其先行先试。同时,上级政府还需兼顾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确保注意力资源分配的均衡性与合理性,以促进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
为了保障注意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并有效减轻基层行政负担,亟须建立一套科学的注意力分配绩效评估体系。一是注意力分配的评估体系需构建明确的目的性,即以评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领导决策科学性,进而强化组织效能。由此,需要构建包括注意力分配均衡性、聚焦度、响应度及决策效果在内的多维评估指标体系。二是注意力评估体系需切实关注民众满意度。民众虽是领导注意力配置的间接受体,却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众,所以要采用科学的民意调查方法,广泛收集民众对领导关注议题解决成效的反馈。
三是评估结果的及时反馈与运用。根据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的反馈,上级政府既要适时调整注意力分配方案,又要加强对政策调整及指标设置的宣讲,提高基层政府的认同感与执行力。为了避免上级政府在评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见介入与利益冲突,可凭借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优势,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治理目标的达成。
(二)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建立基层数字治理规则
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工具,数字技术的嵌合还需要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深度融合,确保数字技术契合基层治理的实际命题,而非成为加剧基层行政负担的工具。一是从基层治理结构上优化纵向与横向组织之间的关系,释放数字治理带来的行政负担,化解注意力层层加码和技术异化引发的数字形式主义泛滥。一方面,增强基层政府在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决策权,打破基层政府被数字技术标准化流程宰制的困局;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为基层政府实质性减负,实现组织结构优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效应。二是建立数字指标循环督查机制,化解数字化考核表象与数字指标硬性下沉。尤其关注数字指标对基层干部的严格控制,通过循环督查,建立上下衔接、左右联动的问题反馈与纠偏机制,避免一刀切的数字指标下沉与技术依赖。三是建立上下贯通、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治理体系,将基层干部从技术性负担、制度性负担及互动性负担等压力中释放出来,切实投身于为民办实事的公共服务中。数字治理的宗旨不是无限细化基层干部的劳动过程,而是针对基层单位的数字化水平与实际承载力切实地提质增效。因此,需要厘清基层治理制度与数字技术的内在关联,明确数字技术是推进基层治理、优化制度设计的工具,而非被领导注意力和压力型体制所形塑的工具。同时,针对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对数字治理的承载力,上级政府应该进行客观的评估,由自上而下单向度地控制转变为上下协同的数字治理模式。
上下协同模式的构建需诉诸公正、合理且适配的数字治理规则,为数字技术应用及领导注意力分配树立明确的边界。一方面,数字治理规则应以实际效能作为督查考核标尺,对数字积分实践中的可视化政绩展示、横向资源角逐、数字留痕等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切实以数字技术“瘦身减负”为基层干部松绑;另一方面,当数字技术的运用不受约束,则容易引发负外部性,所以要加快从宏观层面制定公正合理的数字治理标准,既要推进基层数字治理的标准化与公开化,也要激发基层干部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同时,明确数字治理的边界。数字技术的嵌入以提升治理效能与服务水平为边界,而非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过分迷信数字指标,使基层干部陷入流水线式的数字生产与拼凑式应付的压力循环。基层数字治理实践要推进基层治理实现规范化与人本化。
(三)完善数字治理的配套制度,厘清各级权责体系
有效化解注意力错配,需要从完善基层数字治理的配套制度、厘清权责体系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为了确保基层数字治理与领导注意力的平衡,构建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应为数字治理提供明确的指导原则和操作规程,涵盖从数字治理的基础性法律法规,如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到针对基层实际情况出台的具体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这些规范应覆盖数据采集、处理、共享、利用的全链条管理,明确数据权属、流转规则及保护机制,同时,界定各方在数字治理中的权责关系[33]。二是为确保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需建立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优化制度设计。通过对注意力投射和分配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减少注意力资源的恶性竞争。三是各部门应厘清权责体系,明确自身的主导地位与具体职责,如规划制定、政策执行、监管监督等。通过制定详尽的权责清单与工作流程图,确保各层级清晰地掌握自身职责和工作内容;尤其减少上级政府对基层的直接介入与越级干预,赋予基层数字治理主体更多自主权和创新空间。
推动基层数字治理的深入发展,还需强化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以打破信息孤岛,促进资源的高效共享与业务的紧密协同,从而凝聚治理合力[34]。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在于制定过程,更在于执行与监督。为确保制度得到切实执行,还需构建健全的监督体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智能化监督平台,对数字治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同时,加强社会与舆论监督,拓宽民众参与渠道,鼓励民众举报违规行为。针对发现的问题与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严惩,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力。在强调制度威慑力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合理的容错空间是激发基层政府创新活力的关键。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基层工作中难免会遇到探索性、创新性任务,其间伴随着一定的失败风险。上级政府在考核制度设计时,应鼓励基层干部敢于创新、勇于实践,这就要求对基层干部考核具备一定的容错空间,对创新性行为予以正面评价,避免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进行单向度的追责。这种容错并非放任,而是对基层干部成长规律的尊重,为其提供改正错误、积累经验的机会。
(四)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推进基层负担实质性减轻
考评体系不仅是对治理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治理过程和策略的优化指导。压力型体制下的考评过度依赖上级政府单向度的经济指标与数字指标下放,容易忽视公共服务质量、社会效益及基层单位的实际承载力。构建基层数字治理的考评体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聚焦基层民生服务等核心任务与关键领域,以减负为导向设置科学的考评标准与指标,摒弃重复、烦琐、无意义的考核指标,合并归类相似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全面反映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避免过度追求可视化的数字指标而造成基层压力过载及数字形式主义。此外,指标设计要兼顾质量与效果,增加实际效果、民众满意度等实质性指标权重,减少对过程性、形式性指标的过度关注,引导基层政府重视实际工作成效而非数字流水线生产绩效。二是创新考评方式。改革传统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压力考评模式,引入民众及第三方等多元化考核主体,多维度对基层干部的工作实效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尤其关注民众满意度调查,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使考评结果更加贴近民意、反映实情[35]。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考评方式,形成对基层数字治理效果的全面评估与反馈。三是确保考核体系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建立定期诊断机制。充分发挥考评的诊断功能,通过对考评结果的深入分析,诊断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及负担过载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跟踪问效,确保诊断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形成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同时,建立考评体系的定期评估机制,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优化考核指标和评估方法,增强考评体系对基层治理新变化与新要求的适应性,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与水平。
考核体系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复杂且专业化的过程,应构建一个既能有效制约又能积极激励的机制,以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职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在考评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基层干部是具备能动性、创造性的个体,而非机械的执行机器。考评体系的建设需坚持以人为本,强化责任伦理在考评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塑造基层干部的责任伦理,以专业精神与职业道德为导向,驱动基层干部主动担责、提升服务质量;以责任伦理的强化培育基层干部的职业素养,促进其角色从被动、应付式执行转向主动服务者转型。在考核体系的设计上,坚持考核与激励并重的机制建设,通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基层干部行为进行精准且合理的引导。这种引导不仅强调对消极行为的有效制约,更涵盖对干部积极行为的充分激励,实现监督考核与正向激励的平衡,以此激发基层干部的创新动力与干事热情。
参考文献:
[1]马 亮.数字政府如何降低行政负担?[J].行政管理改革,2022,(9).
[2]吴建南,王亚星,陈子韬.从“增负减能”到“减负增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7).
[3]Cordella A,Tempini N.E-Gover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ICT and Bureaucracy i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5,(3).
[4]孙宗锋,丛楷力.数字赋能何以变为基层数字负担?——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J].行政论坛,2024,(2).
[5]栗伊萱,刘文璋.乡镇政府负担生成的三重机制——一个组织学的解释框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6).
[6]朱春奎,童佩珊.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行政负担研究进展与展望[J].公共行政评论,2023,(5).
[7]于 水,区小兰.基层治理中数字负担的生成与消解[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8]马 亮.数字政府如何影响社会公平:作用机制与理论前瞻[J].探索与争鸣,2024,(5).
[9]陈浩天.后扶贫时代脱贫清单的数字化运作及信息共享理路[J].中国行政管理,2020,(7).
[10]范逢春.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的成因及破解[J].人民论坛,2024,(11).
[11]苏君华,周林兴.注意力资源与信息服务业发展[J].情报杂志,2003,(12).
[12]章文光,刘志鹏.注意力视角下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基于精准扶贫的案例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4).
[13]刘志鹏.常规开展的“运动”:基于示范城市评比的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4).
[14]陈思丞,孟庆国.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基于毛泽东年谱中2614段批示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6,(3).
[15]杨宏山,李 沁.政策试验的注意力调控与适应性治理[J].行政论坛,2021, (3).
[16]刘天文.指标问责:乡村治理中的数字化机制及其实践[J].学术交流,2024,(5).
[17]杨 华.注意力内卷: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逻辑——以F县综合考核指标演变为例[J].开放时代,2024,(5).
[18]陈 宇,罗天正,孙枭坤.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19]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
[20]魏 来,李 伟.“创新突围赛”: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组织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
[21]张瀚禹,吴振磊.数字创新合作、应用鸿沟与区域间共同富裕[J].财经研究,2024,(8).
[22]范炜烽,白云腾.何以破解“数字悬浮”:基层数字治理的执行异化问题分析[J].电子政务,2023,(10).
[23]Gorwa R,Binns R,Katzenbach C.Algorithmic Content Moderation:Technic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Automation of Platform Goverance [J].Big Data amp; Society,2020,(1).
[24]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
[25]金 华.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数据化:风险与因应之道[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 (1).
[26]金 华,高奇琦.从悬浮到融合:积分制的数字化转型与乡村社会双向形塑的内在逻辑——基于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Z村的实证考察[J].电子政务,2024,(10).
[27]陈文琼.基层治理转型视角下的过程内卷与形式主义困境[J].理论月刊,2024,(5).
[28]李沁怡.隐蔽的形式主义:技术执行视域中智慧化网格管理的实践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浙江省“基层治理141体系”的经验考察[J].电子政务,2024,(8).
[29]钟伟军,阎 馨.技术的多重建构:基层常规任务何以导致数字形式主义?——基于Z市M镇的考察[J].电子政务,2024,(5).
[30]李 婷.注意力竞争与适应性选择: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兼论“伪创新”现象[J].地方治理研究,2023,(2).
[31]崔 晶.基层治理中的政策“适应性执行”——基于Y区和H镇的案例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2,(1).
[32]李燕凌,苏 健.地方政府建设数字乡村的注意力分配差异与政策逻辑——基于435份地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4,(1).
[33]李沫霏.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反思、现实解构与优化策略[J].经济纵横,2023,(2).
[34]张会平.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策略[J].人民论坛,2023,(14).
[35]孙会岩,王玉莹.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J].电子政务,2023,(2).
Attention Adaptatio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Burden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Digital Integral Operation Based on Z Village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Leaders’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by different allocation strategies, while digital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burden through vertical pressure transmission, horizontal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internal course of action refinement.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basic patterns, namely, technical burden, institutional burden and interactive burden. The technical burden stems from the goal bias caused by misplaced att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 institutional burden stems from the value bias caused by myopic atten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The interactive burden stems from the lack of cross-departmental synergy caused by an imbalance of attention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burde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limit of attention allocation at the upper level and establish a differentiated alloc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 digital governance rules to promote the balance between atten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improve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clarify the system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t all levels, establish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burden, attention allo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