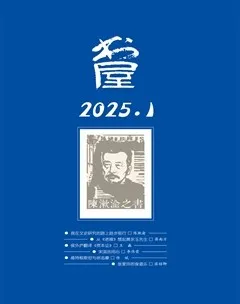“乱离骨肉病愁多”
1940年2月26日,避乱昆明的陈寅恪致信傅斯年:“弟此次之病甚不轻,即心悸心跳,所谓怔忡者是也。”频繁的心悸令他苦倦不堪。医生认为心悸是神经衰弱和脚气病所致,而陈寅恪则以为除此之外尚因“昆明地高”,自己无法适应。1937—1945年,陈寅恪频繁表达了他在恶劣环境下“大病几死”的感受。
陈寅恪给世人的印象是“身体太弱,健康不佳”,在全面抗战期间更是疾痛缠身,以致深感生不如死。心悸是陈寅恪最常提到的症状,曾让他“几死于昆明”。心悸患者常感到心跳强而有力,有时心率快如赛马,心跳剧烈像要从口中跳出,对此陈寅恪曾描述为“心荡”和“因心跳出冷汗”。他一般在夜间入睡前症状明显,以致长期失眠,只能依靠安眠药。
陈寅恪也经常抱怨自己头晕目眩,以致精疲力竭,无法集中精力读书、写长信。只是与心悸相比,陈寅恪对眩晕的表述相对客观简洁。这一症状很可能亦与神经衰弱有关。目眩则可能与用眼过度导致的视力恶化有关。1937年秋,陈寅恪右眼因视网膜剥离而失明。他的左眼则是1944年12月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时失明的。在左眼失明前夕,他曾向朋友感叹:“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可见昏眩既是视力衰退的症状,也加剧了他对失明的不祥预感。
消化不良亦困扰陈寅恪多年。1929年,陈寅恪致信傅斯年云:“弟……近复失眠不消化,故亦病废矣。”1937—1945年间,他对这一症状的抱怨更是不胜枚举。浦薛凤亦回忆陈寅恪“胃不甚健”,下午吃点心时需同时服用消化药片,还说“我此刻觉饿,要吃些点心,但如不加消化剂,则晩餐时又不想吃”。一般而言,消化不良或单纯由慢性胃炎引起,亦有可能是神经衰弱所致。其原因虽不能确知,但据以上史料,不消化常与失眠并举,似与神经衰弱关联密切。
经济困难也是陈寅恪深受疾痛纠缠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早年家境殷实,早已适应了优渥、舒适且西化的生活。抗战以来,陈氏夫妇和小女美延都体弱多病,尽管得到多方资助,但由于医药支出不菲,家用仍然拮据,生活品质严重下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家的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陈寅恪不得不与妻子轮流诊治服药,有时甚至只能忍病不治,因此“医药之功或施或辍”,以致“病亦未能全愈”。社会环境的恶劣和入不敷出的困境亦使他严重缺乏营养。陈哲三回忆:“……我上街买了三罐奶粉送去,想再多买一罐也没有,陈先生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劳忧过度则降低了陈寅恪的抵抗力,成了他“百病转发”的又一重要原因。以学术为天职的知识人本就容易消耗过多的精神,而战乱更使国难、家愁和个人的不幸叠加,压得人喘不过气。作为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陈寅恪在身体过劳的情况下仍认真讲课。而作为急切想为学界留下更多成果的学者,他则用尽全力进行著述:“作文……幸尚不十分累,我亦知停止最好。此我详细酌量我之身体及时局而为之者……”加之两次丢失书稿、妻女病困香港、经济入不敷出、身边缺少知音等因素,他难免经常处于疲倦、痛苦的状态中,以致常向亲友抱怨。对于双目失明的厄运,陈寅恪则认为他自幼嗜书,常于夜间在被褥里偷偷读书,用昏暗的小油灯照明,而且文字细小模糊,久之形成高度近视,视网膜剥落遂不可幸免,“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
短短几年内如此频繁的症状表达在陈寅恪的一生中绝无仅有。当疾病在他的生命中愈来愈有难以承受之重时,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亦必将与之难解难分。
1945年春,在多次手术未见成效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决定“先事休养,再求良医”。他在诗中以“蹉跎病废五旬人”自况,又有“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之叹。毫无疑问,疾痛给他的生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尽管疾痛绝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此外,陈寅恪还时常抱怨疾痛带给他的精神困扰,“苦”与“倦”是较多被提及的状态。左目失明后,他“眼被遮蔽,头不能动,心情很苦闷”,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过程中更加焦急、烦躁和失望,乃至有“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之叹。疾痛与国难家愁交织,一起让陈寅恪自感“忧闷不任”“心绪甚恶”“心绪甚不佳”“进退维谷”,以致“顶发一从忽大变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懒于给亲友写信。在疾痛的长期折磨下,陈寅恪对自己的身体极度悲观,乃至有“今则知国命必较身命为长”的衰颓预感。从后来他对这段疾病体验的追述——“病榻呻吟,救死不暇”“大病几死”便可以看出,重病致死的潜在可能在他心中投下了深深的阴影。纵然如此,他还是在病中认真备课,继续著述。在听闻友人因伤寒逝世后,他以“年长者不必皆较年少者先死,体弱者尤不必较体壮者先死”自嘲。经亲友多方劝导,他重新振作,逐渐走出“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失明阴霾,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明志。
疾痛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亦影响深远。陈寅恪早年对著述态度谨慎,从不轻易下笔,在“七七事变”前只是发表了若干论文和序跋,并未著书。然而随着战局危殆,“年来复遭际艰厄,仓皇转徙”,一方面让他改变了待人接物的方式,对于指导与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乱离和疾痛带来的死亡预感越发强烈,使他意识到“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从而“随顺世缘”“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抓紧著书。他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便如是说:“甚希望能于神识未离身体时(此昔日和尚常语)得完成此作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稍晚写成的《元白诗笺证稿》并称“三稿”,是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前“两稿”作于1939—1941年间,更是他自我期许极高的著作。邓广铭回忆,在昆明青云街居住时,陈寅恪经常卧床呻吟,哀叹自己命不久矣,但又总说:“如果我不写完这两稿,就死不瞑目!”而陈氏在书信中的自白亦可透露“两稿”对他的意义所在:“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可见,只要“自作纪念”的“成绩”写成并顺利出版,他甚至“夕死可矣”。正是这样的态度,才让他克服“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的困难,并不惜“急急于争利”,利用疾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使“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从而留下传世之作。
双目全盲后,陈寅恪自感已变成“旧学渐荒新不进”的“独卧文盲老病翁”。据陈源转述,陈寅恪“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因此他开始调整自己著书立说的方式,“以耳代目、以口代手”,努力做到瞽而不废,并最终恢复讲课。妻子唐筼也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帮助他誊写文稿。此后二十余年,石泉、王永兴、汪篯、黄萱等人陆续担任他的助手,协助他著书和教学。然而,陈寅恪暮年最终转向“心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受到了目盲等诸多疾痛的刺激?一方面,他“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论者如余英时等或指出陈氏史学第三变的深层原因,但目盲而造成的不便也是一大客观因素;另一方面,疾痛难免使他的身体时常处于残缺和被禁锢的状态,加深了他对自己生命悲剧的体会,而在内心情感世界寻求超越便是他与宿命抗争的方式。如学者潘静如所言:“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对隋唐制度、蒙古史的一类问题再发生太大兴趣,他更在意的是关于人、关于命运。”由此看来,疾痛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机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