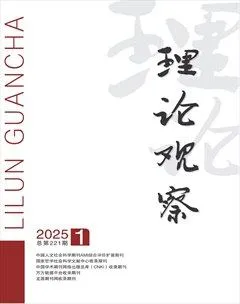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幸福学解读
摘要:亚当·斯密首先致力于道德哲学的学习研究。这种“学术出身”和学术立场,决定了他是个追求公众幸福的学者。为了追求公众幸福,斯密提出并倡导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他创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即以“公众幸福”为目的,以“经济人”为主体,以“看不见的手”为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人假设”“看不见的手”,在他看来,只是更快地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实现共同富裕,进而实现公众幸福的有效方法与工具。
关键词:共同富裕;公众幸福;经济人;看不见的手
中图分类号:F09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25)01—0095—06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1]。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而实现共同富裕又是党和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所肩负的更为伟大而艰巨的历史重任。亚当·斯密也曾倡导共同富裕。斯密的共同富裕理论及实践,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有所帮助。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斯密正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斯密的经济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共同富裕理论,也与斯密的经济学说有着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的关系。斯密的共同富裕理论已形成以“公众幸福”为目的,以“经济人”为主体,以“看不见的手”为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全面了解、深入认识、正确评价斯密的共同富裕理论,就需要弄清楚斯密提出、倡导共同富裕的思想根源、理论底蕴及其实质等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就会明了它们在斯密“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非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与我国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异同,给予我国的共同富裕事业启示。
二、斯密共同富裕经济学说的体系构成
斯密的共同富裕理论,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它贯穿于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贯穿斯密力求创建的整个“学说体系”中。具体来说,它贯穿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巨著中,两书就是围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展开,旨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指出:“被视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科学的一门分支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目的: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或联邦提供一个足以支付所有公共开支的收入。”[3]因此,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它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富裕”[3]。这表明,斯密的经济学说的确是围绕共同富裕展开的。
斯密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1.“公众幸福”是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贫穷而悲惨的,那么这个社会绝不可能繁荣和幸福。”[3]这是斯密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从反面提出并肯定共同富裕。在斯密看来:一个社会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绝大部分成员都富裕且有尊严,这个社会才能“繁荣和幸福”。共同富裕是公众幸福的内在要求和条件,斯密这样看待和规定共同富裕的实质是正确而深刻的。他与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共识。马克思曾预言,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列宁进一步指出,就是让“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这意味着“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走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
斯密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持公众幸福、人民幸福。为此,斯密倡导共同富裕,反对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至于斯密为什么那么执着地关心、支持和维护公众幸福,这有下列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斯密的学术出身、学术立场决定。由于受到道德哲学的深刻影响,斯密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奠基者,以经济学闻名于世。但他是从道德哲学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他开始是一个哲学家,主攻道德哲学,而道德哲学是以研究幸福问题,探讨人类的幸福之路、建设幸福社会、幸福国家为目的与任务。《哲学的慰藉》作者阿兰德波顿认为:哲学的最大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是人生痛苦的解脱之道。换言之,哲学就是谋求幸福的智慧,指引人类追求幸福道路的思想明灯。为此,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称为探索幸福的人,而他的学生柏拉图撰写的《理想国》,实质是“幸福国”。这本哲学名著旨在构建一个为全体公民谋求幸福生活的“幸福国家”。据此,斯密提出并认定:“人的幸福和圆满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所思考的人不仅是一个单个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国家和人类这个大社会的一个成员,是古代道德哲学所力求探讨的对象。在那个哲学里人生的职责是作为从属于人生的幸福和圆满这个主题而进行研究的。”[3]在这里,斯密说得很清楚,道德哲学是以“大社会的一个成员”的幸福,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幸福、公众幸福为对象和目的的科学。为此,斯密批评说:可是“在大多数场合,诡辩术和苦行的道德构成了学校中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哲学所有不同分支中最重要的东西就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最被歪曲了的东西。”[3]由此可见,斯密道德哲学的学术出身决定他的学术立场是以幸福为对象和目的,从而使他忠实和坚持道德哲学固有的幸福本质。这就进而决定斯密采用“立言”的方式,用学术理论作为工具,为公众谋利益、人类谋幸福。
其次,由于富有“同情”这种人的本性。“同情”这个品德、情感,在斯密的伦理学中有着重要地位,这对他关心和执着公众幸福,人类的幸福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可以说,“公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斯密的伦理思想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人,是一位有着浓厚同情心的学者。
斯密对于“同情”这种品德、情感给予很高的评价,把它提升到人性的高度,看作是人的重要美德。他的《道德情操论》的第一章就是以“论同情”为主题,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的表明:“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之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6]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斯密具有“怜悯或同情”这种宝贵的人类本性,因此,“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作为研究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他的眼中,这个“别人”就不限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而是整个人类。的确,斯密从内心里同情关心劳动者的疾苦和利益,他在论及经济增长情形的变化对广大工人的影响时强调说:“所有者阶层也许从社会的繁荣中所获得的东西可能多于劳动者阶层,但是没有哪一个阶层从社会的衰退中所遭受的痛苦比劳动者阶层更大。”[7]
为了深入了解和弄清楚斯密关心和执着维护公众幸福的原因,这里谈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之相似之处。马克思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把幸福看作是人类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坚持“幸福终极目的论”[8]。在他们看来,创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社会,最终目的是让“虚幻幸福”变为“现实幸福”,让广大群众得以过上幸福生活。正因为如此,使得马克思同斯密一样,当他们由哲学园地转身进入经济学园地后,力图通过自己创建的政治经济学寻求“增进社会幸福的办法”[6]。当然,由于两人的经济学说有根本区别,因此寻求“增进社会幸福的办法”不同。至于在同情心这个方面,马克思与斯密一样,也极富同情心。早在中学时代,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少年马克思目睹当时劳动者的贫穷与痛苦,便立志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奋斗终生,让他们脱离苦难屈辱的生活。因此,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看待和解决劳动群众的苦难和幸福问题。
2.“看不见的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和工具
斯密创造性地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看不见的手”。但是,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工具,其他的东西不可替代。
第一种“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来的。斯密在论述富人由于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幸福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因此盲目追求财富和地位这些身外之物时突发奇想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6]斯密的这段论述包含两种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方式,一种是依靠直接把“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使生活资料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让人们过上富足生活;另一种则是由“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使全体社会成员过上富足生活,斯密相信第二种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正如他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里,关于如何使人民富裕起来这个问题由于各国富裕的进程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可以称作商业体系,一个可称作农业体系。我将竭尽所能对它们作出充分而又截然有别的说明,我将从商业体系开始,它是当今时髦的一个体系,在我国和当今这个时代也最为人们所熟知。”[3]
关于这种“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它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斯密认定:“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至于通过什么方式方法让土地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得到土地所能提供的产品而过上富足的生活呢?斯密的回答是:占有大量财富的地主为了消费掉它们,也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与生活需要,“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用最好的方法来烹制他自己享用的那点东西的人;分给建造他要在其中消费自己的那一小部分收成的宫殿的那些人;分给提供和整理显贵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小玩意儿和小摆设的那些人。”“就这样,所有这些人由于他生活奢华和具有怪癖而分得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期待他的友善心和公平待人,是不可得到这些东西的。”[6]由此可见,满足富人生活的欲望和多方面的需求的方式方法,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正是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把富人的财富转移到为他服务的厨师、建筑工人和各种工艺品匠人身上,使他们过上温饱乃至富足的生活。
第二种“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在该书中,斯密分析说:资本家将手中的一部分资财作为资本用于产业的发展,他所算计的只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促进公共利益。但其结果却“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总是被一支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进一个他全然无意追求的目的。而且也并不因为他没有任何这种意图,就对社会更坏。他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时常比他真实地有意促进社会利益时还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7]这里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在斯密看来,自由的市场机制既能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又使广大劳动者、公众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斯密在《国富论》中还以当时北美地区的工人生活的富裕状况为例,用以证明“看不见的手”对于社会利益、共同富裕的确具有积极作用。斯密说,由于财富的迅速增长、积累丰富,使得当时的北美地区的公众“即使在最坏的季节,虽然收入少了一些,他们也有充足的食品维持生活。”“在那里劳动的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是一个负担,反而是父母富裕和家庭兴旺的源泉。”[7]
3.自利自爱的本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斯密倡言:“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这是由于“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对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灵敏。前者是原始的感觉;后者是对那些感觉的反射或同情的想象。前者可以说是实体;后者可以说是影子。”[6]因此,斯密把追求自身幸福和利益视为人的本性。这使他对二者都持肯定态度:“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6]他还告诫世人:“我们并不动辄猜疑某人存在自私自利这种缺陷。它决不是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或我们易于猜疑的缺点。”[6]
在斯密看来,由于人们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幸福所真正需要的东西”[6],因此为喜好幸福,进而追求财富的利己的“天性”所欺骗。“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幸福多彩。”[6]不言而喻,激烈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让物质财富逐渐丰裕起来,并且把幸福的生活资料分配给广大劳动者,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上述三部分内容构成斯密比较完整的共同富裕理论。
三、对斯密共同富裕经济学说的评价
如何准确看待和评价斯密共同富裕理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不唯书、不唯上,不搞本本主义。我们从总体、全局角度看待斯密其人与他的学说,得出下列看法与结论:
1.斯密并非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经济学家
要认识并认定斯密的共同富裕理论,关键是正确判断他及其学说的社会属性问题。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以及理论界都认定斯密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他是资本家在经济学界的代言人,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为此,斯密的经济学说也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他被尊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开山奠基人。
但实事求是地考察斯密的学说,不难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即斯密并非完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而是如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为人类、公众、人民的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孜孜不倦地探索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密的目的超过柏拉图的“幸福国家”,追求“公众幸福”“社会幸福”“整体的幸福”“人类幸福”问题,可见他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幸福社会、幸福世界。确定这一点就不难了解并认定斯密在撰写《道德情操论》之后,接着撰写《国富论》的原因,创建新的经济学说,其目的正是寻找“增进社会幸福的办法”。这意味着,在斯密的头脑中,提出和倡导的“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以及以二者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是“增进社会幸福”的手段与工具而已。他曾经批判有些人忘记了公众幸福这个最终目的,把实现它们的手段当作目的。斯密的后继者就犯了这个错误,忘记了公众幸福,把增加财富这个手段当成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并由此把经济效用、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经济学的主题与内容,把人类、公众、人民的幸福这个终极目的排挤出了经济学领域。
总之,从实际来看,不仅由于斯密的道德哲学家这种学术出身、学术立场决定他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以谋求公众幸福为最终目的,而且由于斯密是极富同情心,并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的学者。因此,他对于广大劳动群众、亿万公众的快乐与痛苦非常关心,极力维护公众的利益,为此曾严厉批评地主、资本家等一切富人对劳动群众的欺压行为,可以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例如,斯密分析指出,在委托职业经营者管理生产的公司里,“而资本的持有人虽然几乎免除了一切劳动,但他却仍然指望他的利润能与其资本保持一固定的比例。”“这样一来,劳动的全部产品并不总是属于劳动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必须与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分享。”[7]在这里,斯密明确地揭示了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斯密还尖锐地指出与北美地区不同,“在其他国家地租和利润吃掉了工资,人民中的两个上层阶层压迫着下面的一个阶层。”[7]在这里,斯密更明确地揭示了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上层阶层”对工人群众这个“下层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对于这种压迫和剥削,斯密批评说:“哪里有巨大的财产,哪里就有极大的不平等。因为有一个很富的人,起码就要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意味着许多人的贫穷。富人的富裕激起穷人的愤恨,匮乏经常驱使穷人妒忌,经常促使穷人去侵犯富人的财产。”[7]在这里,斯密不仅揭示了剥削,而且说明了“富逼民反”的理由,表示了他对穷人的同情、理解和道义上的支持;也告知世人: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难以安宁的道理。尤其是斯密曾尖锐地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买卖人的利益在任何一个商业或制造业部门总是在某些方面与公众利益不同,甚至相对立。”[7]据此,他建议说:“听取这个阶层提出的关于任何商业新法或法规的建议应当极为慎重。”“因为这个阶层的人的利益从来不与公众利益相一致,而且他们通常热衷于欺骗、甚至压迫公众。在许多场合他们既欺骗了公众,又压迫了公众。”[7]我们相信,不仅是雇佣工人,就是一般公众看了这些话也会拍手叫好,感谢斯密这个有良知的学者仗义为他们说话。
2.斯密的共同富裕学说并非纸上谈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指导我们考察评价一切理论、理念是否正确,要让事实说话,以事实为准绳。正是遵循这种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态度,使我们在考察和研究斯密问题时,没有囿于传统观念,从而得以认识和把握斯密共同富裕理论的真实面目及其结果。
实际情况是,斯密把“看不见的手”“经济人”视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而“增进公众幸福”的方式方法、主客观要素和条件,并不是凭主观想象,凭逻辑推导,而是首先以耳闻目见的事实为依据。在《国富论》论述雇佣劳动者的工资问题时,斯密正是目睹当时已出现在波士顿、纽约、费城等一批“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地方”这个事实而得出这个结论:“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不断增长的财富的结果,同样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看来是在社会向获取更大的财富阔步前进的进步状态中,而不是在社会已经获得最大财富时,穷苦的劳动大众——人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得最幸福,也最舒适”;“社会的进步状态实质上全社会所有不同阶层的人都欢乐和舒心的时候。停滞状态是没有欢乐的,衰退状态则使人抑郁的。”[7]
由此可见,斯密的这种理念隐含“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含义。斯密强调指出:“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7],进而不可能有劳动报酬的提高、广大工人的富裕。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让公众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在《国富论》问世后的200多年中,欧美国家和地区在某些时期,基本上解决了斯密给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提出的“人民富裕”“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7]的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有数据显示,从1975年到1998年,在这20多年间,尽管出现了所谓的“幸福悖论”,但美国收入排名最后1/4的人,其中非常幸福的和相当幸福者仍然高达69%,不太幸福的人占31%。据此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再如,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或者曾经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世人与学术界也公认他们的幸福指数比较高。而斯密也曾经批评大富翁,看好中产阶层。学术界认为: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表明已实现了共同富裕。正是因为这个理论,我国把实现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于中产阶层,即中等收入群体。为此,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第十二次会议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9]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案。更有学者设想,如果把刚脱贫的一亿农村人口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将又创造一个共同富裕的奇迹。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斯密不仅提出而且倡导共同富裕理论。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斯密的共同富裕理论,不妨把共同富裕分为低级与高级两种类型,斯密所构想的共同富裕,属于前一种,是低级共同富裕。我们这样看待斯密所说的共同富裕,也合符他的思想。低级共同富裕概念是受斯密的有关论述启迪,由他的这个观念衍生出来的。在斯密看来,人的美德可以分为低级与高级两种,前者是指希腊式的感情——爱、友谊和感激之情,也就是利他的品德;后者是斯密在批判哈奇森的美德理论不承认自爱,即自私自利“好歹是一种能促成具有美德行为的动机”[6]。斯密批评说,这是由于“它没有充分解释我们对谨慎、警惕、慎重、自我克制、坚持不懈、坚定不移等较低级的美德的赞同从何而起”[6]。这是指哈奇森未能理解,斯密之所以把自私、自爱的品德情感也视为一种美德,是由于它们借助“看不见的手”能更好地增加公众利益。当然,较之前者,它只是一种“低级的美德”。这样,在斯密学说中实际存在两种社会,一种是由高级美德维系的社会,另一种是由低级美德维系的社会。关于后一种社会,“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6]这就是斯密倡导的低级共同富裕,它是依靠人的利己之心这种“低级的美德”实现的。
四、结论与建议
1.斯密提出并倡导共同富裕
他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旨在解决“如何使人民富裕起来这个问题”,他不满足于少数人富裕。之所以提出并倡导共同富裕,这与他的学术出身、学术立场有重要关系。他首先是研究道德哲学,而这是一门以幸福为主要内容和目的学问,这使斯密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样,也是一个志在探索人类幸福的人。在斯密的两本著作中,多达几十次提及“公众幸福”“社会幸福”。正是为了让公众得以幸福生活,斯密进而提出并倡导共同富裕。这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公众幸福。
2.斯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不单属于哪一个阶级,而是所有阶级、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国家”。据此,柏拉图可以算是一个公众的、人民的思想家、哲学家。斯密也是这样的学者。斯密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旨在探索“增加公众幸福的办法”,让人民富裕,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斯密站在人民的立场,公开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为此,他提出并倡导共同富裕,旨在把公众幸福作为他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并尖锐地揭露和批评有产阶级“在许多场合他们既欺骗了公众,又压迫了公众”的不良品德和剥削行为。
3.从共同富裕角度研究有助于更全面了解斯密的观点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以它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的道德哲学和经济学说。共同富裕、公众幸福是斯密“学说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归宿和目的所在。在斯密的心目中,所谓的“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只是实现共同富裕、公众幸福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斯密也信奉“发展是硬道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劳动者才能过上富裕与幸福的生活。而要使生产快速发展,财富不断增长,需要依靠自利自爱的“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其他学者完全否定人的自私自利的品质情感时,他却为之辩护,将其称之为“低级的美德”。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个市场竞争的形象说法,其实就是把市场体制视为发展生产的一种有效方法,而不是基本的社会制度。
4.共同富裕可分为低级与高级两种类型
斯密虽然与众不同,把“经济人”的自利自爱也视为一种美德,但只是“低级的美德”。依靠这种“低级的美德”所维系的社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共同富裕是有局限性的,程度水平也是低级的。因为在以自利的“经济人”为主体,以“看不见的手”,即自由市场体制机制为工具的经济形式中,必然存在对共同富裕不利的一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以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也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人民至上,力求社会和谐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同时正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和健康中国。但是,学术界有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共同富裕视为低级共同富裕。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我们虽然倡导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是意味着同等程度的富裕;不意味着生活水平差距越小越好。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的不断增长,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共同富裕的程度将会不断提高,这一切将使低级共同富裕逐步提升到高级共同富裕。
5.西方主流经济学应当回到斯密那里去,进行幸福化改革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费尔巴哈,都明确指出: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斯密的伦理学、经济学秉承幸福终极目的论,矢志追求公众幸福、社会幸福。而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者自称是斯密经济学说的传人,既如此,他们就应当回到斯密那里去,把公众幸福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对现有的以物质财富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经济学进行幸福化改革。不言而喻,对当今的主流经济学进行幸福化改革,有利于实现并巩固共同富裕这个斯密所追求的目标。为此,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应牢记斯密这一金玉良言:“任何改善大部分人生活条件的东西都绝不能视作对整体的一个不利。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贫穷而悲惨的,那么这个社会绝不可能繁荣和幸福。”[3]
总之,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因此,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我国实行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改革,肯定“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实际价值。这就实际破除了斯密完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须知,这两个传统观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明白这个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斯密共同富裕的理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4-01-18(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
[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6.
[6][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8.
[8]陈湘舸,王艺.论经济学的“幸福革命”[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1):32-36.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4.
〔责任编辑:孙玉婷,于海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