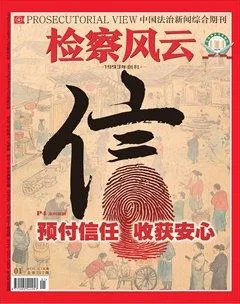唐代法制中的诚信文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华夏大地备受尊崇的一种价值观念,诚信对古代法制产生了深刻影响。李唐时期,中华法系步入巅峰。翻开唐代法典,不论是价值导向层面的定分止争,还是处理方式层面的轻重缓急,诚信对法律的影响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唐代立法者围绕诚信设计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又促使诚信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二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今人常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在古人看来,法律实施能否成功,要诀就在“诚信”二字。唐朝的经验表明,诚信是法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定理,是决定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立法中的诚信
早在先秦时期,诚信就受到了诸子百家的推崇。以对后世法律影响最大的儒、法两家为例,孔子、孟子、韩非子、商鞅等人,都对诚信有过经典论述。孔子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以说是儒家对诚信内涵的最佳注解。《商君书·修权》有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可见其对诚信的看重。西汉以后,儒学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诚信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融入了法律活动的每个角落。
以唐代为例,在与今天法律相对应的刑事、民事、行政等领域,《唐律疏议》中皆有与诚信相关的法律条款。比如,诬告是典型的不诚信犯罪行为,《唐律疏议》共有四条法律专门规制诬告罪。在“律疏”部分,立法者用了较大篇幅来对这些规定进行立法解释,并且列举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帮助人们理解和运用法律。
在“诬告反坐”条中,《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指官,挟私弹不实者,亦如之。若告二罪以上重事实,及数事等,但一事实,除其罪;重事虚,反其所剩。”这条规定的前一句不难理解,但后面部分就显得晦涩,容易产生歧义。长孙无忌等人在撰写“律疏”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律疏”部分特意用案例进行解释,让读者一目了然。“律疏”规定:“假有甲,告乙殴人折一齿,合徒一年;又告人盗绢五匹,亦合徒一年;或故杀他人马一匹,合徒一年半。推杀马是实,殴、盗是虚,是名‘告二罪以上重事实’。又有丙,告丁三事,各徒一年,此名‘数事等’。”简而言之,上述情况只要有一项重罪告发是实,那么告发者就可以免罪;如结果证明轻罪是实,重罪是虚,那么诬告者就要被判处两罪之间的差额刑罚。“疏议”部分再次用盗绢与杀马的案件举例,说明如果事后证明杀马是虚,盗绢是实,诬告者要处以半年徒刑。
就现有史料来看,诬告反坐的条款确实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比如唐宪宗时期,信州将领韦岳揭发上司信州刺史李位“结聚术士,以图不轨”,于是皇帝下令把李位押解赴京,关押在宫中。尚书左丞孔戣是孔子三十八代孙,为官公正刚直。他劝谏皇帝此案应依法交由司法机关审理,不能在宫中审讯——“刺史得罪,合归法司按问,不合劾于内仗”。唐宪宗接受了建议,把案件移交御史台处理。经过孔戣等人三司会审,查清了李位只是“好黄老道,时修斋箓,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别无逆状”,于是依照《唐律疏议》相关规定,判处韦岳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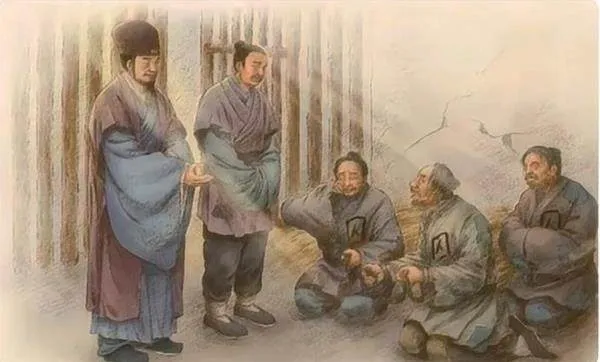
除了诬告犯罪,《唐律疏议》中对诚信的规定还有很多。比如在“十恶”中有“不孝”罪,其中一项内容就是“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去世后,官员必须丁忧三年。一些人贪恋官位权势,生活荒淫,隐匿丧情不报,要受到严厉处罚,比如“匿父母及夫等丧”条规定:“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官员治理地方,更要讲求诚信,特别是遇到水旱灾害,必须如实上报,以及时减轻百姓负担。如果官员隐匿或妄报灾情,将面临严厉处罚,如《唐律疏议·户婚律》“不言及妄言部内旱涝霜虫”条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若致枉有所征免,赃重者,坐赃论。”
在民事方面,《唐律疏议》也有许多关于诚信的内容。比如,婚姻上,《唐律疏议·户婚律》“许嫁女辄悔”条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若男家自悔者,无罪,娉财不追”。与此同时,法律严禁冒名顶替骗婚。“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
执法中的诚信
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这句话既是对诸葛亮依法治蜀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中华法系诚信执法的精妙概括。隋末大乱,失信毁法是隋炀帝杨广身死国灭的重要原因。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君臣深鉴隋朝亡国之教训,十分重视诚信执法。
天下初定后,唐高祖李渊下令大赦天下,不再追究隋末其他割据势力将士的罪责。不久,李渊又下令处罚这些将领,把他们流放到边远恶地。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大臣孙伏伽进谏道:“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断当,许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后,即便无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为取则?若欲仔细推寻,逆城之内,人谁无罪?……今四方既定,设法须与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为无信,欲遣兆人若为信畏?”孙伏伽此奏深受李渊重视,不但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为唐初政局之稳定贡献良多。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广施仁政,愈发重视诚信对法律实施的重要意义。贞观六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录囚。当时监狱里关押着二百九十余名死囚,为了感化这些囚犯,唐太宗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将其全部释放回家,使其暂与家人团聚,约定明年秋天再回京行刑。到了第二年秋天,这些囚犯全部返回京城。李世民非常高兴,认为这些囚犯能够诚实守信,意味着可以教育感化,应当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下令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
在中国法律史上,唐太宗释放死囚是个著名事件,但后世对唐太宗此举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在批评者看来,唐太宗此举“作秀”意味浓厚,是典型的毁法纵囚之举,北宋大家欧阳修甚至为此专门写过一篇《纵囚论》,批评唐太宗的做法不足为后世所取。依理而论,批评者的论据不无道理,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代雄主,李世民恐怕也没必要单纯为了这一点“虚荣”,就贸然行此“毁法”之举。他之所以这样做,亦应有其道理。单纯就法律实践而言,赦免死罪并不意味着直接无罪释放,而往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只是史书记载简略,没有提供更多后续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年后颁行的《贞观律》中,唐太宗把大量死刑罪名改为“加役流”。这场修法争论自太宗即位之初就开始,贞观六年太宗释放囚徒之时,许多死囚所犯的罪责可能本就不在太宗心中的应死之列。为李唐王朝树立诚信的法律观,或许才是李世民之本意。
贞观年间,青州发生叛乱,官府抓捕了大量囚犯关在监狱,朝廷派崔仁师前往处理。史载仁师至州后,“悉去杻械,仍与饮食汤沐以宽慰之,唯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原免”。案件上报朝廷后,连大理少卿孙伏伽都觉得此举不妥。他劝崔仁师道:“此狱徒侣极众,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谁肯让死?今既临命,恐未甘心,深为足下忧也。”崔仁师回答道:“岂有求身之安,知枉不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愿也。”后来朝廷派人到青州复查此案。“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无枉滥,请伏罪。’”无独有偶,中唐时期,元德秀任鲁山令,当地饱受老虎之害。有个关押在监狱的囚犯听说这件事后,主动请缨去捉老虎赎罪。元德秀仔细考虑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有人劝元德秀道:“彼诡计,且亡去,无乃为累乎?”元德秀答道:“许之矣,不可负约。即有累,吾当坐,不及余人。”第二天,这名囚犯果然扛着老虎的尸体回来,赢得全县赞叹。从这些案例来看,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编辑:张钰梅""zhangclaire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