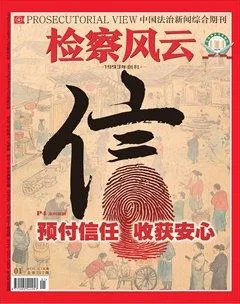完善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体系

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和检察公益诉讼法制定的过程中,应重新审视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已有立法、司法解释和司法经验为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格局上,完善作为我国内生制度的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体系。
贯彻风险预防原则
检察生态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针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提起的公益诉讼制度,应当注意与生态环境领域实体法规定的衔接。
风险预防原则是生态环境法中最独特也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生态环境法制中重要一环的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自然应明确贯彻这一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包括检察机关),对于“不及时制止将使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在提起诉讼前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禁止令,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小时内裁定是否准予。可见,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法治领域内的风险预防原则。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一条已经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有权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
然而,检察公益诉讼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没有将“具有重大损害风险”的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在有关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司法部建议删除“具有重大损害风险”相关规定,理由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都没有关于“具有重大损害风险”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在《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基于风险预防原则,对于人民检察院就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人民检察院及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行政监管消除风险。
前述两份司法解释规定不同的原因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专门针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件,自然应当贯彻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而检察公益诉讼的有关司法解释所规范的类型则较为全面,除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类案件之外,还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案件,对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覆盖的全部案件而言,确实不是所有类型的案件都适合适用风险预防原则。
从实践层面来看,无论是检察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行政公益诉讼,都主要是对已经产生现实危害的行为提起的损害赔偿或执法诉讼。
在相关立法中,可以考虑根据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原理、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及实践中已有案例的经验,增加预防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
第一种考虑是,分别在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检察公益诉讼的有关司法解释已经规定的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明确增加预防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规范内容,主要是在受案范围中增加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重大风险的类型。
另一种考虑则是,根据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原理,将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单独规定为一个独立于所有其他公益诉讼的类型,未来作为检察公益诉讼法中的独立一章予以规定。生态环境公益的实质是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生态环境公益是生态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利益与传统人类社会中的公共利益存在较大区别,这是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单独规定为一章的理论基础。
当然,无论是哪种考虑,都需要与为未来生态环境法典中有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相衔接。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
除了检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外,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也已积累了大量经验。
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没有直接规定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通过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9号)明确检察机关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法院一并审理,但实践中此种尚未法定化的诉讼类型仍不多见。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一并解决民事争议案件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素: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该行政争议与相关民事争议相关联;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必须有一争议是另一争议的先决或前提条件;当事人一致同意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一并审理。
在现有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及其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建立正式的检察生态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学界已经展开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国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主要是由行政机关分领域履行保护职责,分领域的专业分工使得这种保护机制在技术上较有效率。而行政机关作为管理者,引入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其履职行为是自然而合理的制度安排。不过,法律监督机关可能并不如行政机关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管理事项有专业化的理解。以国家司法权威作为后盾,除了增强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有效性之外,还可以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让监督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情况不至于影响行政机关正常履行职能。
当然,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在诉前程序、管辖、诉讼请求、举证责任、和解调解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加之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在证据审查标准、起诉期限和时效、上诉程序等方面本就存在一定的差异,将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一并审理,需要解决一系列因两类案件程序差异导致的实践操作问题,对这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的确需要在传统诉讼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考虑。
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体系之探
检察公益诉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制度,检察机关的职能根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环境不断演化。
在检察生态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中,固然需要考虑诉讼基于司法特性而具有的一般特征,从比较法上借鉴已有诉讼理论和吸收成熟司法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从我国的国家社会具体结构、生态环境治理经验和检察职能合理分配的现实出发,并考虑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重要性,在现有规范和经验上完善检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体系。
这一体系应以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为主体,辅之以预防性和损害赔偿性的民事公益诉讼;考虑到诉讼效率、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和生态环境诉讼的特殊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诉讼工具箱内的备选工具也应予以细化规定,以便在满足法定条件下选择适用。
(学术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编辑:张宏羽""zhanghongyuch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