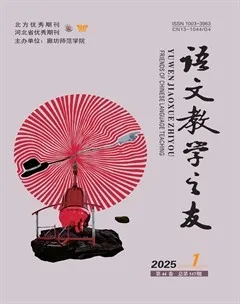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新证
摘要: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历来有歧义,而“小山”则为争论焦点。从“蛾眉”的习惯方法和该词的整体逻辑来看,“山眉说”似更为合理。“金明灭”则指女主人公额头、眉间的花黄或花钿在其辗转反侧时的明灭闪烁。据此可知,这首词所写乃女主人公昼寝初醒时的慵懒情态,其缘由则在于新婚丈夫的远离。炫才自鬻或许才是作者创作该词及《菩萨蛮》组词的主要动机。
关键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山眉;昼寝;炫才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963(2025)01-0022-03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文学史上流播甚广、争议不断的名篇,而“小山”一词又是争论的焦点。如若将该词的关键词语放在古代美女文学的书写传统中加以互文性考查的话,会对某些争议性或模糊性问题作出更为明确、合理的阐释和论证。笔者试从不同角度客观还原该词的故事背景和抒情逻辑,以期为中学生的诗词解读提供积极的思路启发与方法借鉴。
一、“小山”为女子秀眉之意的互文性论证
关于“小山”之意,流行的是“屏山说”和“山眉说”。从关键词语的习惯表达和该词的整体逻辑来看,“山眉说”似乎更合理。
首先,“屏山说”否定“小山”为眉形的一个重要论证,即下文“画蛾眉”有前后重复之嫌。黄天骥认为:“这词的第三句,已说明她准备画的是‘蛾眉’,第一句却说是‘小山眉’,岂不是互相矛盾?”众所周知,“蛾眉”最早见于《诗经》:“螓首蛾眉”(《卫风·硕人》),又作“娥眉”,原指女性细长如蛾须的美丽眉形。晚清侠邪小说《花月痕》第二十一回“宴中秋觞开彤云阁销良夜笛弄芙蓉洲”中主人公韦痴珠对古人画眉的前后类型和具体眉形有过详细介绍:
痴珠道:“一件画眉。《诗》‘子之清扬。’清,指目;扬,指眉。又‘螓首蛾眉。’言美人的眉,此为最古,却是天然修眉,不是画的。其次屈原《大招》‘蛾眉曼只’,宋玉《招魂赋》‘蛾眉曼睩’。曼,训泽,或者是画。后来文君远山,绛仙秀色、京兆眉目、莹姊眉癖,全然是画出来。唐明皇十眉图,横云、斜月,皆其名。五代宫中画眉,一曰开元御爱,二曰小山,三曰五岳,四曰三峰,五曰垂珠,六曰月棱,七曰粉梢,八曰涵烟,九曰拂云,十曰倒晕。”
在画眉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诗经》的经典地位和深远影响,“蛾眉”一词遂以借代形式成为女子美貌或美女的常见称谓。如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长恨歌》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等。
与此同时,“蛾眉”也由最初的一种特殊眉形而逐渐抽象为代指美女的秀眉。西晋傅玄的《艳歌行·有女篇》中“蛾眉分翠羽,明眸发清扬”之言,开始以翠鸟羽毛形容女子的“蛾眉”,陆机将傅玄两句诗加以点化:“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日出东南隅行》《玉台新咏》作《艳歌行》)而明清小说所受之直接影响,历历可见,如:
蛾眉横翠,粉面生香。(《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
蛾眉分翠羽,凤眼列秋波。(《续西游记》第一回“灵虚子投师学法"到彼僧接引归真”)
蛾眉横翠黛,粉脸映红桃。(《东度记》第三十六回“神女化妇试真僧"冤孽逢魔谋报怨”)
于是,“画蛾眉”“淡扫蛾眉”等表述作为女性修眉自饰的泛指,屡见于文人笔下,不赘。
当然,“蛾眉”作为美女秀眉的代称,本身就暗含着眉毛细长且呈弯曲之状的意义指向。因此,古人常将“蛾眉”与“春山”“远山”“月”等作比拟,如:
云鬓轻梳蝉倚,蛾眉巧画春山。(《清平山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浅画娥眉新样、远山长。(邓肃《南歌子·四之三》)
通过对此文学背景和书写传统的梳理可知,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开篇的“小山”,不仅可直接理解为主人公所画之“小山眉”即“远山眉”的略称,甚至也可以简单解释为其眉如“小山”之形状;而且,与后文“画蛾眉”本无冲突、重复之弊。
其次,从词的叙述逻辑和整体内容看,“小山”所指当非小山屏。因为,该词主要围绕女主人公的容貌、梳妆和服饰进行描摹,即以刻画女主人公孤寂自赏的闺怨形象为主,所以,如果将首句中“小山”定义为屏山,则与该词整体的叙述风格和情感基调略不符。
相反,若将“小山”解释为“小山眉”的略称,或眉如“小山”之形状,则可以保证全文内容的统一性和逻辑的流畅性。而“小山重叠”形容的自然就是女主人公眉头紧锁的哀怨情态。由于“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深远影响,古人在描写美女忧愁烦闷之时往往会关注其眉头紧皱的表情细节,常见的说法有“颦眉”“攒眉”“蹙额”或直接曰“蹙蛾眉”,为人所熟悉者有李白《怨情》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以及《红楼梦》中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的“颦颦”之态。其中,又多以山为喻刻画女子颦眉蹙额的哀怨,如:
云鬟乱,晚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李煜《捣练子令·云鬟乱》)
远山相对一眉愁。(贺铸《浪淘沙·四之四》)
甚至有径称“眉山”“眉峰”者,略举名篇为例,如欧阳修《踏莎行·雨霁风光》:“蓦然旧事上心来,无言敛皱眉山翠。”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可见,温庭筠借“小山重叠”来活化眉头紧锁、心绪不宁的女主人自是古代美女文学的书写传统使然。
二、关于女主人公昼寝初醒的情态推断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聚焦女主人公一夜辗转难眠后清晨醒来的慵懒状态,似乎是一种无需深究的共识。但在笔者看来,昼寝初醒才是主人公当时的真正状态。
首先,既然确定了“小山重叠”为女子眉头紧锁之貌,那么“金明灭”自然就非指屏风上所绘之山水,而是女子额头脸颊上的“额黄”或“花钿”明暗闪烁。“额黄妆”作为古代女子特有的妆容,有两种方式:一是染画法,用黄色颜料染画在额头,又称“鹅黄”“鸭黄”;二是粘贴法,用金黄色的纸裁剪成各种图案,粘贴在额头眉间等处,或称“花黄”,《木兰辞》中“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即是。“花钿”一般认为是由花黄演变而来,用金、银、珠、翠等材料加工成薄片,剪成花鸟等图式,粘贴于眉心额头。
至于《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的“金”究竟是额黄,还是花钿,或者具体图案是由颜料涂抹而成,还是由裁剪而来,难以细分。因为在温庭筠笔下两种妆容均有题咏。
蕊黄无限当山额。(《菩萨蛮·蕊黄无限当山额》)
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南歌子·脸上金霞细》)
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南歌子·扑蕊添黄子》)
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归国遥·双脸》)
然而,“金明灭”形容的是女子脸颊、额头或眉间或涂或贴的金黄图案在阳光映射下的明暗变化,则毋庸置疑。
至此,我们须指出一个简单的生活真相,即古今女子在夜晚入睡之前都需要卸妆。如李清照《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中有:“夜来沉醉卸妆迟。”明清小说对女性这一睡前的常规动作多有提及,不赘。而卸妆自然就包括清洗额黄或卸除花钿。比如,唐人小说《续幽怪录·定婚店》中写士子韦固为新婚妻子“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的奇怪举动而疑惑。显然,夜间睡眠必属于所谓的“闲处”范畴。于此反观温庭筠笔下的女主人公,既然妆容未卸,那么她此刻应是白昼卧床。
其次,古代文人在刻画孤寂苦闷的闺怨形象时,除了借助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加以突显外,还时常观照其在闺房内百无聊赖、了无意趣的昼寝情形。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摹写成仙的杨玉环在午睡时被临邛道士的到访所惊醒:“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一折中莺莺自见张生后心绪不佳,红娘提议稍作午休:“(红云)姐姐情思不快,我将被儿薰得香香的,睡些儿。”《牡丹亭》第十出《惊梦》写“春情难遣”的杜丽娘游园后“身子困乏了,且自隐几而眠”。可见,昼寝一般是不需要卸妆的。与《长恨歌》一样,多首宋词作品更是明确描写了闺阁女子因愁怀满腹而致使昼寝不宁,尤其颦眉蹙额、钗钿横坠的细节。比如:“炉香昼永龙烟白。……睡容初起枕痕圆。坠花钿。”(欧阳修《虞美人·炉香昼永龙烟白》)“日长花片落,睡起眉山斗。”(赵闻礼《千秋岁·莺啼晴昼》)
于此可看出,相较于夜眠,昼寝因其“非时”特征,更有利于突显和皴染闺怨女性的愁苦郁结。如此一来,以昼寝写女儿的多情品格和愁怨心境自是为人所瞩目,比如《红楼梦》第二十六回用互文性手法将黛玉的“春困发幽情”与《西厢记》的有关情节相联系,建构一种情意缠绵、惝恍迷离的诗的意境。
综合看来,温庭筠正是着意通过昼寝初醒这一生活片段对闺怨女性进行追踪蹑迹、绘形摄神的描画和雕琢。开篇直接点明女主人公辗转反侧间眉头紧锁、花钿(或花黄)闪烁,及鬓发散乱的娇憨模样;且本身也暗示出她白日不能静心守志、专注女红,反而情思涌动、昏然欲睡的焦躁心态。接着写其昼寝初醒之时无精打采、懒于梳妆的倦怠,过渡到对女主人公如此情态的内因解释上。在“德言容功”的妇教下,虽然“懒起”却不得不“画蛾眉”,即使“迟”缓也毕竟“弄妆梳洗”一番。同时,又从“女为悦己者容”的角度提醒读者,女主人公的苦闷源自情人的离别或摽梅之年未遇良人,是对开篇两句的初步回应;而梳妆完毕后的“照花前后镜”环节,自然隐含了其孤芳自赏的无奈意味。尾句的新帖之“双双金鹧鸪”则明确了女子新婚少妇的身份,最终揭示出其之所以昼寝及醒后慵懒的真正原因,即丈夫的远别而带来的“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时”(简文帝《梅花赋》)的忧虑与哀伤。
总之,我们将《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放在古代美女文学的书写传统中加以互文性观照和辨析,则发现“蛾眉”乃古人表示美女秀眉的惯用称谓,“小山重叠”也是古代形容女性皱眉的习见表述。据此可推知女主人公当时所展现的正是昼寝初醒而非夜眠初醒的慵懒情态,凸显了她在良人远游、独守空房的孤寂落寞中自赏自恋而又自伤自怜,所谓“恐美人之迟暮”的典型心态。
至于《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有无“悲士不遇”的寄托,则是又一个争议性话题。从“香草美人”的角度看,所谓“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的说法似颇有说服力。但结合温庭筠别号“温八叉”的绝世才情和恃才傲物的性格来看,他似乎又不屑做此发愤乞怜之态。又据《唐才子传》和《北梦琐言》可知,《菩萨蛮》组词是温庭筠所撰而由宰相令狐绹进献唐宣宗之作,《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断为大中六年(852)前后,正是作者屡试不第之时。因此,温庭筠此时集中精力创作十四首《菩萨蛮》,于其个人主体动机而言,或许只是炫才自鬻、“露才扬己”(班固《离骚序》)而已。
参考文献:
[1]黄天骥.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J].书城,2023:12.
[2](清)魏秀仁著;尚成标点.花月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120.
[3]王绍军.唐代妇女服饰研究[D].武汉大学,2014:146-151.
[4]傅璇宗,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642.
作者简介:王以兴(1986—),男,山东省潍坊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研方向为古代小说及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