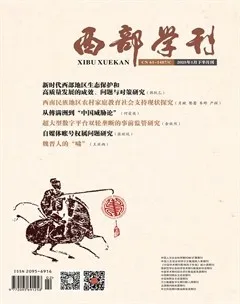魏晋人的“啸”
摘要:“啸”起源于先秦,经两汉至于魏晋,风行一时,为名士高人所好。魏晋人对“啸”的偏爱反映出魏晋时代特殊的精神追求与生命意趣。“啸”之所以为魏晋时人所重是因为,“啸”能传递言不可追的真意,让人逃离俗世的纷扰,将人向“道”之境界提升。对于魏晋士人来说,作为一种隐晦地表达情绪、疏解压力、彰显个性的手段,“啸”能满足士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对于魏晋隐士来说,他们隐退山林、复归自然,“啸”不再是手段,而是本能。
关键词:啸;《世说新语》;言;气
中图分类号:J609.2;K236.1;K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5)02-0081-05
“Xiao” in the Wei-Jin Period
Wang Siyu
(School of Philosophy,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Xiao”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continued through the 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and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Wei-Jin period, becoming a favored activity among celebrities and scholars at that time. The preference of people in the Wei-Jin period for “Xiao” reflected their special spiritual pursuit and life interest. The practice of “Xiao” was valued by the people during the Wei-Jin period because it was believed to convey profound meanings that elude verbal expression, offer an escape from worldly affairs, and lead them to the realm of “Dao”. For the literati of the Wei-Jin period, “Xiao” served as a subtle means of expressing emotions, relieving stress, and showcasing individuality, which met their psychological needs. For the hermits at that time, who returned to nature, “Xiao” had been internalized into their lives.
Keywords: Xiao;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verbal expression; Qi
《世说新语·栖逸》篇中记述了一则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1]560
这段文字虽篇幅短小,但不乏值得考究之处。首先,阮籍拜访苏门真人意在同他交流。起初他像普通人一样,以“言”的方式询问苏门真人,但苏门真人“不应”,拒绝回答。之后,阮籍开始长啸,苏门真人才开口并应之以啸。可见,在经历了语言交流的失败之后,他们通过“啸”联通了彼此的心意,这说明“啸”具有“言”所不具的沟通心灵之作用。其次,从他们的身份来看,阮籍是士族,苏门真人则是隐士。二人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不同,本无法完全地相互理解,但在这里,他们却做到了心意相通。这是因为“啸”具有超越性,能够使他们跨越隔阂彼此联通。最后,阮籍复啸,苏门真人便不再应答;苏门真人再啸,阮籍则难以回应。这说明隐士之啸与士人之啸仍然存在差别,他们虽然能够长啸相和,但不能达到高程度的心意契合。由此生发的问题就是:“啸”是什么?魏晋之“啸”有何特点,为什么能发挥超越语言的作用?苏门真人与阮籍为何达不到心心相印,他们的“啸”有何区别?
一、“啸”之内涵
《说文解字注》解“啸”为:“吹声也。召南笺曰:啸,蹙口而出声也。”[2]121可见“啸”首先是一种声,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蹙口”而作的声。“蹙口”指双唇向前努起,作圆形,以口腔控制气流从舌尖吹出。孙广的《啸旨》中记载了啸的十二种发音方法,每一种都仅是以舌配合唇或齿控制气在口中或含或散。由此可知,啸不同于一般的发声方式,仅靠唇舌配合,以唇为簧,以舌控制气流即可,不需要震动声带以喉发声。
“啸”属于声,自然需满足声的规定。《说文解字注》解释“声”为:“‘音’下曰:声也。二篆为转注。此浑言之也。析言之,则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也。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乐记》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2]1042这说明,声有宫商角徵羽之分,产生于自然。不仅人能发声,草木鱼虫亦可发声。
因而,“啸”也具宫商角徵羽之音调起伏,是人与兽的天然本能。“啸”这种仅来自唇舌的声不仅能为人所发,禽兽亦可为之。与禽兽不同的是,人之“啸”乃是特殊的音乐之声,能产生和乐器相似的效果。日本学者林谦三将“啸”归为“气乐器”,认为“啸”是口腔与唇、舌、指构成的一种笛声[3]。可见,“啸”只借助唇、舌、齿等口腔器官,将气息从腹腔送出并拖长使之曲折变换,形成类似笛的发声方式。范子烨等人认为这种发声方式的特征是,只需要气息在口腔流动就能发声:“蹙口并合圆双唇,将满腔气息从其缝隙间送出,最简单的就是像O或Ho的长音一样将音直线延长。”[4]
无辞之“啸”虽如袁山松所言不能传达复杂的概念和思想,但并非缺乏意义。“啸”的发声方式更原始、更自然,因而它能表达未经人为造作的、本然的心情志意。
先秦两汉时期,“啸”之主体多为女性,表达的是思念、忧伤或愤恨之悲。《诗经·白华》讲:“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诗经·中谷有蓷》讲:“有女仳离,条其歗矣。”朱熹注:“歗,蹙口出声也。悲恨之深,不止于叹矣。”[5]58“歗”古同“啸”。女子在思念或悲怨之时,叹息已然无法缓解她的忧伤和愤恨,只能长啸抒怀。《诗经·江有汜》末章写道:“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5]15讲女子期盼男子归来,但男子屡过家门而不入。女子芳心错付,无人诉说,唯可一声嚎哭。朱熹注:“啸,蹙口出声,以舒愤懑之气。”[5]15说明“啸”表达了此女的怨愤。
魏晋时期,“啸”的主体则不再局限于女子,男子也通过“啸”抒发悲伤之情。《晋书·刘琨传》记载:“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6]1679刘琨在晋阳时被胡人围困,不甘屈服而悲郁万分,于是登楼长啸。闻者皆感其心悲,凄然长叹。这说明,刘琨通过“啸”表达了走投无路的哀伤。《晋书·刘元海传》记载刘元海与王弥送别之时:“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6]2647刘元海与知音故交王弥在洛阳辞别,恐无再见之日,便难掩不舍与无奈,将心中悲郁与离愁别恨发而为“啸”。
此时不仅“啸”的主体有所扩展,“啸”所表达的内容也有所丰富。除了抒发悲情,“啸”还能用以明志。《晋书·石勒载记》写道:“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6]2707石勒十四岁时被带到洛阳,路途中忽发长啸。此时王衍恰巧路过,他从“啸”中听出石勒有戎马天下的壮志,因而视石勒为天下大患。王衍与石勒素未谋面,他之所以能揣测石勒的心志,都是因为“啸”有传情达意的功用。
以上都说明,魏晋时期,“啸”已经不仅仅是女子传情达意的方式;它能传达的也不仅是悲伤情感,还有内容更加复杂的“志”。
二、魏晋之“啸”的境界
作为一种声,“啸”与“言”相同,可以传递信息,搭建交流的桥梁;但“啸”比“言”更自然、更原始。《啸余谱》曰:“人有啸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律有乐,流而为乐府,为词曲,皆其声之余绪也。”[7]可见,“啸”是人最原始的发声方式,甚至是“言”的起源。汉代高士向栩言:“恒读《老子》,状如学道,不好语言,而喜长啸。”[8]都说明“啸”异于“言”。同时,在桓玄看来,“啸”不仅仅与“言”相异,还比“言”更能“致幽旨”。苏门真人对阮籍的“言”无动于衷,却被“啸”打动,这说明“啸”比“言”更契合人的精神,更能传达幽微的情思。“言”仅限于人与人,甚至仅仅是一部分人之间的交流;“啸”却能联通阶级、地位相异的两个人,乃至成为天地神人相互感通的媒介。
“啸”能在魏晋成为超越语言的沟通媒介,与当时的言意之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涉及语言、声音、文字和天道义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众多名士都针对言意关系提出了观点,其中“言不尽意”论与“得意忘言”论盛行一时。这两种观点都认为言与意之间存在断裂,言不能完全表达意。
“言”之局限性首先在于,它出自人为的约定俗成,并非自然本有。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指出:“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9]322语言之产生是为了方便人交流,所以名言不像自然物,并没有实际的、确定的根据。物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指涉,也可以用另一个,究竟采用哪一个全由人所规定。事物没有固定的名称,只是人需要辨别对象、表达思想,才发明了语言,所以对于自然来说,“言”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言”是对象性的。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写道:“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10]198要形成语言,首先需要以主体为中心,把事物作为对象;接着把对象在自身中形成的感觉加以区分,把感觉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名称命名。因此,随着名与称的产生,我与对象之间的界限也就树立了起来。
其三,“言”具有分判性。王弼云:“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10]196语言是以“分”为基础的,只抽取事物的某一个特征、某一个功用,不能兼及全体。语言的这种分判性,必然会遮蔽意义的多样性和完整性。所以本真的义理是不能被言说的,即所谓“至真之极,不可得名”[10]53。
其四,“言”只能触及有形之物。王弼云:“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10]93能够被命名的都是有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不可被命名。而那至真的“意”恰恰是没有特殊性和规定性的“无”。因此,“言”与“意”始终隔着一层。
“言”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故而只落于第二义。王弼云:“大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10]215可见“意”不依赖于“言”,但“言”却依赖于“意”,是“意”的派生物。
“言”无法直接联通“意”,“啸”则不然。“言”由人为规定,“啸”则是自然而然。《啸赋》中称赞啸为“自然之至音”[11]13。钱钟书有注解:“盖啸之音虽必成方、成文,而不借物、假器,故较金石丝竹为‘自然’耳。”[12]“啸”不假借外物,本身就是因循万物的自然性分、消弭是非判别回归自然状态的一种表达方式。《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嘉别传》:“……(桓温)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嘉)答曰:‘渐近自然。’”[1]353“丝”指弦乐,如琴、瑟之类;“竹”指管乐,如笛、箫之类;“肉”指纯粹的人声,即由乐伎口中发出的歌音。桓温感觉到人的歌声之美远胜于丝竹之乐,孟嘉认为这是因为它切近于“自然”。“啸”不必借助丝竹,甚至不必借助肢体,它只是随口发声,因而更加自然。
“啸”亦能规避对象性,因为“啸”之人并不把自身作为主体,他无需发动意识,无需思考、谋划,只是让心志通过气流泻而出。“夫人心志而发乎气,气激于外而发于声。”[11]5“啸”生产自“心志”,“心志”鼓动“气”,发而为“声”。“啸”之所以超越言,是因为“啸”乃是一种直接生发于心的“气”。庄子认为“气”是万物的共同本质,是融通万物的根本元素。只有凭借“气”,人才能恰当地对待万物,不用概念宰制外物,不使主客分立。
“啸”之时,人抛却了分判心,进入与物无对的境界;正如现象学所主张的“悬置”,将直接经验以外的一切事物置入括号,在主客体交融中获得本质意义。《啸旨》言:“我且不竞,物无害者。”[11]1“啸”自能解构“言”加诸存在之上的封与畋,融合到宇宙万物生生化化的洪流之中。如此,啸者就进入了与道冥合的境界,能与自然相融,与万物感通。
“言”无法触及无形之物,“啸”却联通“有”与“无”。王葆玹称“啸”是一种“妙象”[13]。“象”介于“有”与“无”之间。《周易·系辞上》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10]563“几”是易象的语义核心项。王弼解释“几”为“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亲者也”[10]563。可见“几”的特质是若有若无,有无相间。它超越于有形之名与言,直入无之境地。因此,作为“象”的“啸”也具有“无”与“有”的双重特质。
“啸”克服了“言”的限制性,故而能发挥“言”达不到的作用,使苏门真人和阮籍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啸旨》言:“仙君之啸,非止于养道怡神,盖于俗则致雍熙,于时则致太平,于身则道不死,于事则摄百灵,御五云,于万物则各得其所,感应之效,莫近于音,”[11]6这里所说的“仙君”就是指苏门真人。苏门真人的“啸”不为养生,不求长命百岁,而是要达到这种与大道通的境界。当阮籍啸时,他也进入了这种境界,因此能够在与万物融合之时,与苏门真人达到心意相通。
三、士人之啸与隐士之啸
虽说“啸”本不限性别,不分雅俗。但此处所记载的故事却十分特殊,发生在两个男子之间,一位是士族,一位是隐士。起初二人犹如鸡同鸭讲,之后阮籍一声长啸终于引起了苏门真人的注意,获得了回应。阮籍啸而再啸,苏门真人皆是静默而听,最终阮籍自觉无趣,悻悻而去。阮籍走后,苏门真人长啸一声震彻山林,令阮籍自愧不如。这说明士人之啸与隐士之啸既有心志的共通性也有着相异之处。
士人是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出身高贵,享有世代承袭官爵的权利。在司马氏一朝,士族的地位尤为显赫。为与曹氏相抗,司马氏收买士族,优待士人,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和尊荣。刘寔批评:“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6]1192不论贤德与否,士人们都能稳坐在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相应地,司马氏也要求世家大族拱卫其统治,为司马氏马首是瞻。士人们对政治权威不满,却也不敢正面对抗,因为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即便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也要顾惜宗族血亲的安危。比如阮籍,他只有在针对虚拟和泛指的对象时才敢毫不留情地批评指责;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从不臧否人物,生怕祸从口出。《晋书》记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6]1361余嘉锡解释这是因为他们“贪恋禄位”、恐“门户靡托”,担心家族利益受损。所以,面对司马昭联姻的要求,他只能把自己灌醉,消极逃避。士人们如履薄冰、满怀危惧、忧愤深蕴,却怒不敢言,于是只能选择闻之有声、视之无形的“啸”来表达怨刺之意。
同时,“啸”也是他们纾解压力的方式。无可奈何的心口不一始终折磨着士人的内心,在那个政治阴暗压抑的年代,士人们需要一种方式来抒发和宣泄纠结的情绪。酒助人通过热气发散,“啸”则是通过声音发散。南朝墓室壁画的《竹林七贤图》中的阮籍神态怡然,屈右腿伸左腿席地而坐,前方置一瓢樽,樽中酒上浮一小鸭;他左手扶地,身体略向后仰,右手伸大拇指和无名指,其余三指弯曲,大拇指指向口中,一边饮酒,一边吟啸[14]。可见酒与“啸”确可相互搭配。酒是身外之物,所得不由自身,“举杯浇愁愁更愁”,只能让悲愤在心中堆积发酵。啸则是人皆可为,是更加主动直接的抵抗方式,虽然这种抵抗也是迂回曲折,不能被掌权者察觉,却能释放一部分压力。
“啸”也是士人们追求真意,展现自然真性的方式。“啸”在魏晋虽盛行一时,却并非高雅之举,魏晋时期乡野村夫也常常啸歌为乐。魏晋士人多是士族,举手投足皆应儒雅风流,可他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彰显出自身的独立与个性。《世说新语·简傲》记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1]661司马昭炙手可热,坐下宾客都正襟危坐,表现出顺从和恭敬,生怕忤逆他的心意,而阮籍则不愿曲意逢迎,偏要肆意啸歌,旁若无人。“啸”原本就是随意而为,连目不识丁的妇孺都能张口即来,按理难登大雅之堂。阮籍却在朝堂上公然呼啸,甚至踞箕而坐,这与谨言慎行、正襟危坐的朝廷命官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并不高雅的举止,使人深觉缺乏美感,不受尊敬,与地位不符,但它表现的内在气度却是优雅、高尚的。阮籍通过粗俗的举止、言行,反叛扭曲的礼法规矩,正体现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最后,啸是自然之语,能带人进入天地融合的“道”境,士人在其中得以摆脱俗世的束缚,获得自由。这正合于魏晋士人的追求,即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言说方式,把当下的自我改造成另一个超越日常经验的自由个体。郭璞《游仙诗》云:“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15]谢安《与王胡之诗》亦写:“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啸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1]574对于魏晋士人来说,通过“啸”进入超越境界、摆脱世俗才是他们的诉求。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魏晋士人来说,“啸”只是他们在仕途受挫之后自我抚慰的权宜之法。他们并不是真正向往归隐山林,而只是用隐逸体验来补充仕途生活,平衡人生无常之感。“啸”只是他们超越俗世的一种手段与依凭之物。士人们虽与隐士一样,对世俗的污秽不堪厌恶至极,但他们要顾及家族的利益,便不能彻底脱离政治。因而,他们对隐士的生活只能是“心向往之”而不可亲身经历。阮籍听到苏门真人的啸声后,内心震动不已,归去之后便做《大人先生传》。文中描绘了隐士的高蹈脱俗,那是士人们向往而又无法企及的境界。
孙登是魏晋四大隐士之一,其与嵇康也有一段以啸会友的故事:“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1]563这一故事和苏门真人的故事极具相似性,存在混淆的可能。但不论是苏门真人还是孙登,他们的身份都是隐士,他们的“啸”都代表与士人之“啸”不同的隐士之“啸”。
士人们的自由是有待的自由,他们所待的是酒、是药、是“啸”。“啸”是他们反抗传统的手段,但他们也只是隐晦曲折地反抗。他们并不想达到绝对的自由,因为绝对的自由意味着完全击破现有的秩序、背离家族利益,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隐士则追求绝对的自由,他们没有门第牵累,所以能真正地卸下包袱,同鸟兽一样随心所欲地“啸”。
嵇康在《养生论》中也塑造了这种完全复归自然的隐士人格:“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9]231他们感到名利地位于人格有损,于是就隐退山林。在自然中,他们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融合进天地大化中。隐士本已置身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已然获得无待之自由,其“啸”之举动已非是一种助人超越的手段。
四、结束语
从苏门真人和阮籍以“啸”沟通的这段经历能够得知,对于魏晋士人与隐士而言,“啸”能超越约定俗成之“言”,融通天地之道。对于魏晋士人,“啸”是纾解郁结、对抗污秽政局、彰显个性、追求真性的方式,但仍仅仅是通达自由的手段。对于隐士则不同,他们已然不问政事、超离世俗,进入与万物冥合的境界,其“啸”已内化为本能。隐士的“啸”并非为某人而作,不需要倾诉什么,也不需要反对什么,只是自然而然地发声,复返如动物一般的自然状态。因此,隐士之“啸”处于更高的境界,这便是苏门真人使阮籍大受震撼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林谦三.东亚乐器考[M].北京:音乐出版社,1962:327.
[4]泽田瑞穗,颜淑兰,范子烨.“啸”的源流[J].铜仁学院学报,2018(8):21-25,83.
[5]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5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294.
[8]范晔.后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775.
[9]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1657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42.
[13]王葆玹.正始玄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7:336.
[14]罗宗真.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J].文物,1960(Suppl.1):37-42.
[15]王夫之.古诗评选[M].长沙:岳麓书社,2011:710.
作者简介:王丝雨(1998—),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博士,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美学。
(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