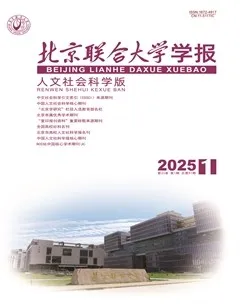中国式司法现代化下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研究
[摘 要] 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背景。当前,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需要明确“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法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的内涵与外延,探明中国式司法现代化应遵循的基本规律,不断提高司法实践中办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应当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理念进行更新,梳理出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面临的主要困境,改变落后的诉讼观念和认识,突破现有司法体制的不合理束缚。目前,我国一步到位地建立刑事诉讼法法典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但应当采用“应修尽修”的修改路径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作出回应。主要包括刑事协商程序的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改革之确认与保障、辩护权的保障与完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构、刑事执行程序的完善、涉外程序的立法补白、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构建、监视居住程序的修改、程序制裁措施的完善、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等方面。
[关键词] 中国式司法现代化;刑事诉讼法;立法修改;重点问题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D9252;D92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5)01-0010-08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国家法治建设的成效与公民权益的保障。近年来,尽管我国在刑事诉讼法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国人大决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新一轮修改的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式司法现代化的基本规律,科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法现代化体系,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探讨中国式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刑事诉讼法学发展时,有必要深入阐述以下三个核心议题。第一,明确“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法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的内涵与外延,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1]第二,认识当前刑事诉讼法存在的问题与困境。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新型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传统刑事诉讼程序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收集与运用不规范、辩护权保障不足、审判效率与公正性难以平衡等问题,也亟待通过修改法律加以解决。此外,涉外刑事案件的增多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国际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深入剖析当前修法与研究的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推进刑事诉讼法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第三,探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关键问题。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需要重点探讨刑事协商程序的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改革、辩护权的完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立、刑事执行程序的优化、涉外程序的研究与立法补白以及涉案财产处置等关键问题,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中国式司法现代化下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理念更新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重大背景。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这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当前亟待深入探究的学术议题,是在中国步入第二个百年历史发展阶段、全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这一宏观背景下,系统考察并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创新路径以及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复杂问题。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进程,其核心研究议题聚焦于三大方面:第一,深入探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之内涵与路径;第二,强调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司法内在规律;第三,聚焦于刑事案件办理的高质效要求,不断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和办理质量。
(一)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
实现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为司法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方向指引,确保了司法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始终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契合。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立场。司法工作需秉承人文主义精神,将人文关怀深植于司法实践之中。三是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如疑罪从轻、慎刑思想,以及少捕慎诉慎押、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理念。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需深入挖掘并传承这些优秀思想,使其在现代司法体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四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中国式司法现代化进程需保持开放姿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在法治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与先进成果,使之与中国特色司法体系相融合,推动司法制度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二)司法现代化要遵循司法规律
在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中,明确并遵循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是至关重要一环。这些基本规律构成了中国式司法现代化路径的独特性与合理性基础。
第一个规律是人类司法工作及司法机关基本职权的发展走向规律。在人类司法工作的发展历程中,第一阶段体现为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尚未明确区分的混沌状态;第二阶段则实现了起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的分离,标志着司法程序开始走向专业化与独立化;到第三阶段,其核心在于确立并贯彻法官中立原则以及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此阶段标志着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与巩固。这一演进趋势构成了司法职权配置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规律,深刻影响着司法现代化的整体进程。诉讼法学要求建立主体论,在任何诉讼进程中,控诉方、辩护方与审判方这三方主体均不容许遭受任何形式的削弱或损害,因为任何一方的削弱都将直接导致诉讼结构的失衡,进而无法构建一个完整、健全且有效的诉讼体系[2]。
第二个规律是人类社会诉讼方法和模式的演进规律。长期以来,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实行的诉讼模式均为压制性诉讼。工业革命之后,诉讼模式由压制性诉讼转变为权利性诉讼。目前,我国的诉讼模式基本符合权利性诉讼模式的特征,即重视司法机关的职权和被告人、被害人、律师及证人的权利。近年来,我国的诉讼模式开始由权利性诉讼逐步地转向协商性诉讼,突出表现为认罪认罚协商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尽管目前仍有律师、司法机关对认罪认罚协商制度存在异议,但诉讼模式从对抗走向协商[3],是司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也是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现代化必须遵守的第二个规律。
第三个规律是科学、民主和文明的规律。1978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诞生,这部法律的主题为拨乱反正、有法可依。待到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出台时,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提出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而这一诉讼原则早已被世界各国所适用。我国在修法之时,对于如何将无罪推定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就形成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无罪推定原则成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成果。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典。随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2018年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法典中。这些基础性原则与制度内在地蕴含着科学、民主与文明的核心价值,显著地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进步与发展。综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轨迹可以总结为六个字——科学、民主、文明[4]。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方向。
(三)高质效办案
办理刑事案件必须坚持高质效。中国式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工作不断地提高办案质量,满足群众的要求,使人民群众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进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高质效办案要坚持三个善于:第一,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的法律关系。第二,善于从具体的法律条文的适用中深刻地领悟发生的事实。第三,善于在法律有机的土壤上实现公平正义。处理刑事案件的核心目标在于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损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对人权保障与人文关怀的尊重。然而,我国当前在人权保障领域尚存不足,具体表现为“连坐式”犯罪记录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即个体犯罪行为对家庭成员乃至更广泛社会关系带来的不当影响依旧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共有24部行政法规直接或间接关联犯罪记录事项,其覆盖范围之广,甚至扩展至物业管理等日常生活领域。
鉴于此,构建并推行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度性安排,逐步消除不合理的社会排斥与歧视,促进犯罪者及其家庭的社会回归与再融入。同时,这一制度的建立也是对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体现了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亦不忘关怀个体权益与社会公正。
总之,刑事司法实践应秉持科学、民主与文明的原则,不仅在案件处理上追求公正与效率,更需在法律适用中展现出法律的温情与人文关怀,确保法律的实施既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又能充分保障人权,真正实现法律的温度与社会正义的和谐统一。
最后,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兼顾天理、法理以及情理的要求,确保裁决既符合法律精神,又顺应社会伦理与公众情感。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案件也是如此。每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性,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应当把法理、天理、情理结合起来,既要坚持整体裁判原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遵守案件的一般规律,也要考虑个案情形,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及其立法建议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前提
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深刻议题时,需要明确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探索科学合理的修改路径与方法。
1.刑事诉讼法修改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面临以下困境:第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受制于人们的诉讼理念和诉讼认识。一方面,我国以侦查为中心、以起诉为主导的诉讼体制阻碍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的贯彻和实施,导致现有的部分审判中的问题和司法问题无法解决。需要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及司法理念等多个层面入手,进一步化解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理念、以起诉为主导的诉讼体制与以审判为中心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实体意识高于程序意识、诉讼观念和行政观念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晰的问题。以往,我国常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诉讼问题,但这种做法违背了诉讼的本质要求。诉讼观念问题的解决,是我国诉讼法学研究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大环节。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观念不改变,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和修改就无法向前迈进。此外,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还存在辩护主体意识不强的问题。律师行使辩护权的保障和完善受制于被追诉人的诉讼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个诉讼的主体,本应具有辩护权等基本的诉讼权利,但在实践中辩护权的保障和完善也面临重重阻碍。
第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受制于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制度性的影响。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国出现了纪检监督与法律监督相冲突的问题[5]。纪检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都是宪法规定的监督,但两种监督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此外,就留置这一法定强制措施的实施现状而言,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频繁出现违规延长留置期限的现象,而在此过程中,既缺乏律师的有效参与,也未见检察机关的及时介入与监督。因此,当前亟须探讨并构建一套完善的解决机制,确保留置措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保障被留置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颇具争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可以被称为特殊的侦查。因此,强制措施的衔接问题和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成为此次刑事讼诉法修改的重点问题。在诉讼程序衔接问题上,应当确保证据适用与审判程序的适用保持一致。亦即,调查中的案件,证据标准的要求要和审判保持一致。同时,在要求移送材料时,应当将录音录像、侦查审问调查询问过程全部移送。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突破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面临的困境,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的旧的诉讼观念和做法。
2.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路径与方法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途径和方法上[6],有观点主张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要将刑事诉讼法法典化,实现一步到位[7]。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证据法典和电子证据法典,刑事诉讼法也仅有粗糙的三百多条,因此一步到位建立刑事诉讼法典的条件并不成熟。还有观点主张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顺应数字时代和全球竞合,并基于科学、民主的“小改”或“微改”[8]。然而,“小改”或“微改”的策略难以突破当前刑事诉讼法修订所面临的瓶颈,因此,有必要摒弃长期以来秉持的刑事法律修订“宜粗不宜细”的传统方法,转而采取一种全面且详尽的修订路径,即“应修尽修”的策略,确保我国刑事诉讼法能够与时俱进,有效应对新兴犯罪形态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重点应当是诉讼程序的建构。当前,我国的刑事犯罪状况、犯罪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的权威数据,均有力印证了“双八十”现象的存在,即超过八成的刑事案件涉及轻罪范畴,且八成以上的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法治进程中犯罪结构的轻刑化趋势及司法认罪机制的成效。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持续深化,司法领域面临的挑战亦日益复杂,其中,“案多人少”的矛盾尤为突出,成为制约司法效率与公正的重要瓶颈。在这种背景下,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需要重点探讨以下问题。
1.刑事协商程序的构建
在刑事案件中应当构建刑事协商程序。在协商程序的具体运作层面,诸如参与协商的方式、程序设计的严谨性、协商内容的界定以及协商成果的终局性等方面,是否应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规范,是关乎协商程序正当性与有效性的核心问题[9]。此外,协商程序是否应践行轻罪案件的实质化处理原则,亦需深入探究[10]。至于刑事协商程序的构建路径,特别是其内含的出罪机制设计,如不起诉决定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安排等,均需我们细致考量其理论基础、实践效果及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初步确立了和解程序,为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学界也有观点主张应当构建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将认罪协商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为轻罪案件,并对相关程序规则归纳整合,安放于“特别程序”一编[11],但现有的和解程序以及相关学术观点相较于全面、系统的刑事协商程序而言,尚存显著差距。未来应聚焦于协商主体的广泛性、协商过程的规范性、协商结果的确定性以及出罪机制的合理性等方面[12],持续推动刑事协商程序的建构与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
2.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改革之确认与保障
在探讨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改革时,需要明确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矛盾,前者是对程序正义与司法原则要求的积极回应,后者则着重于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设计[13]。以审判为中心制度的改革需要聚焦以下问题。一是解决庭审实质化在重罪与轻罪案件中的实现问题[14],特别是针对认罪认罚案件,其庭审是否应达到实质化标准,以及在此过程中律师参与的程度与角色定位,均需刑事诉讼法予以明确界定。对于认罪认罚后于庭审阶段出现翻供的情形,如何有效实现从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向注重庭审实质化的重罪审理程序之转换,同样是刑事诉讼法亟须规范的关键议题。
二是要解决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供述的真实性,以及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是否有告知被告人的权利及认罪认罚后的法律后果的问题。认罪认罚的案件,也应当进行庭审实质化[15]。但此类案件的重点和一般的重罪案件以及其他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实质化要解决自愿性的问题,即被告人在哪一天、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交代的问题。
当前,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需要理清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具体而言:一是在重罪案件的庭审实质化中,要建立和完善质证规则和程序[16]。二是如何在翻案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恢复普通程序。三是认罪认罚的案件实行庭审实质化的标准和内容。
3.辩护权的保障与完善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存在控辩审三方失衡的问题,诉讼中剥夺辩护人和被告人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诉讼过程中的权利剥夺问题、辩护人如何参加刑事和解程序问题、辩护的方法和内容以及辩护权利的保障问题共同构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领域。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辩护律师的法律定位发生了转变;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不断提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日趋扩大;辩护律师权益的保障机制不断健全;辩护律师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17]。但是,在进步之余,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依然面临五大现实难题:一是辩护制度的功能定位受制于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的局限性;二是律师辩护权的扩展受制于被追诉人的地位;三是法官的中立性不足影响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实现;四是被追诉人的法律帮助权尚未得到及时、全面的保障;五是有效辩护受制于律师资源的供给能力。最后,应当明确区分辩护效果与有效辩护制度这两个概念,我国目前在规范层面上尚未建立完善的有效辩护制度。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重点关注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体而言:一是应当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确保庭审实质化的实现;二是正确理解值班律师的地位和职责;三是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三大作用,特别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四是积极创造条件,适时将律师辩护引入职务犯罪的调查程序;五是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改革[18];六是加强刑辩律师基本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提升刑辩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4.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构
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订过程中,应当审慎考虑是否有必要构建一种新型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目前我国还存在“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观念,当前尚有24部行政法典对有前科人员的权利作出了限制,并且一人犯罪会影响其所有的家庭成员,这将严重阻碍社会安定和矛盾化解[19]。
罪犯经过系统的劳动改造与再教育过程,其身份与行为模式已符合社会规范之要求,因此,从学术与法理视角审视,不应再将其继续归类于罪犯范畴,而应视为已获新生之个体。罪犯本人既然回到了社区,就不应当再受到歧视。但上述24部行政法规,却对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作出了权利上的限制,包括升学、参军、担任公务员,提拔,甚至物业管理,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将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写入法典,使其合法化,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落后的“株连”做法,坚持贯彻罪责自负的原则。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存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如果无法一次到位地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此次修法也应当扩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
5.刑事执行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的规定仅有18个法律条文,远不匹配执行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地位,且内容简略,导致司法实践中刑罚执行事项常无法律依据,因此,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机,深入研究并完善刑事执行程序立法,极为必要。
一方面,刑事执行程序的立法需要明确以下内容:一是完善交付执行规定,包括执行期限及非在押罪犯的交付;二是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改与完善[20]。另一方面,刑事执行程序的完善应当与社区矛盾的化解结合起来,改变一诉了之、一放了之等方式,逐步由治罪转向治理。犯罪人如何走向社会、走向社区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层面,唯有实现从单纯治罪向全面治理的深刻转型,方能标志着刑事诉讼任务之圆满达成。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条关于刑事诉讼的目的的表述,需要再次修改。执行程序、社区治理问题、犯罪的预防问题都应该成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并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同时要落实到刑事诉讼过程中。
6.涉外程序的立法补白
当前,就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体系内,除对管辖权的具体规定外,尚缺乏针对该领域专门章节的详尽规制,此现状显著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需求的适应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实践难题,尤为突出的是证据收集与刑事审判过程中的重重障碍,诸如司法协助机制的运行受限、跨国证据认证标准的模糊与不统一等,均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在涉外程序部分作出专章论述,规定上述问题的程序设置内容[21]。
7.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构建
关于涉案财产处置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亦需要设置专章专款来规定[22]。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涉案财产的冻结与扣押措施虽属基本操作,但案件终结后如何妥善处置此类财产,实则构成一个表象简易而内在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设立针对此类情形的专门章节进行规范,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缺乏统一明确的指导原则,具体操作层面呈现较大的随意性与不一致性,面临强制措施使用不当、管理无序、权属审核不明以及判决后执行难度大等障碍[23]。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一方面,可以考虑扩充对物强制措施的体系,在现有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之外,参照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未决诉讼提示”和“禁止令”等强制措施,完善我国对物强制措施的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案外人参与诉讼的渠道,加强案外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24]。此外,要完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促进涉案财产处理程序的规范化。对此,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涉案财产的管理,从而解决办案机关财物管理专业化不足、中立性欠缺等问题[25]。
8.监视居住程序的修改
我国现有监视居住制度存在较多弊端,一方面,该制度的适用在实践中缺乏规范性,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固定居所”是公安机关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重要依据,更有甚者,公安机关会利用异地管辖来达成上述条件[26]。另一方面,在涉及多部门的衔接时,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则更为混乱。对于监察委员会管辖的案件,纪委监委留置犯罪嫌疑人以后就不再管理,而是通知当地公安机关指定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来管理。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和分工负责的安排。法律应当是有温度的,研究刑事诉讼法最大的至理就是要坚持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唯有如此方能把保障人权的这个制度贯彻到刑事诉讼法当中。现有的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存在较大问题,因此,是否要取消指定监视居住制度以及如何规范化、程序化监视居住制度成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如不具备取消指定监视居住的条件,也至少应当考虑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切实将保障人权贯彻到刑事诉讼各领域。
9.程序制裁措施的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上主要聚焦于诉讼主体“可为”“应为”及“确保如何为”的具体要求。然而,该法律体系在构建过程中,相对缺乏了对于“未为”情形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的明确规定,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规范约束力和执行效力。对此,目前存在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一是刑事辩护的有效辩护制度和无效辩护制度的问题。并非辩护效果良好就是有效辩护。有效辩护制度、无效辩护制度与辩护效果的好坏是两个概念。简而言之,“有效辩护”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的辩护过程中,忠实且全面地执行了辩护职责,切实完成了辩护义务,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相对地,“无效辩护”则是一种程序性制裁措施,它是指依据法律规定,针对某些特定情形下未能达到法定标准或违反职业操守的律师所施加的一种不利法律后果。不论是有效辩护制度还是无效辩护制度,辩护人的资格认定、条件设定以及执业行为等各个方面,均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规范和约束。
二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问题。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开始注意诉讼程序违反问题,并进行冤假错案的纠正工作。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构成申诉再审的理由,再审应当出庭审判,撤回原判,发回重审。但目前这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空白领域。因此,应当将制裁程序内容写入法典,针对无效辩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等情形,要明确规定程序性制裁后果。
10.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
对于证据的概念、内容、范围和收集的程序、应用的程序这几个问题,立法应当作出详细的规定。尽管当前构建一部全面而系统的证据法典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鉴于前述几个关键问题对于证据制度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刑事诉讼法作为规制刑事诉讼程序及证据运用的基本法律,亟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而且,为了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也需要完善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从而建立更加健全的规范基础等。
第一,我国证据规则存在疏漏。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全面且系统的证据法典。鉴于证据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众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证据法典。相较于法治建设高度发达的国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相对简略且缺乏操作性,这一现象无疑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适用带来了显著的挑战与难题。因此,推动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27]。
第二,实现证据规则体系化。我国现行关于证据规则的立法体系呈现显著的不完整性与体系性缺失的特征。对证据的运用应当遵循九大证据规则[28],建立规范运用证据的制度体系,并进一步考虑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实现证据规则的体系化。
第三,修改证据的概念和立法表述。当前,我国学术界在界定证据概念时,围绕“材料说”与“信息说”两大理论立场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并进而映射到实务界,使得证据概念的表述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呈现出相对粗糙与不够精确的特征。因此,亟须通过深入的学术探讨与理论整合,以寻求证据概念更为清晰、准确的界定,从而为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与司法实践的精准适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条件,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于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原本旨在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则实际上转变为一个不排斥的规则,从而失去了对侦查阶段取证行为进行有效调控的功能。有观点认为,应当去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中的“可能”来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29]。然而,即便去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依然具有较大的裁量空间,无法彻底解决非法证据的认定不规范问题。总之,刑事诉讼法应当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细化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规定,并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制约[30]。
第五,确立证人出庭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在刑事证据领域内具有重要地位,是庭审实质化的标志。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的“作证义务”与“出庭义务”分割开来,导致证人出庭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未能充分发挥效用,不仅未能提高证人的出庭率,而且还削弱了被追诉人的相关诉讼权利[31]。因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完善证人出庭制度,可以删去《刑事诉讼法》第192条中“人民法院认为证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这一限定条件,削弱法院在证人出庭制度上的自由裁量权,并强调证人出庭的必要性,进一步保障包括对质权在内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
第六,明确数字证据的收集和应用问题。当前,我国在数字证据方面存在立法空白[32],亟须在法律框架内,建立一套系统、规范且高效的数字证据收集和应用流程,以确保数字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因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数字证据领域,一方面要构建一套完善的数字证据取证程序,来应对网络空间取证和跨境犯罪侦查等新兴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数字证据收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实现《刑事诉讼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效衔接[33]。
[参考文献]
[1] 谢进杰:《刑事诉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图景》,《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5期,第52—73页。
[2] 陈卫东:《三重维度下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4期,第20—38页。
[3] 樊崇义:《“把握司法规律 推进司法改革”系列之司法规律的发展进路:从压制走向回应,从对抗走向合意》,《人民法治》2016年第8期,第74页。
[4] 樊崇义:《国家权力监督原理下监察监督与刑事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法学家》2023年第3期,第88—104+193页。
[5] 秦前红,《监检衔接的逻辑与方法》,《东方法学》2024年第4期,第238—248页。
[6] 陈卫东:《〈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前瞻》,《政法论坛》2024年第1期,第45—56页。
[7] 聂友伦:《刑事诉讼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中外法学》2024年第5期,第1141—1162页。
[8][21] 左卫民:《如何展开刑诉法的第四次修改?——基于立法历程观察的思考》,《中外法学》2024年第5期,第1125—1140页。
[9] 孙道萃:《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有效模式》,《学术界》2021年第1期,第154—168页。
[10] 孙道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122—130页。
[11] 卞建林、张可:《构建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思与重构》,《政法论坛》2024年第4期,第13—26页。
[12] 孙道萃:《认罪认罚从宽诉讼程序的独立建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15—124页。
[13] 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的“以审判为中心”》,《中国法学》2023年第6期,第62—80页。
[14] 孙道萃:《轻罪治理的刑法审思与改进》,《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41—153页。
[15] 喻海松:《法典化时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向度》,《法学论坛》2024年第2期,第39—52页。
[16] 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与证据裁判原则》,《人民法治》2017年第7期,第69页。
[17] 樊崇义、孙道萃:《推进实施法律援助法的新机遇与新方向》,《人民检察》2023年第3期,第12—17页。
[18] 王迎龙:《刑事诉讼中的“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87—98页。
[19] 樊崇义:《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下轻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4期,第191—201页。
[20] 罗智勇:《关于刑事执行程序完善的若干问题》,《法律适用》2024年第9期,第77—90页。
[22] 李玉华:《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涉案财物制度改革》,《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2期,第92—106页。
[23] 张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制度的问题与完善》,《法学杂志》2024年第5期,第19—35页。
[24] 张元鹏:《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权利保障》,《法律适用》2023年第5期,第61—70页。
[25] 张佳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财产管理第三方制度的建构——以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为样本》,《求索》2023年第5期,第148—158页。
[26] 陈卫东、王然:《〈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的强制措施问题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5—16页。
[27] 郭志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代化与本土化》,《法学杂志》2024年第5期,第133—143页。
[28] 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29] 吴洪淇:《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路径》,《比较法研究》2024年第5期,第96—109页。
[30]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难点问题解读》,《法律适用》2019年第3期,第81—87页。
[31] 鲍文强:《庭审实质化下强化证人出庭的规范再造》,《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第60—77页。
[32] 郑曦:《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6期,第83—96页。
[33] 陈永生、张睿:《电子数据收集应当被纳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法治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6—118页。
Research on the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unde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Justice
FAN Chongyi
(National Institute of Legal Aid,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background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urrently, research on the amend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quir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out the basic law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Chinese-style judicial modernization an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handling of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should be updated, and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law amendment in China should be sorted out. Outdated legal concepts and ideas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unreasonable constraints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system should be broken through.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ode in one step are not yet mature. However, the “making all necessary amendments”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respond to the key and complex issues. This mainly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negotiation procedures, the confirmation and guarantee of the reform of the trial-centered system, the guarante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ight to defen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for eliminating criminal records, the improvement of criminal execution procedures,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foreign-related proced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cedures for disposing of involved property, the mod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procedures, the improvement of procedural san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vidence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judicial modernizati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legislative amendments; key issues
(责任编辑 编辑刘永俊;责任校对 朱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