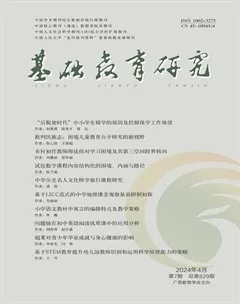斯宾塞“自然后果”惩戒观及其德育启示
【摘 要】斯宾塞基于当时英国残暴的教育惩罚现状,提出了“自然后果”惩戒观,主张教育者在不损害个体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让受惩戒者在亲身体验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获得肯定或痛苦,进而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品质。其惩戒观对突破当前我国教育惩戒在理论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厘清惩戒的育人本质,依法实施惩戒以及促进学校教育立德树人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斯宾塞 “自然后果”惩戒观 德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75(2024)07-09-04
教育惩戒自实施以来,一直广受关注。若是未深入理解和把握惩戒初衷和惩戒本质,容易误将惩戒与体罚或变相体罚划上等号,有时甚至将其演变成教育暴力。近年来,由于有关体罚或教育暴力的事件频频被新闻媒体报道,教师惩戒权的使用一度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惩戒教育要还是不要,用还是不用?“教师惩戒权的正当行使屡遭质疑,以致不少教师不敢惩戒。”[1]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教育部于2020年12月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则》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做出规定,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措施、要求等,旨在把教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更好地推动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这为教育工作者科学合理地行使惩戒权提供了明确的刚性准绳。随后,《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等文件的相继颁布,进一步指导学校完善校规校纪,健全教育惩戒工作机制,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
本文主要探讨斯宾塞的“自然后果”惩戒观,以期为我国教育工作者科学地实施教育惩戒权、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新的思考。
一、斯宾塞“自然后果”惩戒观的缘起
从古至今,教育惩戒就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文的“教”字就蕴涵着“教鞭”,表示一人手持教育工具督促孩子学习。《礼记·学记》中提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楚”是两种体罚越礼犯规者的用具,后泛指鞭策学童的工具,以达到教育目的。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古人教导儿童便借助了一定的工具,以维护礼文化,建设礼仪之邦。西方一些哲学家、教育家如柏拉图、夸美纽斯、卢梭、赫尔巴特、杜威等,尽管在他们关于教育教学的阐述中,所用的是“惩罚”“纪律”“严加管教”“训育”“服从的教育”等词汇,但也都包含着惩戒之意。相较于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倡使用的教鞭、戒尺等工具,西方部分教育家、哲学家则主张自然的惩戒。
“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就提出了隐含自然教育思想的命题。比如,普洛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效法自然’,斯多葛派的‘顺应自然’。”[3]直到17、18世纪,自然的教育理念在夸美纽斯和卢梭的努力下得以充分发展。夸美纽斯主张的自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自然界的‘规则’,即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的艺术中起支配作用的原则”“二是‘普遍的神的预见,或不断在万物身上发生一切作用的神的仁慈的影响’”“三是人的天性及身心发展规律”[4]。卢梭则认为自然指人的天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惩戒观——“自然后果法”。为破除以人为体罚为主的过度惩戒教育,改变当时英国残暴的教育惩罚现状,斯宾塞也极力主张“自然后果”惩戒观,明确强调“在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时,我们应该多使用自然惩罚的方法,而非人为惩罚的方法”[5],并提醒人们“要注意谨慎使用体罚的方式,因为它是人为惩罚中最严重的方式”,“体罚也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孩子”[6]。虽然斯宾塞否认其“自然后果”惩戒观是借鉴卢梭的“自然后果法”而提出来的,但是二者在认同自然、反对人为的原则性问题上却高度一致。
二、斯宾塞“自然后果”惩戒观的主要内容
(一)何谓“自然后果”惩戒观
何谓惩戒教育,不同的学者对其表述有所差异。李镇西认为教育惩戒“是对不良行为的一种强制性纠正,既可以体现在精神上,也可以体现在行为上”[7],区别于惩罚、体罚、变相体罚、教育暴力,它不是为了惩而惩,是为戒而惩,以期使受教育者对自身的行为感到羞愧、良心不安。《教育大辞典》对教育惩罚的解释为:“对个体或集体的不良行为给予否定或批评处分,旨在制止某种行为的发生,与奖励相对,为学校德育采取的一种教育方法,有利于学生分辨是非善恶、削弱受罚行为动机、达到改正的目的,也利于维护校纪校规。”[8]高德胜和殷秀芳认为,教育惩戒与道德情感的培育紧密联系,是“借助被惩戒对象自身所本有的良善与向上之心等积极力量”[9]来实现教育目的。由以上可知,虽然在界定惩戒教育时,学者的视角和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是都包含着教育者对被惩戒者能够养成良好德行的期望和关爱。
对于如何实施惩戒教育,斯宾塞提出要遵循自然,表明了他反对人为而主张自然的态度,也明确了通过“自然后果”进行惩戒的方式。斯宾塞认为,区别于人为惩罚所施加的额外惩罚,自然惩罚“是以等值、等同为基础,对错误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回应,让孩子从中得到相应的经验和教训”[10]。相较于传统惩戒、侧重孩子被动接受成人从事件外部施加的后果,“自然后果”惩戒观看重的是孩子在没有人为干涉的情况下自身承担事件本身的结果,并从中收获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的经验教训。所以,斯宾塞提倡的“自然后果”惩戒观是一种在不损害个体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让受教育者在亲身体验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中获得肯定或痛苦,进而养成良好个性和品质的教育手段。
(二)自我教育的目的观
斯宾塞强调,“记住你的管教的目的应该是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要让别人来管理的人”[11]。从幼儿期到青少年期的智力教育,必须通过“一种快乐的自助式的教育方式”进行,“重点培养孩子的自我教育能力”[12]。为何如此重视自我教育?因为在自主解决疑难问题的过程中,孩子从中获得的经验能够持久而清晰地保存在大脑中,进而对重新梳理认知图式、解决相似问题或问题的变式奠定基础。并且,在做中学的孩子,不仅能磨练其意志、增强其毅力,也能收获快乐。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教育能力和习惯呢?斯宾塞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其一,重视并培养孩子的兴趣。利用兴趣对孩子进行自我教育时,成人不要插手孩子的活动,给予孩子独立探索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此外,家长和教师也不要轻易满足孩子的兴趣,这样才能使孩子珍惜培养兴趣的机会,延长孩子对某件事情感兴趣的时间。其二,提前做好物质准备。要想维持和发展孩子的兴趣,成人需要提前准备好数量少且能够满足孩子兴趣需求的书籍和工具。其三,鼓励孩子社交。让孩子在集体中接受教育,发展兴趣,激励自我。其四,增强孩子的主人翁意识。家长和教师要学会放手,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其自理能力。在对时间的管理上,让孩子自己规划个人时间,学做时间的主人。关于某些事情的处理,可以通过角色互换,由孩子来安排相关事宜。
(三)遵循自然惩罚为主,人为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
在实施“自然后果”惩戒教育时,斯宾塞提出要遵循以自然惩罚为主,人为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自然惩罚的优势有以下三点:一是帮助受教育者建立正确而完整的因果概念。孩子只有在正确的因果概念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根据行为自身和结果来判断是非对错及后果,正视自己的错误。二是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公平、公正的心理感受。自然惩罚通过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干预以不放大惩罚,个体在承担因自身错误所导致的原本后果中,达到自我反省、自我改进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错误未被放大、事实未被扭曲,所以受惩戒者不会感到冤枉,也不会感到委屈,他本人也将能最大程度地体会自然惩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三是促进师生关系。自然惩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有助于将教育者的愤怒值和受教育者的怨恨情绪降到最低,这样他们才能尽可能理智地、客观地处理错误的行为。
由于自然惩罚的后果需要当事人亲自体验,因此自然惩罚法要和后果体验法一起使用。在这里,后果体验法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后果法,另一类是精神后果法,使用时要因“事”制宜。关于物质后果法,斯宾塞认为,应让犯错的受教育者体会物质缺乏带来的不便,或者自己承担经济方面的后果。倘若孩子将自己的文具弄坏了,那么要让他感受没有文具所造成的不便,或者用自己的零用钱去买新的文具。在此过程中,孩子将学会爱惜物品,理解金钱来之不易。对于精神后果法,就是让受教育者“自己承担道义上的后果”[13],并激发其同情心。假如受惩戒者不尊敬师长,随意辱骂同学,他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别人的冷落、批评或来自其他舆论的压力,甚至也同样会尝到被同学辱骂的滋味。这样,在体会道义和心理后果的过程中,犯错者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从而促使其羞耻心和同情心的养成。
需要强调的是,斯宾塞注重根据孩子的年龄差异来分阶段实施“自然后果”惩戒教育。例如婴儿时期的孩子就不适合通过“自然后果”习得经验教训,倘若放任婴儿玩弄锋利的器具,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随着孩子逐渐成长,成人应逐渐减少干预,直至成年后取消干预。
另外,主张自然惩罚并非完全排斥人为惩罚,人为惩罚是自然惩罚的辅助手段。当受教育者在道德上犯下严重错误时,教育者可以用明确的态度表达对该行为的不满,或坚决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人为惩罚之后,成人要发挥出自身的教育作用,及时给予犯错者安慰和引导,使其真正认识到错误,汲取教训,引以为戒,最终达到育德育人的目的。
三、斯宾塞“自然后果”惩戒观的教育启示
(一)厘清本质,育快乐人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不管是学校里的教师,还是家庭中的父母,在实施惩戒的过程中,都要时刻做到心中有人,牢记育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诉求,明确惩与戒之间的相互关系——惩是戒的手段,戒是惩的目的。同时,教育者还需对被惩戒者寄予养成良好德行的期望和关爱的情感,这种育人期望就是实施惩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正如斯宾塞所言,教育应培养具有自我教育能力且快乐的人。一个具备自我教育能力的人,才能真正实现自治和独立;一群快乐的受教育者,才能使个人的小家庭更和谐、集体的大家庭更兴旺。
(二)完善细则,快乐育人
1.科学制定和完善惩戒教育实施细则
虽然国家已颁布了与教育惩戒相关的法规条文,但是其中并没有明确详细的犯错行为及对应的惩戒措施,导致教育者在行使惩戒权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由于学生犯错的严重程度不同,教师惩戒的尺度不一,教师采取惩戒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如言语责备、罚站、写书面检查、隔离、剥夺某种特权等,所以难免会引起诸多纷争,破坏师生情感,甚至会打乱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近期有关惩戒教育文件的相继印发,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教师惩戒权的理性回归。它们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尺度,让惩戒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让教育者敢于重拾育人的“戒尺”,有利于解决教师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这一令人头疼的“三不管”问题。但这也只是在宏观层面为各中小学及教师实施惩戒教育提供了参考,实现了有法可依的愿景。就微观层面而言,各学校还需要立足本校实际,及时制定和完善惩戒实施细则。科学制定实施细则是推动教育惩戒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进一步明确惩戒的具体方式方法和合法性程序,以提高惩戒的可操作性,真正落实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2.遵循“四度”原则,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在实施教育惩戒时,教育者也务必遵循教育惩戒的“四度”原则,即教育惩戒需有法度、力度、尺度、温度,助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实现最佳育人效果。对此,教育者应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充分发挥教育者的榜样示范作用。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人们主要是通过观察榜样示范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学习,因而榜样的特征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基于孩子爱模仿的天性和尚未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等认知现状,教育者自身首先要具备正确的道德认知、健康的道德情感、坚定的道德意志、高尚的道德行为,从知、情、意、行多方面提升自己。在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时,教育者不仅要注重示范行为的生动性、可行性、可信任性、共鸣性,更要考虑学习者的年龄特征。
第二,明确孩子犯错误的原因。教育者在实施惩戒之前,可以结合犯错者自身的阐述、旁观者的阐述来明确孩子犯错误的前因后果,以保证惩戒措施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若是因为教育者自己的教育疏忽导致孩子犯下道德上的错误时,教育者应该先进行自我反省,酌情减轻对孩子的惩戒力度。
第三,把握惩戒方式的适当性。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家在制度层面上为教师行使惩戒权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教师自身并不具备教育惩戒方面的专业认知和有效实施惩戒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教师面对的是在身心各方面存在差异的学生群体,需要处理的是这一群体做出的繁琐多样的失范行为,这就要求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要根据犯错者的身心发展状况和具体的失范行为进行专业的判断和合理的考量。因此,教育和学校管理部门有必要开展教育惩戒的专题培训,丰富和深化教师有关教育惩戒方面的认知,提高其选择惩戒方式的适当性。
第四,营造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一方面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有利于消除教育者害怕孩子犯错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有利于消除孩子对错误的恐惧心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犯错,教育应包容和理解,对于孩子犯下的错误不应全盘否定和过分指责,而是要耐心地聆听孩子的心声,鼓励和引导孩子正视错误、反思错误,提高惩戒的温度。
【参考文献】
[1]刘冬梅.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的调查与思考[J].教师教育研究,2016,28(2):96.
[2]林焕新.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教育惩戒,有“法”可依[EB/OL].(2020-12-30)[2023-10-3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12/t20201230_508113.html.
[3]沈芳芳.夸美纽斯与卢梭自然教育思想之比较[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40(5):133.
[4]同[3]134.
[5]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的快乐教育[M].甘慧娟,编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135.
[6]同[5]137.
[7]李镇西.惩戒不等于体罚[N].中国教师报,2017-04-05(3).
[8]吕立杰.课堂教学管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62.
[9]高德胜,殷秀芳.对教育惩戒核心问题的追问[J].中国教育学刊,2022(2):54.
[10]同[5]135.
[11]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11.
[12]同[5]87.
[13]于书娟,毋慧君.斯宾塞的惩戒教育观及其德育启示[J].教育评论,2017(1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