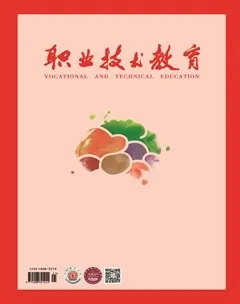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曹靖(1988- ),男,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湖北教育政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武汉,430000);尚嘉珉(2001- ),男,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重点课题“湖北省高职院校推进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的案例研究”(2023GAO39);2024年度“湖北工业大学—湖北省新型智库(培育)”智库建设专项课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与湖北新型工业化”(托举计划24TJ06),主持人:曹靖
摘 要 基于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理论融合的视角,理清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逻辑,呈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内在规定与外在表达。市域产教联合体因政府行为的“边界不清”,制度供给的“差强人意”存在规制合法性困境;因组织行径的“离经叛道”,中间组织的“作用缺失”存在规范合法性困境;因“新生者劣势”存在文化—认知合法性困境。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在多重制度逻辑交互的穹顶规则下获取组织合法性,受多元制度要素作用的制度压力而显现组织合法性。
关键词 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制度逻辑;多中心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1-0038-09
区域产业发展与经济运行方式发生转变的时代趋势,使得产业界与学界对产教融合组织有了新的认识,客观上也渐进地形塑着社会公众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理解与期待。市域产教联合体是集培养人才、深化产教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维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产教融合实践载体,注重对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回应[1],其具有发展理念一体化、建设主体多元化、发展特色市域化和运作方式实体化等特征[2]。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博弈结果的现实选择,也是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路径朝向。然而,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充斥着各种冲突,多重制度逻辑的情境频繁出现,诱发对抗性的制度实践与规范[3]。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体化运作因无法适时、合理应对“多重制度逻辑在组织场域中生成的动态交互关系”[4],将引发外部社会的认知偏差,使其组织合法性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探析并厘清市域产教联合体如何获取及显现组织合法性的作用机理,能拓展制度影响产教融合组织体孕育、生成及成长的理论研究,并化解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组织合法性困境,明晰其运作的实践方向。
一、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理论融合:理论分析框架阐释
制度逻辑塑造或决定了组织环境中的“游戏规则”[5],当组织的运作契合其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或能够满足利益相关主体的期望,则认为是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并被赋予特定的身份来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提高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6]。制度逻辑通过四种具体的机制来刻画组织合法性行为的获取[7]:一是通过“身份认同”明确行为主体的群体性特征;二是通过“社会分类分层”作用行为主体的认知;三是通过调节组织“决策者才能”的配置来影响组织行为;四是通过“组织运行逻辑”演绎组织和个体行为。制度逻辑对复杂的组织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斯科特提出的“制度三大要素”理论基础上,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制度逻辑及组织合法性进行归纳,见表1。
其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规制合法性。基于“规制性”的制度要素,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被看作是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一种制度安排[8],其规制合法性源于政府的政策法规,凸显国家权力的意志。如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决定启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工作,明确的工作目标、条件要求及组织实施有助于其规制合法性的获取。
其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规范合法性。基于“规范性”的制度要素,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规范合法性反映出外界对于其运作的正面规范性评价,其获取源于社会道德规范及价值观的要求,“一种亲社会逻辑,从根本上不同于狭隘的自我利益。这意味着判断一个组织在道德上是否合法不依赖于组织的行为是否有利于评估者的判断,而是依赖于它是否能在社会维度上被认为是正确的”[9]。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运作过程中,其规范合法性受到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相互认同的影响。
其三,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文化—认知合法性。基于“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文化—认知合法性源于社会大众的一般性认知、理解及接受,“只有当产教融合上升为社会文化时,其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认知合法性,成为企业、学校、其他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进而转化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行动”[10]。文化—认知合法性可被看作是规范合法性的延伸,它基于规范性期待又超越了它,即市域产教联合体运作在社会大众的认知中是否符合规范性要求,以至于被看作是自然而然且理所应当的事情。
多中心性(Polycentricity)是指多个独立的决策制定中心和行动者在一定规则和标准的框架内,通过相互调整来组合彼此间的关系[11]。通过建立一个整体限制性规范和约束条件的穹顶规则,可以将不同的中心纳入到统一的制度体系中,利用多中心之间规则、规范的自主性交互来确定彼此间关系,从而达到调整内部主体行为的目的,使得多中心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形成竞合关系,最终确保整个体系的运行活力[12]。利用多中心性理论来探寻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制度活动,能较为准确地阐释市域产教联合体与区域产业形态、经济运行模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理论融合则是基于不同理论间存在的互补性或协同性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进而对社会实践进行解释,从而达到强化事物认知和理解的目的[13]。如何利用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理论融合的视角,来探究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问题?
首先,制度逻辑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作用是通过组织场域来实现的,处于组织场域中的行动者能比场域外的其他行动者形成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且彼此的互动也更加频繁[14]。多重制度逻辑中的同质性要素将转化为组织发展的基本准绳,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在发展目标、组织性质、价值主张、业务领域等方面差异显著,但仍要契合所处制度环境的基本要求,如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有效服务产业发展等才能立足于组织场域。
其次,多中心性的穹顶规则要求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的行为都共存于统一的制度框架之下,要能够满足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期望。制度逻辑在牵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作过程中满足区域产业升级、经济运行方式转变、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等基本规制的、规范的和认知的制度规则,以回应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才能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即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在穹顶规则的制度框架下运作,但也可能在组织场域中导致了趋同现象。
再次,制度逻辑中的制度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使组织场域中出现具有相对主导影响的范畴,“可以根据逻辑的作用效果,将组织场域划分为不同的、具有独立的行为规则和特征的场域单元,并对其中的行动者产生差异化作用力”[15]。制度逻辑影响着组织场域内的制度多中心结构,而制度逻辑中各制度要素的动态均衡能够保障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协同配合以实现有序运行。因此,运用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理论融合的视角,可以观照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也为寻求其如何达到产权明晰、组织完备、机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实体化运作提供理论参考。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审视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逻辑
“结构和运作是理解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关键要素”[16],在审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之前,有必要梳理及明晰其组织结构及运作逻辑。
1.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结构
“组织的价值与目的越来越趋于混合化,多个生存逻辑的共存与共演成为混合组织的新特征”[17]。首先,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价值目标和使命追求可以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二元价值中进行混合,其组织性质介于传统商业组织与传统非营利性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之间,在撷取经济价值的同时还要协调社会价值的平衡发展,并由此形成混合型组织形态。其次,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履行社会责任或是具有社会责任的组织,其实体化运作需要平衡在其他组织形态中表现为矛盾的绩效目标,即妥善处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且要顾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诉求。再次,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四方协同的命运共同体,也是各参与主体之间形成的显性及隐性契约的集合。产教融合的应然意图引导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形成信任的互惠关系,与产业升级、经济运行模式转变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关联。总之,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产教融合组织范式,是具有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社会经济组织,其组织合法性要符合现代社会中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嵌入、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内在统一的要求。
2.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运作逻辑
“运行逻辑既是组织使命目的的反映,更是组织行为方式的决定因素,通常能够体现组织所属的‘社会部门’,并显性化地刻画为资源配置方式与原则”[18]。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各主体协同配合以实体化运作融合了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的运行逻辑,体现出“第四部门”的特点——“指的是那些超越传统部门边界与目的、服务于大量底线社会需求,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混合在一起、受使命驱动的组织,即灰色部门组织(GSOs)”[19]。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私营部门侧重经济价值的获取和创造,也会基于自身社会责任而适时涉及社会价值创造;公共部门看重社会价值创造,其经济价值获取主要受政府、组织、个人等外部因素影响。从组织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三个维度剖析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作逻辑。其中,价值主张说明市域产教联合体创造和获取什么价值,两者关系如何;价值创造描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服务、产品等如何创造价值;价值获取说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成本结构及收益来源。
其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主张。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主张既触及社会价值创造,也强调经济价值获取,经济价值为社会价值提供资本、劳动力、管理等方面的支持,社会价值同样会为经济价值的获取扩大社会影响力,以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经济价值创造与社会价值获取是一体的,通过适时调整组织行为,也将社会价值的获取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中。
其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创造。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创造是在其运作过程中,基于机会成本的权衡,使其利益相关者的总效用增加。如联合体内的企业在政策支持、经费补充的利好之下,被激发出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宜的办学、从教、育人动机,出现与生产对接的培训行为、开发与产业吻合的专业,涵养与产业共进的意愿,进而生成价值创造。首先,服务区域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要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为核心主导产业,反映出市域产教联合体要契合区域产业形态的发展需求,以服务区域发展战略,主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充分挖掘发展潜力,并履行社会责任。其次,服务人才培养。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企业将在投资兴办职业教育、接收学生实习培训、接纳教师岗位实践、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方面积极作为,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再次,服务产业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公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打通科研开发、成果转移链条,其内部产教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产教融合特色能够显现,企业育人并促进就业的优势得以突出,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工艺改进、产品升级、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以有效服务产业发展。
其三,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获取。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获取是其在测度运营成本及风险之后,在所举办或参与的职业教育活动中获取的一切价值。一方面,源于政策的优惠。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条件中明确提出支持职业教育的金融、财政、税费、土地、信用、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激励政策的具体举措,落实落地见效果;另一方面,来自技能培训的获利。市域产教联合体将在就业岗位提供和职业资格培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既能作为消费者接纳合格的学生进入相关企业工作,使技能转化为生产力,也能为生产者提供优质的技能培训,让学生的技能转变为企业发展的战略资产。此外,市域产教联合体内企业员工技能升级所带来的长远收益是其运作过程中的重要隐性获取。
综上,基于组织结构和运行的判定,市域产教联合体可被界定为:一种将社会价值创造及经济价值获取相融合,其组织结构映射出产教学研用与协同创新综合活动的开展,在运作过程中体现市场逻辑、公益逻辑和理性选择逻辑相结合,是组织自身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新的混合型产教融合组织体。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内外审视
1.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内在规定
市域产教联合体以追求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但在实现方式上是按市场经济运作规则开展各项活动。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内在规定如下。
其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理想样态。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是将多重制度逻辑融合共生成一种新型的、均衡的组织行动指南,是联合体内各主体自身价值主张与时俱进的体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是以“共生—相容”的多重制度逻辑同构于自身发展的内外环境之中,并影响自身的经济行为、道德行为及社会行为来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活动。同时,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将转向“文化—认知”制度化,并悄然出现组织变革及组织互融。此外,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将处于更直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体系中,定期接受第三方评价其育人成效,以获取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支持。
其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使命运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自生成之始就突显出其是经济“嵌入”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调适联合体内企业的生产要素以形成内生性动力,并导向其在运作过程中的组织行为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如市域产教联合体内企业的“资本”摒弃“功利性”流向,把社会财富增长归因于技能开发,并把技能开发当作国家战略时,资本会向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信息咨询等领域流入,继而联合体内企业潜在的教育功能被唤醒,企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更具主动性。
其三,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价值共生。从组织结构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是由其组织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及文化—认知合法性高阶均衡的体现。多重组织合法性的均衡是通过联合体内各主体“价值共生”的机制创新及稳定的制度供给来实现的,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会形成良性的制度安排,将以“协同机制”及“利益代理机制”加强政府、行业组织、学校、科研机构和各类企业间的产教联动发展,并促使各主体达成市域产教联合体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
2.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外在表达
(1)恪守管理措施:组织合法性规约组织行为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要遵行管理措施,通过园区申报、省级推荐、建设培育等程序。一方面,组织行为要规范合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反映其创造社会价值的动机,必须端正其获取经济价值的行为。另一方面,组织行为要突出公益性。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亦反映出其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或提供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服务,或推进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四方协同的命运共同体的生成。
(2)明确价值理念:组织合法性明晰组织定位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反映出其在运作过程中要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社会价值创造凝练为发展的核心理念,才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市域产教联合体将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运作,会受到政策法规、产业形态、社会期许,联合体内行业需求、企业自身发展愿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只有清晰定位,凝练价值理念,制定合理的运作目标,才能体现组织合法性。
(3)平衡长短价值:组织合法性彰显组织作为
组织运作的内在需求既有短期利润,如财政补贴、经济收益等,也涉及长期的创新性价值需求,即人力资源开发、商誉、技术和创新成果。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要使长期社会价值创造与短期经济价值获取达到和谐状态,促成其主动参与、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并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
三、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困境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属性决定其具备组织理性特征,即“组织在特定的环境和问题情境下,会努力通过理性的计算或者以最小的成本来解决特定的问题,从而实现特定的目标”[20],还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将是否对社会有利作为其行动的重要参照,并以社会利益的增长为行动目标”[21]。作为一种嵌于复杂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中的组织,市域产教联合体运作过程中在法律裁决、道德支配及社会文化支持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组织合法性困境。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规制合法性的困境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制度多为政策性文件,缺乏有力的法律法规约束,且存在制度不协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规制合法性的困境。
1.政府行为的“边界不清”
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各主体在市场机制下协同配合,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移、社会服务与有效服务产业发展进行衔接,政府的各项规制行为则要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产教融合政策以补充市场机制所不能实现的功能。在产教融合过程中,“以政府为中心的共治成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无法深度融合的重要缘由,政府又不得不通过以政府为中心的共治推动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22]。政府“放任”所引发的监管缺失会导致产教融合在资本逐利的影响下,失去原有的价值定位,甚至走向违法的禁区;而政府的“越权”行为又会打击学校与企业作为融合主体的积极性,破坏市场机制优化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23]。因政府的角色及权力边界的不清晰,“政府悖论”致使市域产教联合体在运作过程中的规制合法性面临较大的挑战。
2.制度供给的“差强人意”
“当前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可归结为一种‘自我复制与自我维持’的过程,并未很好地激发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24]。我国产教融合在顶层设计上缺乏具体的规划,各类产教融合组织体的建设也缺乏系统性、持续性、操作性强的制度供给。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体化运作需要法律法规层面的细化与协同,联合体内各类主体在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形式契约”的现象,无法真正落实政策规定的义务要求,部分地方政府未能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特色及经济运行现状进行产教融合政策细化。就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而言,还缺失联合体内促进学校服务产业发展,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促进技术创新、工艺改进、产品升级,解决企业实际生产问题的激励政策;缺失促进联合体内企业主动参与、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各环节的制度性路径等。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跨领域制度组合,而各部门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意愿参差不齐,在政策推行中亦存在各自为政、互补性不强的情况,从而对规制合法性产生影响。此外,相关立法“停滞不前”,国家层面未出台“产教融合促进法”或“产教融合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产教融合组织体或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进行限定,致使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缺少法律确认、法律推进及法律保障。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规范合法性的困境
“组织的行为符合特定环境中的社会价值观与道德规范,也就拥有了规范合法性”[25]。规范合法性是一种对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否在做“应该做的事”具有约束力的社会期望。
1.组织行径的“离经叛道”
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是以“项目制”为载体调配产教资源在横向上的流通及互补,以介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市域产教联合体内企业的参与行为会为其带来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政治身份等利好,其中“身份效应”是企业在与政府关联中最为“外显性”的表达。因此,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企业可能通过“仪式化”参与,在短期内为自身发展斩获资源,也运用身份效应来顺应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浅尝辄止的行为不利于其结合自身不同的资源禀赋与能力条件,从关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角度规划自身发展与社会责任履行和谐共生的远景。另一方面,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高技能人才培养具有长时性和延时性,但企业可能通过学生顶岗实习、生产性实训基地实践教学等形式取得短期性人力资源,或通过订单班、企业学徒制等形式获得符合企业需求的养成型人力资源,而职业院校无力涉及制定学生在企业实习的监管流程,无法对学生实习效果的评估及技能养成的评定,这将导致市域产教联合体规范合法性的消解。企业着眼于实习学生对企业的好感度、忠诚度,或建立师徒情感联结,并明确人力资源的流向,而职业院校则可能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视为每一届学生都需要完成的企业体验式教学活动。
2.中间组织的“作用缺失”
“我国经济运行模式决定了中介组织的必然参与,中介组织的参与节约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26]。经济运行模式转变对产教融合组织实体化运作的方式提出新要求,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人才培养、服务产业发展需要多个专业化的中间性组织协调配合。中间性组织在尊重联合体内各主体育人客观能力意愿的基础上合理发挥辅助作用,激活由政府、企业、学校及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的效能。中间性组织的缺失导致市域产教联合体无法通过内在生成的职业教育技能养成体系为育人的出发点,无法使“企业元素”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持续增强教育性,继而以一线生产实际为载体的育人方式亦无法实现。
(三)市域产教联合体文化—认知合法性的困境
“文化—认知合法性旨在强调以社会为中介的共同意义框架,是一种基于共同理解的信念与行动逻辑”[27]。市域产教联合体因“新生者劣势”(Liability of Newness)还未被社会大众认为具有社会共享意义。同时,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对产教融合的认知程度亦会影响其文化—认知合法性的获取。如在以中高端制造业为“内核”的新产业形态选择之下,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劳动力市场的诉求以及个人成长的需求,但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中职、高职(含职教本科)学校及普通本科学校在办学主体、办学理念和办学路径上存有差异,特别是部分职教本科院校创建时间较短,尚未构建起系统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如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标准体系缺失、人才培养制度供给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且无法对接产业发展需要。此外,陈旧认知使企业习惯性将自身摆放在“支持者”“付出方”诠释产教融合的未来形态。企业的重视不足导致对产教融合相关政策价值意蕴的理解以偏概全,“形式上”的产教融合不利于产业整合态势的向好发展,也无力承担起引导制造业向中高端价值链攀升的重任。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是赋予联合体内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发挥教育功能,承担相应教育职责,并将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中,以强大且鲜活的教育生命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突破,若企业无法结合自身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能力条件,秉持的育人目标就与助力社会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的期许不匹配。
四、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管理
“进行合法性判断并不是为支持或抵制制度逻辑的影响,而是为了形成一种判断来有助于选择对组织而言最为合适的发展路径”[28]。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管理是产教融合组织实体化运作时多重制度逻辑间实现“求同存异”的结果,也是其实现跨场域单元流动以提升组织场域活力的依托。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获取:多重制度逻辑交互的穹顶规则
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获取是在一个总体的穹顶规则下,通过多重制度逻辑交互来驱动组织的行为范畴。制度逻辑内在的一致性要求,能确保联合体内各主体在共同的行为规则下开展差异化的社会活动。
1.强化制度制定,以校正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经济行为
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引导者、支持者及执行者。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作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制度环境,政府要引导产教资源合理地投入职业教育活动,并积极识别、回应及支持多样化的产教融合组织体运作模式。政府强化制度制定,以校正市域产教联合体在运作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如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企业获取可以被量化的经济收益及不能被量化的非经济收益。政府强化制度制定,以厘定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主张、约定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创造、规定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获取。此外,建议地方政府采用“负面清单”制度,通过行政法规的制定、修订及终止来引导自身职能的转变,朝向“不越位”的有限政府、“不缺位”的责任政府、“不错位”的效能政府发展,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创造更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形成产教融合管理制度。设计针对市域产教联合体负责人的问责制度,切实加大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未履约”的惩戒力度,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完全经济理性行为产生震慑。使政府的相关补贴投入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的活动中,提高补贴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并降低政府的监管密度,减轻政府的工作量,提升工作实效。此外,还要出台专门法律法规。政策工具效果的发挥需要与逐步完善的产教融合法律形式相匹配,要提升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分”的含金量,就要给予其建设培育应有的“法制空间”。
2.优化制度执行,以引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道德行为
一方面,优化制度执行,以确保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运行顺畅,助力市域产教联合体是“社会福利缔造者”角色的塑造。第一,设立专责管理部门。引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道德行为需要使能的制度环境,设立部、会层面的沟通协调平台或专责的管理部门,促进相关政策工具、财务选项的组合、选择及推行,便于对联合体内各主体提供专业、合理的指导。第二,加大政策优化力度,通过政府购买、鼓励企业探索混合所有制等途径探索创新,先行先试,以调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企业的积极性。第三,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要增强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能力、教育教学能力、技术服务能力等关键办学能力,以更好地支撑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优化制度执行,以中间性组织的“协同机制”及“利益代理机制”加强政府、行业组织、职业学校、科研机构和各类企业间的产教联动发展,表达各方对于产教融合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协助市域联合体内企业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解决其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所涉及到的产权保护问题。中间性组织能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氛围以提升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认可度,并促使各利益相关方达成产教融合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
3.实化制度转型,以唤醒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社会行为
“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正式制度和法律体系也会随之不断完善,整个社会网络将由强关系网络向弱关系网络变迁”[29]。因此,制度转型需要经历从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迈进。在制度转型期间,政府积极推进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正式制度改革,能够节省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所付出的交易费用,减弱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政治关联的动机,消释政府寻租、设租的利益源头。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间的行为互动模式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各主体基于法律规约和道德准绳承担相应责任、履行对应义务,并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来加强互动合作。此外,在国家强调“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技能型社会”建设和“产教融合赋能提升”等背景下,引导联合体内各主体客观、深入地理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以形成融洽的产教融合组织氛围。政府加大力度面向联合体内各主体对产教融合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宣传,及时总结、推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典型案例和突出成果,营造全社会积极支持、充分理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风尚,使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在产教融合过程中从“被动进入”转变为“主动参与”,并激励更多类型产教融合组织体积极投身职业教育活动。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显现:多元制度要素作用的制度压力
“组织场域及其内部嵌套的场域单元形成的多中心性制度秩序是一种源于叠加管理范畴的复杂系统,也决定了其中的内部单元必然会受到嵌套制度压力的作用”[30]。制度逻辑间的异质性诱导多元制度要素作用的制度压力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场域划分为三个“绝对化”的场域单元,“每个场域单元都有相当的自由度来制定和执行规则”[31],结合萨奇曼对组织合法性的标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有以下具体显现。
1.实用主义合法性显现:规制要素主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
其一,交换合法性。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作要以产权保护得以落实、风险分担机制建立为前提,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形下,调动联合体内各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因此,不应简单地将联合体内“产”和“教”的资源汇集,而是在产教资源优化调配的基础上借助校企合力以显现其交换合法性。其二,影响力合法性。强调但不鼓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育人活动,赋予主体权利以保障其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如强调联合体内企业育人的主体地位是要明确保障其育人的权利、筛选人才及留住人才的权利,护卫企业的知识产权,亦不会使企业过于迎合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而淡化自身的“经济理性”,或过于依赖政府的补助和支持而丧失独立经营管理的能力。其三,气质合法性。当组织所倡行的价值观能与组织内各主体产生共鸣,其就会显现气质合法性。通过利导性而非干涉性的制度安排,“创造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机制,通过劳资协议、压低学徒工的工资差异等手段,减少企业间的挖墙脚行为,坚定劳动力流动性,鼓励和保障培训合同的签订与执行,让企业更有动力长期持续地投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中”[32]。让市域产教联合体在运作过程中把握政策导引和机制建设的平衡点,既提振联合体内各主体育人的积极性,又消减其育人的顾虑。
2.道德合法性显现:规范要素主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
其一,结果合法性。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应合理解释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判断未来产教融合的发展趋势并积极调整自身战略规划,联合体内的企业需要持有“‘创造、分享、责任’的财富观,保持发展的理性与自主性”[33]。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与时俱进地调整产教融合行为模式显现出应有的结果合法性。其二,过程合法性。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企业及学校应坚持嵌入的自主性,企业需智慧地处理政治关联与自身发展战略间的关系,也应结合自身实际的经营状况与职业院校合作,以积极推动区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联合体内的企业要增强“组织感知合法性”,优化育人动机;倡导“组织惯例变革”,明确育人目的;重视“中间性组织”作用,迭代育人方式。其三,结构合法性。结构合法性侧重于一般性的组织特征,市域产教联合体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突破即能反映其结构合法性。联合体内的职业院校通过加强产业学院、产学研创新战略联盟和校企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于人才培育。同时,联合体内的职业院校应积极推进内部生成的技能养成体系建设,以涉及专业技能形成与职业素养的提升,触及职业教育人才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贯通,企及个人就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此外,联合体内的职业院校要积极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攻克行业企业技术难题为重点,定期征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3.认知合法性显现:文化—认知要素主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
承接并实现国家所赋予的时代使命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显现的时代土壤。“如果人们要获得社会威望和社会地位(声誉),他们的行为表现必须超越狭隘基础上的个人私利,必须使得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颂的。社会承认逻辑的基础是‘合法性’机制”[34]。当前,我国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轴的产业形态选择、依赖“人”的技能提升的制造业升级、偏向协调企业行为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等,均能晕染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所需“社会承认逻辑”的图景。文化—认知制度要素主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对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间在要素流动等方面有着新的时代诉求,通过“技能型社会”建设,营建尊重技能型人才、崇尚职业技能的社会认知,以强劲的符号意义及价值标签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制度的变迁一般会在一定文化—认知的驱动下有秩序、有目的地进行”[35]。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是文化—认知制度要素主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的“根基”,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式创新、广泛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岗位成才的中国特色学徒制,鼓励普通本科学校招收符合条件的中高职毕业生和企业优秀员工就读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即以高质量的人才输出“反哺”社会各界的认知及期待。此外,文化—认知制度要素主导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要体现出区域发展特色,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生态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关市域产教联合体运作的主要目标、阶段任务及工作举措等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不同,因地制宜、差异化运作。
参 考 文 献
[1]梁晨,廖园园.高质量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理性审视、逻辑关联与实践方向[J].教育与职业,2023(10):5-12.
[2]冯海芬.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特征、价值意蕴与建设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3(25):14-19.
[3]GREENWOOD R,RAYNARD M,KODEIH F,et al.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1,5(1):317-371.
[4]MICELOTTA E,LOUNSBURY M,GREENWOOD R.Pathway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43(6):1885-1910.
[5]DUNNMB,JONESC.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the contestation of care and science logics in medical education,1967-2005[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0,55(1):114-149.
[6]FRIEDLAND,R.,R.R.ALFORD.Bringing society back in:symbols,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A].in powell,w.w.,and p.j.dimaggio 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1:232-263.
[7]THORNTONPH,OCASIOW. Institutional logics[M].Greenwoodc.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London:Sage,2008:99
[8]马树超,郭文富.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经验、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8(4):58-61.
[9] SUCHMAN,M.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571-610.
[10]刘宝.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合法性问题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2(1):45-52.
[11]李晓丹,刘洋.制度复杂理论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启示[J].管理学报,2015(12):1741-1753.
[12][31]OSTROM,V.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democracies:a response to tocqueville’s challenge[M].AnnArbor:Univert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11.
[13]王涛,陈金亮,罗仲伟.二元情境下战略联盟形成的嵌入机制分析: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融合的视角[J].经济管理,2015(8):55-64.
[14]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M].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2008:567.
[15]REAY,T.,C. R. B. HININGS. The Recomposi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health care in alberta[J].Organization Studies,2005(3):351-384.
[16]齐海丽.制度逻辑·话语分析:公共服务购买场域的政社依赖关系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6):72-96.
[17]RAWHOUSER,H.,M.CUMMINGS,A.Crane.benefit corpora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 hybrid categor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5,57(3):13-35.
[18]肖红军,阳镇.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合意性组织范式[J].中国工业经济,2018(7):174-192.
[19]WADDOCK,S.,M. Mcintosh. business unusua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a 2.0 world[J].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11,116(3):303-330.
[20]魏姝.效率机制还是合法性机制:发达国家聘任制公务员改革的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7(3):114-124.
[21]李金.冲突与整合:现代学徒制中企业责任的双维价值向度[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7):47-52.
[22]李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新尺度、新挑战与新方向[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4-33.
[23]李政.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障碍及其消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8(9):87-92.
[24]方益权,闫静.关于完善我国产教融合制度建设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5):113-120.
[25]黄继生.网络嵌入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42.
[26]周英文,徐国庆.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机制分析——以美国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21(7):53-60.
[27]关晶.英国和德国现代学徒制的比较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1):39-46.
[28]王涛,陈金亮.双元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融合情境的组织合法性——兼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J].经济管理,2018(8):38-53.
[29]PENG,M. ZHOU,J. How network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evolve in Asia[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22):321-336.
[30]MCGINNIS,M.An introduction to iad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ostrom workshop:a simple guide to a complex framework[J].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1,39(1):163-177.
[32]李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制度要素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江苏高教,2017(1):85-89.
[33]梅伟霞.当前我国政企关系存在的三种风险及其防范[J].探求,2013(6):39-44.
[3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66.
[35]朱雪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61.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of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a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olycentricity Theory
Cao Jing, Shang Jiamin
Abstrac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olycentric theory,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can be assessed, and the inherent regulations and external expressions of the legitimacy of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organizations can be analyzed.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face legitimacy challenges due to the “unclear boundaries” of government actions and the “mediocre” supply of institutions, which constrain regulatory legitimacy. Additionally, legitimacy challenges arise from the “deviant behaviors” of organizational actions and the “lack of role”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ffecting normative legitimacy. Furthermore, cultural-cognitive legitimacy challenges exist due to the “newcomers’ disadvan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acquires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nder the overarching rules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s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from diverse institutional elements.
Key words" municipa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nstitutional logic; polycentricity theory
Author" Cao J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ormal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00); Shang Jiamin, postgraduate of Normal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