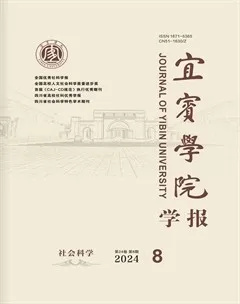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的“象天法地”意匠论析
关键词: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象天法地
中图分类号:G127;B958
DOI: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8.11
宜宾真武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区西北隅,南俯戎城,西连翠屏山,北瞰岷江,东眺天柱,与三塔对峙,是集山水、树木、文物古迹、三江自然景观和翠屏山为一体的整体风景区。在四川道教史上,素有“北青城,南真武”之说。明隆庆元年建三台书院,其中作为祭祀场所的文星祠(今文昌宫)为道教神祇入主真武山之始,在此以前没有任何宗教建筑。[1]明万历元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奉命征讨都掌蛮时,托词真武祖师助其师,平蛮后于次年扩建原有真武祠,而这正是效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借助真武大帝“显灵”的幌子,即位后又大规模敕修武当山这一历史事件[2]。这使得真武山之名大盛并得以传播,随后真武山得到极大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经专家结合相关史料论证,真武山现存古建筑的始建年代都在明代中后期[1],因此可以得出真武山道教的空间形态在明代已经定型。佛教于清代入主真武山,由于清王朝崇佛抑道的统治思想,真武山道教逐渐衰落,佛教虽基于传道布教的需求对衰败的原宗教建筑进行了培修和改建,但并未对整体空间形态进行改变,清代真武山形成佛道并存的局面。在近现代时期,真武山宗教势力逐步退出。1996年,宜宾真武山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
明隆庆年间邑人周爻著有《三台书院碑记》:“孔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昔者,圣人仰观俯察,以尽裁成,辅相之宜,盖取诸此……丙寅夏月,偕郡人、观察使苏溪卞君,陟彼三山,眺此三江,心怡神爽。爰请于当道,建置三台书院。中为文星祠以主兹山之胜……夫天之三台,象也;地之三曜,形也……”[3]225-226通过此文可以看出,三台书院营建之初就秉承了古代“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为道教神祇入主真武山之始源,加之曾省吾效仿明成祖建武当山之举而增建真武祠,因此在统治阶级推崇道教和真武大帝的时代背景下,真武山道教的营建必会承续“象天法地”这一规划思想和文化基因。由于真武山经历各种动乱,所留史料和图文甚少,从科研检索来看,对其学术研究成果偏重于宗教史略论述、文物考古发现、古建筑文物保护等方面。本文通过对真武山进行实地考察和查阅相关文献,结合中国古代“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对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的意匠进行探讨,以期拓展、补充宜宾真武山道教研究。
一、“象天法地”的文化观念
“象天法地”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周易·系辞下》中,“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304。古人通过长期实践和观察,掌握了恒星和行星的运动规律,同时在日月众星、人间万物及神话传说之间建立联系,古代天文学中传世的天文图空间结构代表了古人对“天”的深刻认识,并形成包纳了表征形象和文化内涵的完整体系。天文图的空间结构,其中以《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和《步天歌》为代表,分别为“太微、四守、二十八宿”“五宫、四象、二十八宿”和“三垣、二十八宿”三种空间格局[5]。传统的天文学制定了历法,指导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同时人们也通过观测天象来预卜吉凶,并从中找到对未知神秘的解答,因此上观天象和下察地理成为古人普遍的活动实践。《史记·天官书》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城。”[6]119出于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崇拜,古人将对星空的认识投射日常生活,形成象天法地的空间结果。
陈春红认为,象为模仿的表现之义,象天为模拟天象,法为施法、效法,法地为效法大地和自然环境的法则;“象天法地”的含义是指人们通过参考天体位置或其形象及其所呈现出的天文现象来创作建筑或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这种“人为”的设计发生在人们观测天体了解天文知识之后,而这些天文知识的形成又发生在天体基本形态和天文现象的存在以及由其衍生的“文化精神”之后。[7]“象天法地”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典史上记载的“定之方中”的楚国宫城、伍子胥“象法紫宫”的吴都阖闾城、“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秦咸阳都城等都是“象天法地”原则运用的典型代表。中国很多古代都城通过对天文形象,特别是对星象的具象模仿或抽象隐喻,表达城市空间布局与“天”的同源同构关系,同时又通过这种关系表达特定的“文化精神”。
二、真武山道教的空间形态
宗教场所空间形态是指宗教场所空间在一定地域、一定时间范围内,各构成要素所表现出来的空间形态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宗教场所空间形态从人的认知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及微观等层面。[8] 本文主要从山水形态、山林形貌、建筑布局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真武山道教的空间形态。
(一) 宏观层面——山水形态之“四象环抱”格局
“风水”观念和“象天法地”观念都源自《周易》,且两种观念均涉及“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象天法地观念中的“四象”对应天神系统中的星宿神祇,风水观念中以“四象”对应风水要素中的地形地势和山川河流。在某种意义上风水与工艺、建筑具有相近的美学特征,同属“表现性空间艺术”,都以可视性的形体诉诸视觉,以其创作材料的质感、结构及其布局的形式感作为其重要的审美因素[9]。结合前面关于“象天法地”的论述可以看出,“风水”观念和“象天法地”观念同本同源,都是古人进行空间环境营造的方法体系,二者都具备“表现性空间艺术”的美学特征,因此“风水”四象和“象天法地”四象具有一致性。在道教风水思想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格局,《易经》一书认为山为静止的,应属阴;水则是流动的,宜属阳,故“负阴抱阳”即是“背山面水”之意[10]。传统的风水理念中,背枕龙脉(玄武)、左右砂山(青龙白虎)环卫、前面河流(朱雀)环绕、隔水有案山相迎,则形成“枕山面屏”“气聚风藏”的理想风水格局。然而在现实中不可能每个场所都符合理想,因此局部风水要素是可以转化的,如在村镇中或者城市中的建筑选址,可以将主体建筑右侧的道路视为砂山白虎,左侧的河流视为青龙,并于主体建筑轴线正前方人工修造半月形水池作为朱雀。
清乾隆年间,邑人周潜修撰在《古师来山碑》一文中对真武山形貌进行了描述:师来山发源于峨眉,蜿蜒逶迤,由西北而南下,盖即郡城之祖山也。山高可六七里,巉而不削,骨而不肤,直而不孤,秀而不露,旷而豁,曲而幽,侧而峰,横而岭。如太华之有少华,太室之有少室,太岱之有梁父,真灵区也。[11]250-251文中的“师来山”即真武山的另一个名称,比拟太华、太室、太岱的描述说明真武山具有名山之姿,“祖山”和“灵区”的描述说明真武山为风水之地。从宏观区域的山水空间形态来看,真武山北临岷江,遥对宜宾江北片区;东眺长江,遥对催科山山系;南俯戎城,遥对金沙江和南岸片区;西枕翠屏并与其连成同一山系,山势整体呈东西走向,西高东低,山上峰峦起伏、古树名木挺拔。结合风水理念,真武山符合了“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风水总体格局:翠屏山系绵亘于后,呈龙脉之象;翠屏山海拔高于真武山,成为真武山背枕之主山,对应玄武星象;真武山正对的三江口水域乃金沙江和岷江汇合之处,并形成长江绵延东流,对应朱雀星象;北面的岷江和南面的戎城则寓意左右沙山,分别对应青龙和白虎二星象,催科山隔长江与真武山相对,如案屏相迎,对应案山。综上所述,真武山宏观的山水形态形成“四象”的环抱之势态,具备风水总体格局,这也和“象天法地”四象具有一致的意象联系。
(二)中观层面——山林形貌之“壶中天地”意象
道教主张“道法自然”,崇尚自然无为,返璞归真,敬仰大而无垠的宇宙自然空间,希望人能融汇到宇宙中去,从而得到永生。道教理想的修仙境界三种模式:昆仑山模式、蓬莱模式、壶天模式。其中昆仑山模式意指为拔地通天、与世隔绝的高山;蓬莱模式意指远隔重洋、偏远孤绝的海岛;壶天模式也称洞天模式,意指地理环境优美、幽深僻静、四壁围合的山林[12]。这三种模式各不相同,又有共同的特点,与世隔绝,非仙羽所不能及的,超越现实并不可及的理想模式,体现的是道家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东晋时出现了洞天福地之说,包含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均系国内著名山岳和洞窟的雅称,故凡名山大岳几乎都有道教的足迹,这种理想的仙境模式一直影响了道教场所的选址。
真武山另有两个流传更早的名字,即“师来山”和“仙侣山”[2],其均得名于神仙传说,其中师来山的传说为道教祖师张天师入蜀隐居而经过真武山,“仙侣山”的传说源于杨仙和郁姑相遇于真武山,并得道修仙。道教把幽静的山林看作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也是避开尘世、接近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修仙得道之地,从真武山道教的相关神仙传说来看,真武山是求仙得道的理想之地。从山林形貌来看,真武山道教为典型的山林道教,其位于山林自然环境之中,由山门、香道、观门及各式殿堂组成,形成一个以宫观为主体的、与外界隔绝的、幽静而安详的空间环境。从真武山现存道路和现有古建筑群来看,真武山建筑群依山就势,布局灵活,建筑群落的平面组合不刻意追求轴线对应关系,但却结合地形高低和建筑形态强化着纵向轴线。初入山门时从外围不可窥得真武山全貌,宫观建筑群“隐”于山林之中,沿香道入山后各宫、殿、洞、台等建构筑物一一呈现,如入“仙境之地”,序列末端是地势最高的文昌宫建筑群,在此整个空间序列达到高潮。这种先抑后扬的空间效果和步步攀高的游走流线象征“心坚克难,寻仙悟道”的天路历程,同时也体现了“壶中天地、内藏乾坤”的仙界意境。
(三) 微观层面——建筑布局之“北斗七星”形态
北斗星通常指北斗七星,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故名北斗,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分别把它们称作: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星斗崇拜和星占之说,北斗七星被人们赋予丰富内涵,逐渐形成北斗崇拜。道教重视北斗七星的崇拜,称“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凡是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后北斗七星被人格化为玄天上帝,也即真武大帝,其相貌多呈披发赤足(或头戴圆帽),手持北斗七星剑,右脚踏蛇,左脚踏龟状,人们祈求延生长寿,都要奉祀真武大帝。
《古师来山碑》还记载了旧有的建筑布局情况,该碑记内容成为今天比照真武山古建筑群原整体布局的重要参考,碑记记载:“昔人伐石为梯,约二百余级,稍得平地,俗所谓头天门也,建有关帝殿。循此而上,如蜕龙之脊,为二天门,再上为三天门。更近数武,势颇平衍。前为灵官殿,后侧为救苦殿,中则筑石为台,构楼其上,楼高数仞,宽广如之。上可坐数百人,下可建数丈之旗,窗棂屏槅,皆可去取,是为望江楼……楼之下有谷,涧水沮之,跨以石桥,桥下聚水为池。池之北有小殿,折而右则山径迂回,凡数折始至第一峰,即元极宫也。宫后为释迦佛殿,殿最后郁姑台遗址犹有存者。其西则斗姆宫,三府宫,文昌宫,星罗棋布,前人之修创备矣。然不过百数十年而高楼既已倾,曲池亦已平……” [11]参照该碑记描述,结合真武山现存布局来看,处于外围的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关帝殿、灵官殿、救苦殿、遇仙楼等已毁;作为庙群主体的望江楼、祖师殿、玄祖殿(无极宫)、无量殿(原释迎佛殿)、斗姆宫(斗姥宫)、三府宫、文昌宫、谒仙桥等宗教建筑尚存,并保存有杨仙洞、郁姑台遗址和多座汉代崖墓,其间衬以若干名树古木,当年风范犹存[13]。玄祖殿、无量殿、斗姆宫、三府宫、文昌宫等主体宫观建筑群位于真武山最高处;望江楼、祖师殿和放生池组成的建筑群落位于真武山山腰处,通过登山步道和山上主体建筑群相接;导引空间(原香道)从山脚下的山门开始,随山就势衔接到真武山山腰处的望江楼。若复原《古师来山碑》中所记载的被毁宗教建筑物,并遵循真武山的游走流线来看,真武山道教的建筑布局具备“北斗七星”的空间形态。沿山门上山至望江楼的香道流线形态如北斗七星的“斗杓”,若复原三座天门及相应建构筑物,则以三座天门为代表的建筑群分别对应组成北斗七星“斗杓”的玉衡、开阳、摇光三颗星象;现存的古建筑群平面布局形如北斗七星的“斗魁”,将其分解成以文昌宫为中心的建筑群、以三府宫为中心的建筑群、以玄祖殿为中心的建筑群、以望江楼为中心的建筑群,则分别对应组成北斗七星“斗魁”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颗星象。综上所述,可以推断真武山宫观建筑群的原始空间布局结合了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宿形象,以“北斗七星”的形态布局建筑,同时也强化对主神真武大帝的崇拜。
三、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的“象天法地”意匠——与天同构、天人合一
“意匠”一词,原指作文绘画时的精心构思;建筑之意匠,指的是指导建筑规划设计的哲理和原理、原则及其追求的艺术境界。[14]“意匠”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感知层面,代表外化的意象表征;一是内涵层面,代表内化的文化思想。真武山道教秉承“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其意匠表达着特定的意象和内涵。
(一)“与天同构”的空间意象
在古代天文图的空间结构中,“拱卫”和“居中”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从《史记·天官书》复原的天文图来看,“五宫、四象、二十八宿”呈现的结构体系是四象拱卫中宫,中宫居中,凸显中宫的至上之位;从《步天歌》复原的天文图来看,“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呈现的结构体系是“四象拱卫三垣”,三垣又以太微垣和天市垣拥立紫微垣,紫微垣居中,紫微垣也称中宫。“五宫、四象、二十八宿”和“三垣、四象、二十八宿”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总体观念均是强化“拱卫”和“居中”的结构关系。中宫象征人间帝王的宫殿在天上的位置,这里的星宿大多以皇宫中的人员和事物来命名,北斗七星就位于中宫,它象征皇帝外出乘坐的御车,“四象”居于东、南、西、北四方,比喻周边护卫城池,这种拱卫和居中的结构关系强化了“中宫”至尊的观念,而古人“象天法地”设立都城时将皇城宫庙居中设置,也正是为了寻求天地镜像和同源同构,从而强化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的思想。
从真武山的空间形态来看,宏观层面的山城具备“四象环抱”形态,周边的山城和真武山形成了天文图空间结构中“拱卫”和“居中”的关系;中观层面真武山的山林形貌隐蔽围合,内有乾坤,各宫、殿、洞、府等道教建筑中供奉不同等级层次的神祇,其中既有地位崇高的三清四御等道教至上之神,也有修炼得道的仙真,这构成非仙羽所不能及的天宫仙府,因此真武山呈天文图空间结构中的“中宫”形态;微观层面真武山的建筑布局呈“北斗七星”形态,合乎天文图空间结构。
由此可见,真武山道教的宫观建设采用了“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本着“法彼上天、天地同构”的初衷,以古代天文图空间结构中的“中宫”为意象之源,其场所营造隐喻“天宫仙境”在人间的映射和对真武大帝的至上崇拜,这与当时明王朝推崇道教,强化其在西南区域的王权统治具有关联。
(二)“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道家以“天道自然”作为理解天人关系的核心,还天以自然之天,讲究“以天合天”,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用“我”之自然去合“物”之自然,使人的自然与物的自然相契合;道教的天人合一就是修炼者与身边的人、物、山、川、日、月、星辰等大宇宙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15]老子的“道法自然”虽没有明确提出“法天象地”思想,但其“法自然”的美学思想,即是对自然的遵循,是“法天象地”思想的渊源,天地之间的运行范畴中,“道”可以回归自然,也就是法天象地的根本,所以法天象地者,即是行其道也[16]。
真武山道教建筑规划结合了“象天法地”的观念,通过对城市格局、山林形貌、建筑布局的综合考虑,形成了人与环境的协调。真武山四壁围合,隐于山林,“隐”才能超尘脱俗,静心修炼;主体宫观建筑群建于山体高处,宫观中供奉各大道教神祇,“高”方可通天近神,遇得仙缘。正是基于道教信众“隐修”和“通神”的需求,真武山道教在理想环境的营造中把宗教信仰、天文星宿、地理环境等因素结合起来,通过“象天法地”的规划设计思想将“天宫仙境”映射到人间,以求“天人相通”,践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念,追求天、地、人的融合统一。因此,真武山道教场所的营造实现了道教自然时空模式与人文时空精神的相互融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
结语
宜宾真武山道教宏观的山水形态、中观的山林形貌、微观的建筑布局三个层面的场所隐喻和物质营造形成了“象天法地”意匠,即“与天同构”的空间意象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建立了空间形态和人文内涵之间的联系,这对发掘真武山道教之精彩或有拓展补充,特别在当前城市存量更新和城市森林公园建设的背景下,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