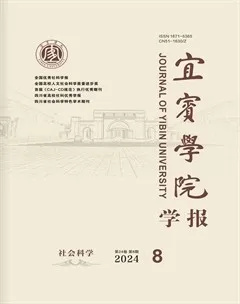西方中国民歌研究现状及其启示
关键词:中国民歌;跨文明比较;他者视角;海外汉学
中图分类号:J607
DOI: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8.09
中国民歌因其简洁朴实性、基于集体传唱的生动灵活性特征,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对象。西方对中国民歌的研究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汉学家大力推动中国民歌研究,发展至今已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荷兰汉学家施聂姐认为,“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民歌是一个相当容易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尽管它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处于中心位置……中国古典诗歌的伟大遗产——包括文人改编的民间诗歌——已经被汉学家更加细致地广泛研究”[1]。倭讷(E. T. C. Werner)也谈道:“在中国发现的民间资料已被一些有能力的学者进行了部分调查,但这个领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由于中西文化语境、学术话语等方面的差异,西方中国民歌的研究尚未得到国内学界足够重视。事实上,西方学者采用了与国内学者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他们融合学术前沿研究成果,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去调查和阐释中国民歌,拓宽了中国民歌的研究视野,对国内学界具有“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同时,由于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性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影响,西方学界在开展中国民歌研究时,不免出现某些偏见、误读和变异等情况。在提倡跨文明对话、跨学科互鉴的当下,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理性认识西方中国民歌研究的优势和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中西学者在中国民歌研究领域的交流互鉴,推动以中国民歌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及其影响力的提升。
一、西方学界的中国民歌研究概况
西方对中国民歌的研究,按类别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译介类专著。西方对中国民歌的译介类专著及论文多以介绍普及性资料为主,主要集中在20 世纪出版或发表,有倭讷的《中国小调》(Chinese Ditties,1922)、谢廷工和郭长城合著的《中国客家:他们的起源和民歌》(The Hakka Chinese-Their Origin amp; Folk Songs,1969)、伊维德的《激情、贫困与旅行:传统客家歌谣》(Passion, Poverty andTravel——Traditional Hakka Songs and Ballads,2015)等。此类资料对于了解中国民歌的海外翻译现状十分重要。
其次,学术类论文著述。以美国学者苏独玉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民俗学学者对于民歌的研究更倾向于围绕历史、社会、文化、种群的背景界定。苏独玉于1988年提出名为“传统构想”的研究方法,以中国西北地区(青海、甘肃、宁夏)的中国民歌“花儿”为研究对象,将这一民歌题材置于社会语境中,把“传统构想”的理念付诸实践。苏独玉的代表性专著及文章有《中国传统的构想:以花儿、节日、学术研究为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声音维度—— 音乐表现与转型》《文体的社会生活——中国民歌的动态》《文化隐喻与推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与思想》等。汉学家、民族音乐学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运用社会学、人类学、音乐学等方法详细分析中国民歌。陈璐萱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歌:古老民族的宝藏》(Chinese Foik Song: Hidden Treasures ofAn Old Nation, 2000)中,讲述了自己的调查实例,并以历时性歌曲的创作发展为主题,阐释了这些民歌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另外还有查义高研究的“川江号子”、葛融研究的“中国陕北民歌手王向荣”等。西方的学术类研究著作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特点,尤其是关于汉民歌的分类方法,西方学者较多使用机器学习及统计学的方法,相较于国内研究,西方学者研究更加注重综合性、科学性和逻辑性。
再次,具体作品及艺术形式的研究。此类研究占比较大,多数为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中国民歌对某一作曲家、某一作品的影响。如C. Chang amp;Richard Cornell的博士论文《弦乐四重奏〈祖国民歌〉》分析了这部弦乐四重奏;常朝建的《以弦乐五重奏、三个打击乐手和电子声音制作的〈我的祖国〉民歌》(The Folk Song from My Fatherland forString Quintet, 3 Percussionists and ElectronicSounds)分析了以弦乐五重奏、三位打击乐手和电子音响而创作的乐曲;张怡的博士论文《东方遇上西方:盛宗亮钢琴作品的风格分析》(When EastMeets West: A Stylistic Analysis of Bright ShengsPiano Works)对美籍华裔作曲家盛宗亮近二十年来创作的钢琴曲风格进行了分析,以此说明盛宗亮在钢琴创作体裁上的发展与创新等。
二、中西方对中国民歌研究的比较
中国民歌作为中国音乐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影响范围、风俗内涵、接受群体等方面数量最多、传播最广、记载最完备,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对中国民歌的研究已有一百余年历史,西方学界的研究相比较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更注重民歌与中国文化、民俗之间的关系,往往从民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去窥探中国民歌及其背后的文化世界,不仅考察民歌的传承现状、民歌特色、民歌手的生活环境,还记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变迁、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给民间音乐生态带来的多元影响,体现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苏独玉是海外西北“花儿”歌研究的重要学者,她将西北“花儿”置于“中国传统”的框架内,融合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扩展和重新表述为一个称为“ 传统想象”(Imagined Tradition)的理念,认为花儿作为民族中的想象结构,具有特殊的“文化人造物”的属性。同时,她又引入音乐学和民族学的内容,探讨花儿研究和民众在政治、艺术和学术上的交叉和互动。而国内研究无论是从民歌的体裁分类,还是从旋律、节奏、调式、曲式等方面的理论归纳,更多的是注重民歌的音乐本体形态和资料的研究。
第二,更注重实地调查。一些学者为了研究原生态的中国民歌,已经不满足早期关于中国民歌研究的“二手资料”,他们多次来到中国,长期生活在中国民歌地区,采用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观察、采集和研究中国民歌,不仅展现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也体现出西方学者严谨、求是、负责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例如,施聂姐对中国苏州南部地区的山歌(吴歌)开展了长达十年的田野考察,她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对山歌(吴歌)的文化背景、文本、音乐、歌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她的专著呈现出充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整的工作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相较而言,国内研究有良好的实地调查条件,早期的民间音乐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建立在采风、走访等实践基础之上,“民族志”“采风报告”“案头分析工作”等研究成果细致繁多,学界因此出现对已有文献的二次研究、资料本体的细致研究等普遍现象,但整体缺乏宏观的视野,研究成果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力,随之也不能上升到全国乃至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理论高度。
第三,西方学者跳出文化语境,具有更加客观理性的研究视角。在人类学学科研究中,西方研究者更关注中国民歌中的民俗情歌,这里的民俗情歌并非婚俗歌一类以结婚为目的的民歌歌曲,而是单纯以性交为目的的,涉及性本身和以性爱为目的的民歌,这种主题在国内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禁忌视角。人们普遍有意地回避这方面话题,如杨民康提到“婚姻恋爱民歌与两性相与”,实际上,中国民歌中的情歌一种便是以求偶为目的的,总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寻求爱情、婚姻为目的;二是以寻求性伴侣为目的。前者多与婚俗、仪式歌等联系在一起,后者反映的是纯粹的性活动和风俗。[3]167他对性俗活动的描述较为隐晦,称其为一种“娱乐活动”。但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全球学术体系的研究者未回避这个问题,他们也敏锐地发现了国内学界对这一主题的回避,例如香港中文大学臧一冰称这种现象是由于“文化权利的限制”[4],杨沐认为:“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刊物上出现了一些民间音乐研究论文,涉及当地民俗中的‘婚姻’‘爱情’方面,有的则更明确地从婚俗入手对音乐进行探讨”,“这些文章有的也涉及性俗,但基本上是将性俗事象也纳入‘婚姻’‘爱情’范畴进行讨论的”[5]。
除此之外,从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民俗学、近年来兴起的新音乐学、女性主义音乐批评、音乐心理学、统计学、心理声学等视角的研究思路也被西方学者纳入中国民歌的研究,为中国民歌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三、西方学界对中国民歌研究的几个问题
经典民歌作品对于一个族群的文化性格特征的显现最具直接性,而正是由此属性,在跨文化语境的背景下,中国民歌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在向西方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也是中国民歌在域外传播范围不广、影响程度不深的重要原因。
(一)翻译问题
翻译是中国民歌语际传播的第一步,这是中国民歌在西方传播存在障碍的首要原因。民歌的翻译涉及歌词翻译和旋律翻译问题。歌词以文字为载体,具有整体的文学性特征,但夹杂了大量方言、俗语,独具的地方性在语言理解层面又“罩上了一层纱”,如何准确地翻译歌词便是一大难事;而旋律翻译比较繁杂,这涉及歌曲的韵味、风格和一系列民族性的约定俗成的演唱特征,且这些是无法体现在五线谱中的,需要对其有深入的文化理解才能恰当地表达这一“弦外之音”。由于民歌系统庞大,且西方学者主要来自民俗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领域,他们获得的材料往往是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虽然资料充足,但是没有准确的译文仍然无法支撑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因此民歌的文化传播遭遇瓶颈。
首先,歌词的文本往往存在汉语与英文演唱时不对等的问题。本雅明提出了跨文化传播中文本的“可译性”概念,并认为真正的翻译是对可译性的追求而非对原作的意义的追求。本雅明的“可译性”有两种含义:其一为能否“在作品的读者的总体性中找到胜任的翻译者”;其二为作品的“本质是否适于翻译”[6]。所以,作为民间文学的民歌,自古以来表达的是这一种族的风俗习惯,带有强烈的独立性,很难为外来者所理解,这就造成在“可译性”的选择上,研究者往往选择更易传播和理解民歌的手段。劳动人民创作的歌往往没有太高的学术价值,通俗的语言在可研究的质量和区别度上都较低,对于翻译来说这是一种比较贫瘠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民歌歌词进入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时,歌词的含义往往没有那么重要,而将最朴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出来才是译者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在劳动号子的翻译过程中,由于歌词多为叠字音节,文学内涵较低,所以在可译性的问题上选择直接音译,若以英语单词呈现反而累赘。
其次,汉字的单音节结构与英语语言中的多音节不对等。在演唱过程中,汉字的发音习惯往往与英文不同,同样的含义若译为英文,会破坏歌曲原有意境。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Lu-Hsuan博士,在翻译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时,在“月亮出来亮汪汪”一句时,译为“moon comesout shine brightly shine brightly”,其实这样翻译并不准确,“月亮出来”一句在这里本意表达的是月亮升起的状态,是阿妹盼望着阿哥终于等到月亮升起的随时间变化的心情,而不是单纯的“comesout”,这样的翻译,并不能表现出阿妹对于阿哥的“思念”,造成的原因在于象形文字(汉语)与拼音文字(英语)的不同,二者追求“同一性”基本不可能完成。德国哲学家潘维茨(Rudolf Pannwitz)指出“翻译家的基本错误是试图保存本国语言本身的偶然状态,而不是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来语言强有力的影响。当我们从一种离我们自己的语言相当遥远的语言翻译时,我们必须回到语言的最基本的因素中去,力争达到作品、意象和音调的聚汇点,我们必须通过外国语言来扩展和深化本国语言。”[7]280所以,翻译过程需注意根据外在文化语境,适当调整原文含义,在不影响美感的前提下尽量还原包括音节在内的本意才是恰当之举。
(二)界定问题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西方,人们对“民歌到底是什么”仍有很大争议,有的将作曲家用民歌材料创作的作品称为民歌,有的将词作家重新填词的音乐作品称为民歌;更有人将中国流行情歌当做民歌……大多认为只要是“俗曲”都可以称为民歌,但这种界定并不准确。学界对于中国民歌的界定有“口传心授”和“专家创作”两种标准:一类是具有口传心授、在民间自由传播、非专业创作的性质歌曲,这类歌曲的作者通常不会留名,具有“原生态”的属性;另一类是专家创作的具有民歌元素的歌曲,是作曲家、音乐家设定主题并融入民歌的元素,精心编曲、作词,专业创作出来的歌曲,这类歌曲是有明确作者的。如《康定情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是原西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歌,虽经李依若填词,吴文季、江定仙对原始曲谱进行改编,但是未脱离原民歌的基本曲调,是由中国传统民歌发展来的,所以《康定情歌》属于民歌。而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如《我的祖国》《映山红》《绒花》《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等常被误以为是民歌,它们的传唱度也十分广泛,具有民族代表性和一些民歌的风格。但是,它们都是由音乐人精心创作的歌曲(有具体作词者、作曲者),虽然这些歌曲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传唱度和影响力,但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歌,而是属于创作歌曲。
西方学界存在对民歌界定混乱的现象,不少研究成果以“folk song”为题但内容却与中国民歌毫无关系。如The Prof. Fuzz 63乐队于2016年由Dreamy Life Records出版社发行专辑Chinese FolkSongs(《中国民歌》)、Lily Chao(赵晓君)演唱的CD专辑《中国民歌》(Chinese Folk Songs)、OrganicThree 乐队的《巴赫和其他中国民歌》(Bach andOther Chinese Folk Songs)……均未涉及民歌或相关素材。
(三)异质文化问题
文化的“异质性”是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大壁垒。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民歌时看到了许多让他们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由于不同文化、不同国情和不同思维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学者认为,在研究中国民间艺术上,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研究范围会受到政策的限制,这使得采集调查并不充分。其实,西方学者非常认同中国学者关于民间器乐结构分析方面的学术研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是唯一比较便利、不会受到阻碍的。许多人将民间艺术认为是植根于仪式和(半)宗教实践中,是“封建迷信”,需要被消除……这便导致在民间音乐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往往忽视其仪式、宗教、文化的背景,而倾向于单纯研究音乐文本方面。
第二,国内学术研究没有及时与国际学术前沿同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界的孤立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有各种原因阻碍他们参与到国际学科前沿的讨论中,这表现在西方音乐学前沿文献在国内的译介不及时,国内较难获得西方全面的学术资源;中国的学术前沿的成果资源,没有在国际学界中得到共享并产生影响力。
第三,中国的音乐研究的学术传统与音乐美学知识、音乐阐释能力有关,充满直觉感悟式的体验,这有时会悖于客观事实和经验;而西方学者的思维通常强调客观和理性。产生这种差异在于:
首先,东西方文明有着明显的异质性,审美标准不一。文化的异质性导致了中西方对中国艺术审美价值截然不同的理解,如泰戈尔1924年在北京讲学时,他所宣扬的先验性美学对当时的中国人实在难以理解,现场感觉似“对牛弹琴”,事实上听众并非怀有敌意,只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其次,西方人并不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西方霸权主义统治的世界格局之中,西方人已经习惯了全世界都模仿他们的生活习惯、服饰、审美、思维、艺术等,他们掌握文化主导权,“西方人认为应该是东方适应西方,而不是向东方学习。但是传统的东方价值、社会模式和艺术技能正开始在西方,并常常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们的表达途径,进而开始对西方的文化产生微妙的影响”[8]296,西方站在代表“国际形象”的制高点,通过各种手段对这种现象进行矫正。文化是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向世界的输入呈现并非持欢迎的态度,而是用各种贬低说辞成为其文化阻拦的掩耳之门。
四、西方学界的中国民歌研究启示
民族音乐在国际音乐领域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中国民歌自被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发掘传播以来,其“他国化”的变异活动正是西方接受中国民歌的重要体现。曹顺庆等认为“在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除了可以确定的实证性影响研究因素之外,在文化过滤、译介、接受等作用下,还有许多美学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难以确定的因素作用下,被传播和接受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9]。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体系中,形象学、接受学、译介学都可以说是变异学的一种。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民歌的歌词内容、旋律走向、唱法特点尽管大体稳定,但也会随着不同的演唱者和演唱的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对象而发生改变,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语词上发生变异,产生诸如中国民歌在西方传播过程中艺术形象的变异、接受以及“他国化”现象。综上所述,在比较分析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西方学界的中国民歌研究融入了前沿学科理论。例如,在民歌研究过程中,传统的中国艺术理论往往重视对文本的分析,通过文本的深刻分析来找寻内部规律;而西方学者善用社会学、历史学理论,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广阔的前沿学术思潮下,通过与不同研究方法的交融,以拓展其研究视野,更新传统认知。再如,国内对中国民歌书写的关注更胜于对创作者的关注,导致对民歌本体过度解读,如研究各式各样的民歌分类方法、五花八门的行腔和演唱法等;而西方学者则着重以人为研究重点,将民歌手置于最重要的“文化传承者”的地位,研究他们的艺术思想、创作理念、为民歌发展做出的贡献和价值等。如葛融的《民歌之王:连接着当代中国的人、地点和过去》,以民歌手王向荣和其他歌手为研究对象,通过民歌手进而探讨民歌的表演、创作、思想观与在他身上呈现的传统、现代、乡村、城市和社会变迁问题等。
第二,西方学界采用田野调查和原始资料的研究值得借鉴。学术研究大量引用、借鉴“第一手资料”,是西方学者们研究中国民歌时的特点,因为民歌的“口传心授”“即兴”等特征,使其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学者亲自前往发源地进行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储存、归类进而进行研究分析。例如施聂姐,她从1986年开始对中国苏州南部地区的山歌进行了从研究视角、背景、文本、音乐、歌手等一系列的研究考察,最终于1997年完成出版了专著《中国民歌和民歌手:苏南的山歌传统》,此间的调查长达十年,令人钦佩。西方大量的民歌研究资料多是学者们在进入发源地考察过后整理完成的,这无疑对相关研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西方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视、对待学术的严谨求实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西方中国民歌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拓展。民族主义者称,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的方法论进行分析,试图将中国艺术纳入西方艺术研究的领域中,以形成“中国学”这一西方学术体系。从学术全球化角度讲,每一次方法论的拓展也将带来研究成果的飞速发展,打开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再者,西方研究也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纠错、不断前进的过程,从研究分析来看,西方学者从早期对中国民歌传播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到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民歌“宝藏”式的尊称,并在20世纪末掀起民歌研究热潮,其艺术自律性、再创作的多样性、市场的丰富性成为研究热点,持续修正了早期对中国民歌研究的误读,还原了文化遗产,贴近了艺术真貌。
第四,在中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在中国的“海外汉学”,西方的“中国学”学科领域不断交融的现状下,西方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前沿视野的华人留学生,包括常住海外的华人,这一群体所拥有的东西方视野,为国际学术舞台贡献出了东方话语,也为国内艺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西方学界中国民歌研究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如旅澳并担任教职的学者杨沐、旅美并担任教职的作曲家周文中、陈怡、盛宗亮等,他们不仅将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各地,还在北京、天津、香港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经常传递海外学术、音乐的前沿信息,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五,面对属于“异质文化”的中国民间艺术,西方学者在接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选择、再创作乃至于创造性的叛逆,进而出现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的现象。但是,“过滤与误读不仅体现了接受者在文学交流中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而且扩展了主题文学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接受者的文学,为交流主客体提供了互识、互证、互补的通道” [10]170。因此,理性地看待西方研究的有益之处,结合国内自身研究现状,以寻求学术突破和创新,才是对西方研究的回应。除此之外,对西方学界的理论除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寻求互动外,还应坚守住中国文化的根基,对扑面而来的西方繁杂理论要进行辩证地思考和吸收。随着世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异质文化间的吸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我们更应该在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洪流中坚持文化自信、坚守思想独立,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中西文化交流对话中自我建构、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