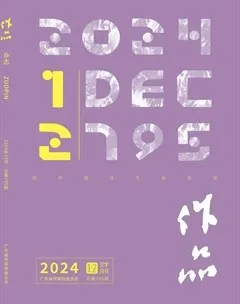在双重经验中的文学原创(随笔)
近几年,我专注于海外新移民小说的写作,并注重双重经验中的文学原创。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新颖独特的,有着与众不同的别样感觉。我曾停笔多年,始终认为作家的写作必须停顿和补充,不能像机器那样长年累月地批量生产。因此,2009年我访学于斯坦福大学,后又去康奈尔大学进修后,我就停笔了。我停顿下来潜心读书,是我真正的“放下”。一个人要有“舍”,才有“得”,就看你如何选择。
其实写作是个积累的过程,有时我想,从前我对写作的追求是一种智性表达。智性在语言表达里有四种:苏格拉底的死亡式、耶稣的神性式、孔子的虚幻式和佛陀的虚无式。停顿写作前,我仿佛是为虚无而写作。我的虚无感常常有流浪者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穿梭,他们成为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心灵是漂泊的、流浪的、转换的,也是寻找的。比如:我的中篇小说《无家可归》中的叶凌,《走出荒原》中的沈越,《精神家园》中的周梦琪,《逝去的玫瑰》中的邬云云,以及长篇小说《杭州女人》中的池青青、苏艺成等,从这些主人公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永无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怯懦和无奈。我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一书中,观察着女性是怎样被自身的虚幻性所击败的事实过程,又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中,探索女性在逆境里的智慧、柔韧、坚强和力量。
这种探索使我觉得女性在各自的视野里,及不同的生活经验中,提炼自己的智慧、提升到一种哲人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2005年,我出版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就是以哲思的力量来表达思想和故事的。
有了这种理念,我总是热衷于女性题材的小说写作。女性写女性,比之男性写女性更有一种切肤的感觉和心灵体验。写女性是我的使命,我所要表达的女性世界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也许,只有高尚才能使女性进入一种更理想的境界。我的写作和阅读、表达和交流已成为一种过程。过程是美丽的,它使我在如泡沫一般的圆球上呈现自己,以及整个宇宙。因此,我从前写女性题材的小说时,比较关心女性文学的历史。
如果要说女性文学,那么要从中国女性几千年的历史来说。我想,在封建社会女性是很可悲的。她们实在活得太压抑,太没有自由了。她们没有机会像男人那样读书,游历山川,在仕途上进取,或者去做教师等多种工作体验;也不像我们现在的女性那样,可以表现自我,可以出门旅游,更别谈出国了。她们什么机会也没有。她们只能在家里等待着丈夫回来,丈夫就是她们生命中的唯一寄托。所以较早出现女性手笔的文学作品,主要就是表达一些情感的东西,譬如:春闺啊,春怨啊,还有私定终身后花园啊,等等。
“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中,女性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所有关于写女性的作品,也都是男人写的。但男人写女性未免有不周全之处,这是事实。因此女性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就像一个羸弱的女子。她们头上插着簪钗,大襟衣衫上斜插着手帕;她们的心也想像头上的簪钗那么硬,但在那种环境她们又硬不起来,只能拿着手帕擦眼泪。那时候文学的功能之于她们,就是手帕的功能。
到了“五四”时期,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女孩子,进学堂读书受到了教育,接受了新思潮。她们开始想冲出禁锢的“小我”天地,投身民族解放的“大我”世界里去。这时候女作家庐隐说:“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
所以我国女性文学的起点,是“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提出。“五四”时代,也就是“人的发现”的时代。但在后来的三十年中,女性文学也没有形成气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女孩读书还没有普及,读书的女孩也不是人人热衷于写作;而写作的那些女性,由于自己生活空间的狭窄,除了爱情和婚姻,其他社会性题材很难涉足。这就使得女性的写作题材十分单一。那时候要想这个文学羸弱的女子丰满起来,实在是不可能的。尽管出现了萧红和张爱玲,还有其他的一些女作家,但总归形不成“群芳谱”的格局。她们也只能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坛上,成为几抹亮丽的霞彩。
不过,我倒是蛮喜欢萧红和张爱玲的,她们一个去过日本,一个后来到美国定居,直到去世。她们也可说是双重经验中的文学写作者,但她俩各有特点,都是精神贵族,只是由于出身、经历等的不同,其作品也就大相径庭。当然萧红比张爱玲境界更高一些,苦难更重一些,生前死后也更寂寞一些。萧红集国难、家愁、个人悲痛于一身,灵魂和肉体都受到严重创伤,而她的文字,却是血泪和生命绽放的花朵。《生死场》《呼兰河传》《后花园》以及《北中国》《小城三月》等,都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思想价值,成为中国文学的重量级作品。
很多年前,我去过萧红的故居。它坐落在呼兰县城一条冷清的街上,两扇黑色大门关闭着。我们买过几元钱一张的门票,从边门走进去,却没看见有其他参观的人。如此冷清,让我感到意外。这场景仿佛正应了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说过的:“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
张爱玲生前死后比之萧红,可就热闹多了。二十三岁写出《倾城之恋》的她,也应了她“出名要早”的话。这句话后来被不少年轻人效仿,而效仿她最多的还是她的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没有人去效仿萧红的作品,而偏偏那么多作家作品中都有张爱玲的蛛丝马迹?我想一方面是她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也就是她的“现代感”和海内外居住的双重经验比萧红多,比较适合当今年轻人的一些梦想。
其实写作就是表达思想、阐述见解和立场。但真正要写好并不容易。因此,我在2020年夏天恢复写作时,我就想,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达呢?
这就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恢复写作后,我也恢复了从前的勤奋,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齐头并进。不同的体裁,是不同的表达。有时内心的情感强烈时,就想写写诗。有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表达出来就是一篇散文。当然沉浸在小说想象里,暂时逃离生活中的现实,之于我是一种精神世界进入海洋的感觉,仿佛让我枯燥乏味的生活涂上了色彩,实在是件美好的事。因此只要进入写作,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我的心情总是不错的。
我最早是写诗的,特别讲究语言功夫和诗性的语言精神。我读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发表诗歌,但我现在写小说之余仍然写诗歌。我写过一首三百六十多行的长诗《女性独白》,被《诗选刊》选载,这首属于现代派的诗歌吧,是当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写的,因此有较多的西方经验。
应该说,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劳动者。他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人的生活,从何种角度去审视社会、历史、生命自然。因为这种精神立场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作者的创作,将如何选择自身艺术表达方式的问题,以及尽可能抵达的艺术深度。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的时候,诗作者们对诗歌的虔诚与狂热,令当今的文学爱好者难以想象。那时候的诗坛是以北岛、舒婷们为代表的诗坛。到了80年代中期,诗坛色彩纷呈,主义林立。热闹的年轻诗人们谈起诗,就像谈一种手艺和技术。他们把诗当作由语言作框架结构的艺术品,认为只不过是谁心灵手巧,谁就可能登峰造极的一件玩意儿。其实不然,诗歌创作是与生命体验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了诗歌的质量。而这期间,国内的诗人们出国越来越多了,诗坛普遍倾向西方诗歌。
在我的写诗朋友中,他们一谈起诗歌就会搬出叶芝、艾略特、波德莱尔、马拉美等等,当然我也蛮喜欢这些西方诗人,尤其喜欢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她的诗醉心于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把悲剧式的自我揭露推到了极端。譬如,她在一首《晨歌》中这么吟唱道:“一声哭,我从床上滚下,母牛般笨重,穿着维多利亚式睡衣满身花纹。你嘴张开,干净得像猫的嘴。方形的窗。”我从她这里学到了如何运用意象。不过对于西方诗歌,我始终认为在吸收营养的同时,更要回归自己的土地,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也替代不了谁。
有一天我忽然想如果我们把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和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融合起来,那么我们要表现的诗歌就是一种新的东西了。于是,当时我开始写最适合表现我所在地域的诗歌。我80年代出版的诗集《火的雕像》和《西子荷》,就是以西湖为背景,抒写了自己当年的心境与情境。这就是我独有的东西。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中国的西子湖畔,而不是普拉斯的美国社会。当然这两本诗集里,除了写西湖也有写别的,譬如《圆明园》一诗。《圆明园》这首诗,2002年还被收入南京的高考模拟卷,收入很多诗选版本。全诗是这样的:我来看你了/看你残壁下的小花/断柱旁的茅草/唱你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你的圆,不会再圆/宛如一弯残月/钉死在历史的冷空。
这短短的八行诗,运用了“残壁、小花、断柱、茅草、残月、冷空”等意象,丰富了诗的形象。而语言的自然质朴,结构形式的严谨,饱含感情的倾诉,有效地揭示了被侵略的耻辱和中国人民心中永远存在着的残缺,从而撩拨着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这也许就是这首诗被看好的原因吧!
2006年8月,我在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顾艳中英文短诗选》。这部诗集也是近些年我对短诗的探索和尝试。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达了海内外不同种族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我更喜欢的是长诗,一写几百行,觉得很过瘾。
去年我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风和裙裾穿过苍穹》,里面就有好多首长诗,有美国生活的经验,也有国内生活的经验,感觉双重经验让我的人生都丰富多彩了。
其实写诗的人很多,但要一辈子是个真正的诗人却很不容易。真正的诗人是精神的,灵魂的。他们并非在舞台上热闹非凡,也许在寂寞的沉思中归隐着田园。你不能说他们是避世,消极;相反他们更是积极的人生准备。人总是活到老,学到老。宁静致远,是毫无疑问的。
小说虽然不是抒情诗,需要强烈的感情来支撑,但小说不能缺乏内在的感情。内在的感情就像一股气流,是否与你笔下的人物想融洽,实在取决于你的眼界和格局。一个作家的眼界和格局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你的认知高度和广度。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里上网课,我没办法有大把时间坐下来写作。因此,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就成了我的首选;但要把短篇小说写好,确实不容易。我读过不少短篇小说家的小说,譬如契可夫、欧·亨利、亨利·詹姆斯、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还有汪曾祺的小说等。这些作家的短篇小说有的诗意,有的简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无论哪一种风格,其语言、结构,内容意蕴方面,都有着比中长篇小说更为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把短篇小说看成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那么作家就需要有高超的艺术审美力,以及智性的思维表达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和驾驭好万把字的小说空间。
道理大家都懂的,就是写起来难。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除了结构上的统一、紧凑和重点突出,还需要在有限的文本中,蕴藉着无穷的艺术感知和审美韵味。也就是让读者品味到你语流中那浓浓的艺术质感。这就需要长年累月地进行阅读和写作训练。说实话,一个优秀成熟的作家,基本都是博览群书,经过几百万字的写作训练的。但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才华和艺术感觉,那么写出来的小说也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怎样才能写出优秀的短篇小说呢?我记得俄国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任何一个短篇小说,如果不能抽出某一部分,不能把它挪到另外的地方,不能去掉一个角色,否则一切都将崩溃,那么这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正确的。”短篇小说写不好,关键还是结构问题。就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固,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当然重新回归写作,是困难重重的。最现实的,从前我熟悉的编辑,大部分退休或者调走了;再没有邮箱里塞满约稿信的好风景,投出去的稿子石沉大海,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我恢复写作的头两个月,都在写诗歌和散文。我每天写一首诗,发在微信朋友圈。后来在《钱江晚报》开了个散文专栏,也开始给《今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写读书随笔和散文。后来我重新开始写小说,一口气写了好多,先后发表在《作家》《作品》《山花》《中国作家》《清明》《湖南文学》《百花洲》等刊物上。
在美国这些年来,我对来美读文科博士的留学生有比较多的关注和了解。他们各有各的困境和难处,漫长的读博生涯,即使拿到博士学位,找教职仍然是件非常困难痛苦的事,我就有一种想写写他们的欲望。
如今新移民文学在国内主流文坛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找了一些海外作家的作品来阅读和学习,发现各有各的视角和表达,但由于作家的天赋秉性不一样,表达的东西也就不同了。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只有抓住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那一份天赋和诚实,表达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是独特的。我想新移民文学的独特性,根基就在于此吧!
现在我恢复小说写作四年多来,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海外新移民写作的点,基本能够呈现自己色彩斑斓的各个不同的故事和场景。然而什么是新移民小说,什么是双重经验中的原创,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中国作家待在海外,写的是国内曾经的生活,这算不算新移民小说呢?在我的理解中,新移民小说,应该是居住在海外,用母语写着海外移民生活中的故事和感悟,展现其所在海外群体中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判断,为母国文坛提供一道域外风景线;而双重经验中的原创,对我来说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像我这样在自己祖国待了几十年才移民的,母国经验大大超过了异国他乡。因此我是带着中国文化的熏陶,从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到职场,再从作家到教授,涉及参与了不少各个不同领域的学习和工作。可以说,我是带着中国故事漂洋过海来美国定居的。因此,我与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老移民不同,想要写出真正的新移民小说,就得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子,拓宽北美生活疆域,融入到北美社会生活中去探寻和摸索。
想起早些年,我住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寝室,在校园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老师和学生,后来搬到学校公寓楼,接触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还有中国学生的父母们。有时我去洗衣房,遇到他们就会和他们聊天儿;特别是中国学生的父母们,待在美国有些家长又不会英语,又不会开车,无所事事,就想出了个主意,到斯坦福大学偏僻的空地上种蔬菜瓜果,从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几年下来,我在斯坦福积累了不少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我的短篇小说《没有告别的离别》,里面写到留学生父母种菜的细节,就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留学生家长种菜的故事。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海边的椰子树》,主要展现中国外婆在美国的生活。中国外婆在美国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她们从故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帮着管孩子的孩子。她们不会英语,不会开车,最要命的是儿女们下班回来很累,也不想和她们多说话。她们的等待落了空,难免沮丧。有些老人包容着,有些就和孩子们产生了矛盾。天长日久,隔阂越来越深。
短篇小说《海边的椰子树》里的外婆,是一个上海女人。为了儿女来到美国,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肩负着管教第三代的重任;但海外生活对老年人来说是更加不容易的,她们需要克服许多心理障碍,尽心尽责,且姿态始终是低到尘埃里去的那种。小说中有一段对外婆在孙辈面前的胆小怕事的描写:
在阳光的照射下,外婆发现厨房墙上海瑞森画的《海边的椰子树》出现了霉斑。她拿着抹布去擦,结果被她擦成了一块五彩的云团,破坏了画面的审美效果。她“啊呀呀”叫出了声,害怕海瑞森回来责备她。她走到后院,希望微风能安抚她紧张的情绪。她的手在颤抖,树枝划过了她的头顶,黄昏即将来临了。
外婆骨子里是中国传统女人,有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在孩子们面前,她内心也是最柔软的,同时又具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外婆这一角色,也就是一个女人从出生到成长、再到衰老的最后历程。她们有着丰富的人生历练,或悲或喜,但是到最后都不可能一个人孤独地存在。她们必须与亲人、与世界共存,直至生命的结束。
再后来,学校公寓楼的房租越来越贵。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便宜的租房信息,原来是一个白人教授,他想出租一间房,我就租了下来。好比现在的民宿,我租他一间房,还可以用他的客厅和厨房,以及洗衣机和烘干机。后来彼此熟悉了,老教授还会讲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和家人同事的故事给我听。我小说中写过不少美国白人家庭的故事,有的是我的体验和感悟,有的是我从老教授那里听来的,因此就有了我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一篇篇小说。我的短篇小说《斯坦福的秋天》,就是我租住在老教授家的经历,当然小说是虚虚实实的,有切身的体验,也有虚构的故事,这才是小说,并非散文。
几年后,我从加州搬到弗吉尼亚的列克星敦,一开始我也不太习惯。因为从斯坦福大学比较热闹的地方来到偏僻小镇,忽然觉得冷冷清清的。尤其是小镇没有公交车,如果自己没有汽车,那么到哪里都不方便。小镇有些路段没有人行道,走路不安全。再说乡下小镇比较空旷,望得到对面的场景,走过去却要花几小时。
列克星敦常住的亚裔很少,但小城有两所大学,也有一些国内来的留学生。我非常关注华人留学生在美国小镇的生活。因为从国内来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内的大学生活,多半是热闹的城里人生活;而到我们这美国地处乡下小镇的大学里,想去中国超市买东西,需要开一个多小时的汽车,且路上根本看不见行人,的确孤独感会油然而生。因此国内来的留学生,第一个学期确实会不太适应,但随着时间,慢慢熟悉了地理环境,就会发现小镇可玩儿学习的地方很多,还隐居着不少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说不定某天就邂逅了他们呢!
我的中篇小说《鲁卡》和短篇小说《初冬的气息》,还有中篇小说《山岗上的野天鹅》等题材都来自列克星敦小镇。《鲁卡》这个中篇小说,是我写拿到博士学位又找到大学助理教职的鲁卡在小镇的生活,以及他面对学校同行的内卷,与六年后非升即走的压力;还有他与来美国小镇探亲的父母的隔阂。这篇小说表达了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比如探亲的父母是带着中国经验来美国的,但来到美国后发现儿子身上的中国生活习惯所剩无几,观念也与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开始父母还能忍,但终因话不投机,发生争论,气愤得改签机票回国去了。
我在列克星敦小镇待了几年后,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华盛顿特区对我来说,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从前我对它的认知来自新闻报道,以及后来的到此一游;但真正居住下来的感受,却别有一番风味,也深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因此,我特别关注这座城市里的华人移民和留学生的命运。
在华盛顿,我住的是公寓楼。我的中篇小说《楼下》,主要讲述发生在华盛顿特区公寓楼里的故事。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住在华盛顿特区公寓楼里唯一的中国邻居。当然故事是虚构的,华盛顿的外部环境和公寓楼的内部结构是真实的。如果我不住在华盛顿特区公寓楼里,那么许多硬件部分的细节无法亲身体验。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安米,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女人,而男主人公小阳恰恰相反,他胆小、颓废、窝囊、身体虚弱,这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在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面前,男主人公小阳肯定被淘汰出局。这个不会说英语又有着病病歪歪的身体,起伏跌宕的人生的男人,最后还因为打人进了拘留所。然而人总会有变化的,这个一直在妻子眼里无用的窝囊男人,却并不因此沉沦,而是自我救赎,他用每天记日记的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从而得到反省。
我在华盛顿特区公寓楼里,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玫瑰园草地》,这篇小说讲的是“外嫁女”丈夫丢孩子的故事。因为夫妻有着不同的国别,就有了更复杂的背景。我写小说都有原型,但并非生活实录,是一种提炼,赋予某种意义。这篇小说,我以寻找失踪女儿为小说叙事框架,描述了这对夫妻遇到危机时不同的人生态度。因此,小说展开的过程,就是这对夫妻不断互相发现的过程。从而在虚与实的艺术转换之间,故事超越了现实的隐喻意义。华裔女主人公独立自强,敢于发声,掌控着家里的主动权,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同样是写丢失孩子的故事,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迷途》和《玫瑰园草地》完全不同。《迷途》是写孩子失踪后父亲的感受。我用男性视角,用梦幻般的第六感官和诗意般的语言来叙述故事,揭示人类心灵所面临的复杂而深邃的问题,使男主人公灵魂深处的痛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从这个男主人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中年男人的绝望无处不在,但他们有着女人无法知晓的隐忍和克制。因此,当他们被沉重的痛苦缠绕时,想说的话越来越少。痛苦有时与生命顿悟有关,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范永和就是在极其痛苦中,最后意识到自己才是事件的原罪。
来到美国后,我对种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所思考。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之时,白人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等级制观念,少数族裔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并且一直被主流社会拒之门外。因此,中篇小说《楼下》中的女主人公安米身上的自信和强势,确实是移民的生存之道。
如果说,我们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越来越大,农田越来越少;那么美国除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一些城市外,基本都是小镇和乡下农村了。我在列克星敦小镇住了好多年,刚搬到华盛顿特区时忽然有些无所适从了。首先,华盛顿特区时不时地响起警笛声,让人心生厌烦。其次,偌大的公寓楼,一通到底的下水管里响着“哗啦啦”的流水声,吵得人无法安眠。虽然久而久之都已习惯,充耳不闻了,但想想还是懊恼,必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就向物业提了意见。
最后我说说恢复写作四年多来,我是很拼的,一共发表了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散文随笔,编了两部小说集、一部散文集,去年出版了诗集《风和裙裾穿过苍穹》,但最重要的成果是今年再版了长篇小说《荻港村》。
《荻港村》完全是中国经验,它是我2006年写的,2008年8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4月在北京出版社再版。这里我谈谈我是如何写这部长篇小说《荻港村》的,说说它的起缘吧!
2006年,我刚完成了《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与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精品工程签约了一部描写浙江农村的长篇小说《许村》。许村从前是海宁县的一个村庄,如今是海宁市布衣名镇。我祖籍浙江海宁,虽然从祖父一辈已离开海宁,读书生活在北京和上海,但海宁就像梦一样萦绕在我脑海里。我想写许村的理由,就在情理之中了。
初夏的某日,莫干山杨局长听说我完成了一部学术著作,让我去莫干山休息几天。其实休息对我来说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我心里这个江南村庄小说与许村镇有太多的差别,我渴望找一个古村,就和杨局长说,你能给我找个江南古村庄吗?杨局长说没问题,你来了我帮你找。于是我到了莫干山的第二天,杨局长就派人带我去荻港村参观,我一下就被这个很浓的古老村庄吸引住了。我忽然觉得我要写的就是它——荻港村。
荻港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四面环水,河港纵横;青堂瓦舍,临河而建,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大村庄。从残照烟柳的“演教禅寺”,到清嘉庆年间御赐“玉清赞化”金匾的道教胜地,从沿河而建逶迤连绵的靠街走廊,到积川书塾依然清晰的八角放生池,隐然传续着荻港人文的琅琅书声。
我第二次去荻港村,是那年的八月底,秋日的天气依然炎热,村领导章金财书记引领我走遍了整个村庄。那古桥、流水、桑树林,那村西门窗斑驳的古老房屋,村东竖起的栋栋别墅,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公园等,都正好与我心中的图景吻合。由此,我知道荻港村在历史鼎盛的两百年间,出过五十多名进士、状元和一百多名太学生、贡生、举人。其中的章、吴、朱三家,更是英才辈出。他们中有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实业家等。历史的积淀,使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书香底蕴。
崇文园是古时一所私塾学堂,左右的石壁写着该学堂的历史;正中门顶上的红五星与下面已经模糊了的字体,则是历史留下的残迹。那天崇文园的木门紧锁着,我只能透过破旧板门的缝隙向内张望;当然这样的张望是看不出名堂的。
距崇文园不远处,就是新建的名人馆了。这里陈列着村里的名人:有李四光的老师、地质学家章鸿钊,中国民族资本家章荣初,中国近代史专家章开沅,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先驱邱望湘、陈啸空,外交家章祖申与瑞典王子罗伯特·章,中国著名矿物学、晶体学家章元龙,“赤脚财神”朱五楼,中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吴厚贞等。一个村庄能出这么多名人,在全国的村庄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走出名人馆,我一下就有了古村的感觉。如果说村口的那些仿古建筑和公园,是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成果,那么大量的名门望族的家族建筑,如,三瑞堂、鸿志堂、钟飞滨旧宅,以及清末沿河靠港而建的民居,历史悠久的古桥,便是古村的一大特色了。
我特别喜欢运河边上,已经破旧不堪的外港埭走廊。它全长五百多米,南北走向。民国时期,廊屋外皆为商店阁楼。当时小镇公路不通,水路交通相当兴旺,南通杭州,东往上海,北至湖州、无锡、苏州。兴盛时,各类店行都聚于此,有中药店,如朱正阳的百乐堂、陈荣生的泰源堂,还有茶店、彩云楼、聚话园、南货店、菱行、鱼行、丝行、米行等。想当年,这里就像一个交易品中心。
长廊边的老屋已经斑驳,年轻人老早搬走了,剩下的是老人和外地来的租户。我看到一间老屋排门敞开着,里面一对老夫妻正在吃饭,见我们来了两个老人都站了起来。陪同我的村书记章先生说:“他们开着茶馆呢!”这就是最地道的农村茶馆了。
这茶馆还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店名:彩云楼茶馆。茶馆里四张八仙桌,几张长条凳,破旧的朱红色雕花木门,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繁华。老人也不怕赤膊,站着让我照相。他相信毛泽东主席,墙上的毛主席像已经贴了几十年。右边的八仙桌旁,是通往二楼的木梯。木梯已经相当破旧,不仅颜色完全褪尽,连楼梯栏杆的柱子也断了几根。走上去,木梯便会吱吱嘎嘎地响。木梯旁的墙上,有一股霉腐味。老夫妻每天都要上下楼梯无数趟,天不亮赶早市儿的茶客就来了。当然他们的茶客,基本是村里的老人。
走出茶馆,沿着外港埭走廊看看那些斑驳的排门,想着1919年10月,村里第一个到上海换乘保加轮去法国的留学生,就是从外港埭走廊搭上运河的船出发的。外港埭走廊,还是那时候的走廊,只是岁月的风霜无情。
绕过外港埭走廊,在一排旧宅矮房中,我看见一架百年前的消防用具。村领导章书记说:“有关部门要收去进博物馆,但我们把它留了下来,陈列在村里,让来村里参观的人看看。”百年前的消防用具,现在看起来完好如初,只是想那时光这样的消防用具,能起多少作用呢?
湖州荻港村不像周庄和西塘那样闻名遐迩。它是那么古老宁静地安卧在运河边上,任风霜雨雪剥蚀着它的每一寸土地。它的历史就像村庄中那条曹溪河,从远古汩汩流淌而来。这样的一个村庄,正好与我心中的图景吻合。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这个村庄,并以“荻港村”这个村庄的名字,作为我长篇小说的名字。
当年我在荻港村采访蹲点三次,走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我所说的荻港村的这些东西,是一部长篇小说必需的内核,它的根基坚固结实和故事细节同样重要。因此有了这么个现实世界的古村庄,小说的硬件部分就非常理想了。
我这里没有说我长篇小说框架,也没有说故事内容,但明智的读者就知道,有了这个古村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村庄的风土人情,心里模糊不清的长篇小说框架和模糊不清的人物,在有了合适的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后,那些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就都在我心里成长起来,并从这块土地上冒出来了。
因此,如今作为海外作家的我,要讲好中国故事,双重经验是必须的。文学原创中的双重经验,以我的理解就是切身的体验与文学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当然对艺术的追寻,需要我们极大的激情和热情,还需要我们的诗性语言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努力把小说写得好一些,达到其独特新颖的目的。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