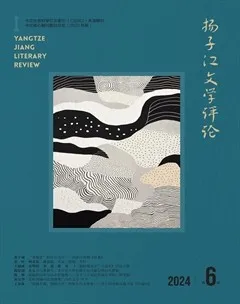犹疑的诗学与历史的镜像
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进行总体性的观照,“犹疑的诗学”无疑揭示出了隐而不彰的文学表述及文学史形态,特别是其通过现代主体犹疑不定的内部辗转及其崎岖演变,呈现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心灵史。所谓“犹疑的诗学”,与决绝果断且高歌猛进的诗学相对,意味着彷徨与疑惑、退避与绝望、沉沦与分裂、动摇与幻灭、惊惧与质询,甚至在无力与无能中,显露出复杂丰富的现代主体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格局,烛照曲折幽微的人心图谱和精神序列,因而也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迂回波折的精神结构与掩埋遮蔽的文化质地,并在与进化论、革命史观、启蒙观念等相互周旋激荡中,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主体形态和诗学镜像。
一
1919年,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提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狠(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a随后,他以文学实践了这一主张,在小说《一个问题》中,借朱子平之口,抛出了人生之问:“我这几年以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起先他们给我一个‘哲学家’的绰号,后来他们竟叫我做朱疯子了!小山,你是见多识广的人,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b胡适对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充满忧思,试图以写实的方式,通过人物及其心迹的表露,牵引事件,暴露现实,从而寻求问题的实际解决。“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c在胡适、叶绍钧、罗家伦、冰心等人创作的问题小说中,“朱子平们”所透露的人生犹疑,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写实主义式的解决问题的呼声,写作主体内部的态度则表现出一种“同一性”的决绝。
1926年8月,鲁迅的《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小说皆收于此,“大革命”前后的彷徨与疑惑不断冲击此前态度一致的新文学阵营。以此前胡适所提及的“朱子平之问”,联系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可以见出文学主体的“犹疑”发生了新的移变。《祝福》中的“我”作为受新文化浸淫的知识者,面对祥林嫂无比迫切的魂灵“问题”,却只有“惊惶”无措,“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灵魂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么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d祥林嫂与“我”的双重困惑,代表了对于不可预见的未知与无法解答的“问题”的犹疑。“我”起初想要以“希望”及对末路人的怜悯加以敷衍塞责,然而随后又陷入了深深的“诧异”与“不安”,究其原因,“魂灵”之问及其处理,不仅在于祥林嫂,更关乎“我”及“我”背后的知识态度与文化姿态。很明显,无论是对于朱子平,还是祥林嫂,这都是关乎今生来世的弱势底层之问。弱者的问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不得不直面的所在。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胡适等人所创作的问题小说,其实是上升到社会学的层面,对人生之“犹疑”进行考量的,文学不过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形态之一;而在鲁迅那里,则代表着怀揣问题的“犹疑”者,从客体走向了主体,也意味着新文学走向了纵深,尤其在写作《野草》时,鲁迅更是在“彷徨于无地”中,将苦闷的“犹疑”推向了极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e在《近代的超克》中,竹内好曾提到鲁迅文学中的“无力感”,“文学是无力的。鲁迅这样看。所谓无力,是对政治的无力。如果反过来说,那么就是对政治有力的东西不是文学……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f。需要提及的是,对于鲁迅而言,“犹疑的诗学”不是进化论,也非退步论,而是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进退维谷,是难以抉择与不可妄断,故而时常只能陷入悬置和延宕,甚至选择避离、逃脱或反抗;寄寓于这样的“无力感”之中的诗学形态,是有所蕴蓄和收束的,左右摇摆与前后矛盾的修辞背后,对应的是彼时人心人性与现实政治的晦暗不明。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形成的文学变革力量,在思想启蒙与精神革命的一致呼声中,代表了一个新旧对峙的时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态度。然而,在态度的“一致”与叙述的“连续”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众声喧哗”的多重变奏。其中,那些出于外在或内生的压抑而形成的惶然不决的美学话语,构成了所谓的“犹疑的诗学”,其中代表着一种潜行的现代性,尤其在线性的进化思维与统制式的革命话语中,彷徨与疑惑、退却与省思,构成了一种辩证式的“执拗的低音”g,在文学文本中透露出复杂多元的个体声音与精神讯息,尤其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思想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在相关表述中形成固有的美学形态和修辞方式,甚至构筑了一种文学叙事的精神范式,延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坚固内核。“历史之流是连续的,即使想抽刀断水,但水还是继续往前奔流。所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连接,基本上都可以说连续的。而‘后见之明’每每把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造成了思想发展是一个单纯延续的印象,近代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也往往加强了单纯延续的印象。”h不得不说,在这个过程中,代表着“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却始终缄默的“少数”,迂回曲折,进退失据,充满了精神的惊惶和心灵的斡旋,从而构成所谓“犹疑的诗学”,这与那些一往无前、斗志昂扬的诗学相对,形成了或主动隐匿、或被动遮蔽的个体精神史脉络,那是现代主体心灵格局中的丰富及其裹挟的痛苦,也意味着二十世纪文学迂回波折的情感结构与幽微盘曲的精神流播。
二
可以说,从问题小说而始,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者往往是与“问题”紧密纠合的,为其困惑,也为之焦虑;关键在于,这样的基于“问题”的“犹疑的诗学”,在现代文学进入纵深之际,真正回到了文艺的美学属性之中,其拆解与处置的过程也呈现出主体性的丰富与深化。在这个过程中,“犹疑”本身的曲折通幽,提示了文学面对“问题”时所应秉持的有效方式,具体而言,这个过程充满着内外的博弈和周旋,甚至叙事者本身,都不得不经历必要的困惑和疑虑、无望与绝望,甚至承认自身的无助、无力与无能。《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i尽管狂人并没有直接的批判与强硬的质疑,而是一种来自内部却并不向外扩展的“犹疑”,对他而言,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存在任何的态度一致,甚至于只是一个沉沦于绝望之中,不见容于外在世界的“狂人”的妄语,但却在指向虚妄情绪与主体病兆的同时,触及了最确切的现代中国。
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里,作为零余者的抒情主体“他”,同样存在着内部的周旋,其中多层次的自我意识经常是悖谬的,踟蹰、分裂的心绪精神之中,有着人性与病症双重映射下的心理曲线,在犹疑中不自觉地螺旋般直抵幽微的魂灵,这其中充满着自我的发觉、剖析以至否定、批判,建构起充盈着不同声部的新的内在——一个躁动不居的未完成的现代主体。郁达夫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东方的醒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j零余者的问题,与决绝者的诗学有着定然的分化,在他们那里,一往无前的现代主体精神出现了回旋的余地,从而在同时代的激进诗学中,开拓出新的美学空间。具体而言,《沉沦》中,“他”赴日留学,到头来“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想逾越世俗,又担忧遭人冷眼;来到了都市,却得了无所适从的“怀乡病”;风华正茂的“二十一岁”,却自认为“槁枯”与“死灰”。一方面因在日本自觉受辱而眷念祖国和故土,一方面又怨恨“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精神主体遭受着犹疑与摇摆、分裂与苦闷,对事对物往往思虑再三仍难下决断,在瞻前顾后中滞步不前,可以说,通过此间生发的多重疑虑、猜忌和自省,郁达夫在试探现代主体的精神形塑过程中的诸般形态及诸种可能。
在郁达夫那里,自叙传主人公的精神“犹疑”,主要体现在精神的裂变与忧郁,其中的迟疑不决与裹足不前,代表着现代主体形成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折叠、曲折与复杂,这与“五四”前后激进的文化/政治运动中,大势所趋的决绝精神以及用进废退的新旧对垒,显然是有所区隔的。在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表现出来的不无“犹疑”的知觉、性格以至抒情美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线索,那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低音部所呈现出来的修辞与诗学。可以说,正是“犹疑”本身,打破了不同的叙述脉络中的“现代”文学的单一指向性,进而形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多维线索与多重传统,甚至于“犹疑的诗学”已经演变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内生叙事。需要指出的是,“犹疑”也并非单一维度的所在,而存在着与种种话语的协商、周旋和博弈,郁达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拯救民族危亡的大环境中,完成了一种自我的政治身份与美学观念的转变,自觉投身于决绝的革命者与救亡者的行列之中,由此见出“犹疑”之诗学的变移和转圜的过程。
“五四”往后,革命文学兴起,文学文化与革命政治的深切互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时被必然性规律与断然性叙述所贯串,然而其中同样存在着种种历史的和精神的曲折。1927年,茅盾的长篇小说《幻灭》问世,小说中,静女士身上的革命、友谊、情爱的希望逐渐走向式微,更走向了精神的内在犹疑,与此同时,那也是斗志昂扬的革命美学中的退却忧思。事实上,在革命文学内部的沈雁冰(茅盾)、冯雪峰、夏衍、田汉、瞿秋白等人身上,无论是思想认知,还是文艺实践,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现代中国,走向了自身的曲折。“犹疑的诗学”内部存在着一种深层的抵抗,当然这种文学层面的抵抗并不是直接的对垒,而是通过自身回旋幽微的方式,经由语言的形式塑造犹疑的主客体,以此彰显心绪思想的反复或者言行操持的反思。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学落潮,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35年,瞿秋白在就义之前,写下了《多余的话》。作为革命者的写作者在文中袒露心迹,“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k。原本革命者身上钢铁一般坚定的意志,却仿佛充满了勉强而为之的精神疑虑,那些“多余”的却又不吐不快的“话”,成为了关乎革命的深切“犹疑”,那当然不是自我的清算与革命的逆反,而更多是生命的怜悯、自我的性情以及革命踟蹰摇摆的侧面再思。“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l事实上,作者并不惧于生死,甚至是昂扬与乐观的,其更多地在精神的凝滞中反观和剖析自身,在革命经验与文化实践的追溯中,映照出一个革命者百转千回的心灵史/精神史。钱理群认为瞿秋白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哈姆雷特,在他身上呈现出来的矛盾和痛苦,事实上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曲折以及革命主体精神犹疑中的丰富及“丰富的痛苦”m。反观同一时期的“左联”,追求的是反封建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化合流之间,彰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写实主义与革命话语,而瞿秋白却在遗作《多余的话》中,叙写了一个现代革命主体的精神自传,其中的内部辗转及崎岖演变,无疑代表着二十世纪革命历史中的复杂镜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接续“五四”问题小说传统的,是解放区的赵树理。“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n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包含着一种阶级政治的实践主义美学,其现实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o。但赵树理在将中国农村纳入政治与政权“问题”序列中加以考量时,农民切身的“问题”成为这一序列中的“犹疑”所在,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甚至是反面的民间形象,事实上呈现出了切实的生活现场、底层的思想状况以及多维的精神需求,为政治/革命文学提供了另一重人性样本,避免了阶级政治视阈中对于问题小说的盲视与不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时期的农村书写中,农民自身的生活、思想、精神状况与政治形态相对接,容易造成文化上与政治上的先入为主,成为既定装置中的文学表述。因而,如果回到当时的政治历史语境,赵树理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毕竟难脱其局限,落后的小人物被迅速推至边缘并成为批判的中心。丁玲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经提及,“当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马上要来到这个地区,全国解放战争马上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p。不仅对于丁玲,在当时的革命政治表述中,所谓的“问题”是漫溢而出的,与其说“决定了人物”,不如理解为其将人物覆盖与淹没了,无论是主体的延伸,还是结构的搭建,都挣不脱既定的“问题”的框架,主体的“犹疑”不断被淡化甚而取消,如是代表着对于“五四”以来所塑造的文学形象范式与形式规律的新的背离。
因此,“问题”本身事实上并不直接指向“犹疑”,其中的诗学倾向也可能是坚定而决绝的单向度表述。相比而言,此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等,对妇女、民主等问题进行直接针砭,却显示出了一种真正源自“五四”的精神之“疑”。丁玲《三八节有感》中提到,“‘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q在小说《在医院中》,丁玲笔下的陆萍则是一个怀抱着理想,对现状心存不满的女医生,她沉浸于医院的日常之中,为其所忧、为其所扰,甚至于在经历了生死之后,不觉产生了对革命的疑惑,“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r。从主体的发现与觉察出发,进而“有感”与“需要”,彼时成为某种不合时宜的“犹疑的诗学”,这样的情态首先建立在人物及其觉知的自为性上,不被外部左右,审视内外的曲折变移,在叙述中兼及人物的多重视角与多维情势,在生成踌躇与犹疑的同时,不为单向度的话语所裹挟,避免问题无序张大的同时,出现自我的窄化。
三
1949年,与胡风同年创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的“坚定”与“镇定”不同,沈从文却显得忧郁惶惧,对他而言,旧有的意义系统出现了紊乱,而于焉建构起来的主体精神话语面临着溃散:“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s在这里,与其说是沈从文在一种新历史情势下的心理反应,不如视之为“五四”以来的个人觉醒在新抒情时代中发生的主体犹疑。“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t其中之“无能”,不禁令人联想到前文引述的鲁迅的“无力感”。在沈从文那里,时代转圜时期的文化心结在认知结构中不断发酵,以至于难以整合消化而最终不得不另作转向。及至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既有杨沫《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对人生的怀疑发问,“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u也有“双百”方针中的疑窦和究察,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问起赵慧文,“你幸福吗?”赵慧文却一脸“疑惑”,难作可否。v然而,随着“反右”运动及“文革”的发生,中国文学陷入一个不容怀疑与质问的时代,“犹疑”自然也无从表述。
及至“新时期”,在万象更新的文学现场,韩少功却充满了对文化本身明灭存亡的忧思,由此形成的文化犹疑,通向了“寻根”之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引入新的场域。“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其更是不无焦灼地提出了“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w韩少功的精神犹疑使他不得不进行后撤与回望,以再造一种文化美学,而基于此形成的“文化犹疑”,也形成了“寻根文学”内部最重要的美学话语机制。“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是国家的事,是几代人的事,想要达到先进水平,早烧火早吃饭,不烧火不吃饭。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做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写改革,没有深广的文化背景,也只是头痛写头,痛点转移到脚,写头痛的就不如写脚痛的,文学安在?”x因而,在“寻根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观照,这是建基于文化中国的疑虑与重审之上的,不得不说,“犹疑的诗学”本身便具备着生产性与创造性。
如是之故,建筑在大文化视野下的“犹疑的诗学”,在同时代的朦胧诗及后朦胧诗的写作中,得到了新的延续。北岛诗歌中的悖谬便是一种历史的质疑、文化的拷问与人性的忧虑,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犹疑”是一种决绝的、不寻求任何回答的所在。在诗歌《回答》中,恰恰不需要外部提供任意的答案,而重要的是“问题”悬置与精神“犹疑”的背后,代表着对革命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海子的《麦地与诗人》,分为“询问”和“答复”两个部分,“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y诗歌以标志性的意象麦地、太阳,楔入“我”的情绪表达,发出的是一种人类之问与生命之问,以此完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一次脉冲。在海子的诗歌那里,呈现出了文化的与精神的总体性以及基于此而生成的内在犹疑。在《黑夜的献诗》中,海子同样述及“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z,《远方》中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7,等等。可以说,诗人的“大诗”意义上的个体精神犹疑,喻示了1980年代的浪漫主义尾声,甚至意味着世纪末临近的文化症候,那是一种不及物的精神远方,冲击着后革命时代无处皈依的灵魂主体。在海子的诗歌中,混杂着对过于宏大的文化神话的崇拜及疑惑,这往往表现为诗歌内部的语言沉思,并最终走向自我的裂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子的诗中,不是单纯的质疑或怀疑,而是将信将疑、疑信参半,故而他一面高歌逐梦,一面却自感一无所有,因此,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的与文化的“犹疑”也许更为准确,诗人正是以此呈示自身的文化雄心与精神万能,却不得不遭遇理想浪漫的总体性内部的分解。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总体犹疑中,开启1990年代的文化之旅。而二十世纪末以来的文学发展,便是不断被切割被分化的历史进程,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城市文学、新乡土写作等依然在延续着传统的文学理念,而王朔的痞子文学、张艺谋的商业电影、野蛮生长的网络文学等,总体性的文学理念不断瓦解,而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与启蒙变奏与互渗的意义系统也发生了崩坍,新的“犹疑”便于焉产生。“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81990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激烈裹挟中,中国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人文精神大讨论”则对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充满了疑虑与不信任,文学自身的位置与功能、诗学与格调,不得不在内部的自我“犹疑”中,走向新的认知,“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9。在悲观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五四”以降建构起来的现代人文精神,发生了不容乐观的衍变与转圜。中国文学正是在如是这般的整体性忧患中形成内部的自我犹疑,从而在失却轰动效应与精神引领之后,不得不重新考量与建构自身,也因而预示了直至21世纪的当下依旧无法穷尽的重要课题,更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断求新寻变的内生动力。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文革”结束后的巴金开始创作《随想录》,巴金的犹疑一方面来源于对如何言说的探索,一方面则是通过言说以形成自我反省与历史反思的统一。“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做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0通过一种自我的解析以达到对他者的剖断,进而理解历史,发现人心,在巴金的《随想录》中,“犹疑的诗学”一寸寸地深入抒情主体的精神内在,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甚至是有一种“无力感”,“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1这样的无力感,与竹内好述及鲁迅时提到的文学的无力有重叠之处,尤其体现在文学对政治历史施以的周旋与抵抗。然而其又是有所区隔的,巴金的《随想录》更多地涉及对被戕害与被损伤者的认同、缅怀与纪念,抒情主体在忍耐锥心之痛的同时,将爱与恨推向更为沉郁的灵魂拷问。
因而不得不说,纵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叙事与主体生成,经历了国族、革命、政治、文化、精神等层面的衍变与糅杂,其经常不是从一而终与一以贯之的,当中有着内部的摇摆、矛盾甚至争斗,在文学叙事与文化表述中形构出“犹疑的诗学”,塑造层次繁复的主体形态、交叠互渗的声色语言以及回环往复的修辞结构,最终建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极为重要却时常被遮蔽忽略的诗学形态。
四
钱理群在《漫说“鲁迅五四”》中谈到鲁迅对启蒙主义的犹疑,“‘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再一个是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了,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吗?”#2鲁迅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也在于此,甚至他还认为,“不愿以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3。而汪晖在谈到鲁迅时也说:“《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彻底超越了‘希望—绝望’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或者为希望而欣喜、奋斗,或者因绝望而颓丧、消沉,或者在无可奈何的情境中添加光明的尾巴——极度的悲观与轻率的乐观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尤为明显,很少有人像鲁迅那样对历史的沉重感体验得那样深切。”#4或可将鲁迅及其作品中的“丰富的痛苦”与复杂的犹疑,视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诗学形态,那么其间映射出来的,显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曲折幽微的精神境况与犹疑凄惶的思想历史。
概而述之,“犹疑的诗学”时常蕴蓄于中国现代主体的形成过程,思索进与退,辨认真与伪,在勇毅与怯弱的交杂中,渗透历史的不同岩层,探询自我与他者的多重对照,以完成美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建构;而以二十世纪中国为中心,“犹疑的诗学”寓决绝与疑虑、直面与逃避、褒扬与批判等多重辩证于一体,尤其在近现代以来以至二十一世纪的诸种诗学实践中,不断触及政治历史的叙述方式以及文学文化的丰富面向。“各种《选编》、各种资料辑,也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特定议题是单纯的前后相连,这些文章原来分散在各种刊物、分刊于不同时间,但是选编或数据集里往往把这种零散感及时间距离感去除了。各种以‘origin’为题的研究,很容易造成这种单线延续的印象。事实上,即使是连续的,它们中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连续方式。”#5可以说,“犹疑的诗学”为进化史观、启蒙意识、革命史论等提供了新的镜像,在不断缠绕中补充彼此,为现行的历史线索和美学话语创生出多元化的内部参照,使之立体丰富,证其真伪究竟;在此基础上,洞见立体完整的灵魂图谱和伦理境况,展露复杂丰富的现代主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
【注释】
a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第31号。
b适(胡适):《一个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7月第32号。
c仲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2月第7号。
d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e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f[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4页。
g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h#5王汎森:《启蒙是连续的吗?》,《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i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j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353页。
kl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4页、694页。
m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n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o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页。
p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页。
q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
r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s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t沈从文:《致张兆和、沈龙珠、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u杨沫:《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v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w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x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y海子:《麦地与诗人》,《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页。
z海子:《黑夜的献诗》,《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7海子:《远方》,《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8@9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论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58页。
#0#1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Ⅳ页、Ⅲ-Ⅳ页。
#2钱理群2009年3月1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国家历史讲堂”作《漫说“鲁迅五四”》的演讲,后发表于《书城》杂志2009年第5期。
#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42页。
#4汪晖:《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王晓明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