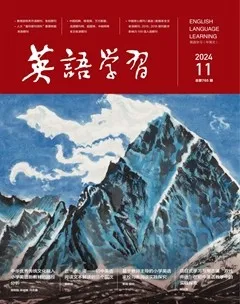从盎格鲁-撒克逊语到世界英语:来自英语史的启示
引言
如今,许多国人对是否学习英语感到困惑,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政策的变化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同看法。国人对于学习“他人”的语言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其次,大语言模型支持的人工智能工具消减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语言障碍,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如果有机器帮忙处理英文写作和翻译,人们为何还需要学习这门语言?本文从文化史与语言史的角度探讨了英语从一个西欧岛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其命运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或许能帮助学习者厘清思路、扫除困惑。
英语是谁的语言?
针对国人为什么要学习“他国”语言的这一困惑,本文通过分析英语是谁的语言这个问题,说明全球化的当下,像英语这样的语言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全球通用语。
一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The Anglo-Saxons)将不列颠岛上说凯尔特语的人称为Wealas(Baugh & Cable,2013:46) 意为外国人,这个词流传至今就变成现代英文中的Welsh,即威尔士人。但是慢慢地the English就包括了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在英格兰的丹麦人等。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之后,新统治者在管理中使用法语,英语一度成为下层人民的语言。但几百年后,英语再次崛起,成为国家管理和宗教事务的语言。过去的诺曼贵族也逐渐认同了英国人这个身份。在英语传播到全球之前,它是不列颠岛上这些人的语言。
如今,据大卫·克里斯托(Crystal,2008)估算,全球有约20亿人说英语。虽然统计标准可能不一,但英语使用者众多确是事实。语言学家提出了多种模型来呈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布,其中Kachru(1985)提出的同心圆理论最为著名。三个同心圆中的内圈,是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二个同心圆,即外圈,涵盖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如南非、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近几十年来,随着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人数激增,又出现了第三个同心圆,即扩展圈,涵盖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韩国等。虽然Kachru学派更关注第二个同心圆的特点及变化(Schneider,2014),并主张这些国家的英语变体有其自主价值,但许多学者自然把内圈作为评判标准和追求目标,外圈和扩展圈的语言特点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英语使用者的分布愈加复杂,圆与圆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国家为界不足以解释现在的分布状态。Mair (2013)通过大型语料库的研究,包括网络语言语料库研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以国为界的静态研究局限性,更全面地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多语环境为常态的英语的特点。今天,理想的英语使用者生活在一个非同质(日益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分类)的社会中。例如,多文化伦敦英语(Multicultural London English, MLE)就出现在一个典型的多元语言环境。它源于伦敦东区,融合了工人阶层的考克尼(Cockney)和来自非洲、加勒比等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的语言影响,形成了在发音、词汇和语法上与考克尼不同的新方言,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中流行。由于其多元来源,很难明确指出某些特征的具体来源,说这种语言的人也无法简单地用国籍界定。可以说,他们的语言也是英语。Pennycook(2003:10)认为全球化已经超越了同质化和异质化之争,他在评论一支由伦敦第二代南亚移民演唱的牙买加风格的说唱歌曲时写道:“在我看来,有趣的是这里的混合和讽刺。…… 一个非洲-加勒比说唱音乐的空间,一个庆祝伦敦第二代南亚青年新生活的空间,而他们在工厂工作的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电视上观看过Naya Zindagi Naya Jeevan(New Way New Life)这个剧。…… 这种文化遗产(经过改造的南亚文化)与流行文化(挪用了伦敦-加勒比地区的风格,但也包括全球说唱乐)、变革与传统、跨越国界与种族归属、全球语言挪用与本地化的流动混合体,在许多方面正是全球新秩序的内涵所在。这既不是同质化,也不是异质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一语言已经不能满足沟通需要,多语言应用能力才是全球化时代的趋势。显而易见的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是我们多语言能力培养的首要选项。谁能充分利用它,它就是谁的语言。
英语学习者是否应该追求“纯粹的英文”?
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英文”。自公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定居以来(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日耳曼人进入不列颠),英语就与许多其他语言发生了接触。这些语言包括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拉丁语、丹麦语和诺曼底法语,以及更广泛的非洲、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语言。语言接触有三种可能的结果:语言变化、语言涌现和语言死亡1。前两者都会形成“不纯粹”的语言。首先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可能包括单词、短语及多种语言特征的借用,长时间的深度接触还会导致语法变化。其次,语言接触促使新语言涌现,如皮钦语(Pidgins)和克里奥尔语(Creoles)。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迫使不同母语的人们创造一种语言来相互沟通。皮钦语是在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之间通过接触发展起来的通用语。每种皮钦语都基于一种源语言(通常是英语或葡萄牙语),没有母语使用者。在流传一段时间后,皮钦语可以作为一种母语,这时就被称为克里奥尔语。
语言变化充满了偶然性,却时刻体现着人的创造性和价值观。观察语言变化就是观察人的变化,对我们认识世界、做决定、做选择都有启示。当代英语(Present-day English, PDE)中,80%的词汇源于非盎格鲁-撒克逊语(Crystal, 2011)。虽然“英文的纯洁性”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常引发争论,英文实际上在不断吸纳外语词汇,极大丰富了其本身的词汇库。许多英文单词有大量近义词,如果说话者能够在不同语域、语境中选择恰当的词汇和表达,其语言运用就会显得更加细腻、严谨、精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We have a date.”和 “We have an appointment.” 两句看似相同,但意义不同。date和appointment这两个词在词典里意思都为“约会”,但其场合与参与者关系、衣着、目的、态度等都不一样。特别是在美式英语中,date通常指称有亲密关系或准备发展亲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约会,而appointment通常没有这层意思。不论用英文写作还是从事翻译工作,会用同义词词典(thesaurus)是一项重要能力。再者,查词源会发现这两个词都来自拉丁文,在中世纪经由法文进入英语。因此,对英文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有更透彻的了解,能增强读者的选择意识,使表达更加精确、适宜。虽然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实现部分交流目的,但还远未达到人类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能够流畅地道地使用英语仍是一项重要能力。熟悉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是更好地参与世界交流、促进共同进步的前提。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的过程带来了哪些启示?
虽然不能说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是必然的,但分析其过程仍具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有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后文中涉及一些语言学术语,限于篇幅仅提供简单解释,有需要的读者可进一步参考语言学词典。
英文最早使用如尼符号(runes)记录,公元8世纪开始使用罗马字母,至公元10世纪左右完全使用罗马字母,这多少是受罗马教廷宗教传播活动的影响。与德语是近亲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属于西日耳曼语族,其语法系统经历了长期的简化过程,使之从古英语时期的综合语变成现代英语时期的分析语,形态系统的简化让英文更容易学,这属于语言内部原因。下面我们回顾这个变化过程。
传统上西方语言学家按照形态(morphological system)丰富程度把世界上的语言进行分类,排在两端的分别是综合语(synthetic language,屈折形态复杂,语法标记众多,以拉丁语为代表)和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形态贫乏,鲜有形态标记,虚词众多,中文就是这样的语言)。
古英语是西日耳曼语的一支,它的词汇屈折变化(inflectional paradigm)十分复杂。单词由词根(root)和词缀(affix)构成,标记变格变位的一般是后缀(suffix)。名词和代词有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语法系统赋予名词和代词规定的性,和生物的自然性别没有必然联系,分别为阳性、中性、阴性)、数(number,包括单数、双数、复数)、格(xNx/QuDa0lhAdM/5is7TfdZjJ3FjHx0AhdLgGy+oKKM=case,标记名词性成分和谓词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有主格、宾格、与格、属格和工具格)变化,称为变格(declension)。与之搭配的形容词也必须与之一致变位。动词有数、时态、人称、语气变化,称为动词的变位(conjugation),动词要与主语在数和人称上保持一致。图1是古英语动词keep和help的屈折变位表(Algeo,2010:101—102)。古英语动词的变位包括人称、数、时态和情态。现代英语仍对其进行标记,但已大大简化。表格最左栏分别列出了不同时态、语态下的主语,右侧两栏是keep和help在这些不同语境中的变形形式。可以看出,古英语中 keep 和 help 的各种动词形式在现代英语中已简化为四种形式:keep / keeps / keeping / kept; help / helps / helping / helped。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古英文表示keep的所有形式,有一部分是保持不变的,即cēp,发生变化的都是其后缀部分。而help的变化除了词缀,词根中的元音也有变化。现代英文中这两个词根都没有变化,词缀只有四种变体。

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应该都记得当年刚开始学习英文时,对进行人称、数、时态变化感到麻烦,其实跟古英文和其他印欧语相比,现代英文已经大大简化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简化呢?主要原因是古英文所属的日耳曼语族,与法语、意大利语等所属的罗曼语族有一个重大差异——单词重音位置。日耳曼语的重音通常在词根上,不论后缀如何变化,主要重音位置不变,而罗曼语的单词重音会随着音节量的变化而变化。词根重音这个特点在古日耳曼语中就已经开始造成词缀非重音音节的磨蚀(leveling)。在古英语形成之后,这一趋势继续作用。由于词尾的音节没有重读,发音轻,慢慢地就不容易听出差异。不同的拼写形式自然慢慢合并或消失。这也是省力原则2的体现,即使没有这些词缀,理解句意通常也能通过语境推测出来,因此词缀的磨蚀变得可以接受。
以下例1取自《圣经·创世记》第七章中诺亚的故事,斜体为古英文,下方为现代英文对应词,均引用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语言研究中心提供的早期印欧语言线上教程(Early Indo-European Online),中文译文由笔者提供。
例1. Him þa Noe gewat, swa hine nergend het,
Him then Noah went, as him the savior commanded
under earce bord eaforan lædan, weras on
on (of) the ark board (his) sons to bring, men into
wægþæl and heora wif somed;
the ship and their wives also
现代英文译文:Then Noah went, as the Savior commanded him, to bring his sons on board the ark, men into the ship and their wives also.
中文译文:于是诺亚像神要求的那样走去,把他的儿子们带上方舟,男人也带着他们的妻子。
在这个例子中,nergend、eaforan和weras是阳性名词,earce 是阴性名词,而 bord、wægþæl和wif 都是中性名词。这种“语法规定的性”概念如今已不复存在。读者也许会说:“真是松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复杂的性属性了”。这么想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现代英语使用的是自然性别,而且只在代词中使用自然性别,当所指事物的自然性别很容易确定时,就为说话者提供了方便。然而,假如性别尚未确定,说话人在寻找正确的代词时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尴尬。2019 年,美国历史悠久的词典之一《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在其当年更新的词典中认可了they作为单数、中性代词的用法,指代那些不区别性别或不想透露性别的个人。下方的例子取自《韦氏词典》网络版 they词条的用法3,其例证取自网络真实语料。
例2.A student was found with a knife and a BB gun in their backpack Monday, district spokeswoman Renee Murphy confirmed. The student, whose name has not been released, will be disciplined according to district policies, Murphy said. They also face charges from outside law enforcement, she said.
在例2中they指不愿表明性别的单个人。
在例1中,第一行中的 hine 是宾格,是动词 het 的直接宾语,因此即使它出现在动词之前也不会引起理解上的误会。这种词序在现代英语中并不常见,因为现在格的概念通常是通过词序和介词来表达,宾格名词通常出现在动词之后。earce在现代英语中译为 of the ark(方舟的)。earce bord的意思是方舟的木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表达同一语法关系的两种方式,形态变化和词汇表达。在古英文中,属格标记在名词词干上,属于屈折变化,而在现代英文中,属格用介词 of 组成短语来表达,这种方式被称为the peripheral way,即用词汇表达而不是在名词词干上做形态标记。
由于屈折形态的简化和虚词使用的增多,语序相对固定,现代英文更像中文这样的分析语,也更容易被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接受了。
我们将语言接触视为外部因素,有学者认为英语语法系统的简化与历史上的语言接触密切相关。英语是5世纪时西欧大陆上的日耳曼部落入侵不列颠后在不列颠岛上形成的。与其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包括弗里西亚语、荷兰语、德语等西日耳曼语支,以及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等北日耳曼语支。最早与英语发生接触的是日耳曼语族中的近亲。到了8世纪,不列颠岛迎来了被称为维京海盗的新一批入侵者。
维京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8世纪至11世纪在北欧、西欧当海盗,也在陆上掠夺(Vikings:OED)。8世纪末期维京人开始小规模零散的袭击活动;9世纪时他们对不列颠进行了大规模抢掠。在威塞克斯发生了许多战役,其中包括公元871年的阿什当战役,丹麦人(就是之前的维京人)在这场战役中被击败。877年,阿尔弗烈德大王(后人称他为Alfred the Great)迫使丹麦人离开威塞克斯,他们在默西亚东北部定居下来;但877年冬天,维京人的一次进攻差点征服威塞克斯。阿尔弗烈德大王退守萨默塞特沼泽地。翌年春,他秘密集结了一支军队,在爱丁顿(Edington)击溃了丹麦人。丹麦首领古特鲁姆皈依基督教,并率领他的军队前往东英吉利亚,在那里定居下来。约880年,阿尔弗烈德大王与丹麦首领古特鲁姆签订了《韦德莫尔条约》(The Treaty of Wedmore),建立了英格兰东部地区,由于该地区受丹麦法律管辖,因此被称为丹麦法区(Danelaw)。以下引文节选自《今日英文》杂志(English Today) 的文章“The Germanic Heritage”(Christophersen, 1990)。3
在大约公元950年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的约克郡由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统治,宫廷中使用北欧语言。在11世纪前半叶丹麦征服英国以及随后丹麦人统治的时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定居者数量增加,并开始对英语产生显著且日益明显的影响。……在曾经被称为丹麦法区的地方,至今仍有许多村庄名称包含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元素,如-by、-thorp、-thwaite或-toft,这证明这些地区曾经使用过某种形式的丹麦语,也表明丹麦人定居点广泛存在,有些地区甚至非常密集。然而,纯正的丹麦语似乎在1200年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定居者适应了新的环境,并且为了在两个群体之间进行交流,发展了一种所谓的“接触语言”,这种语言具有简化的语法结构,词汇随机来自两种源语言。……现代英语中的代词they、their和them,连词though,以及both等词汇都来源于北欧诺斯语(Norse)。虽然英语起源于西日耳曼语族,但在许多词汇和某些语法结构上,它更接近斯堪的纳维亚语言。
另一次影响重大的入侵当属1066年的诺曼征服。《英格兰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的作者詹金斯(Jenkins, 2011: 62)指出:“维京长船使得斯堪的纳维亚人得以征服克努特统治下的英国,并在北欧地区建立了诺曼人的聚居地(the Norman diaspora)。哈罗德王(King Harold)和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都是维京后裔。”哈罗德王和征服者威廉就是诺曼征服的主角,前者是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后者是法国诺曼底公爵。法国人当上英国国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方面都对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克里斯托(Crystal,2018:30)指出:“诺曼底的威廉登基后,法语迅速在权力走廊中确立了地位。新受命的讲法语的爵爷带来了自己讲法语的随从。不久之后,讲法语的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也纷纷上任。……在入侵后的 20 年内,几乎所有的宗教机构都由讲法语的人管理,一些新成立的也完全由法国人管理。大量法国商人和手工业者跨过英吉利海峡,利用新政权提供的商业机会。贵族与诺曼底的联系依然紧密,贵族们在诺曼底保留了自己的庄园。毫无疑问,双语在那些跨越社会鸿沟的人中间迅速兴起——英国人学习法语,以便从贵族那里获得好处,而爵府的工作人员学习英语,作为与当地社区日常接触的一部分。但在新的贵族等级制度中,几乎没有使用英语的迹象。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法语词汇大量进入英文,以至当代学生可能以为英法两种语言是近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拉丁语词汇经由法语再次借入英文。词汇方面的深度融合使英文表达更加丰富细腻。Crystal(2018:47)列举了英语中的法语借词,从行政管理到宗教、军事、食品、时尚、休闲、科学、艺术等,不一而足,反映了中世纪贵族对法国生活方式的效仿。
诺曼征服之后,英文一度处于最低地位,因为拉丁语是教会用语,法语是行政管理用语,英语是底层百姓的语言。上层人士对英语的评价是uplandish,意为质朴、粗俗、未开化。由于不再用于书面文件,英语失去了书面语的地位,词汇量减少了一半。缺乏标准化导致拼写和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说《艾凡赫》(Ivanhoe) 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评论(Scott,2005:29):
法语代表荣耀、骑士精神,甚至是正义,而更具男子气概和表现力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则只有乡下人和老粗们说,他们不懂其他语言。然而,地主和那些受压迫的下等人之间的必要交往,使得法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方言,他们可以用这种方言相互交流。
一方面,诺曼底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失去诺曼底后,诺曼后裔与诺曼底的联系也被切断了。根据历史学家麦考莱 (Macaulay,2008:30) 的说法,当“懦夫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于1204年被赶出诺曼底时,“诺曼贵族被迫在英伦岛屿和大陆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与迄今为止一直受他们压迫和蔑视的人民一起隔海相望法国,逐渐将英格兰视为自己的国家,将英国人视为自己的同胞。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 年)中,法语作为敌人的语言逐渐被放弃”。
除了与法国的战争,其他因素也促进了英语的复兴。其中之一是黑死病,这场 1347 年至 1351 年间肆虐欧洲的大流行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大量劳动力死亡,耕地面积急剧减少,这对许多地主来说是灾难性的。劳动力短缺迫使他们提高工资或同意以劳务代替租金以留住佃户,工匠和农民的工资也普遍上涨。这些变化为僵化的社会分层带来了新的流动性,劳动人民和他们的语言——英语,开始占据新的重要地位。1258 年,国王亨利三世及其贵族用英语、法语和拉丁语三语制定了《牛津条例》。1362 年,法庭陈述(pleading)4和议会开始使用英语。1399 年,亨利四世用英语宣誓就职。从1380年开始,《圣经》翻译在民间展开,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是第一个把《圣经》从拉丁语译为英文的人,后来者包括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到了詹姆士王时期,用英文编撰《圣经》得到国王支持,于1611年编成了著名的詹姆士王钦定版《圣经》。至此,英文就彻底战胜法语和拉丁语,成为英国社会各领域都使用的语言。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在欧洲崛起,并开始开拓海外殖民地。随着殖民地增多,英文也在全球传播开来。后来,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发展让英文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通用语言,在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了英语的全球地位。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各种英文似乎无处不在,各种变体层出不穷,是不是会出现所有变体平等的情况呢?Mair(2020:374—375)指出,“对以电脑为媒介的沟通交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的社会语言学案例研究一再表明,网络并不是一个无常的‘无空间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的语言都可以随处可见,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以一种可定义的、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要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现实世界中的购买力继续对其在网络上的存在产生影响,网络空间就不会完全脱离线下社会语言秩序。在 CMC 中,许多语言规范可能会变得不固定,但有些语言规范仍然非常牢固。举一个微不足道但显而易见的例子:尽管有自动生成的搜索建议和更正、深度学习和机器人对人声的应答,但可靠的键盘技能和对标准美式英语正字法的熟悉仍然对搜索和使用万维网大有帮助。”可见,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各种影响语言地位的因素,如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展,有其历史脉络,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好机遇。据互联网国际数据网站的统计,互联网上英语和汉语的使用者数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并没有形成刚开始人们担忧的英语独大的局面,但是英文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结语
本文围绕英语学习者关心的三个问题,回顾英语发展史带来的启示。在当今全球化高度发展的语境中,掌握英文这一全球通用语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任务,而是多语言能力常态化的必要一环。我们不仅要掌握简单的日常交流,还应该深入地了解英语的文化传统以及英语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机遇。
1 接触造成的最坏情况是语言死亡,随之消失的还有其特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英文在一些地方的传播造成当地语言的死亡,这是英语广泛传播的负面效应。2021 年4 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据科学家统计,世界上7000 多种语言中的五分之一将在本世纪末死亡;后者中40% 的语言已经濒危。该报道指出“语言中有大千世界,那些最濒危的语言所包涵的世界观可能为当代的最大危机指出解决方向(Within languages lie entire worldviews. And the worldviews that are most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could help show the wayout of the biggest crises of our time)”。
2 笔者认为有两种倾向在语言变化中起重要作用,一种是交流倾向于用最少的力,另一种是表达需要足够清晰,二者就像拔河比赛一样平衡着说话者的选择。前者符合普遍的语用省力原则。
3 作者Paul Christophersen 是丹麦人,师从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和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译文由笔者提供。
4 指在法庭上进行的审判前的口头陈述。确定事实问题供陪审团裁决。在中世纪,诉状是口头的,大多数法律辩论发生在审前阶段。( Pleadingwas the means of defining a factual issue which could be tried by jury. In medieval times pleadings were framed orally, and mostlegal argument occurred at the pre-trial stage.)
参考文献
Algeo, J. 2010.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6th ed.) [M].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Baugh, A. & Cable, T. 2013.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6th ed.) [M]. Boston, MA: Pearson.
Christophersen, P. 1990. The Germanic heritage [J]. English Today, 6(3), 3—7.
Crystal, D. 2008. Two thousand million? Updates on the statistics of English [J]. English Today, 24 (1): 3—6.
Crystal, D. 2011. The story of English in 100 words[M]. London: Profile Books.
Crystal, D. 2018.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rd 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S. 2011. 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 [M]. London: Profile Books.
Kachru, B. 1985.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A]. In R. Quirk & H. G.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0.
Macaulay, T. B. 2008.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Volume 1 [M/OL]. (2019-05-10)[2024-09-02]. https://www.gutenberg.org/cache/epub/1468/pg1468-images.html.
Mair, C. 2013. World Englishes and corpora[A]. In M. Filppula, J. Klemola & D. Sharm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Englishe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3—122.
Mair, C. 2020. World Englishes in cyberspace[A]. In D. Schreier, M. Hundt & E. W. Schneider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orld English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0—383.
Pennycook, A. 2003. Beyond homogeny and heterogeny: English as a global and worldly language[A]. In C. Mair (ed.).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msterdam [C].The Netherlands : Rodopi: 3—17.
Schneider, E. W. 2014, New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World Englishes[J]. World Englishes.33 (1): 9—32.
Scott, W. 2005. Ivanhoe[M]. San Diego, CA: ICON Group International.
作者简介
梁昊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英语史,语法化、英汉对比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