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卫东:教师成长,有“慢”才能“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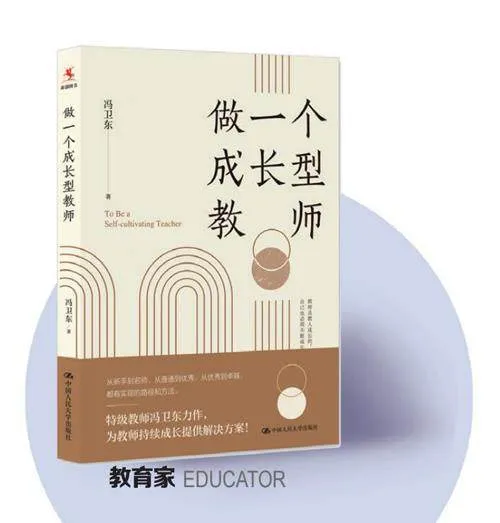

冯卫东,江苏省特级教师,中小学正高二级教师。曾任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南通市教师发展学院副院长。著有《今天怎样做教科研:写给中小学教师》《为“真学”而教:优化课堂的18条建议》等。
“阅读冯老师这本书,仿佛与一位智慧温和的长者对话。谈话间,既有督促青年教师提振精气神击败怠惰自我的鞭策,更有包容青年教师按照自己的节律从容成长的关怀,他不断告诉我们:‘慢成没关系,只要是真长。’”
“我在冯老师文字的浸润之下,一次次进行心灵的自我追问: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老师,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成长型’教师……”
上面是两位教师写在《做一个成长型教师》读后感中的话。的确,作者的文字里有一种浸润人心的温和与力量,他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譬喻自己的教育生活,犹如邻家大哥娓娓道来,结合自身与周边教师的事例,给教师们提出忠告——成长,不必过于求快。
《教育家》:您在书中表示:“关于佐藤学教授提出的‘教师向以学为主的专家转变’这一主张,我有很多想法。”能否结合当前教师成长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新问题来谈谈您的思考?
冯卫东: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总体目标分成两个阶段达成:经过3至5年努力,教育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到2035年,教育家精神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对于教师的成长,我想谈以下两点看法。
基本功厚积不已,新知识乐学不止。没有基本功,就没有教育活动的一切。基本功的修炼,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刚刚入职的新教师才要做的事,而是需要教师用一辈子时间去修炼的。基本功不只是我们常说的“三字一话”,那只是技能层面的基本要求,教师更需积累的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文素养,要多读一些教育基本理论、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在书中与前人对话,汲取营养,才能有较为充盈的底气、较为丰富的底蕴、较为美丽的底色。基本功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和转化力,如果较为厚实,对新知往往就能快速悦纳,并吐出新的、优秀的能力。
同时,对新知识要乐学不止。今天的教师除了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科基本理论,还要与时俱进,通过手机阅读了解一些社会经济与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我每天手机阅读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小时,在阅读过程中我会将自己感到受益的内容复制到手机笔记本里,现在已积累了上千条信息,时常利用碎片化时间去“咀嚼”,还能以此来对抗遗忘。
在结构化思维中“积攒收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总结、复盘、升华型的学习,将大脑里碎片化、混沌状态的知识,转化为相互联结的思维区块,从而生成一种结构化思维。年轻同仁们可以有意识地使自己的思维趋向结构化。拥有了结构化思维,你获取的信息就会自然链接到相关思维区间,在搞研究或是想要表达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提取出来。反之,如若缺少这样一种思维,许多零零碎碎的知识,读过之后很快就会忘记。这种方法不是我着意寻求的,而是在多年的学习与实践中,通过边阅读边体悟、边观察边反思总结出来的。
《教育家》:教师要实现自我突破、自我成长,就必须走出“舒适区”。但现实中,也有不少教师一味满足并停留于“舒适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层面该如何引领他们走出舒适区呢?
冯卫东:教师要化解“浅度舒适”依赖,追求“深度舒适”。深度舒适,不是舒服,而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诺尔·迪奇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将个人在学习和改变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划分为三个区域:舒适区、学习区、恐慌区。当人们身处学习区时,通常会因为感知成长变化,引发积极心理。同时,随着认知的增加,舒适区的边界会扩大,从而获得更大、更深的舒适感。
教育行政层面,要培养、发现和树立“深度舒适”典型,并以典型驱动广大教师。让教师们更多地去谈谈,在不辞辛苦的教育历程中,怎样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逐渐感受教育的奥秘,化解过去的懵懂无知,进而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教育幸福感。这其实是一种价值导向,能够给其他教师一种暗示——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舒适”。学校层面,校长一定要做“深度舒适”者,培养梯次型的“较深舒适者”,并引领教师们适时进阶。
总之一句话,教育要想方设法培养更多“对事情本身感兴趣”的人。
《教育家》: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应该是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在这个方面,教师需要怎么做?
冯卫东:教师要对成长上瘾,形成一种“成长依赖”,助成“贪学”小学生,玉成“上瘾大先生”。教师本身就应该是自我教育的先行者,在成长过程中自己学到了什么,有哪些体会,也可以与孩子们分享交流,进而感染并影响他们。
比如李庾南老师,其本身就是一门好的德育课程。首先,她用刻苦自学、勤奋成才的事实,把自我“修”成好的德育课程;其次,她“用自我来教学”,推己及人,将教学方法变革与创新的逻辑起点确立在自学之上,在教学中不断实现自身作为德育课程的价值;最后,她还通过故事讲述、成长经历分享等,适时为学生生成师本显性德育课程。
《教育家》: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近年来,厌学的孩子越来越多。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孩子的厌学情绪呢?
冯卫东:在我看来,学生“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出在教师的“教”上。据我的观察和一些校长的反馈,有种感受越来越明显—— 一些新教师接受的知识或许是新兴的,技术赋能方面也做得较好,但教学方式仍停留在过去,课上还是以讲为主,孩子们则被动接受。我认为这是孩子们不愿意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10年前,我们和南通的一所学校创设了“学会玩的动课程”,提出“学活于嬉,智起于动”的理念,让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处在游戏化环境之中。李吉林老师也曾表示,情境教学还有两类涉及得比较少,一是网络情境,二是游戏情境。
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教育理应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我们需要探索小学教育的游戏化,对此我曾表达过两个观点:第一,情商是教师的“第一智商”;第二,爱哄才能赢。我以前的一位老同事——江苏省特级教师李凤,当年在县里教学时,县教育局局长就曾评价说“李老师是个‘骗子’”,就是因为她善于把孩子们哄得团团转,在他们感觉知识学习比较苦口的情况下,为他们包上“糖衣”。
即便到了初高中阶段,除了要培养学生的学习意志力,也可以尽量让学习好玩些,由此我们提出了“三玩”教学策略:玩味,即学习与欣赏;玩索,即思考与探究;玩绎,即应用与拓展。“玩味”是学习活动的开始,思维尚处于较近和较浅的感性层次;“玩索”是从现象走向规律的一种纵深与理性掘进;“玩绎”则主要是在横向上的拓宽与延展。如果老师们能做到这“三玩”,课堂样貌和学生的学习热情一定会有所改变。
《教育家》:教育的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要求教师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从关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到培养学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您看来,当前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或缺失是什么,该如何解决或弥补?
冯卫东:在与教师、校长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到最大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老师不愿动自己的“奶酪”,也可以说是不愿动脑筋。究其原因,大多数教师仍受制于传统的教育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分数的较量。因此,我提出教师要为“真学”而教,切莫培养新时代的“卖油翁”(无他,但手熟尔),要基于熟练,更要超越熟练,培养创新型人才。
教育行政、教育科研、教育教学评价部门,一定要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的局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启亮曾提出,基础教育应以培养普通劳动者为具体目标,这一阶段的评价应当由选拔性评价转向合格性评价。对此我深表赞同。
学校层面也要进行“静悄悄的革命”,比如以金句来照亮课堂生活:在“似知区间”里重点发力;用“劲道”的问题把智慧问出来;用棘手的问题驱动真实而有效的合作;好教师要善于做“智慧型的‘麻烦制造者’”;等等。学校可以引导教师领取自己认可的金句,并在教学中不断去印证。相信,通过微观生态的改变,也一定可以推动整个教育生态发生改变。
《教育家》:近几年,教育领域的新名词、新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教师迷恋于追风赶潮。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建议?
冯卫东:我感觉,教师“自追”的现象还不是蔚然成风,主要是受外界的影响,包括外界的驱动。
成长型教师可以或应该有自己的新名词、新概念,这其实也是新思想、新理念的表征。“重新定义教育”不是不可以,但要有自新魄力、内在动力和学理依据,最关键的是付诸行动。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我的指导下提出“大生”的教育和文化理念,起初也不被一些人看好,现在则没有人予以怀疑,这自然不是或不只是因为我说得好,而是他们做得好。
教师自身可以以一种很朴素也很实在的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是不是我“郁之于心而发之于外”的?如果是,那就要勇于提出、敢于唱响。我个人也不时会推出一些新的名词、概念和理念,如“为‘真学’而教”;近来则提出,“为‘慧学’而活”。
这些年来,我和一些学校、教师或为一些学校、教师作过文化设计与教学主张“炼制”,并写过一本专著《点亮教育人生的“灯”:“教学主张”论》,其中自然出现了不少新名词和新概念。前不久,我还和苏州市相城区御窑小学的校长、老师们提出“四LIAN课堂”的教学品牌构想。这一构想基于御窑及金砖意象,呼应我为他们提炼的核心办学理念:“教育即陶冶,成长须修炼。”这“四LIAN”具体是指:恋,让课堂成为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沃土,老师喜欢孩子,孩子喜欢老师;练,即“做中学”,不仅要练题,还要在无形中对孩子进行思维训练;炼,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孩子攻坚克难,锤炼意志品质,同时要教孩子概括、提炼所学知识的规律和本质;链,包括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一种人际之链,还包括知识的牵引,让课堂实现前后关联地教、互动生成地长。把以上四点做好,课堂焉能无改进,学生焉能不优学,教师焉能不成长?校长和老师都表示认可这样的理念、概念及说法。
《教育家》:名师工作室是教师成长的摇篮。您有较多机会近距离观察一些名师工作室的发展状况。在您看来,名师工作室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引领教师成长的作用,普遍而言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冯卫东:在名师工作室的建设方面,可以说南通走在了全国各地的前头,很好地发挥了引领教师成长的作用。至于还有哪些提升空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更好地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结合,更大力度地促成工作室成员从“外铄”走向“自养”。就此我也作过报告“优秀教师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此外,名师工作室的领衔人要注意更多在“神”上引领,而不要过多地作“形”上的规定;领衔人更要有自我反省意识:我的方向是对的吗?我的引领会不会产生误导和负面作用?要不时追问自己的影响力,适当破解“近亲繁殖”。领衔人还要做“有理性自觉的实践家”,要有高度的“自我监控”意识,或者说“元认知”自觉。领衔人不能成为名师工作室里教师的“他人设限者”。我以为,其最优角色形象是“伴导者”,要与所带领的教师结成“成长伴导体”。
《教育家》:教育写作对教育发展、教育研究和教师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有不少教师不重视教育写作或者认为自己不擅长教育写作。您能给这两类教师一些建议吗?
冯卫东:不重视教育写作实际上就是不重视自我修炼、自我进阶、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我常说:“写作是一项全身运动,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写作的教师,用一位教育哲学家的话说,他“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
我记得,李希贵校长在《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一书中写到美国戴维教授,他说:“只有说,才能想。”是的,不表达的人又怎么能有好的思想,他的思想又如何得到检验、校正、提升和进阶呢?要成为一名秀外慧中、“好得彻底”的教师,那非去写作不可。除非他甘落人后、甘沦平庸,这是谁都没办法拯救的。
至于不擅长写作的教师,我想说:第一,不要为写而写,丰富“食材”要先备好;第二,要在写中学会写;第三,绕过闹市走曲巷,要让新意出肺腑;第四,要有写作方面的目标对象,以学习、揣摩并借鉴。
最后我想说,优秀教师不要“宝山空回”。我现在即将退休,有较多机会接触许多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在与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有无限的写作资源,因此我也正在鼓励和助成一些优秀同仁构划和写作自己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