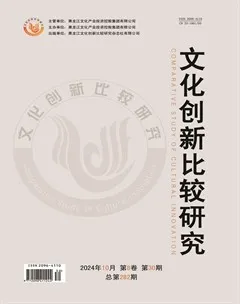基于电影媒介“重构”历史类人物的三个层面
摘要:近年来,“两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视域下故事新编成为影视作品热衷表达的焦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荧屏上经久不息的题材,继神话传说、志怪传奇后,创造者将目光转向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何让观众已经熟知的人物焕发出新的风采,成为电影取胜的关键。该文以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故事新编”下重现的长安和盛唐为文化背景和前提,以李白的人物形象为研究重点,浅析《长安三万里》基于“文化符号”中的谪仙李白所重构的李白的角色形象,以此梳理历史人物在现代文化视域下如何进行再创造,展示历史人物的“两创”重构,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可能。
关键词:《长安三万里》;李白;角色重构;故事新编;文化符号;历史人物
中图分类号:G206;J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0(c)-0049-04
Three Dimensions of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Figur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Film
—Taking the Characterisation of Li Bai in Chang An as an Example
YAN To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w storytell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re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become the unceasing themes on the screen. Following myths and legends, and the legend of the mythical, the creator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characters and events, and how to make the audience's already familiar characters glow with a new style has become the key to winning the film. How to make the audience already know the characters with a new style has become the key to win the film. In this paper, we take Chang'an and the Tang Dynasty, which are reproduced in the film Chang An under the "new story", as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background,and take Li Bai's character a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e Li Bai's character image reconstructed in Chang An based on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banished Li Bai, so as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image.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 image of Li Bai, which is reconstructed in Chang An based on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banished Li Bai, in order to analyse how historical characters are recreated in the modern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demonstr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wo creations" of historical characters, and to provide a new possibility for the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ang An; Li Bai; Character reconstruction; New story; Cultural symbols; Historical figures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提出了“两创”方针,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新进展,以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方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文化学者陈林侠认为在当下文艺创作领域“两创”是“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方法”[2]。《长安三万里》便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为观众展现了一幅精彩的长安图景。
作为“新文化”系列的第一部,《长安三万里》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关于李白的历史文化热。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这位早在唐代就被妇孺皆知的诗人,在影视界和文学界的人气一直不减,曾在数十部影视作品中担任主角或配角。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创作者或以纪录片的形式忠于历史还原李白的生平(如纪录片《李白》),或以截取人们熟知的生活片段来塑造谪仙形象(如电影《妖猫传》)。而《长安三万里》则是打破了对李白形象“神化”的传统塑造,以高适的角度创新性地进行故事新编,将历史和虚构相结合,重构“陌生化”的李白,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核。本文以“故事新编”下的长安和盛唐为文化背景,浅析《长安三万里》基于“文化符号”中的谪仙李白所重构的李白角色形象,以此梳理历史人物在现代文化视域下如何进行再创造。
1 基于文化背景的“故事新编”历史人物
故事新编指的是以文本改写的形式讲述人们熟知的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主要表达精神的重塑,在旧文本中增添现代性,为历史人物、故事“注进新的生命”,使其“与现代人生出干系”[3]。故事新编实际是在“把古老的素材转变成对当代情势的社会批评”[4],旨在通过文本重读来隐喻社会现状。年轻观众熟悉好莱坞电影,无法忍受经典故事中的刻板形象和陈词滥调,要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电影观众中的传播,创作者需要用现代方式重构经典IP,也就是“故事新编”型的故事创作[5]。
《长安三万里》使用故事新编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叙事,过去的动画电影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长安三万里》则是用写实的创作手法重新想象。很多理论家认为,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往往对立比对,然而“历史题材作品只是当代主体基于当下现实、心理的需要,表达对历史表象的一种全新的、当代的认识与评价,在反映出某种历史真实与历史趋势的同时起到‘以史鉴今’的作用……”[6]表现在《长安三万里》中,盛唐与长安作为文化背景,承载着观众重读历史的心理期待,片名取自陈子龙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碛西头”,以长安城、大明宫、三峡、扬州等景物作为展现盛唐气象的标志。“长安”是唐代文人如李白、高适等人心中的“理想之邦”,而“三万里”则表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7]。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唐代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8]。唐朝继隋后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领域都达到了顶峰;开创了南北、中外文化大融合的空前历史时期,形成了年轻激越的文化气质、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统一灿烂的文化气象。如冯天瑜所述:“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汉胡融会、中外交通发达基础上的隋唐文明,规制宏伟、气氛宽松、创造力活跃,达到古典文明的全盛佳境。”[9]
“长安”是中华传统文化叙事中的永恒意象,具有体现地理、历史、文化等多重内涵的象征意义,寄托着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盛世、国家统一的家国天下情怀与人生理想。康震认为:“长安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上重要的大一统都城,不仅在盛世叙事体系上具有表层象征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与社会气象,更是对形而上的社会国家意志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价值体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0]
因而,在《长安三万里》中,“长安”就是整个大唐气象叙事中的“神圣空间”,是一个带有朝圣性质、具有特殊意义价值的地理空间的抽象符号。影片主角通过自己的感知描绘出长安的景象,在真实历史背景中加入了超越现实历史的普遍情感维度。影片构建了一个超真实的空间,观众步入这个独特的“虚拟真实空间”,与之产生视觉和感知上的互动,便完成了“时间与空间、历史和现实、过去和未来”的穿越[11]。
2 传统思维塑造下“文化符号”型历史人物
提及李白,绕不开唐诗。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巅峰之作,它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方式,概括了唐代诗人的理想情怀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陈望衡指出:“唐代的美学理想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唐诗之中。唐诗既可以说是唐代美学的代表,也可以说是唐代文化的代表。唐诗又以开元、天宝时代(盛唐)为黄金时代。”[12]袁行霈也指出:“唐诗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亮点。”李泽厚论及唐诗时说:“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13]在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课程标准版教材中,李白的诗歌在古典诗歌的收录比例中占据显著地位。从小学到高中,该教材共收录了101首古典诗歌,其中李白的作品有15首,约占总数的15%。李白的诗歌体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和崇高的时代精神,极具盛唐气象。“李白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代表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14]若无李白,人们对盛唐巅峰的评价或许会有所下降,“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15]。故此,诗歌便是李白身上最为浓重的文化符号,从文学视角审视,李白的形象极为多元,贯穿于每一首诗作。然而这也表明,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要求创作者在宏观上重新建构。
对文化符号的重塑与创新在现代电影中尤为关键。传统的文化符号通过新的解读和创意改造,以新的内涵和手法展现出更加现代化的审美和文化形象[16]。在作品的特定情节或场景中,经典文化符号通常被集中地展现。随着对符号的阐释或强调,观众能够通过对作品的整体把握来理解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从而直接领悟其代表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意义[17]。当《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作出“床前明月光”的诗句,儿童观影者在电影院里异口同声念出“疑是地上霜”时,这表明影片中的“李白”已在影像叙事中指示为唐代的谪仙李白。同时,这也代表着受到文化教育的儿童已经将《静夜思》这首诗歌默认为与李白相关的经典符号表征。
在文化符号的重构与创新过程中,对传统符号的重新诠释与展现尤为关键。在当代电影艺术的语境下,传统文化符号常被赋予新的视角和内涵,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进而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文化形象。例如,在《长安三万里》中,采用了现代化的制作技术与视觉表现手法,对古典文学作品《将进酒》进行了创新性的视觉再现,增强了视觉冲击力,成功地引起了年轻观众群体的关注与兴趣。文化符号的转变与创新同样反映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新解上。电影常常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新解,为其注入更深层的意义和内容,进而为观众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文化享受。以《长安三万里》为例,该影片深入挖掘了宫廷文化、诗词雅趣等古代文化的核心符号。尽管这些符号源自古代,但在影片中它们被赋予了现代审美和情感的诠释。这种重新的审视与解读,有助于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新颖思考和体验,进而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进步。此外,文化符号的重构与创新为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当动画影像媒介与纸质媒介产生“互文性”互动时,影像与图画的刺激不仅引发了观众的视觉体验,还激发了听觉、情感等非视觉体验,这些体验共同促进了“联觉效应”的产生。在动画影像中的空间与影院现场空间的互动中,观众除了沉浸在画面和情节之中,还可能产生深层次的思考,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18]。观众在观看《长安三万里》时,随着诗人出现,吟诵诗歌,唤起观众的情感和记忆,并追随影片人物、场景和道具的最终表现形式,这正是观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像建构模式。
《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人物形象,直接挪用传统文化符号中人们对李白的刻板画像。从表象上来看,符合“三型李白”的形象塑造,所谓“三型李白”,即历史原型、诗艺造型和传说特型三位一体[19]。表现在用视听符号(素白色长衣、走路豪放、醉酒状态、爽朗且高昂的声音等)共同塑造出李白的人物肖像模型:在视觉上延续了李白历史画像中的脸型、五官等面部特征;在唐诗的吟诵中回到李白的时代,以诗歌作为纽带串联观众对李白形象的印象;在文化上以其穿着的白色长袍作为飘逸与超脱的象征,符合人们对传说中谪仙人的形象想象。在模塑系统的作用下,《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完成了对诗歌符号下谪仙李白的指涉与表征[20]。在此基础上,《长安三万里》也在有意地打破李白的固有角色形象,对李白的形象进行重构。
3 现代文化塑造下“角色重构”型历史人物
《长安三万里》以表现唐朝的历史作为出发点,但在表现人物时,并不严格遵守史实,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处理某些历史故事。在影片中,李白的形象展现及其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在真实历史图景之外构建了一个协商的空间,从而引发了观众与历史之间的对话。这种对历史的重写与再创作,体现了影像媒介的独特效用:“一种记忆的行为,一种新的阐释,由此产生新的文本侵入记忆空间。”[21]影片的虚构元素与历史事实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例如,在电影中,高适与李白之间有着深厚情谊被巧妙地编织进历史的大背景中,这不仅让观众对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影片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情感触动。
“角色”这一术语,最初由乔治·赫伯特·米德带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我国学者周晓虹提出,尽管学者们对“角色”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们仍能从他们的讨论中提炼出角色的两个主要方面:社会的客观期望和个体的主观表现。综合这两方面,角色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处于特定社会地位的个体,根据社会的客观期望,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来适应社会环境,并展现相应的行为模式[22]。在艺术的处理方式下,角色重构使李白的形象有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在诗歌传统文化符号背后,在谪仙李白背后,作为一个官场失意的李白所过的人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包括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的人物性格”的李白如何在银幕上展现“典型的中国环境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23]。在《长安三万里》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李白在人世间的放荡不羁,更能觉察到他在几番仕途之后的苦恼。《长安三万里》影片深入剖析了李白的多重身份与复杂的一面,对文学史中李白形象塑造绝对化与单一化倾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该作品通过对李白生平事迹及诗文传说的深入挖掘,发掘并利用了传统文学史所忽略或简化的影像元素,从而重构了李白形象的立体性。简而言之,《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就是角色重构后“去魅”[24]的李白。
尽管影片似乎倾向于“褒扬高适,贬低李白”,其亦从另一维度揭示了李白悲惨命运的侧面以及其生活中的无奈境遇,最终为观众指向了一个更符合现代审美的角色形象。“李白的浪漫主义,不是一个浮浪少年的意气用事,而是在命运浮沉中对生命伟力的呼唤和护养,颇有老庄的风骨”[25]。这不仅塑造了一个观众更容易被带入的新时代历史角色形象,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更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
4 结束语
在传播领域,为观众提供真实的历史体验与新颖的观看感受同样关键。每个时期都拥有其特有的风貌,应当将悠久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相融合,为此,讲述历史传承文明的方式方法应当与时俱进。历史人物的角色重构正是一种符合现代气质的传播手段。历史在经历角色重构后创造出新的画面、新的人物形象,以创新的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再传播,通过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段,使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角色形象化为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力,既为“陌生化”的创造手法,也是诗意的传达,更是历史人物出现在二次创作中获得生命的又一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全文[EB/OL].(2014-10-13)[2023-07-1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13/c_127090941_8.htm.
[2] 陈林侠.论两创方针与当下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0):22-29.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 D·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J].文学评论,1999(6):145.
[5] 陈可红, 马晨荇. 想象与回归:《长安三万里》的文化再生产及传播逻辑[J].传媒观察, 2023(9): 111-120.
[6] 沈义贞.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
[7] 靳丽娜,于小凡.《长安三万里》:中国古典诗歌的视觉探索和特效呈现[J].现代电影技术,2023(9):57-63.
[8] 陈望衡,范明华,等.大唐气象:唐代审美意识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9] 冯天瑜.中华文明五千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10]康震.长安叙事: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构建[N].光明日报,2023-08-09(11).
[11]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27-274.
[12]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3]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4]袁行霈.中华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房日晰.李白诗歌艺术论[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16]邓亚男.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中华文化核心内涵研究[J].今古文创,2024(4):91-93.
[17]孙金诚.以光影艺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N].人民政协报,2024-03-27(2).
[18]刘鎏,路海波.延伸的电影,扩展的空间,从戏剧影像说开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3):15-21.
[19]何念龙.李白文化现象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20]何超彦,彭佳.中华文化符号的间性建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以中国当代民族动画电影为例[J/OL].民族学刊,1-16[2024-10-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731.C.20240926.1719.006.html.
[21]马健.论当代中国历史电影与民族记忆的重构叙事[J].艺术学界,2022(1):31-42.
[2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3]夏衍.关于中国电影问题:答香港中国电影学会问[J].文艺研究,1984(1):14-18.
[24]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
[25]张启忠.诗注人生的时空宏卷:评历史文化题材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N].中国电影报,2023-08-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