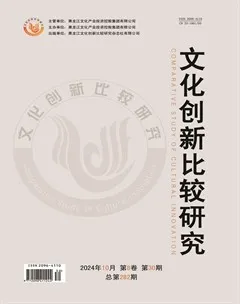苦难与诗意并存
摘要:莫言的小说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全篇描写的是一个身世悲惨但有着超强的感知力的小黑孩与同在滞洪闸工地干活的菊子姑娘、小石匠、小铁匠等人的故事。该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萝卜的含义入手,“透明的红萝卜”是作为黑孩想象而产生的诗意存在;其次分析了主人公黑孩之所以能够产生奇幻而充满生机的想象,是因为这是他对抗苦难的方式;尽管如此,苦难的生存空间实际上也有温暖存在,文本的最后探讨了苦难与诗意并存的生存空间之下人性的复杂,以及作者在洞悉一切残酷与美好之后,仍然表达了对人性的悲悯,并赞颂对抗苦难的美学和在苦难中对诗意的创造。
关键词:《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形象;萝卜含义;苦难;诗意;生存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0(c)-0009-06
The Coexistence of Suffering and Poetry
—Exploring the Living Space of Heihai Through the Meaning of "Radish"
XU Yibo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o Yan's novel Transparent Carrot depicts the story of a tragic but highly perceptive little black child, along with Juzi, a stonemason, blacksmith, and others who work at the detention gate construction sit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starting from the meaning of radish, "transparent carrot" is a poetic existence that arises from the imagination of black children. Secondly, the reason why the protagonist Heihai is able to generate fantastic and vibrant imagination is because it is his way of fighting against suffering. Nevertheless, there is actually warmth in the living space of suffering. At the end of the text,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under the coexistence of suffering and poetry is explored. After understanding all the cruelty and beauty, the author still expresses sympathy for human nature, praises the aesthetics of resisting suffering, and creates poetry in suffering.
Key words: Transparent Carrot; Heihai image; The meaning of radish; Suffering; Poetic flavor; Living space
《透明的红萝卜》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中篇小说,于1985年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萝卜”在文中是一个独特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含义。通过分析“萝卜”的含义及其诗意特征,可以看到黑孩超强感知力之下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虽身处苦难但却通过自己的方式对抗苦难,进而生发出“透明的红萝卜”这一美好诗意的意象。在生存成为问题的背景下,成人的现实世界因为食物的匮乏充满着荒芜与空洞,同样也充满着苦难。作者对苦难以及由苦难产生的复杂人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怜悯,表现出人道主义关怀。
1 萝卜的含义
作为全文的核心,“萝卜”的含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萝卜的含义不同。通过分析《透明的红萝卜》全文,“萝卜”的含义可以分为三种:作为食物的萝卜、象征着权力的萝卜,以及在主人公黑孩的眼中作为诗意存在的萝卜。
“萝卜”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它是作为食物的存在,能够填饱肚子。莫言的小说对于饥饿与苦难、生与死的人类文化学的主题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在《透明的红萝卜》的开篇,饥饿问题就被作者揭示出来。“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秋天原本是丰收的季节,但作者开篇写秋天却塑造的是阴冷潮湿肃杀的压抑气氛,这是一个荒凉的年代。而在这荒凉之中,生产队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 。作者将视角投射在这物质匮乏、生活凄苦的农村。食物代表了权力,生产队的队长毫无疑问是拥有权力的人,他“披着夹袄”,手中又有高粱面饼子又有大葱,权力的威势通过队长狼吞虎咽地“吃”的动作和发号施令的“说”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队长的权威姿态,以及对村民粗鲁霸道而不乏亲切的言行举止,将古已有之的阶层之分跃然纸上。而作为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饥饿早已占据了全部的感官,人们只剩下对于食物的渴望和内心的荒芜。小说开头通过描写群众“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木偶”“一齐瞅着队长的嘴”,表达了人们内心充满对食物的渴望,所以关注点也就集中在生产队长嘴巴的咀嚼上。同样,食物成为权力的象征还体现在小铁匠的身上。黑孩第一次偷萝卜的夜晚,小铁匠向菊子姑娘发出一起吃萝卜的邀请,萝卜成为彰显小铁匠此时身份地位的标志。小铁匠偷师学到了淬火的核心技术,他即将取代老铁匠成为打铁铺的最高统治者。他指使黑孩去偷萝卜是想通过拥有食物来拥有权力,从而向菊子姑娘示爱,对食物的占有象征着权力,象征着身份。因此,在没有食物,生存都成了问题,并且食物成为权力的代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萝卜成为炫耀权力的方式时,“萝卜”作为食物的意义被突出,萝卜能填饱肚子,而填饱肚子才能够生存。当人们生存成为问题,对食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人们的精神也注定会处于异常的状态。人们的感官都聚焦于食物的信息,精神世界产生巨大的空洞。“女人们脸上都出现一种荒凉的表情,好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自身难保的境遇之中,人们也很难再对外物有所感触。
较之普通人,黑孩处于乡村中的弱势地位,他的生存状态不仅是对食物的欲求问题无法解决,除此之外黑孩还承受着成人世界所施加的暴力。然而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黑孩眼中“萝卜”的意义不同于成人。在他的眼中,“萝卜”是充满诗意的,是美丽的、是漂亮的,是奇幻的。作者站在黑孩的视角描写道:“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这样生动且富有生命力的描写完全出自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吃不饱、穿不暖,还承受着成人暴力的孩子的视角。有的研究者提出,“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的萝卜是一个儿童关于“生殖器官”的隐喻性想象,是黑孩此时的心理焦虑和性幻想的形象化的展露。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在文中多次出现的“萝卜”,其含义又绝不仅如此简单。“莫言小说的思想与美学的容量、在由所有二元要素所构成的空间张力上,已达到了最大的程度。”[1]“萝卜”作为本文的核心意象,其内涵容量一定是丰富多样且充满张力的。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作为权力的代表,以及作为黑孩的性幻想符号之外,“萝卜”更是一种诗意的象征。这个“透明的红萝卜”是由菊子姑娘亲手洗过之后而在黑孩的内心世界里生发出来的,不仅意味着黑孩对菊子姑娘的感情,更代表了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希冀与向往。“萝卜”对黑孩来说是诗意的、美好的,这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中作为食物的“萝卜”。黑孩看到了和现实世界中成人眼中完全不一样的萝卜,这个萝卜是美丽的、充满诗意的,而不再是填饱肚子的物质和权力的象征。这个“充满诗意的、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则代表了黑孩对现实世界、对苦难的抵抗方式,代表了黑孩拒绝苦难诗意生活的精神,这样一种对抗苦难、对抗残忍的诗意精神,以及在苦难之下所爆发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生命意识也正是隐含在文中的作者想要赞颂及传达给读者的核心内容。
作者所赋予“萝卜”的复杂含义,使得《透明的红萝卜》在发表之初就引来了一片赞誉[2]。但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或者说作者究竟表达了什么,批评家们无法给出具体而微的论证。事实上,这篇作品的魅力就在于作品内涵的不确定性,论文如果从作品中关键符码的隐喻内涵出发,或许能够会让读者豁然开朗:这是一篇关于生存的故事[3]。
2 黑孩的生存空间及其对抗苦难的方式
在小说文本中,黑孩一出场就给予了读者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作者描写道:“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DFAvt7BVV+eQOm+SyuIJtA==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这是一个生存困难、经历过无数伤痛的儿童形象。他没有名字也没有姓氏,“黑孩”不过是一个代称,他没有确切的自我身份[4]。因此在他所生存的村庄里,作为儿童,黑孩没有收获到原本应该有的关心和爱护,反而成为乡村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任人欺负的对象,吃不饱穿不暖更是他日常生活的常态。黑孩的形象是苦难的形象,他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温暖,无论是在家庭环境还是在社会环境中。黑孩的生存空间是悲惨并且充满苦难的,这一方面源于黑孩的家庭——父亲的缺失,继母的动辄打骂;另一方面则归因于社会的问题,成年人的谩骂、无视和奴役指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欺凌这样一个弱小的儿童。“后娘一喝就醉,喝醉了他就要挨打,挨拧,挨咬”,黑孩的父亲离去,后娘喝酒之后就会对他打骂,这是家庭之中的暴力。在乡村社会中,暴力则表现在对黑孩的称呼和言辞之中。生产队长“你这个熊样子能干什么?放个屁都怕把你震倒”,刘副主任“他妈的这个小瘦猴!”,还有安排黑孩砸石子时骂他“脑子肯定有毛病”,并且“拧着黑孩的耳朵大声说”等。成人粗俗的语言行使着霸权,对黑孩生存空间进行毫无顾忌的挤压,表面上是黑孩的所见,但其背后却是成人视角对丑陋现实世界的批判[5]。
作为“弱者”的黑孩,他的生存空间充满着化不开的苦味,具体表现在小铁匠对黑孩无端地责骂和指使,近乎奴役地让黑孩完成各种工作。黑孩身处在比缺乏食物的普通人更加糟糕的生存状况之中,他所遭受的苦难是家庭暴力与社会暴力的双重叠加。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苦难,黑孩有其自己的应对方式。注重非听觉的感知器官的表现力,在莫言的各类作品中,不再是一个具体规定情境中的描写特色,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审美境界,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底色。黑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对一切外部世界无感,却对各种自然事物有着细腻体味,并从这些自然事物之中汲取力量,也正因为如此黑孩的想象世界是“诗意”的世界。黑孩通过对自己回忆的不断回味,获取力量切断与成人的交流。在刘副主任训话时,黑孩听到的是“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像火车过铁桥”;被安排到菊子姑娘身边砸石子时,他一边砸一边又沉浸在自己丰盈的内心世界中:“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他早忘记了自己坐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仿佛一上一下举着的手臂是属于另一个人的。” 凡是他在现实世界听不到的,便在另外一个想象世界中听到,而且是更奇异的声音;凡是人世间得不到的欢乐,他便在另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得到加倍偿还。心灵感应的对象与途径变了,感觉的方式与形态也会相应变化[6]。黑孩只有在“开小差”的时间里,才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意识幻象,才能屏蔽周遭的痛苦和成人的训斥,黑孩为自己逃离苦难构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黑孩的幻想世界,表现出黑孩对大自然的亲近,既然现实社会中充满着争夺和压抑,那么大自然则成为生命意志的最后栖息地,干瘪焦枯的心灵从广袤的自然之中汲取养分从而重获丰盈的活力,投身于自然的黑孩也就由此获得了异于常人的感受力[7]。
除了沉浸在个人的梦幻世界之中,黑孩同样还通过钝化的感官,即对疼痛的无感、对苦难的无感,来反抗苦难。在砸石子的过程中,黑孩指甲都被砸掉了,但是黑孩对此却没有反应,只是“嘴里突然迸出了几个音节”,仿佛被砸的不是自己的手指一样。作者以完全冷静、客观,毫无感觉的叙事口吻来描写这一本应该充满痛感的情节,从而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另外,小铁匠指使黑孩捡刚烧熟的滚烫钻子,“他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钻子沉重地掉在地上”,“他一把攥住钢钻,哆嗦着,左手使劲抓着屁股,不慌不忙走回来。小铁匠看到黑孩手里冒出黄烟”。黑孩屏蔽了对苦难的感知,也就不会产生生存空间中任人欺凌的创伤感,以对苦难无感来作为抵抗苦难的方式,这是一种对现实苦痛近乎麻木的忍受,然而黑孩本身却没有忍受的意识。也就像《颠倒的乡村》一文中提到的,“因为黑孩的感官对‘现实’是‘关闭’的,只对‘现实之外’的幻想世界打开,这种特殊感官对后娘的虐待、刘副主任和小铁匠的欺负‘毫无感觉’,但大自然却在它面前展现了自己的极端之美,极端之自由。黑孩正是为这现实之外、处于幻想之中的‘自由’而活着的。在1970年代,这也是一种‘活着’的意义”[8]。黑孩不说话,完全将自己封闭了起来,没有自觉的对抗意识,无论是对他的关心还是对他的谩骂,他都选择通过无声无感的反应来作出应对。但是,黑孩的想象世界又是奇异的、充满色彩的、独一无二的,感官的钝化与由敏锐感官带来的想象的无限扩张同时出现在了黑孩的身上,构成了人物的张力。他对疼痛感麻木,他所有感官都是麻木且钝化的。黑孩正是将对苦难的无感作为对抗苦难的方式,他没有创伤感更没有挫败感,也正是这样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知无感”以及丰富的内心幻想世界催生了黑孩心中充满银色汁液的、极具美好诗意象征的“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种温暖生命中的诗意,赋予了黑孩重塑甚至创造生命的力量。黑孩的身心构成了一种逆向统一的性格系统,一方面对现实苦痛近似于麻木地忍受,另一方面却以极大的热忱追求理想美好的事物;一方面对外界反应极其冷漠,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表现对爱的渴求[9]。这是黑孩对抗现实世界的苦难、反抗成人暴力的手段,也是黑孩生命力的所在。莫言曾经在自己的创作谈中提到过“黑孩就是我自己”,黑孩是创作者诗意的自我投射,是成年经验对童年经验的再书写。莫言的写作有自己的诗学见解作为支撑,而他的这些见解同样也在有形或无形之中建立在他对生命、对生命主体精神的理解与感悟之上,带给读者诗学的感受和精神的启示[10]。
可以说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隐含作者所高度赞美的一种对抗苦难的方式,同样是作者莫言在现实生活中对抗曾经岁月磨难的方式,以心中之诗意武装自我,抵抗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苦难。
3 黑孩苦难生存空间之中的温暖关怀
如果说黑孩的苦难来自现实世界中成人的欺压和不重视,那么生存在现实世界中的成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苦难。黑孩身上凝聚着化不开的苦味,这点和其他人的命运是相同的。普通人在饥荒年代吃不饱,身为师傅的老铁匠被自己的徒弟算计,黑孩后母酗酒背后是丈夫离家的苦痛,生产队长刘副主任面对完成生产任务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承受的苦难,每个人都在时代背景下自身难保。作者注意到了这些人所背负的痛苦,所以对待成人,作者并没有对他们口诛笔伐,而是体察到了人性的复杂,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每个人也都有个体生命的悲哀之处,从这一点来说,无疑表现了作者隐含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人性的包容与悲悯。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描绘苦难的现实世界,作者依旧描写了其中人性的温暖,也就是在这充满苦难的世界,众人给予黑孩的关怀。
首先,是来自菊子姑娘和老铁匠给予的直接关怀。黑孩在被安排去砸石子后,认识了邻村的菊子姑娘。菊子姑娘作为美和善良的代表,给予了黑孩他从未体验过的关心。在语言上,菊子姑娘尝试与黑孩沟通,菊子姑娘问黑孩的名字,对黑孩的存在给予身份认同。即使黑孩没有回答菊子姑娘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与老蒺藜作战,菊子姑娘依然会赞赏黑孩。在动作上,菊子姑娘会温柔地摸黑孩的伤疤,并揉黑孩的耳垂。在与菊子姑娘接触时,黑孩并没有像之前一样沉浸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或是不说话只是怔怔地盯着看,而是反馈给了菊子姑娘适当反应:“黑孩感动地仰起脸来,望着姑娘浑圆的下巴。他的鼻子吸了一下。”另外还有后文写道:菊子姑娘给黑孩带吃的,黑孩给予的反应是“耳朵使劲忽扇着,左手举起窝窝头,右手举起大葱腌黄瓜,遮住了脸”。对于菊子姑娘的关心,黑孩不再是沉默不语或者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而是对关心的行为传达自己的反馈。
除了菊子姑娘关爱黑孩以外,老铁匠同样对黑孩给予了相当的关照,一方面是在烧火技术上给予黑孩帮助,另一方面是在生活上关照黑孩。在黑孩初到铁匠铺时,与小铁匠责骂黑孩的态度不同,老铁匠主动让黑孩拉风箱生火,并且将拉风箱的要领教授给黑孩。“黑孩畏畏缩缩地走到风箱前站定,目光却期待什么似地望着老铁匠的脸”,反映出黑孩感受到了老铁匠对他的承认。老铁匠请假回家时,黑孩烧火不专心、无精打采;在小铁匠被骂时黑孩的反应却是“嘴角上漾出两道纹来,谁也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难过”。由此可见,在老铁匠的影响下,黑孩开始依靠作为成人的老铁匠,并愿意将自己的情感寄予老铁匠。老铁匠不仅给予了黑孩技术上的指导,还会关注黑孩的冷暖感受。在下过雨的清晨,天气转冷后,看到黑孩依旧光背赤足,老铁匠会关心地问黑孩“冷不冷”,并且主动拿自己的褂子给黑孩披上。老铁匠教授黑孩烧火的要领,为黑孩披上褂子,他以不经意的举动传达了一个人心尚未冷漠的老者对于儿童的怜爱。黑孩虽然沉默,但他心里明白老者的好意,同回应菊子姑娘一样,黑孩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老者的关心,他会卖力地拉风箱,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模仿老铁匠——在腰上拴一根红色胶皮电线,甚至会去追逐老铁匠离去的背影。
其次,是来自他人的间接关怀。像生产队长及刘副主任这样的权力拥有者,虽然作者对于他们的“领导”身份表达质疑,对掌权者的特权和权利上位者的优越性表达批判和不满,但考虑到人性的复杂,霸道和同情并在,作者依然写到了他们对弱势者——可怜孩子的不忍与同情,而给予黑孩一定的关照。他们对黑孩的关照虽然不像菊子姑娘和老铁匠落实到了行为上,但又确实存在于只言片语中。生产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关心黑孩的生病情况;“回家找把小锤子,就坐在那儿砸石头子儿,愿意动弹就多砸几块,不愿动弹就少砸几块”,考虑到黑孩的瘦弱,告诉他做工的技巧,从自己的身体状况出发;“队长把夹袄使劲扯了扯,对着孩子喊:‘回家跟你后娘要件褂子穿着,嗐,你这个小可怜虫儿。’”关注黑孩的冷暖,这是来自乡村人粗糙的关怀。刘副主任考虑到黑孩的家庭背景,同意让瘦弱的黑孩在他的公社干活,看到工作完的黑孩首先关注到黑孩的工作情况,“黑猴,今天上午干得怎么样?噢,你的爪子怎么啦?”;看到黑孩受伤后,思考着为黑孩更换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小石匠对黑孩的关注:“小石匠友好地拍拍他的光葫芦头,说:‘回家跟你后娘要把锤子,我在桥头上等你。’”“小石匠也走上来,摸摸黑孩凉森森的头皮,说:‘去吧,去摸上你的锤子来。砸几块,算几块,砸够了就耍耍。’”[11]这些关怀是来自成人世界的温暖关怀,是苦难之中的诗意。
由以上两点可见,黑孩的生存空间是一个苦难与诗意并存的世界。现实世界是残忍的、冷酷的、充满暴力的,但是在这苦难的现实世界中,也同样有着温情的存在。因为苦难不仅来自成人自己,更是时代背景下人们自身难保之下的无可奈何。黑孩通过感官的钝化以及沉默来构建自己丰富的内心幻想世界,并以此作为抵抗苦难的方式,从而生发出了“透明的红萝卜”这个充满诗意的意象。在这个过程中,苦难的现实世界也给予了黑孩相当程度的温暖。尽管现实成人世界充满了暴力和斗争,但是,作者也描写了他们为生命做出的挣扎,隐含了作者对于这些在苦难环境之中挣扎的普通人,对每个人身上复杂的人性给予的怜悯和同情。诗意的“萝卜”之外的人性的温情,包含的是作者无限的怜悯,与对人性复杂的包容。
小说最后以老铁匠的被迫出走、菊子姑娘和小石匠的离去、小铁匠的发疯,以及黑孩再一次变成最初那个没有人关怀的“弃儿”这样一种充满悲凉之感的情节作为结局,这一点是值得思考的。黑孩试图寻找那“透明的红萝卜”,试图寻找曾经拥有的温暖,但它终究如同一道虹消失了,黑孩终究是没有再找到那美好与诗意。笔者以为,这是黑孩对诗意不复存在后,无处可去而又无路可逃现实的最终妥协,即回归自然,重新获得生命力。黑孩将曾经的苦难与无法消解的疼痛留在了黄麻地之外,带着对“透明的红萝卜”的向往与重新找回的希冀,返回大自然,就像鱼儿回归海洋。然而,跳出文本回归现实来看,黑孩钻入黄麻地也带给读者以反思,即在人们自身难保的现实苦难境遇之下,爱与生存的可能性问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者表达了对黑孩生命力的赞颂,对黑孩对抗苦难产生诗意的赞颂。黑孩沉浸于个人的想象世界,屏蔽了对世界的感知,同时也屏蔽了对苦难的感知。他的感官钝化、沉默寡言都是他对现实苦难无感的表现,也是他对抗苦难的手段。作者描写了黑孩对自然的细腻感知,构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对苦难的无感,表达了黑孩充盈的生命力,对因苦难而生发出的充满诗意的“红萝卜”高度赞美。同时,通过文本中小石匠、生产队长和刘副主任等人的形象塑造,作者还表达出对复杂的人性及精神匮乏时人性冷漠与温暖并存现象的深刻体察,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包容与怜悯,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与礼赞。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J].当代作家评论,2003(2):59-74.
[2] 张清华.细读《透明的红萝卜》:“童年的爱情”何以合法[J].小说评论,2015(1):96-102.
[3] 王向辉.鄙俗世界里的理想化生存:《透明的红萝卜》的隐喻叙事分析[J].文艺论坛,2020(4):100-104.
[4] 罗思琪,周春英.爱的缺失与失真的世界:论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人物形象[J].名作欣赏,2015(14):59-60.
[5] 周佳燕.苦难与童趣交织的奇幻世界:《透明的红萝卜》陌生化叙事[J].今古文创,2022(23):4-6.
[6] 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J].上海文学,1986(4):121-132.
[7] 朱文琦.无拘无束的黑色精灵: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精神阐释[J].绥化学院学报,2019,39(2):67-70.
[8] 程光炜.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J].当代文坛,2011(5):16-22.
[9] 北川.《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意蕴[J].当代作家评论,1984(4):32-36.
[10]张灵.叙述的极限与表现的源头:莫言小说的诗学与精神启示[J].小说评论,2010(4):114-118.
[11]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43.